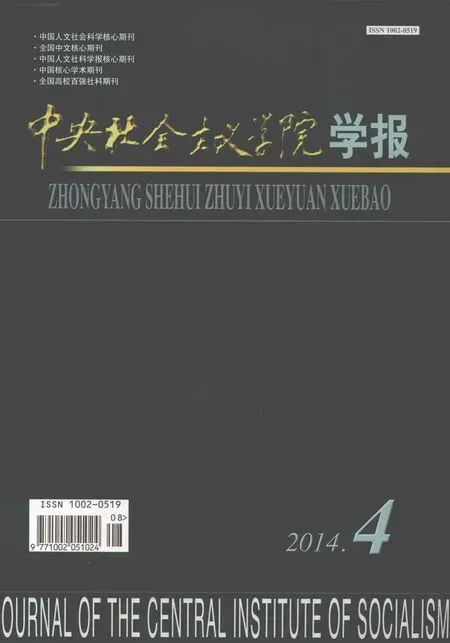试析选举改革与香港的有效治理
2014-02-04徐锋
徐 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港澳台研究·
试析选举改革与香港的有效治理
徐 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选举、选制包涵特定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对统治或治理产生直接且深刻的政治影响。受政制架构及选制设计的影响,回归以后的香港民选政治既有突出的成就,也有显然不适应有效治理和民主发展要求的地方。应当开放性地看待香港选举与治理的优化问题,审慎处理好中央—香港政府—香港公众的关系问题,互谅互让、彼此妥协,超越唯管治权之争的敌我二分意识以及非理性、非地方政治本位的泛政治化冲动。
选制改革;有效治理;香港政府;政党政治
全力促进香港民主政治稳健发展,向来是港民权利与福祉所系,也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发展、政府治理都取得了明显的绩效。但要看到,由于“一国两制”无先例可循、需要逐步积累经验,由于选举制度、权力结构等体制机制的局限,因此,特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些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特区政府和广大港民密切沟通、形成共识,创新理念和制度,不断深化发展香港的民主。中央政府承诺,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此后香港立法会亦可由普选产生。在选举改革近在眼前、特区治理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当下,深入探讨选举和治理问题,溯其源流、反思现实、揭秘将来,无疑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选举、选制同现代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尽管选举就是依据公认的规则、程序从所有人或一些人中挑选少数人出任特定职务,但其意义、作用却远非选人做官、掌权那么简单。民主的选举起码有如下重要功能:一是招募、培养和录用政治精英。二是意见表达和确立政策议程。政府议程、社会议程往往相异,甚至相左,选举为公民提供了自主表达意见和为未来的政府设立政策议程的机会,能敦促、迫使政党及其候选人了解和回应民意,尽量缩小上述两个议程间的差距。三是赋权和统治的合法化。合法的统治(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渊源于市场经济的委托和代理关系,而选举则是选民周期性地同政治精英、政党政府订立权利(权力)委托—代理契约的过程。四是组织政府和制衡权力。选举使选民得以左右政治人物和政党政府的前途,因以激活分权、制衡机制,从而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控制公权力。五是确立责任政治和深化民主。限定政府任期、权责,使得“代理人”仅以其政策向“委托人”负“有限责任”,促成责任政府和有回应的政府[1]36合二为一、推动民主深入发展。六是化解冲突和凝聚共识。选举中多数和少数的经常性转换,给参与政治的所有人带来同等的机会和希望,因而能有效消解败选的愤懑、能以选票计算的政治代替流血冲突的政治。参选各方对民意的顾忌(特别是对中间选民的追逐),也能促其在政治上相互认知和熟悉、彼此尊重和沟通,起码能形成各方都接受的通用政治规则以及各方都不会轻易碰触的政治底线。七是公民教育。作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选举以切身的经验,使公民直观感受到国家、公共事业中确有自己的“股份”,因而会自觉主动地热爱国家、配合政府和致力公益。
长期以来,民主选举以及由其派生而来的一系列的体制与机制,多被当成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的重要分水岭。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强调治理更甚于统治、管治。与传统单向度的统治相比较,现代治理更加关注公权力系统及其运作的网络化、扁平化、透明化和开放性,强调精英、政府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沟通和持续互动,尤其突出发生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对称的政治过程中的反思、谈判与妥协。[2]要把这一切变为现实,就有必要因地制宜、把适度竞争的机制引入政治领域,形成既能从宏观上保持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适当分离(以便各自按其内在固有的规律和要求健康运转),又能整体上有利于保障和发展公众和社会权利的健康的“买方市场”。在与政治发展阶段性要求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适度竞争的选举迫使政治人物、政党、政团不得不寻求既能满足自身权力愿望、又能维护公众权利的政策,不得不把较好地服务于公众当作通向实现自身权利目标的唯一途径。权力多是被迫才向权利妥协的。没有科学和有效的牵制权力的体制、机制,政府、公众和社会间难有平等和有效的沟通、互动。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行使。不从权力授受与夺的源头出发,一切旨在节制权力的体制都形同虚设,相关作为也难切实奏效。正因其如此,选举方能成为民主、法治系统中,所有旨在平衡、限制公权力的其它政治手段奏效的可靠保障,成为民主体制、现代治理的坚实基础。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好的选制是好的治理的重要开端。广义上看,选制就是政治系统中与选举相关的全部规范、惯例和法律的统称;狭义上讲,是投票结束后继续完成计票并向候选人和政党分派公职、将选票转换为当选席次的方式和方法。狭义选制整体上可分为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混合制三大部类。其中,多数制可区分为绝对多数制和相对多数制;比例代表制可分做无门槛或低门槛限制的类型,以及高门槛限制附加当选奖励的类型;混合选制一般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又可细分为偏向比例代表制的联立制和偏向相对多数制的并立制。总的来看,广义、狭义的选制都是规范性的,但狭义的选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比较单纯的技术性规范。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人们选择、适用特定的技术规范的原因并不单纯。选举当然能如实呈现初始、本真的民意。但特定的选制及其所隐含政治目的的差异,会使选举结果呈现为对初始民意的某种剪裁。
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政治的主轴则统统是各种特定的选制所规范的民选政治。由此,特定的选制不仅“塑造民意”,而且能够直接决定政党体制的类型,深刻影响政权运作的模式。由于政党、政党政治始终位居现代政体、现代治理的中枢,因此,选制的选择、改革自然也就成为各方瞩目和角力的重镇。一般来说,有怎样的选制、选举,就会有怎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换言之,人们在设计、选择选制时到底埋藏了怎样的政治动机,又希望透过选制的适用产生怎样的政治效用,不仅决定了选举的性质、内容与形式,也决定了治理的架构、水平和质量。故而,我们对于选制问题不可不慎重,不可不做系统、深入和细致的考量。
二、香港选举与治理的现状及比较突出的问题
基于前述思路,细致考察香港现行的选制设计及其适用,就会发现:现阶段香港选制设计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把握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政治目的和政治效能两方面关系的兼顾和处理,还略显粗糙、不够圆融。譬如,选举及其所适用的选制、所塑造出来的民意,究竟是要被用作管治的工具和手段,还是被用作地方治理的基础和途径?究竟是要侧重传统和权威,还是要侧重民主和民生?究竟是要纠结于意识形态、政治理想,还是要专注于现实利益、政策实践?其中,多数问题能在选制选择和适用层面上加以解决或改进。但也有某些问题,尽管在选制这个规范的、技术的层面上留有表象,其实质却已超出了这个层面,进而蔓延、指向了更高层次的基本法、香港政制以及中央—特区政府—香港公众关系领域。
具体来说,由于上述选制设计上的模棱两可,尽管回归后香港的民选政治有了长足进展,但其对于特区治理的匹配和助益却并非尽如人意。
第一,在“一国两制”基本上得到较好落实和体现的同时,香港民选政治、地方政治中持续传导出不少杂音。特别是一些常见的有违宪法和基本法精神、僭越了地方政治界限的言行,不仅以民粹化的形式不断撕裂香港社会,也诱使中央政府加深疑虑,不断强化其潜在的危机意识、刺激其强化管治甚至是干预的意愿,因而整体上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也不利于中央和特区政府凝聚共识、团结力量以共同致力于香港的民主发展与长期繁荣。
第二,在香港政府基本上维持高水准专业化和正常有序运转的同时,特首及其“非党化”的“中道政府”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特别是来自立法会的有力支撑。在立法会已经高度“政党政治化”、政府也加强了对政党人士的政治吸纳的条件下,各政党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建制内外,都无望成为执政党。政党人士个人的行政经验并不等同于政党的执政经验。没有执政经验的党天然喜欢挑战现体制。香港政党在问政特别是立法实践中就程度不等地展现出某些有权无责乃至不负责任的气质,使政府在立法会中缺乏坚定、强大的支持,而它所面对的仿佛只有“反对党”。[3]在责任政治无法底定的情况下,由于选举渐趋常态化(向日常政治生活延伸)的压力,各政党基于本党利害考虑,纷纷转向引人入胜的政治议题,反而会轻忽亟待筹谋的经济与民生问题。
第三,以小范围、间接推举和选举产生特首,确能使其较好地效忠且配合中央政府,但其在本港的政治认受度却一直不高。以功能组别推选总量一半的立法会议员,能充分体现香港各行业领域的政治和权利意愿,也容易在立法会中形成建制派的力量优势,但这种优势却因小范围、间接选举和有违平等原则等事实而频遭质疑。此外,由此产生的议员多为上层精英,其固有的利益和政策偏好也往往会与大众和香港整体利益疏离。
第四,以不加门槛限制的中选区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总量另一半的立法会议员,虽能够比较充分和完整地代表民意,但也加剧了政党体制的碎分化,形成一个多党林立的立法会,立法效率不高但牵制政府能量有余,使特首及其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使特区治理绩效打了不少折扣。此外,没有门槛限制的比例代表制也使小党及其政客得以仅凭锁定少数公众即能轻松当选,因而在政治上可能不断地趋向于剑走偏锋、极端偏狭,从而引导政党政治逐渐滑向离心和极化竞争。
总括来说,这些状况及其消极影响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法所规定和期待的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深受掣肘、难能有效施展。从法理上看,特首及政府虽然拥有广泛的权力,但由于政府产生和立法选举并没有紧密关联起来,政府也就难能像英国内阁那样可以强势操控议会活动。理论上讲,各自产生的法源彼此相异的特首及政府、立法会可以像美国总统与国会那样彼此平衡与牵制,但由于政府又必须向立法会负责,于是在这一特定领域中也就实际形成了政策过程中特首及政府相对弱势、立法会相对强势的非对称局面。而当前所适用的特首及立法会选制事实上又加剧了这一局面。
第二,香港地方政治的泛政治化。地方政治的正常态是专注于本地事务特别是经济—社会事务。泛政治化的基本表征是以政治正确性标准剪裁、判断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地方政治不是去政治化,并非不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但相关讨论应在其范围、层次上有所节制,应谨守其地方本位。遗憾的是,香港社会一部分公众始终对国家和本港政治发展抱持不切实际的期待,频频将地方政治的焦点引向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权威,进而诱发了日渐广泛、深刻的政见对立,使得政治激情与现行政制、选制所固有的不足相互诱导和彼此强化,导致专注于地方事务,特别是破解香港的经济—社会矛盾问题的理性政治活动反而备受冷落。
第三,中央管治和地方治理的低效能化。客观地讲,由于内地在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上皆有待于现代化,尽管中央心存善意且在政治宣示上一贯坚定地支持香港高度自治,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却不无应予反思和检讨之处。香港市场化、现代化程度较高,政治发展也领先内地,它的确需要合体适宜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能有效整合民意、设立理性议程的选制。出于对泛民主派在选举中不断坐大的担心,有关方面在具体工作中过多考虑了管治权问题,因而对政制和选制问题抱有疑虑、着力不多,事实上忽视了它们对于香港地方治理的消极影响。其结果是在管治和治理两个方面都未能很好地实现预期。
三、影响选举改革的因素、选制的选择及其后果
构成各种选举制度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影响和左右着选举改革。这些因素包括:其一,前面已略有提及的政治发展、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文化与政治传统的留存等目的因素;其二,选民、候选人资格,选区的规模、数量和人口分布,议会规模,选务机构和选票样式等实体因素;其三,有关政治献金、使用媒体、竞争文宣,以及有关选举作弊、选举仲裁与诉讼等方面的规范要素;其四,有关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和确认,选区划分与调整,竞选,投票合计、监票,当选资格(当选门槛),以及选举公告等方面的程序要素。在品质、分布上都存在诸多差异的上述要素,分别组合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行选制,也构成它们选举改革的现实基础。选举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现有选制基础上对相关要素作更进一步的优化和重组,使之能更好地适应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新要求。受上述四个方面要素的综合影响,选举从整体上体现为受控或自由选举、直接或间接选举、差额或等额选举(强竞争性与弱竞争性的选举)等不同的类型及特征。而在技术层面上,选制也会呈现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混合制的分别。选举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使新组合即新选制能在类型、特征、技术层面上有所改观和超越,进而成为“最不坏”的选择与安排。
纵览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制及其演化的历史,相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是适用最多和最悠久的两种。英美两国有相近的政治传统,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适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为数不少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或仍在适用比例代表制,其中荷兰、以色列等国的比例代表制只有较低的门槛限制,而俄国、瑞典、意大利则有较高的门槛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强化政党政府的稳定性、弥平地区鸿沟和提升治理效能,意大利多次改革此前没有门槛限制的比例代表制,不仅设置差别性门槛限制(政党独自参选时为4%,加入政党联盟参选时为2%)鼓励政党结盟,而且特别给予当选的第一大党自动获得议会55%多数的议席奖励。[4]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改良或放弃了比例代表制,转向其它选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出于遏制派系分化、政党恶争和政治腐败的考虑,相继放弃了中选区比例代表制,转而实行略倾向于相对多数制的单一选区两票并立制。此种选制和德国的单一选区两票联立制同属混合选制。
依据迪韦尔热法则,绝对多数制天然倾向于塑造离心竞争的两党制,相对多数制容易塑造出向心竞争的两党制,而不加门槛限制的比例代表制则容易导致碎分化的多党制。[5]从选举操作及实效看,绝对多数制主要优点在于当选者有较高的民意支持,代表性强。其主要缺点则在于,两轮投票中第一轮往往无人胜出,须得第二轮,费时且劳民伤财;而且,第二轮选举前,政党结盟时往往倾向于政治立场的区隔,不利于凝聚共识且有较高极端化的可能,这些问题都会对选举过后的议会活动产生不良影响。相对多数制的主要优点在于程序明了、计票方便,由于在单一选区中只有两大主要政党才有机会胜选,所以天然倾向于奖励大党、惩罚小党,易形成两党制。又由于两大党在长期经营的选区中往往旗鼓相当,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不是两党的基本盘,而是那些模棱两可的中间选民。为吸引这些对两党“好处都想要、坏处都躲开”的中间选民,两党立场自然会彼此接近,因而导致政策趋同和向心竞争。相对多数制的主要缺点在于候选人不过半数选票也能当选,死票多、有代表性不足之嫌,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英美两国不时出现过的少数当选和统治的“宪政危机”、“正当性危机”。比例代表制的主要优点在于能避免选票浪费、充分反映民意。由于少数支持即可获得席位,小党较易生存。其主要缺点则是政党更倾向于表达其意识形态及原则,容易促使政党分裂且易于产生偏激、极端的政党,容易造成政党林立,彼此间政见分歧大,会加剧政府政治的不稳定。比例代表制下附加适当的当选门槛,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但很难消除此种症状。混合选制一定程度上能够兼收相对多数和比例代表制的好处,同时也能较好地缓解两者的弊病。
四、香港治理与选举改革须深入探讨和稳妥处理的问题
务实地讲,不存在最理想的选制,也不应片面地、浪漫地去追求最好的选举及其效能。只有从既有选制所积累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人们才能最终找到、接受一种“最不坏”的方案。在新兴民主社会,选制改革应呼应特定时期内政治发展的需要和公共治理的要求,不可能一役功成而只能渐进地调适。长远来看,有关各方还是应当着眼于治理和善治,立足选举但不局限于选举,理性地、负责任地擘画香港的选举改革、政制发展。
第一,一个最直观、受关注最多的问题,就是技术层面上重新设计或选择新选制的问题。不管未来香港到底采用什么选制,首先都应当基本上满足以下要求:一是能够诱导向心竞争,能从长远上确保特首及政府施政的连续性,亦能从整体上致力于遏止香港业已出现的政治上极化对抗的苗头;二是能够塑造某种温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减少出现在立法会中的有效政党[1]150数目,以消除小党林立、效率低下的弊病;三是能够直接、迅速和尽可能真实地体现民意,并因而能为当选者履职塑造必要的权威;四是平等、公正,具有较高开放性、透明度,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游戏规则,塑造一种“愿赌服输”“败者同意”的健康的政治生态,有助于政治妥协且有助于降低对抗性。这里有必要指出,选制改革的主导方应当慎重、理性地对待和利用自己在制度创制过程中的先天优势,但又不能企图便宜占尽、好处独揽。必须考虑到选举带来的政治力量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自己预期中的好处也完全可能为对手所斩获。
第二,一个最富争议也亟待突破的问题,就是香港民选政治中政党的地位问题。香港存在常态化、地方性的政党政治,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香港立法选举政党政治化程度已经很高,立法会因选举自然分化为多数、少数,分化为主流派、反对派,若专注于政策理性,此种力量格局在整体上还是有利于香港民主发展和内部治理。当前,香港政党竞争之所以呈现非理性、泛政治化倾向,在于选举内在的、本质的责任政治要求因政府“非党化”而无法贯彻到底。民选政治的未来发展迟早会将政党政府问题提上日程。特首既要向香港公众负责、又要向中央政府负责,保持非党色彩有利于履职,无疑是合理的。但政府不同。权责分离,政党永远只是在议会中监督,特首和政府总是遭遇既没有行政经验、又未担当过政府责任的政党的重重羁绊,缺乏必要的立法和政治支持,这是一个容易强化政党恶性竞争的体制弊端,应当考虑通过创新制度来予以改进。
第三,一个最具根本性的检验标准问题,就是香港民主发展与特区治理效率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地方政治,须率先注重特定层面上民主政治与治理要求的匹配、协同。必须明确,民主并不能解决香港全部的治理问题,但民主发展内在地要求自由、平等,要求厚重和坚守权利本位并合理地规范和限制权力,因而能从整体上有利于香港治理的过程和效能。香港治理所需要的不只是民主,其整体影响也不仅限于民主本身,它追求以最少的资源和代价收获最大、最广泛的社会效益。效率是香港治理最基本的标准,它对民主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于不断地降低制度和决策的成本。基于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立场,离开治理的现实的、迫切的要求去搞民主,不会产生适宜于香港特区的民主;而缩减治理的范围和目标,消极对待基于现实治理要求的民主化进程,过于强调对香港社会、香港地方的有效控制,以保守的姿态对待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香港政制的优化改良,也不会产生人们所深切期待的有效治理。
第四,一个最具直接现实性的关键问题,是香港治理与中央—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选举改革及相关的香港治理和政治发展不只是特区内政府、政党与公众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是高度自治的,但此种自治又是中央政府依法授予的。中央政府不直接介入香港自治,但香港的主权、治权始终都属于国家而非香港地方。为了协调好中央与香港地区的治权、治理关系,使两方面都能接近各自所预期的目标,在涉及宪制原则和香港基本政治体制的问题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公众、相关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实现同情理解、妥协让步并最终达成共识。尽管不能排除未来会适时修法,但相关各方都必须接受和尊重基本法及其原则精神——这将是一切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基础。由此,一方面,香港地方选举和治理不得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以至全国统治的合法性,不管是谁参选或当选特首、立法会议员,都应谨守分际,不得僭越;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应对香港地方政局保持适度的中立与克制,不宜直接介入和干涉分属香港地方治理权限的事务,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使自己矮化为香港选举中一个隐形的投票对象。总之,因为高度自治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中央政府必须有适度的妥协,以呼应香港的民意;因为地方政治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香港有关政治力量必须向中央政府妥协,不能要价太高,更不能任性诉诸第三方外部力量。
概言之,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香港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表面上风光、热闹的政治纷争,更在于经济社会的良性改革,在于破解港英治理时期就严重积压而来的、回归以后又逐步累积的深层次矛盾。由此,香港地方治理应尽快回归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政策本位。否则,要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与稳定就成了空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日解决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香港政制的内在矛盾,撤除阻滞香港社会深层次变革、限制以至削弱香港活力和竞争力的体制、机制障碍,无疑是紧迫的、必要的。但香港选举改革与治理改进的具体走向、方式、途径及最后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各方面要素、力量的组合与平衡。其中影响比较突出者,一是香港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以及这些政治力量的政治智商与情商的高下;二是香港特区相关政治主体与中央政府彼此妥协空间的大小、关系融洽的程度;三是香港特区政治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能否成功搭建起某种相对舒适的良性协调关系。
就内地相关政策当局和观察家而言,对于香港的政治发展、选制改革和治理优化,还是应当抱持一种审慎、开明的姿态。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必须充分重视香港社会公众因英国长期殖民统治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文化心理移民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出于敌我矛盾斗争的定位和需要,仅着眼于管治权问题去考虑、处理包括选举改革在内的香港政制革新发展问题。我国是世界性大国,对香港有公认的、无可辩驳的主权,在香港有驻军、有宪法和基本法蕴涵的充分的策略手段储备,不必激化香港内部、中央与香港地方之间的政治矛盾。相反,服膺和遵循内因决定论的基本逻辑、相信和尊重香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一切从有利于香港地方治理和善治的角度出发,以雍容、自信和开放的气象和姿态对待香港政制、选制改革,提升香港治理的水平和效能,才是正道、王道,才能在直接、有效地服务于香港大众的基础上赢得民心,也才能从根本上使所谓管治权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1]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M].台北:台湾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5.
[3]朱世海.香港政党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137-147.
[4]刘光毅.论意大利现行选举制度[J].欧洲研究,2011(1):121-132.
[5]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M].London:Methuen&Co.Ltd,1954:216-255.
责任编辑:杨 东
On Electoral Reform and Effective Adm 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XU Feng
(Central Institute of Socialism,Beijing,100081)
There are specific objectiv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election and electoral system,which will pose direct and profound political impacton governance or administration.Being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design of electoral system,the democratic election in Hong Kong after its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as both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omething not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We shall treat the optimization of e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with an open mind,cautiously deal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Hong Kong governmentand Hong Kong people with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ommodation,and abandon the dichotomy concept on fighting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and irrational,non local governance oriented pan-political impulse.
election;electoral system;effective administration;party politics
D618
A
1002-0519(2014)04-0064-06
2014-04-21
徐锋(1973-),男,山东临沂人,法学博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策学、政党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