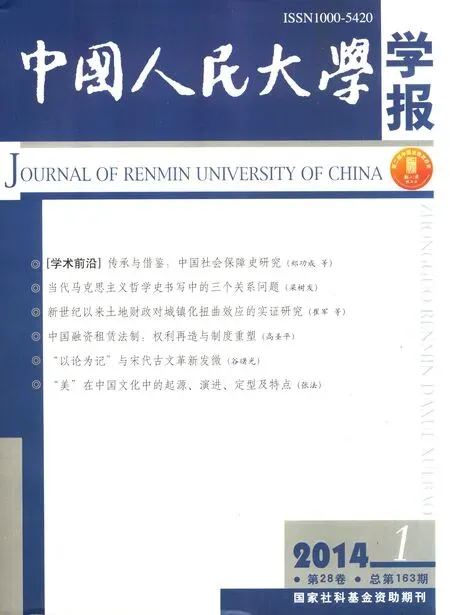中国融资租赁法制:权利再造与制度重塑
——以《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为参照
2014-01-24高圣平
高圣平
中国融资租赁法制:权利再造与制度重塑
——以《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为参照
高圣平
《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及三大议定书反映了融资交易法制的最新发展。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保有租赁物权益的实质在于担保租金的清偿,但无须将其重构为担保交易。基于融资租赁交易与担保交易之经济目的的共通性,担保交易的相关规则应当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只要采取书面形式、出租人具有处分权、标的物具有特定性,出租人利益即构成公约所保护的国际利益,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国际登记采取声明登记制和物的编成主义,通过电子化的登记系统起着公示动产物权的作用。同一标的物之上竞存的物权依其登记先后确定优先顺位,但允许法定担保物权依缔约国的声明而取得相应的优先顺位。承租人出现约定或法定的违约情事,出租人可以在法院的同意之下,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可在终局裁决之前采取临时性救济措施。
融资租赁;开普敦公约;担保权;国际利益;国际登记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的日益发达及高新技术复合材料的广泛采用,动产设备(包括航空器、铁路车辆、空间资产等)的价值不断攀升,已然成为相关经营者沉重的财务负担。基于自有资金的限制,经营者大多寻求来自商业银行、制造商及其他信用授受者的信用支持。其中,融资租赁以其融资便捷和节税等优势,在融资交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交易模式的生成和发展端赖于交易安全与交易成本的综合考量。就信用授受者而言,无论是租赁公司,还是商业银行,其所关注的重心乃在于其对于动产设备的权利是否得到承认和保护。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结构错综复杂,结合寻求高回报而跨境流动的资金,事渉不同国籍的多数当事人[1](P385),由此而造成权利保护和救济措施上的不确定性,许多信用授受者对为此类资产提供融资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一直致力于动产交易法制的统一化,意在架构高价值动产融资的一整套实体法规则和一个国际化的权利登记系统。[2]2001年至2012年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先后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一起通过了《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以下简称《开普敦公约》)、《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航空器设备特定问题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航空器议定书》)、《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铁路车辆设备特定问题的议定书》(以下简称《铁路车辆议定书》)、《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空间资产设备特定问题的议定书》(以下简称《空间资产议定书》)。《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是目前调整融资租赁交易的最新国际规范。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是国际私法史上最重要的商事公约之一”[3],反映了高价值动产之上国际担保权利的制度需求,提高了动产融资的法律确定性,降低了动产交易的制度风险[4],无论是动产融资交易的统一化,还是公约本身所采取的“伞状”结构,均得到很高的评价。[5]《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植根于国际融资实务已发展成型的结构安排与风险管控模式,强调规则内容的实用价值,重视实务操作者的商业习惯和要求,而由航空法学者以概念拟设的规范体系在这里被置于次要位置。《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还尽量避免创设非实践所需的额外制度,并以当事人意思自由作为决定融资交易所生权益的基本原则。[6](P377)截止到目前,共有57个国家或经济体批准或同意了《开普敦公约》,51个国家或经济体批准或同意了《航空器议定书》。我国是《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的缔约国,《开普敦公约》及《航空器议定书》已于2009年6月1日起对我国生效。
但是,《开普敦公约》对于动产融资交易所采取的立法方法和制度安排,与我国法律之间的差异较大,尤其是相关动产(担保)权利的成立、效力、登记、优先顺位和实行等方面的实体法规则更是不同。在我国,融资租赁交易被纳入《合同法》作为一种有名合同进行调整,但其中租赁物的占有或交付不能起到公示租赁物之上权利负担的作用,相关法律对此均未置明文,给交易本身带来较大的制度风险。目前,融资租赁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在信用授受市场上日益活跃,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风险控制,均需理论支撑。同时,针对日益增加的融资租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的起草,至今已数易其稿,其中的法理不可不辨。本文仅以《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为中心,简要介绍融资租赁法制的最新发展,并就我国法上的融资租赁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二、融资租赁交易的体系地位
融资租赁交易本属美国融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交易类型,各国在引进这一交易形态时,面临着对其重新进行类型化、概念化的困难。关于融资租赁交易的性质,各国学说和立法例上并不一致。在学说上,融资租赁素有分期付款买卖说、特殊租赁契约说、消费信贷说、动产担保交易说、无名契约说、独立交易说等之争[7](P41);立法例上有单独立法、混合立法和未作立法等多种形态。[8](P46)如此多样的国内法,无形之中形成了高价值动产跨境融资租赁交易的制度风险,增加了高价值动产融资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才着力于统一动产融资的实体法规范,以降低动产融资成本并提高动产融资交易的效率。[9]
《开普敦公约》的本意是想构建一个单一体制,不仅调整依担保合同所创设的典型担保权,而且规范在功能上等同于担保权的一些权利,如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出卖人保有的所有权,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享有的所有权。但是,如将后者界定为担保权,《开普敦公约》将面临着北美洲之外的国家拒绝加入的风险。奉行北美式动产担保法制的国家在担保权的认定上采取了功能主义立法模式,只要在功能上起到担保作用,不管当事人如何安排交易结构,都是担保权。但大多数国家在权利类型化上会首先区分所有权与担保权(他物权),然后再对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进行细分[10],进而采取了以交易形式为依据的类型化方法(形式主义立法模式)。这些国家的国内法大多不乐意将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或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所享有的权利界定为完整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11]因此,《开普敦公约》在其调整范围上既采取了功能主义方法,又采取了形式主义方法,凡是在功能上意在创设国际担保权的交易均属《开普敦公约》的调整范围,但这一方法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开普敦公约》还在此之外规定了两种依其形式而由《开普敦公约》调整的交易: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和租赁交易(《开普敦公约》第2条第2款)。
不过,这三种类型化上的区分更多只是概念上的,并不影响实际操作。在本质上,包括出租人所享有的权利在内的国际利益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物权,仅在主债务履行受阻或不能实现时才发挥作用。[12]无论是权利的对抗要件、优先顺位,还是权利的实现条件和规则,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权利均等同于担保交易中担保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虽然在《开普敦公约》之下,融资租赁交易在形式上是不同于担保交易、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一种交易形态,但在实质上,《开普敦公约》将三种交易作一体处理,仅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和融资租赁交易的特殊之处作了特别规定。不管这一技术处理基于何种目的,都为我国的制度重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在我国法上,融资租赁交易主要受《合同法》第十四章调整,由此可见,我国并没有将融资租赁交易作为担保交易来对待,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化交易(有名合同)加以规定。在典型的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权益属于所有权,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权益属于债权性质的使用权。[13](P370)我国《合同法》第十四章以14个条文对融资租赁交易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指引当事人的融资租赁行为、补充交易当事人的意思的作用。但是,由于《合同法》本身调整范围的限制,对于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物法因素未置明文,直接导致权利人保护规则的缺失。及至《物权法》起草,立法者已然注意到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物权问题。例如,在典型的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的所有权由出租人保有,但租赁物却由承租人占有和控制,租赁物的占有本身无法达到公示标的物之上的权利状态的目的,立法者遂在《物权法》第117条中明确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试图以“出租人所有权+承租人动产用益物权”的权利架构来解决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物上权利冲突问题。[14]但由于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立法已经启动,《物权法》就仅作了一条援引性规定,具体制度设计拟留待融资租赁法去解决。我国法上有关融资租赁交易本身的制度设计缺失之处较多,出租人的权利得不到周延的保护,直接影响到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我国目前融资租赁交易法制的发展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颇为一致,维系着“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承租人对租赁物享有债权性利用权”这一法律结构,追求着大陆法系物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形式理性。但这一僵化的体系安排早已为多国学者所关注,其中隐藏的制度风险几乎成了经济转型国家法制改革中意欲克服的一大障碍。我国在2003年启动融资租赁立法之时,就充分注意到融资租赁这一具有体系异质性的交易形态的特殊性,在我国并未建立为购置财产提供融资所形成的担保权的超优先顺位的情况下,明确地将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结构规定为“出租人的所有权+承租人的租赁权”,以所有权的效力来保护出租人资金的安全。但为解决传统动产公示方法的不足所带来的“虚假财富”问题,明确以登记作为融资租赁交易的公示方法,同时仿效美国的融资租赁法制,该登记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而仅具对抗效力,亦即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第三人主张。我国目前融资租赁法制的地方实践亦是沿着这一路径在发展,天津滨海新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即明确:凡在该地区所开展的融资租赁交易,当事人均应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登记,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辖区内金融机构在接受这些租赁物作为融资担保时亦应查询该系统,否则,其担保权将劣后于租赁公司的所有权。
由此可见,我国法上基于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以及担保物权的体系定位,并未将融资租赁交易视为一种担保交易,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租赁交易。但也认识到融资租赁交易确实有一些与担保交易相类似的特征,出租人的所有权与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在经济上的目的是相同的,均起着担保主债务清偿的作用。对于这种在功能上起担保作用但无所有权移转的潜在必然性的交易,令其受担保物权公示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出租人与担保交易中的担保权人一样,只有公示其权利(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若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公示,承租人依其占有租赁物的事实即被视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承租人在租赁物上设定的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有可能优先于出租人的所有权。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明显地迁就了大陆法上植入融资租赁交易制度时的体系障碍,明确了融资租赁交易虽然依国内法不构成担保交易,但因其功能仍在于担保而仍然适用《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融资租赁交易除救济措施不同于担保交易外,其他如出租人利益的构成、公示(登记)、优先顺位、让与、实行等均应适用《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如此看来,我国也没有必要依功能主义进行体系重构,没有必要将融资租赁交易依其功能归入担保交易并进而受《物权法》(担保物权编)的约束。但是,即使不将融资租赁交易重构为担保交易,亦应使其在物法因素的相应层面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三、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利益的构成
国际利益是《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所保护的最主要的利益[15](P24),系指特定种类动产之上因合意而生的起着担保债务履行作用的物权,涵盖了依担保合同所生的(担保)物权、依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所享有的物权(所有权)以及依租赁合同所享有的物权(所有权)。易言之,国际利益就是动产之上的抵押权、质权等担保权,或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或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所有权。[16](P759)在这里,《开普敦公约》并未强行将这三种物权归于同一种类,而是尊重各国在权利类型化上的特殊性,但纳入公约调整的三类物权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担保。这一处理方法可以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同时,作为国际上所承认的物权,国际利益独立于依国内法所产生的物权,既不来源于国内法,也不依赖于国内法。
根据《开普敦公约》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权利构成《开普敦公约》所称的国际利益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协议采取书面形式; (2)出租人有权处分该标的物;(3)按照议定书的规定指明该标的物。即使根据相关准据法的规定,满足这些条件并不足以创设动产权益,即使该国际利益在该准据法中并无规定,均不例外。[17](P175)由此可见,《开普敦公约》尽可能地简化了形式要件,且不允许缔约国任意增减、变更。如果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融资租赁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即不能有效地成为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利益,即使将其登记于国际登记处,也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正如前述,在我国现行法之下,融资租赁交易采取“出租人所有权+承租人租赁权”的法律结构,虽然所有权的经济目的仅在于担保租金的清偿,但依体系解释,这里的所有权仍为完全的物权,并未将其架构为担保权。准此,《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中对融资租赁交易中国际利益的构成与我国法并无实质上的冲突。
(1)关于书面形式。我国《合同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与《开普敦公约》完全相同。至于书面形式,则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第11条),与《开普敦公约》第1条中关于书面形式的含义几近相同。
(2)关于出租人的处分权。在我国《合同法》之下,通说认为融资租赁是一种三方结构的交易安排[18](P344),包括出卖人与买受人(出租人)之间的买卖交易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交易。除了买卖交易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标的物的所有权自出租人将标的物交付承租人时起转移。就航空器物权变动而言,我国法上采登记对抗主义,但即使是登记对抗主义,航空器所有权亦是自交付时起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只是在登记之后才能对善意第三人主张所有权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了转移。准此,承租人对于出卖人、出租人(买卖人)而言,虽为第三人,但因其知悉所有权在出卖人和出租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事实而不构成善意第三人,即使此后发生权利冲突,出租人亦可对承租人主张其对航空器设备的所有权。由此看来,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处分权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法上可堪确认。
(3)关于标的物的特定化。在我国《合同法》之下,融资租赁交易标的物的特定化实为题中之义,否则无法交付承租人使用。依我国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航空器所有权、占有权登记,申请书中应载明航空器型号、制造地点、航空器制造者名称、航空器出厂序号和出厂日期等,虽然称谓与《开普敦公约》及《航空器议定书》的要求并不一致,但仅我国法上对航空器的描述而言,应已达到《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规定的必要、充分要件,足以识别航空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尚未践行航空器发动机的单独登记,这些都是将来在修正登记规则时应考量的。
综上,虽然出租人对于租赁物的所有权在解释上先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交易,其是否设定(构成)在我国法之下不是融资租赁合同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此前出卖人与买受人(出租人)之间的买卖交易所欲解决的问题。但是,仅就《开普敦公约》及三大议定书所规定的出租人利益构成的几个形式要件而言,我国法上的相关规则与之并不矛盾。《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利益的构成除了上述三个形式要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要件,但依《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文义,应当作绝对化的理解,即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要件,否则,《开普敦公约》所倡导的统一动产担保权利的创设规则的基本理念即被严重扭曲。[19](P8、13-14)这也是我国在重构相关法制时应当注意的。
四、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利益的国际登记
在《开普敦公约》之下,国际利益被界定为一种物权,其效力除了及于交易当事人外,还及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同时,国际利益不以移转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传统法上“动产的占有即为所有”,亦即动产权利以占有为公示方法,显然在国际利益的变动上失去意义,公示制度的构建也就成了公约的重要一环。国际利益实际上就成了赋予标的物的物权人通过在国际登记处登记来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20](P27)
《开普敦公约》的核心在于国际登记制度[21],但在该公约之下,登记并非国际利益的生效要件,亦非国际利益存在的证据,是否登记并不影响国际利益的构成或设立。但已经登记的国际利益如果不是有效成立的,也不产生任何效力。在这里,登记的功用在于确立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亦即使一项有效成立的国际利益的优先顺位取决于简单、客观而又明确的“先登记者优先”规则。[22](P47)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针对三大类标的物及相关权利分别设立了三个国际登记处。国际登记处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完全电子化的系统,是登记国际利益的中心所在地。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融资租赁协议所进行的利益登记,并非所有权登记,仅系出租人所持有的利益的登记。因此,出租人对于标的物的利益不是经由租赁协议而获得,而是通过先于租赁协议的另外一个协议所产生,只是在订立符合《开普敦公约》要求的租赁协议之后,这一利益才能登记。
国际登记处采取声明登记制而非文件登记制。登记时仅须向登记处输入登记所需内容,但无须提交协议文本或副本。[23](P118)录入数据库中的内容仅涉及与现有或预期利益有关的最少信息。除了描述国际利益所及的标的物外,《开普敦公约》将其他登记内容授权各登记规章去规定。在《开普敦公约》之下,国际登记必须由债权人提出申请并获得债务人同意后,登记才生效,未经同意即径行登记,该登记不产生效力,以保护债务人以及潜在的债务人。
我国尚无统一的动产登记制度,在公约所涵盖的三大类动产中,目前仅建立了航空器登记制度。就航空器权利的登记,我国在《民用航空法》之下由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以下简称《登记条例》)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这两部主要的规范性文件调整。仅就航空器融资租赁交易登记而言,这些规则亟待修改。
第一,登记的权利类型有待修正。在国际登记中,航空器设备融资租赁交易登记的是构成国际利益的出租人利益(主要是出租人的所有权)。在我国现行航空器设备融资租赁交易登记中,出租人可申请登记航空器所有权,但承租人亦应申请登记航空器占有权。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对航空器所取得的租赁权在这里被直白地表述为占有权,但这一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债权,是否有登记公示的必要值得怀疑。同时,同一航空器的权利登记簿上同时登记所有权和占有权,两者之间并无须依登记先后确立彼此间的优先顺位,这一占有权登记的制度设计实与动产登记的基本功能相违。
第二,登记内容需要简化。现行登记规则规定的登记内容详尽,体现了文件登记制之下登记管理的基本思路。登记的作用仅为公示标的物上可能存在的权利负担,一不保证这一记载是真实的,二不过分披露当事人之间的商业秘密。所以,登记内容的设计至为重要。相比较国际登记,我国的登记内容过于详尽。
第三,纸面化的登记体系亟待改变。我国现行航空器权利登记体系是1997年以后构建起来的纸面化登记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迁就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与数字化信息相比,纸面信息易于因蓄意破坏、盗窃或火灾、洪灾或其他灾难而受到破坏或损坏。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化的录入和查询在速度上比纸介质的要快得多,成本也比纸介质低得多。[24](P304)为提高登记效率,简化查询程序,节约交易成本,宜仿国际登记改行电子登记系统。
第四,尚需增加新的登记类型和新的航空器标的物。我国现行航空器权利登记体系仅仅及于民用航空器。在《民用航空法》之下,民用航空器是指除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务外的航空器,这里是否可以涵盖直升机尚值得研究。而《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所称的航空器设备,包括航空器机身、航空器发动机和直升机,这些标的物均应纳入登记范畴。此外,《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中增加了不可撤销的注销登记和出口请求许可书的备案登记,我国也选择性地加入了该条款,这一新的登记类型亦应在国内登记中得到反映。
综上,《开普敦公约》所倡导的国际登记系统是基于登记对抗主义的理性选择,符合动产登记法制的基本法理。由于国际登记系统的国内接入口的相关登记规则适用国内法,我国相关登记规则即应在公约框架下进行重构。我国航空器权利登记制度置重于航空器的行业管理,漠视了权利登记制度不同于国籍登记的功用,亟须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修改相关规则,以与《开普敦公约》所规定的国际登记系统相衔接。
五、竞存权利或利益的优先顺位
高价值动产设备的跨境交易往往涉及不同国籍的当事人,加上设备本身具有国际性和高移动性,使得标的物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仅依准据法难以解决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问题。因此,《开普敦公约》设计了统一简单客观的规则体系,以避免因国内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复杂问题。国际利益之间的优先顺位架构仰赖于国际登记。《开普敦公约》所规定的优先顺位规则非常简单:已登记的利益优先于在其后登记的任何其他利益和未登记的利益。知悉在先的未登记权利,并不影响已登记的权利人的优先顺位[25](P237),但当事人可依约定改变竞存权利之间的顺位。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的利益不得对抗在其之前已登记的利益。出租人如依担保协议的约定将其利益为债权人(担保权人)设定担保,在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或法定的违约情事时,担保权人可以对承租人所占有的标的物主张担保权。此时,承租人与担保权人之间发生权利冲突。[26](P225-226)由于承租人的利益无法在国际登记处进行登记,因此,担保权人无法在设定担保之前通过国际登记处查询得知标的物之上的权利负担。相反,如果担保协议在租赁协议之前即已存在,出租人的国际利益登记之时,则代表租赁协议的存在,也等于通知承租人在此项利益之下该担保利益的存在。如果出租人使担保权从属于承租人的利益,就可能造成担保权人无法通过国际登记处查询得知两者利益重叠的不公平情况。[27](P210)因此,为维护登记系统的完整性,《开普敦公约》的基本原则是使交易当事人不受任何未登记利益的影响。《开普敦公约》明确规定,承租人取得的对标的物的利益或权利不能对抗在出租人持有的国际利益登记之前已登记的利益[第29条第4款(a)项]。这一规定表明,承租人与担保权人之间的优先顺位,取决于出租人利益和担保权两者之间的登记顺序,如果担保权在出租人利益之前登记,则担保权优先于承租人的利益;反之,如果出租人利益先于担保权登记,则担保权劣后于承租人的利益。
就动产之上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我国法上的规定并不清晰,尚须结合《物权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的规定综合起来进行解释。(1)动产之上竞存的抵押权之间依其登记先后定其顺位,同时登记的,按债权比例受偿;已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未登记抵押权之间的顺位相同,按债权比例受偿。(2)动产之上的抵押权和租赁权竞存时,依两者设定的先后顺序确定彼此之间的顺位。(3)动产之上先设立的抵押权或质权与后成立的留置权之间,留置权优先。(4)动产之上的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时,已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权。这一优先顺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信用状况之下的无奈安排,但其过分强调权利类型,并未体系化地综合考量优先顺位规则的基本法理。竞存权利之间实际上是依其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来确定各自的优先顺位,但权利类型不同,取得对抗效力时间的判断标准就不一致。例如,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登记时间即为其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动产质权以交付为公示方法,交付时间即为其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留置权等法定担保物权的法定时间为取得对抗效力的时间。如此无法形成一套统一的、明晰的优先顺位规则。
在《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框架下,竞存权利之间依登记的先后顺序定其顺位,登记同样是国际利益取得对抗效力的前提条件,但《开普敦公约》剥离了第三人的主观善意的判断。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虽未登记但仍可对抗恶意的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设立在先的权利未登记,设立在后的权利的持有人在知道在先权利的情况下办理了登记,在先未登记的权利仍可对抗恶意的在后的已登记权利。如果如此,竞存权利之间就会多一个主观判断因素,徒增优先顺位上的不明确性,就会招致事实上的纷争,引发不必要的诉讼,终将导致成本和风险的增加。[28]此外,《开普敦公约》不考虑当事人是否知悉竞存权利的存在,仅以登记作为确定竞存权利之间优先顺位的唯一客观因素,增加了优先顺位规则的确定性。但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航空器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明显地植入了第三人的主观因素。对此,我国在制度重建时如何处理,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六、融资租赁交易中债务人违约时的救济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主要反映了信用授受者的合理预期[29],对于权利人的保护较为周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兼顾了债务人的利益,此点在债务人违约时救济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一套及时、充分、可强制执行的违约救济措施对于信用授受者而言至关重要。《开普敦公约》第三章设计债权人救济权的规范目的在于:当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能充分预期并能立即采取违约救济措施,其中将出租人作为标的物的有权处分人,一旦合同解除,出租人即可任意处分标的物。
在意思自治原则之下,《开普敦公约》允许融资租赁当事人在任何时候对构成违约或导致公约所定权利和救济措施的具体情形作出书面约定。《开普敦公约》关于违约构成的规定在性质上仅是缺省规则或任意性规范,仅在当事人未作约定的情况下才予适用。在高价值动产融资交易中,鲜有不对违约的构成作出约定的。在当事人对违约构成未作约定的情况下,应依《开普敦公约》的规定,以“实质性地剥夺债权人根据协议有权享有的期待”来认定违约,《开普敦公约》在这里使用了“实质性地”的用语,以避免各国不同法制之间可能产生的诸如“严重的”、“根本的”等法律用语的歧义。
根据《开普敦公约》的规定,在发生违约情事时,出租人可以解除协议、占有或控制标的物。《开普敦公约》允许权利人就标的物寻求私力救济途径,但须取得当事人同意。在债务人对债权人依《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享有的违约救济权发生争议时,法院的审判程序往往受限于各国法制而旷日费事,标的物在诉讼过程中,极有可能毁损、灭失,损及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从标的物受偿的利益。[30]准此,融资者最为关心的是违约救济权在实务上的实现,诸如执行所费时间等。快速的实行机制就成为《开普敦公约》所置重的主要目标之一[31],《开普敦公约》因此规定了终局裁决前的临时救济措施。
同《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相比,我国法上有以下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关于违约的认定问题。我国《合同法》上虽然没有明文允许当事人就违约的定义和构成作出约定,但法条就违约的构成使用的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这一宽泛的界定,在解释上自是已经允许当事人就违约的定义和构成作出约定。
第二,关于违约的救济方式。《开普敦公约》第10条规定的是解除合同并占有或控制标的物,我国《合同法》也规定了承租人违约支付租金时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但就合同的解除条件,我国法上规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同时允许当事人约定合同的解除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轻微的违约不能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在法定解除条件中,有一项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实际上传达的是和《开普敦公约》“实质性地剥夺债权人根据协议有权享有的期待”相同的意义。
第三,关于违约的救济途径。我国法上就权利的实现,历来限制私力救济途径的适用。[32](P87)私力救济迅捷、及时地保护权利的优势世所公认,《开普敦公约》仿北美动产担保法制,规定了国际利益的私力(非司法)救济途径[33],但同时考虑到许多国家基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强烈反对私力救济方式,《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也就允许缔约国对此作出保留。我国在加入《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时对此作了声明,要求必须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同意后方可施行。由此可见,国际利益的私力救济在我国没有实施空间。但我们也注意到,我国在加入《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时申请加入了《航空器议定书》第13条(注销登记和出口请求许可书),这两种附加的救济权在性质和功能上相当于私力救济[34],因为其行使无须取得法院的同意或令状,一旦债务人违约,已经备案的许可中的受益人(被许可人)即可行使上述附加救济权,请求登记机关注销登记,或请求有关机关准予出口和实体转移,缔约国的登记机关和其他管理机关应当迅速配合并协助被许可人实施上述附加救济权。由此可见,我国在不允许私力救济的同时,允许另外两种具有私力救济功能的非司法救济路径。
就公力(司法)救济途径而言,我国法上并未将融资租赁交易界定为担保交易,而是定性为一类特殊的交易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租赁交易,也不同于担保交易,由此而决定了我国主张相关利益时应适用《开普敦公约》第10条(附条件卖方或出租人的救济)的救济方式。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增设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允许担保物权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许可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裁定,从而无需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这一特别程序旨在更好地保护担保物权人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资源。[35](P334)但在我国法之下,出租人对于租赁物的权利在性质上并未被重构为担保物权,自然不能利用这一新设程序所带来的便利。
第四,关于终局裁决前的临时救济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有保全措施可资采用,但《开普敦公约》规定的快速救济措施是完全独立的制度设计,它不依赖于、也不来源于国内法上的临时救济和禁令措施,也不能按照国内法上的临时救济或禁令措施来解释。也就是说,采取《开普敦公约》上的快速救济措施,并不排除依准据法采取其他形式的临时救济措施。《开普敦公约》上的快速救济措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是在《开普敦公约》所要求的快速实行机制和各国国内程序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36]国内法上的临时救济措施大都根植于衡平原则,其目的在于避免给当事人一方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通常只有法院基于自由裁量权才能采取临时救济措施,其所追求的是公平。但《开普敦公约》规定的快速救济机制与国内法上并不相同,其所置重的是:通过规定一个客观标准(债务人违约的表面证据)来达到商业上的可预见性。[37]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全条件是“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财产保全的措施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这里,查封针对的是不动产,扣押针对的是动产,冻结主要针对的是债务人在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38](P165)和《开普敦公约》的快速救济措施相比,我国法上的保全条件是法定的,而《开普敦公约》规定的条件是可以约定的,我国法上保全措施少于《开普敦公约》,《开普敦公约》规定可以出租和管理标的物,并收取由此发生的收益,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特别同意的情况下,还可以变卖标的物并分配变卖价金。由此可见,《开普敦公约》所规定的快速救济机制可谓更为周全。
综上,我国在违约救济途径上不允许非司法救济,《开普敦公约》所规定的各种救济权均需取得法院同意后才能行使,且须依照我国的法定程序进行,司法救济途径的现代化无疑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有程序和规则来看,我们的程序供给并未达到《开普敦公约》规定的标准。虽然我国在加入《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时对采取临时性救济措施的时限作了规定,但这毕竟只是针对终局裁决前的临时措施而言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争议还得仰赖于审判和执行程序。仅就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而言,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出租人并不能直接申请许可拍卖、变卖标的物的裁定,其主张权利还得经过审判程序取得生效裁判,进而通过执行程序实现自己的权利。
《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反映了当代担保融资和租赁交易的基本价值追求:明晰的优先顺位规则、快速的权利实现规则,且优先顺位规则、权利实现规则并不受破产程序的影响,至于国内法上采取什么样的交易类型化方法,无论界定为担保交易、所有权保留交易还是融资租赁交易,只要是寻求为高价值动产设备的购置和利用提供融资担保,均在《开普敦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我国融资交易的立法与实践与此相差很远,我国既已加入《开普敦公约》和《航空器议定书》,就应履行公约义务,在国内法的程序建构上应与其相协调,并借助《开普敦公约》及相关议定书的法理念重构我国融资租赁法制。
[1] 黄居正:《航空器融资的新国际规范》,载氏著:《国际航空法的理论与实践》,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 Ronald C.C.Cuming.“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Aspects of Security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Uniform Law Reviews,1990—1991(64).
[3][11] Roy Goode.“The Unidroit Draft Mobile Equipment Convention:Confluence of Legal Concepts and Philosophies”.In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Denis Tallon.D'ici,d'ailleurs:harmonisation et dynamique du droit,Paris:Société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1999(69).
[4][29] B.Patrick Honnebier.“The Convention of Cape Tow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The Solution of Specific European Property Law Problems”.European Review of Private Law,2002(3).
[5] Lorne S.Clark.“The 2001 Cape Town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nd Aircraft Equipment Protocol:Internationalising Asset-Based Financing Principle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ircraft and Engines”. Journal of Air Law and Commerce,2004(69).
[6] Ronald C.C.Cuming.“The Characterisation of Interest and Transac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In Iwan Davies(ed.).Security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Hants: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2002.
[7] 刘敬东:《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8] 程卫东:《国际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9][34][36][37] Jeffrey Wool.“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viation Finance Law:An Overview of the Proposed 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s Applied to Aircraft Equipment”.Air& Space Law,1998(23).
[10] Roy Goode.“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arth and Space:The Preliminary Draft 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Uniform Law Reviews,1998(1).
[12] 于丹:《〈开普敦公约〉体制下的国际利益研究》,载《当代法学》,2011(2)。
[13][18]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4] 高圣平、王思源:《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架构》,载《法律科学》,2013(1)。
[15][17][23][26] Roy Goode.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nd Protocol Thereto on Matters Specific to Aircraft Equipment:Official Com mentary.Rome:UNIDROIT,2008.
[16] Philip R.Wood.Comparative Law of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itle Finance.London:Sweet&Maxwell,2007.
[19] Steering and Revisions Committee.UNIDROIT 1998 Study LXXⅡ-Doc.41.1998.
[20][22][27] Roy Goode.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nd Luxembourg Protocol Thereto on Matters Specific to Railway Rolling Stock:Official Commentary.Rome:UNIDROIT,2008.
[21] Ronald C.C.Cuming.“The Registry System of the(Draft)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nd the(draft)Aircraft Equipment Protocol”.Revue du Notariat,2001(103).
[24] 高圣平:《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5] Roy Goode.“The Unidroit Mobile Equipment Convention”.In Michael Bridge,Robert Stevens(ed.).Cross-Border Security and Insolven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8][31] Anthony Saunders and Ingo Walter.“Proposed 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s Applicable to Aircraft Equipment through the Aircraft Equipment Protocal: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 Air&Space Law,1998(23).
[30][33] Jeffrey Wool.“The Case for a Commercial Orientation to the Proposed Unidroit Convention as Applied to Aircraft Equipment”.Uniform Law Reviews,1999(2).
[32]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5] 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解读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Financial Leasing Law in China:Re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s and Remodeling of the System——Focusing on Cape Town Convention and Its Protocols
GAO Sheng-ping
(School of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Mobile Equipment and three Protocols to the Conventioned reflecte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leasing law.The interest vested in a person who is the lessor under a financial leasing agreement is to guarantee the satisfaction of rent in essence.However,it is un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it as a security interest.As the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has the same economic purpose as the secured transaction,the relevant rules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shall apply to financial leasing.Where the agreement providing for the lessor's interest is in writing,relates to an object of which the lessor has power to dispose,and enables the object to be identified,the interest is constituted as an international interest under the Convention.The interest is effective as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only from registration.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is a kind of notice-filing and asset-based system,and functions as publication of real rights on the object through the electronic system.The priority of competing interests on the same object is decided on the registration date. However,a contracting state may declare those categories of non-consensual right or interest which have priority over the registered interest.In the event of default which is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parties or otherwise stipulated by the Convention,the lessor may exercise the relevant remedies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court,and obtain from a court speedy relief pending final determination.
financial leasing;Cape Town Convention;security interest;international interest;international registry
高圣平: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 李 理)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金融担保创新的法律规制研究”(12SFB20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法律保障研究”(13JZD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