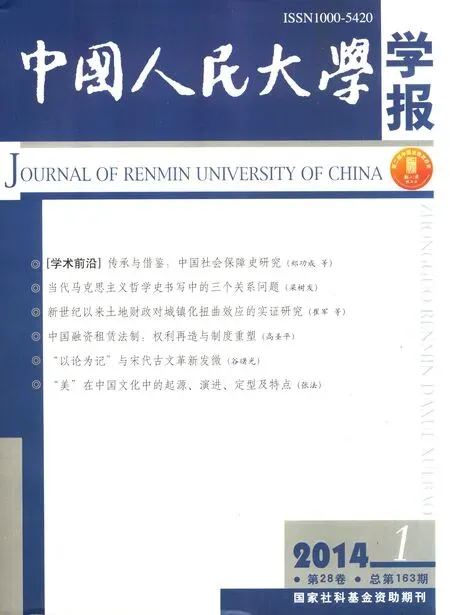神话“精卫填海”之“女娃遊于东海”文化原型考略
2014-01-24林美茂
林美茂
神话“精卫填海”之“女娃遊于东海”文化原型考略
林美茂
《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所包含的史前文化原型,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神话《精卫填海》的核心内容之一“女娃遊于东海”的文本分析得以还原的。根据该神话传承中的几种文献、考古学上文化地理资料以及古文字字义等内容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所谓的“女娃”并不是具体的人名,而是炎帝族少女的泛称;“女娃”所遊“东海”,也只是指称东边的水域;为此,“女娃遊于东海”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女性在水边举行的一种与生殖崇拜有关的巫术祭祀活动,神话中“溺而不返”的“女娃”之死,是指少女们通过沐浴告别少女之身,成为生育年龄的女人。因此,《精卫填海》神话可能是炎帝族少女的一种巫术性成人仪式传承上的变形。
精卫填海;女娃;东海;遊;文化原型
问题的缘起
《精卫填海》这个神话,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一直作为一种精神性象征被人们所喜爱。所谓精神性象征,是指小鸟精卫勇敢无畏地面对大自然(大海)的复仇行为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因此,“精卫”的形象成为勇敢无畏者的人文借喻。形成这种社会文化的审美心理定型,来自于我们向来对这个神话的解释向度都是社会学视角,具体地说,也就是从社会学的描述性、解释性功能出发,理解与把握这个神话内容所体现的精卫行为“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并且上千年来在中国几乎达成了不可思议的一致。
根据清代吴仁臣的《山海经广注》,可以把这种心理向度上溯至晋代。晋代的文人左思、陶潜最先把“精卫”分别作为:“怨(冤)禽”、“志鸟”来歌颂。[1](P183)①左思的《魏都赋》:“精卫,衔木偿怨……”。陶潜《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参见吴仁臣:《山海经广注》,7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这种文化心理传统,一直被后代所继承。南北朝的任昉,唐朝的崔融,明朝的徐光启等,都有歌颂“精卫”的诗文,其视角也都基本一致。而我国当代神话学界,这种认识的传统基本没有改变。如袁珂、刘城维等都是如此。[2](P73-74)[3](P351)②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说:“我们想想,这样一只小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从高高的天空中,投下一段小枯枝,或一粒小石子,要填平大海,这是多么悲壮!我们谁不伤念这早夭的少女,又谁不钦佩她的坚强志概?”参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刘城维也认为:“在精卫填海中,美丽的形态与不幸的命运,娇小的身材与坚毅的性格,天真的行动与顽强的斗志,集中于精卫的形象里,织成了一幕撼人心弦的悲壮剧”。参见刘城维:《中国上古神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而郭沫若在《读诗札记四则》里概括了这种理解的价值观基础:“‘精卫填海’行为有类愚公移山,古代留下了这个传说,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精神十分可取。”①参见《光明日报》,1982-11-16。这种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传统的沿袭,没有更多新意。也就是说,历史上关于这个神话的研究和解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从研究者所处的文明时代的价值观、人生观的社会学立场出发理解或阐释这个神话所体现出来的某种人文精神,或者某种与生存状态有关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即使时代不同,由于出发点一致,也就容易产生一致的结论。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上述这种理解体现出一种文化“基本性格”的心理结构。当然作为形成这种“基本性格”的“第一制度”并非原理论中以先史文化习惯的制度化为基础,而是之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中深感压抑的人们通过对于神话的理解凸显其“第二制度”的特征,从而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对于“反抗”或者“斗争”的憧憬。“精卫”的形象成了人们某种诉求的最好象征。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理解也是一种解读的角度,其中的生产性和情感性成果都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对于多数源于史前文化断片而形成的我国神话资料,仅仅从社会学的立场进行诠释,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讲无可厚非,但其能否真正做到接近这种记述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我们不否认我国神话的史前文化因素,那么就应该对于我国的诸多神话进行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的实证性考察。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最新考古发现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以及从语言学、民族学角度考察语言、行为与社会环境、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还原先民文化的原型,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
也许源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国关于神话研究的学术倾向,在国外鲜有共鸣者。从日本汉学界来看,他们解释这个神话时采取的显然不是社会学的思考倾向。甚至有的学者对于这个神话根本不关心。比如日本汉学界中国神话研究代表性学者白川静和御手洗胜,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对“精卫填海”这个神话的任何论述。而著名汉学家森三树三郎虽然提到了这个神话,却也显得相当冷淡和有所保留。他说:“这只鸟(精卫)也许不是实际存在过的鸟,在贫乏的中国神话里,像这样的零星片断大概可以找到很多吧!”[4](P265)日本学者显然不像中国的学者那样,把神话的叙述上升到文明时代的人文意义的领域去理解,没有用文明时代的人文思考框架去替代古老神话的原型。这不仅是方法论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价值取向上的迥异。同样是森三树三郎,他对中国神话的研究问题提出一个重要认识,他认为:“在上古中国,有一种把各种动物当做神圣物看待的风俗……那些(传说)大概在实际的巫术行为(的理解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倾向是故事性的因素贫乏。”[5](P248)这是一种富有见地的认识。近年我国学者对于“精卫填海”神话也出现了类似的审视角度。比如,谢选骏在《中国古籍中的女神》论文中指出:“现代人在面对‘填海’的壮举时,仅视之为意志的表现,其实,精卫填海并非空头泄愤,而有实际功能,即含有巫术功能。”[6](P182)这些观点,显然已经脱离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学视角,出现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觉醒。
上述谢选骏的指涉与森三树三郎是一致的,已经超越了神话内容的叙述表象,捕捉到了其内在的“巫术功能”的文化原型。但是,如上所述,森三树三郎对“精卫”神话冷淡而有所保留,而谢选骏虽然直接指出“精卫”神话的“巫术”文化原型,却仍然把“填海”行为视为“复仇的、死本能”的隐喻,从而又回到了传统思维的框架,依然是以内容本身所传达的“感情”为旨归,不得不说这与“不屈的意志”、“复仇”的精神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如出一辙。也许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所致,他仅仅在此表达了直观的印象,而最终对于“巫术功能”没能做到任何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论证。因此,其中认识上的文化人类学元素的觉醒也就只能停留在觉醒的层面,没有任何更为具体的内容。
这种研究现状让我们认识到,对于“精卫填海”的神话,虽然向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传颂,然而由于人们总是拘泥于叙述内容的表象上的把握,没有深入地进行叙述表象后的原型挖掘,因此对此研究可以说几乎处于一种认识上的抄袭传统之中,“精卫”作为勇敬、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的象征,在学术界获得了惊人的统一,一致得使其成为一种几近完美的定型。虽然已有人捕捉到其“巫术功能”的文化倒影,却由于认识上所形成的稳定性,以及站在新视野上的论述不够深入,因而无法改变从来的认识传统而形成的崭新学术向度。可以这么说,对于“精卫填海”这一神话的研究,学术界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片面理解,无异于一种历史空白。深入研究这个神话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型,对于我们探索上古的文化历史应该是富有意义的。当然,仅凭一篇论文,由于篇幅的局限,无法涉及这个神话内容的全部,拙论仅围绕神话叙述中的“女娃遊于东海”问题进行分析,呈现这个神话所包含的文化人类学的一种视角。
一、相关文献资料的再检讨
其实这个神话,不仅在可作为参考的研究文献上内容相当匮乏,而且关于该神话的文献记载也存在着许多不一致。既然先行研究资料匮乏,我们就必须从其记载的历史文献所存在的不一致入手,找到可以接近这个神话真实的某种线索。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神话的文献记载上的异同进行梳理和辨析。
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常被学术界引用的一直是以下三个文献。
(1)郭璞注《山海经·北次三经》记载:“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啄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7]
(2)张华《博物志》记载:“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媱往遊于东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为精卫。(注云……自昔赤帝至此二十二字原并脱去,依御览九百二十五卷补与山海经合)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8]
(3)任昉《述异记》记载:“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之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犹存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鸟誓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9]
上引的三个文献,其中的异同一目了然。三个记载的相同之处是:炎帝之女溺死之后化鸟,鸟名为精卫,溺水处为东海。因此衔木石以填海。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三个不同之处:(1)炎帝之女的名字不同:《山海经》(郭注本):“女娃”。《博物志》:“媱”。《述异记》:无名字。(2)《博物志》的记载存在着重要内容遗漏的疑点,即“昔赤帝女媱往遊于东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为精卫”遗漏,这就存在着关于精卫来历的记载内容有无的问题。(3)《述异记》记载存在着前后矛盾。前述“炎帝女溺死东海中”,而后面却说“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溺水处由“海”变为“川”,我们知道,海与川是两个不同的名词。
根据上述三个文献,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神话传说来源于古本(区别于郭注本而言,以下同)《山海经》,郭璞只是为此做了注释(当然,也进行了编撰、收集、整理①根据《伪书通考》记载,古本《山海经》只有13篇,今天所传《山海经》共有18卷,是经过郭璞的整理编撰加上注释而形成的。)。张华的《博物志》也受到了古本《山海经》的影响,这可以从《博物志》卷一开篇的叙述中得到佐证:“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博物志》卷一)对此,袁珂也在《中国神话史》中指出,《博物志》的卷一到卷三的内容完全像是《山海经》的缩写。
任昉属于张华、郭璞之后时代的人,他的《述异记》中出现的“精卫填海”的内容明显地受到张华、郭璞,左思、陶渊明的影响。但是,古本《山海经》已经散佚,就连散佚的年代都不清楚。根据《伪书通考》,郭璞在编纂、整理、注释《山海经》的时候,其所见到的《山海经》与我们今天见到的似乎不太一样。然而,现在可以看到的《山海经》,只有郭注本最为古老。由于古本《山海经》的散佚,比较三者的记载谁最准确变得相当困难,要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只能对三个文献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找线索和答案。
传到今天的郭注本《山海经》与古本《山海经》最接近,是现存文献中最具权威性的文献,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用日本学者前野直彬的话说:“即使不能达到完全一致,至少可以说内容和风格上是相同的。”[10](P9)但是,问题在于郭注本《山海经》与张华的《博物志》谁更准确。郭璞为东晋人,而张华为西晋人,郭璞晚于张华。虽然《博物志》的确切成书年代不明,但大致的范围可以断定,《博物志》大概出现于西晋武帝年间(265—297),即张华33岁以后的著作。张华比郭璞年长了44岁①张华出生于232年,郭璞出生于276年。,那么,《博物志》问世之时,郭璞尚未出生,或者尚处于童年或少年时代。由此推断,《博物志》上的记载,显然比郭注《山海经》来得早。然而,张华的《博物志》也已散佚,现存文献只是后人根据散见于其他文献的有关《博物志》的引文及参照郭注本《山海经》等书编撰而成的。②参照《四库全书》中有关《博物志》的成书说明。为此,《博物志》的可信度只能委让于郭注本《山海经》。③《四库全书》1047卷中对于《博物志》的提要中写道:“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採他小说以足之故”。因为我们首先不能断定张华的《博物志》上是否拥有这个神话的记载。其次,即使拥有关于“精卫填海”的记载,其详细内容是否与现存的经后人重新编纂的《博物志》的内容完全一致也同样无据可考。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些学者索性不提《博物志》的“精卫填海”神话记载,前野直彬与袁珂就是如此。[11][12]④前野直彬在《山海经》译注中,其“补遗”中只看到《述异记》的引用,没有提到《博物志》(参照《山海经·列仙传》)。而袁珂与周明编撰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有“精卫”一项,而没有收录《博物志》的记述。
然而,不能肯定并不排除拥有这个记载的可能性。只要不能否定其有记载的可能性,就需要对此二者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前文已指出,炎帝女的名字郭注本为“女娃”而《博物志》却为“媱”。在张华和郭璞所处的晋代,古本《山海经》仍然见存于世,并且两人可能都读过此书。那么,为何会产生以上所说的不同呢?我想有如下三种可能:
其一,“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当时除了古本《山海经》以文字记载之外,可能还有一种存在于民间的口头传承的资料,而口头传承中的炎帝之女名为“媱”,张华综合了两种资料而辑录于《博物志》中。其中炎帝女的名字采用了民间的口传资料。前文提到的《博物志》卷一的引文中说到“出所不见”是否与此类内容有关是值得思考的。
其二,流传于晋代的古本《山海经》可能不只是一种文本,而是有两种或者更多的文本。西晋的张华与东晋的郭璞所采用的文本不同,那么两人所记载的炎帝之女的名字,由于采用的文本不同而存在着以上的不同是很正常的。
其三,炎帝之少女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只是郭璞与张华注释或记载上的新内容。甚至于张华的《博物志》中炎帝之女也无名字,只是《太平御览》的编纂者根据郭注本《山海经》和民间口头传承的资料补充而成的。收入《指海》的注释中说:“依御览九百二十五补与《山海经》合”的一句容易让我们提出这个疑问。
那么,《博物志》里所欠缺的重要内容,即缺少关于“精卫”来源于炎帝之女“女娃”溺死而化鸟的部分内容该做何解释呢?其实这明显是后人传承上的遗漏。依据如下:首先从现存的《博物志》的记载内容看:“赤足,曰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仅从这句话“精卫”填海的原因不得而知。显然,这里的“故”字是承接前文原因的用语,但是这里“故”字之前没有任何有关“精卫”来历及“填海”理由的内容,那么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可以断定在“故”字前面遗漏了说明来历及填海原因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是否与郭注《山海经》相同呢?我们可以从同处晋代的文豪左思的赋中找到证据。左思的《魏都赋》说“精卫”的填海行为是为了“偿怨”。很显然,这与郭注本的记载内容基本相符。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古本《山海经》里应该有关于炎帝之女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的记载,两晋时期此书尚见存于世,张华、郭璞、左思等都熟读此书,而现存《博物志》中的欠缺内容,应属于后人辑录时的遗漏所致。
再看看任昉的《述异记》。在这部著作中,“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显得相当详细而富有故事性,其中增加了新的内容的部分也显而易见。从《述异记》的记载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意外的事实。即古本《山海经》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失传,当时能见到的只有郭注本的《山海经》,而任昉在搜集整理《精卫填海》的神话资料时也遇到与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即炎帝之少女的名字模糊不定,郭注本《山海经》,张华的《博物志》及民间口传资料各不相同,为此索性不写出具体的名字,只写作“炎帝女”,从而使我们今天见到的南北朝时的文献内容变得更为丰富。除了张华、郭璞以外,还有左思、陶潜的赋、诗中的“冤禽”,“志鸟”的文学形象。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任昉的《述异记》中“精卫”的神话传说又多出了“冤禽”、“志鸟”、“帝女雀”等新内容。
通过以上的梳理、比较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关于《精卫填海》的神话记载最初出现在古本《山海经》,而现在对我们来说,主要的内容与细节,只有郭注本《山海经》较为可信。至于“炎帝女”的名字,当时存在着三种情况,很有可能本来就没有名字,“女娃”或者“媱”只是传承上后人附会的结果。这其中的纠结、原因何在,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分析、考证。
二、“女娃”何指?“东海”何处?
对于“女娃”的原型,学术界有两个主要观点,一种是袁珂的“女娲”说,还有一种是丁山的“禺”说。其实,这两种观点的思考很相近,即他们都是从一神多面的思维角度出发而得出结论。
袁珂认为,“女娃”可能就是“女娲”。其理由是“精卫”填海的行为与“女娲”的“补天”后“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治水业绩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他的推理是:“精卫”的填海行为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渴望”,而“女娲”的补天治水同样是征服自然的壮举。[13]根据袁珂的理解,女娲补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水”,而女娲的“治水”与“精卫”(“女娃”)的“填海”行为存在有某种内在衍变关系。换句话说:在袁珂看来,“精卫”的“填海”也是属于一种“治水”行为的隐喻。而丁山则认为:“女娃”即东海之神禺。①《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东海神”。丁山根据甲骨卜辞分析,认为卜辞中将“”写作“虎”或“”,而“”与“娃”为一音之转。“禺”又能作为“女”字的音转,即东海之神“禺”,溺死于东海的“女娃”当然有可能被作为东海之神来祭祀。所以,“女娃”就是东海之神“禺”[14](P63)。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学界历来解释上类似的思维,那就是孤立摘取神话中个别、局部的细节加以联想,以偏概全,建立假说,没有从整体上去考察这个神话的意蕴,那么,其结论各执一端也就在所难免了。
(1)袁珂把“填海”理解为“治水”显然是过于表面化的联想。在没有弄明白“填海”行为的意义的情况下,就进行简单的类比显然过于武断。更何况女娲之“治水”究竟能否作为“征服自然”之解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丁山从汉字的读音角度去推定“女娃”的原型,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值得商榷。前文已详述,在关于这个神话记载的不同文献里,炎帝之女的名字各不相同,或“女娃”,或“媱”,或索性以无名形式出现。由于无法确认古本《山海经》上的记载如何,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那就是如果原文是“炎帝之女娃”,这里的“女”和“娃”不一定是一个单词“女娃”,如果各自分开,“娃”字可以不作人名解,而应该是作为美丽的少女来解释。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娃”的解释:“圜深目皃、或曰吴楚之间谓好曰娃,从女圭声。”[15](P108)这里的“圜深目皃”,“好”皆为美貌少女之称。而如果古本《山海经》的原文为“炎帝之少女媱遊于东海”,这里的原文中“媱”字不仅可以不作为人名解,还可以进一步把“媱”字与后面的“遊”结合,可以作为“媱遊”一个单词来解。根据《说文解字》,媱为“曲肩行皃”即女子的“游戏”或“舞容”。《说文解字义证》曰:“曲肩行皃者,广雅媱戏也。方言媱遊也。江沅之间谓戏为媱,楚辞九思音晏衍兮要媱。注云要媱舞容也。”[16](P1089)
根据上述的假设,我偏向于前文中提到的第三种可能性,即炎帝之女本无名。正如任昉以“炎帝女”泛指一样,在这个神话里关于“炎帝之女”问题,可能仅仅只是炎帝族女性的泛指或总体意象。到了晋代,经张华、郭璞等人的搜集、整理、引用和注解,使炎帝之女变得更为具体,就有了名字。那是一种传承和理解的产物。当然,由于我们见不到古本《山海经》的原来记载,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倾向性或者可能性的假设。不过,只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关于“东海”及“遊于东海”问题,通过细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印证,上述的假设将会变得更具说服力(后文详述)。为此,丁山认为“女娃”溺于东海,自然成为东海之神,这种推论缺乏内在的理论依据。从来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女娃”成为东海之神的记载,不仅如此,“女娃”溺水的“东海”与“禺”所处之“东海”(丁山认为即今之渤海)是否是同一处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地名上肆意的简单同定,成为丁山建立“女娃即禺”假说的依据所在。
(2)根据《山海经》(指郭注本)的“五藏山经”部分的统计①所谓“五藏山经”,即《山海经》最初部分的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东、西、南、北、中五经《山海经》中最古老的内容。,有关“海”的地名共出现28次,其中东海5次,西海3次,北海2次,渤海2次,海泽1次,海15次。这里出现的东海、西海、北海、渤海今为何处是一项值得考证的工作。更进一步说,在《山海经》中关于“海”的文字含义与今日的“海”是否相同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版图与位置,只有东部与南部面临海洋。而西部与北部却远离海洋,那就不可能有“西海”与“北海”的地名。然而,为什么《山海经》中存在“西海”与“北海”呢?当然,如果从中国人起源于西北方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学说来看,西边与北边与大海近邻可以想象。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东边与西边、北边距离太遥远了,对于先史时代的部落民来说,只可能临近其中的某一个海域,与四方的海域都近邻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山海经》中出现了东、西、北边都存在海洋的记载呢?以下的推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先史时代中国大陆各地散开居住着许多小部落,并且这些部落民应该都是选择水源地附近居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战争、兼并等手段,小部落逐渐被大部落所吞并、同化形成更大部落,各小部落的文化都融入到大部落之中,最终只剩下炎黄两大部落的对立。那么,曾经居住在东西北各地的小部落,在融入大部落之后,一方面,他们对于祖先的历史文化只有通过口头传承的形式,在后世子孙中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长期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大部落一定会经过数次文化与习俗的大统合,原来小部落的历史与文化就成为大部落文化中的一个小符号,构成了大部落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在文字产生之后,后人在对于这一时期的习俗通过文字符号的形式进行追述时,小部落时代附近的水域就成了一种“海”的追忆。因此,《山海经》中出现的关于“海”的记述,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海”的含义。其中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海”是同样的,而大部分可能只是先民曾经生息地域中的大川、大湖、大泽,也就是属于一种具有较大面积水域的水源地的指称。那么,根据这个推断来理解《精卫填海》中出现的“东海”这个地名,就应该是与这个神话有关的炎帝族的活动地域中的水域有关。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对炎帝族的活动范围的考察,寻找对于炎帝族来说“东海”究竟意味着什么。
(3)有关炎帝族的活动范围,通过以下文献可以得到基本的把握。
根据历史记载,黄帝与炎帝“相济”之地有两处:(1)《新书·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飘杵。”[18](P33)(2)《列子·黄帝》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19](P596)
以上的引文中有三个地名供我们考察。即炎帝的出生与成长地:姜水①据记载,炎帝的出生地还有一个:“华阳·尚羊”。《初学记》卷九中引“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氏也。母曰姙娰……名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惑女登于尚羊,生炎帝。”。炎帝与黄帝交战之地:涿鹿或阪泉之野。
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我们大概可以找出其所在范围:“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岐山县西。源出岐山,南流合横水入于雍。《水经注》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固以姜为姓。”[20](P607)顾祖禹的《读史方与纪要》云:“姜水城,在县(今宝鸡,笔者注)南七里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乔氏所居。”[21](P1173)
如上所载,姜水应在今陕西省境内,这里应是炎帝族的发源地。那么再看看涿鹿与阪泉两地如何。同样上述两书认为:“涿鹿之野”应在直隶县(即今河北省)北,而“阪泉之野”应在直隶县东。[22]②参照《古今地名大辞典》“涿鹿山”、“涿鹿县”、“阪泉”项。根据《轩辕黄帝史迹之谜》观点:“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涿鹿山便依山下长竹子。竹林有野鹿而得名为‘竹鹿山’。轩辕黄帝约在距今4500多年历史上,曾居于此山之下一个黄土丘陵之上。并战蚩尤于竹鹿山东北的平野之地。战炎帝于竹鹿山北的阪泉之野”。参见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423页、8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涿鹿之野与阪泉之野同属一处。但是,《梦溪笔谈·辩证一》却认为:“阪泉在今山西省运城县”。阪泉究竟是在山西还是在河北,尚待具有说服力的考古发现,由于缺少有效的资料,本文无法进一步考察。根据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的观点:“炎帝起源于‘姜水’,所以姓姜。虽然姜水究竟在何地,我们目前尚不能回答,但炎帝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今日的中原即河南省的伊洛平原上,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传说中炎帝的受孕地在华山南侧的陕、豫交界之处……其建都在陈(今河南新郑)。而黄帝族团的起源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泰山、曲阜一带……炎帝族的活动区域是比较偏居西南的。”[23](P163-164)
不管怎么说,从上述与炎帝族活动有关的三个地名的位置,我们基本可以推断炎帝族活动的大概范围。那就是炎帝族发源于今陕西至山西一带,其势力慢慢向东并沿黄河流域而下,进入河南之后得到重大发展,这里成为主要的活动舞台。后来,其势力进一步向东北方向移动至河北省的西部或中南部,与黄帝族的势力遭遇,并被黄帝族渐渐吞并而灭亡。经过漫漫数千年的历史,中华大地的两大势力逐渐走向融合,成为今天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
从上述炎帝族的活动范围看,与其说其与东部的海洋有关系,不如说其与黄河息息相关。如果根据何新的观点,认为炎帝是周人的祖先,那么其与东部的海域更是关系不大。因为周人起源于西北,甚至与草原的骑马民族有关。为此,“精卫填海”神话中炎帝之女往遊之地“东海”,不像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东部海洋,更不可能是丁山所说的渤海。
其实,“东海”不应理解为“海”的问题在任昉《述异记》叙述上的前后矛盾也有所体现。前文已经指出,《述异记》记载的开头部分说炎帝女“溺死东海中”,而后面却说“曾溺此川誓不饮其水”。这种前后矛盾不应仅仅理解为叙述上的不一致,而有其对“东海”认识上不确定的某种踌躇的暗示。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或“东海”或“川”都只是关于水域的名词,没有具体地名上的实际意义。其实,在我们中国,把湖称为海的命名现象到今天还仍然存在,比如,云南省的“洱海”,那只是一个大湖。而较近历史的北京“后海”、“北海”等都能说明在中国这种语言使用现象是存在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任昉来说,无论“东海”,还是“川”,都只是广阔水域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前文所述那样貌似前后矛盾的记述。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炎帝之女本无名,这个神话里关于“炎帝之女”的记述,可能仅仅只是炎帝族女性的泛指或总体意象。“女娃”或者“媱”,都只是传承上的产物。而神话中所谓的“东海”地名,也不具有地名上的实际意义,只是作为体现大面积水域的意指。“东海”的“东”,可能只是方位的意义,“东海”只是指“东边的水域”。我们可以把其认为那是炎帝族活动范围内的河川、湖泊、溪谷,甚至可以联想到其可能是几千年前的某个时期的古黄河雨季来临泛滥时所造成的大片汪洋般的水域。
三、“遊于东海”该做何解?
当我们对于“女娃”与“东海”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那么,拙论的核心问题“遊于东海”的叙述原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与遊有关的有“斿”、“游”、“遊”。关于这三个字的区别,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字统》的解释值得参考:“遊:声符斿,斿是氏族揭其氏族之旗外游之意的字,‘遊’为最初文字,也写成‘游’。所谓遊,指遊行、移动之事象。《诗经·周南·汉广》:‘汉有遊女,不可求思’句之遊女,指的是水的女神。这首诗是古代祭祀汉水的女神时咏唱之歌。《诗经·秦风·蒹葭》被认为其诗意不明,其实这首诗也是祭祀水神之歌,咏叹追悼女神,这是祭祀女神的基本形式。移动的自由不拘都称作遊,其最初是与神灵遊行有关的用语。”[25](P838)
从甲骨文的字形看,“遊”为人执旗而行,对于这个字,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这个字与古代先民的游牧、游猎有关,但我觉得白川静的学说有相当独到之处。前文已经分析论述,“女娃”为炎帝族的女性之泛指,“东海”为水域之意象。远古的原始先民,女人们在水边“执旗而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遊戏”活动,这应该是带有某种巫术功能的行为。
关于在水边的巫术(或者其他原始宗教活动)的仪式,根据古文献记载,多与求子祭祀活动有关。孔子的《论语·先进》有“暮春……浴于沂”一段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蔡邕的《月令章句》注之曰:“《论语》‘暮春浴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除于水溪,盖出于此也。”[26](P900)另外,《周礼·春官宗伯·女巫》也有与此相近的记载:“掌岁时祓除衅浴。郑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27](P1762)
“上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节日名,每年三月三日举行。对其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源于群婚杂居时代部落民的生活习俗。原始先民在春天万物复苏之时,生命力勃发,情欲旺盛。对于男女来说,这是群婚杂居时代求偶的最佳季节,由此发展成为后来文明时代的具有宗教文化意识的祭祀(宗教)活动,其节日的性质自然地与求子祈育联系起来,并赋以某种巫术宗教功能。
对于上巳节源于求子祈育的节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另费笔墨。但是,对于上巳节的“沐浴”仪式,有必要作更为深入的探讨。宋兆麟的观点可以代表学术界具有新意的理解。他认为:“上巳的沐浴,实际上是一种巫医的水疗法,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驱走各种恶鬼,为妇女生育创造条件。”[28](P31)
把宗教或巫术仪式之前的“沐浴”解释为洁身驱邪的认识应该是我们现代人的常识,在世界许多民族的民俗及民间宗教仪式里几乎都有此现象,并且我们基本都作如此解释。但是,宗教组织化、体系化是在人类脱离原始阶段之后的事,各种宗教经典的成立和解释更是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才能做到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在阐释理解宗教起源时,不免带着时代的痕迹,不可能全部接近原始时代人类的巫术宗教心理。而这对于上巳节求子的“沐浴”仪式的理解,同样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上巳节中的“沐浴”的原始宗教心理,不是就这么简单,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巫术比宗教的产生更早,与原始文化更为接近,其仪式、行为更具神秘性和非理性的特征。那么,对与那些特征相关的各种文化、习俗需要充分的认识与挖掘,对其每一种仪式的神圣意味必须进行详细的考察。因此,关于上巳节中“沐浴”仪式,需要跟中国古代先民对于水的神秘信仰文化现象结合起来考虑。
在中国的先史时代,对于水的原始心理,总是与生命之源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先民们认为,水不仅可以带来生命,还可以赋予人强大的生命。不仅中国如此,印度的兴都教也拥有同样的思想。当然,原始人的这种宗教心理,只是他们朴素的自然观的表现,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地球的生命从水开始诞生属于不同层次的认识。
从以上两例中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从水边或者沐浴中获得的生命,其成人之后,都成为人中的王者。水可以带来生命的信仰文化心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但是,《老子》的帛书《道篇》中的一节,可以作为究其原因的一个事例。“浴(谷)神不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用之不堇(勤)。”[31](P419)
对于老子的“谷神不死”,从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多是从“道”的角度去理解,正如何新所指出:“所谓谷神,究竟何指?前人鲜有能确指者,因此这一句话,两千年来,竟一直未得到达诂”[32](P56)。根据他的观点,“谷神”为月神,“谷神不死”,指月之盈缺。不过,我更倾向于萧兵的新解[33](P552)。虽然他的推理值得推敲,但是其结论是可取的,即把“谷神”与女性的生殖系统联系起来思考。他的分析是:“谷”字从水,玄牝是指有水的溪谷,是女性的生殖器的象征。“谷神不死”变成了“天地之根”的“玄牝”,是因为溪谷里注满水,水是生命尤其是农牧民生命的来源,有如女性的生殖系统充盈液体以及子宫充满羊水孕育、养育、产生生命,当达到“谷”成了生命之“神”,“绵绵若存,用之不堇”之时,便进入一种永恒的境界,与天地万物的根源“神玄的女性生殖器”合二为一,成为宇宙的本质。
可以说,何新的观点想象的因素太多,缺少应有的依据。与此相对,萧兵的观点可以接受,即把溪谷当做女性的生殖器来解释有一些道理,但是得出该结论的过程分析仍然让人难以全部接受,即为什么“溪谷”成为“玄牝”的原因没有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我认为,“玄牝”即指女性的生殖器,女性的生殖系统能够获得“绵绵若存,用之不堇”的无限生命力,其原因正是通过女性的身体与大自然的“水”接触,即“沐浴”之后,与大自然成为一体性的存在,从而获得大自然的根源性力量,拥有了与大自然同样的巨大生殖能力,从而成为“玄牝”。为此,老子所谓的“谷神不死”,指的是女性通过某种巫术仪式与“水”接触,其身体就与具有绵绵不绝生成能力的“水”融为一体,其生殖系统就成为孕育生命的不死存在。帛书中的“谷神”被写成“浴神”,应该就是这种思考的一种体现。上述的历史传说以及《老子》中的记述,说明古代中国的先民们,把“水”作为具有无限生殖能力的神秘性信仰文化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显然“上巳”求子祈育过程中的“沐浴”仪式,不一定与“水疗法”有关,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驱邪”而为之,这应该是上古女性,通过与万物的生命之源“水”的接触,寻求其生殖能力达到与“水—自然界之本源”同样的绵绵不绝的存在,从而获得自然界生命和生命力的注入而孕育子孙。除此之外,似乎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原始人心态,即由于这种生命是从与自然界—水的直接接触(或可以说为一种巫术“交感”)而获得的,其所获取的那个生命的生命力也将与自然同样拥有巨大有力的原始人的朴素追求。我们只要从各种关于来自水边的生命及水边感生神话里,不难发现这一原始心理的倾向。由此可见,史前中国的部落民们在水边举行的各种祈子求育巫术活动,其隆重而神圣的程度,不是现代人所能想象的。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即这种水边求子祈愿的巫术行为与炎帝族的少女们水边之“遊”是否有关联的问题。我们从《毛诗》注释中不难发现,简狄就是高辛氏之妃。(“简狄,配高辛氏”)。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指出:“从典籍记载看,炎帝族号高辛氏。”[34](P156)显然“上巳”与炎帝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我们不能肯定炎帝族与高辛氏存在着必然的传承关系,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女娃”遊于“东海”时的“溺而不返”,恰恰就是这种求子祈育巫术祭祀活动中的“沐浴”仪式的变形,“溺而不返”可能就是这种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①当然,如果从前述部落民吞并融合的发展历史角度看,这种“溺而不返”与后来的化为精卫鸟的“填海行为”,也可理解为一种关于祖先之“死的记忆”与“复仇心理”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关系,从而展开另一种关联性解释,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将另文论述其与“填海行为”的关系。本文仅就选择史前文化的文化人类学视角,把此作为生殖崇拜巫术文化的变形理解。其实,关于少女入浴作为一种神圣的成人仪式,在现代的民俗学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源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保存。比如在南太平洋某岛上居住的土著的习俗中,当女孩初次来月经时,必须进入一种名叫“月经屋”的特殊地方居住入浴三天,三天过后清晨未明之际,母亲为其准备椰子的新芽并对其念咒文,当身上涂抹着黄粉从“月经屋”出来时,让其戴上椰子新芽结成的名为“乌普多”的吉祥避邪物,标志这个女子已经是成年女子可以生育。之前少女时期只能在腰部围着芦苇细条编的围裙,经过“月经屋”入浴仪式之后,就要围上氏族妇女们为其准备的织好的岛布遮羞,从此进入生育阶段(详见:濑川清子:《女の民族誌——そのけがれと神秘》,东京: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0)。在我国,与此相似的风俗在陕西省合阳县洽川镇也存在。这个镇紧挨着黄河,到处都是温泉一年四季从地下冒出来,是黄河重要的水源之一。相传这个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史前时期。古镇上有一处“处女泉”,女子临出嫁时都必须到这个温泉浸泡沐浴,因此得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于“精卫填海”神话中“女娃遊于东海”部分该作何解可以获得比较明确的认识,结论是:这个神话中的“东海”,是指一种大面积的“水域”,所谓的“遊”,从字义上看,属于“与神灵游行相关”的用语,那么很可能这与炎帝族在水边举行的某种巫术仪式有关,“遊”指的是舞蹈行为。这个仪式的主角是“女娃”。而这里所谓的“女娃”,不应该仅指某一个特定的女孩,而应该是炎帝族少女全体概念。那么,所谓的“女娃遊于东海”,意味着炎帝族的少女们在水边举行某种隆重的巫术仪式的舞蹈场面,其目的应该就是祈子求育,甚至可以考虑那是后来史书中所记载的“郊禖”、或者与上巳节存在某种起源性关联。那么,进一步可以推断,“女娃”的“溺而不返”,应该是其仪式中最隆重的一环,即少女在水中“沐浴”与水神圣接触(“溺”),通过“沐浴”,其少女之身从此成人,再也回不到原来少女的状态,而是进入了需要孕育生命的成人身子,其作为母亲时期从此开始(遊于东海的少女“溺而不反”可能就是此意的原型)。我们甚至可以大胆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神话很可能属于炎帝族少女的一种成人巫术仪式传承上的变形。
[1] 吴仁臣:《山海经广注》,载《四库全书》,1042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2][13]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刘城维:《中国上古神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4][5] 森三树三郎:《中国古代神话》,东京,弘文堂书房,1969。
[6] 王孝廉、吴继文编:《御手洗胜博士退官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联经出版,1988。
[7] 郭璞:《山海经》,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江安付氏双箭楼藏本(明成化刊刻本)。
[8] 张华:《博物志》,载《百部丛书·指海》第五函。
[9] 任访:《述异记》,载《四库全书》,1047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10][11] 《山海经·列仙传》,载《全释汉文大系》33,东京,集英社,1975。
[12][18] 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4]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5] 许慎:《说文解字》(四部丛刊初编缩册本十五)。
[16]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国语·晋语》(四部丛刊本)初编缩册本十五。
[19] 《列子·黄帝》,载《四库全书》,1055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20] 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21] 顾祖禹:《读史方与纪要》索隐二,光绪二十七年仲秋二林斋藏版图书集成局铅印(霞山文库)。
[22] 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3][32][34] 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24]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学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25] 白川静:《字统》,东京,平凡社,1990。
[26] 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27] 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三)·周礼注疏》,东京,中文出版社,1989。
[28] 宋兆麟:《生育神与性巫术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9]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
[33] 萧兵:《老子的文化解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张 静)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Archetype of“Nüwa Parades on the Eastern Sea”,a Scene of the Myth of“Jingwei Fills up the Sea”
LIN Mei-mao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Starting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through the text analysis to“Nüwa parades on the Eastern Sea”,a core scene of the myth of“Jingwei fills up the Sea”,restore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prototypes that the myth contains.According to several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yth,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cal materials,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classical meaning of ancient writing,you can discover the so-called“Nüwa”is not a specific name,but the general name of girl in the Yandi tribe.“The Eastern Sea”is just a reference to eastern waters.So the true meaning of“Nüwa Parades on the Eastern Sea”should be some kind of witchcraft and reproductive worship festival that girls held at a waterside.So the myth of“Drowning without returning”,a maiden's death,should refer to a farewell to a maiden body through a baptism,to become a woman at the childbearing age.Therefore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myth of“Jingwei Fills up the Sea”is based on a grown-up witchcraft rite taken by females in the Yangi tribe.
Jingwei Fills up the Sea;Nüwa;the Eastern Sea;Parade;cultural archetype
林美茂: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