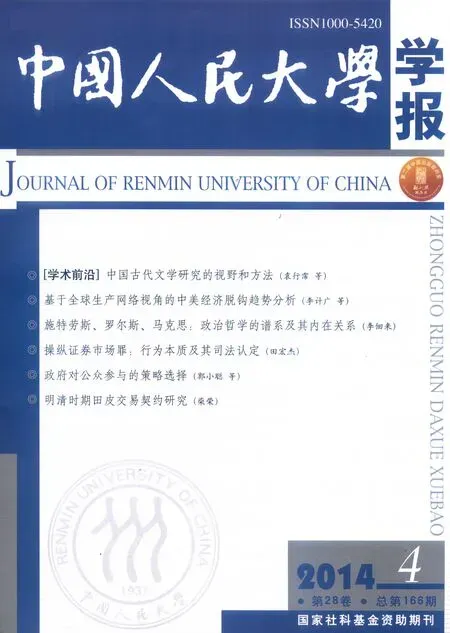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及其验证
2014-01-24张培丽
张培丽
中国经济能否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再延续20年,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震荡徘徊,2012年经济增长率13年来首次低于8%,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有多长?中国经济由高速经济增长转向中低速经济增长的拐点究竟在哪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和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
(1)崩溃说。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而且由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的一些深层矛盾已经显现和爆发,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并很快走向崩溃,特别是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呈下行之势。保罗·克鲁格曼在2011年年底预测指出,中国有可能成为欧债危机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危机发生地。[1]米歇尔·司谷曼也认为,中国的危机大约将出现在2014—2015年左右。[2]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吉姆·查诺斯则直言中国的硬着陆已经开始。以2001年中国入世时出版 《中国即将崩溃》而闻名的美籍华人章家敦更是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最近,他将2014年确定为中国经济崩溃的时间点。①2011年年底,章家敦在 《外交政策》上发文,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将崩溃。2013年年底,他在福布斯网站发文,第13次预测中国经济将崩溃,并认为时间是在2014年。很多研究机构也纷纷在研究中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心。比如,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就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后硬着陆;野村国际经济研究部也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4%以下。诺顿认为,从历史上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类似,都经历了超高速增长,但这种超高速发展阶段基本都在25~30年内终结了,他据此得出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即将结束的结论。[3]郎咸平多次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与此同时,国内也有学者表示了同样的担心。李佐军和牛刀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崩溃。崩溃说的最主要依据在于对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2013年6月国内出现的 “钱荒”,更是坚定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认识。2013年7月,克鲁格曼再次指出,中国经济碰壁,遇上了大麻烦。[4]夏斌则直言,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5]
(2)中低速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根据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和消失、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全球化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全要素生产率难有大幅度提高等因素,通过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或者说,中国经济进入 “换挡期”。孙学工等指出,如果按照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2011—2020年经济增长率将比2000—2010年下降2.9个百分点。[6]蔡昉预测,中国 “十二五”和 “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7]祁 京 梅 指 出,未 来 一 个 时 期我国将会维持6%~8%的中速增长。[8]余斌也认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未来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十二五”期间GDP增长将保持在7%~8%。[9]
(3)5年说。刘世锦指出,人均GDP在达到11 000国际元之后,会遇到 “高收入之墙”,增速下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3—2017年下台阶,增速下降30%左右,由10%降低到7%左右,如果应对得当可以持续10~20年。[10]王一鸣等测算指出,2011—201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8%~9%,2015—2020年将下降到7%~8%。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消费市场加速、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大、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城市化推进、区域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从而确保中期经济增长高速度。[11]
(4)10年说。认为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 《春季经济蓝皮书》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从目前的8%~9%下降到2020年的6%~7%左右,未来可能进一步降为5%。[12]
(5)20年说。林毅夫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仅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 和8.3%的增速。据此,中国未来20年也完全有可能持续8%的经济增长速度。[13]刘伟在考虑了工业化因素以后也指出,日本及 “亚洲四小龙”完成经济高速增长时基本都完成了工业化,我们离工业化还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中国经济还有保持20多年高速持续增长的潜在机会。[14]黄泰岩认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前后结束经济高速增长的,我国目前工业化仍处在中后期,城镇化刚刚跨过50%的门槛,仅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区域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这都为未来2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15]
(6)不确定说。这主要是因为,实际经济增长会受到众多可计量和不可计量的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管理改善、人力资本积累、国际环境等[16],其中,重点领域改革被认为是决定未来经济走势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张军指出,在当前经济因为外部冲击而出现减速的关键时刻,启动新一轮结构改革并顺势推进人口的城市化,将是未来10年全要素生产率得以维持年均3%的增长趋势的重要机会,未来1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在大约7%~8%范围内就可以期待了。[17]彭文生则区分了基准情形和改革情形两种情况,认为在基准情形下,“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期间为6.0%左右,2020年下降到5.5%;在改革情形下,“十二五”期间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期间为8.0%左右,2020年下降到7.5%。[18]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框架明晰之后,国内外对中国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向乐观转向的迹象。比如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米歇尔·希尔弗斯坦基于2013年底我国公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描绘的改革情形,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乐观的预测。[19]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不仅决定着我国的命运,而且关乎世界的未来。就我国而言,从理论上说,如能再有10~20年的高速增长,打破韩国等经济体的30年高速增长大限,无疑将证明 “中国模式”的生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实践上说,要达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就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经济发展不能滑出的 “下限”,关系到“中国梦”能否实现。就世界而言,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就将结束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霸主地位,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如果中国经济崩溃,不仅会拖累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必将对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构成巨大的冲击。这就意味着,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绝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的自娱自乐,而是关乎世界命运的大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关乎世界命运的大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论?究其原因,是因为迄今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完整的判断高速经济增长拐点的理论依据或分析框架,大家只是依据各自的评判依据得出结论,这就难免会出现 “瞎子摸象”的图景。因此,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做出科学的研判,就需要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总结提升和验证的视角,构建出一个包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判断经济高速增长拐点的理论假说,解析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从而为回答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增长,如有,还有多长时间等问题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当然,本理论分析框架仅用于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已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及保持多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
依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即现代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经济发展就是现代工业经济部门的不断扩大,以及用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业不断工业化、现代化,“如果资本主义扩展速度足够快的话,那么,它迟早会包容整个经济”[20](P68),最终使整个经济从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即实现工业化。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并具有巨大优势的支撑要素,即可以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他认为,由于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人的工资就不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工人的生存决定,即生存工资,因而可以假定工人工资不变。“工人在扩大中所得到的全部好处只是他们之中有更多的人按高于维持生计部门收入的工资水平得到就业”[21](P18)。但由于工业部门的效率高于传统农业,即使是生存工资,也高于农业收入。这样,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成为城市市民。因此,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两个驱动力。反过来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没有了,当然,经济发展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因此,他认为,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干以后,劳动力市场会发生改变,劳动力的供给低于需求,工资不变假定改变,这时工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弱,经济扩张停滞或者萎缩,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正常发展阶段,工业化至此基本结束。
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束也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基本结束,经济进入稳定的正常发展阶段。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工业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只有推进工业化,现代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形成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又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需求,进一步推动产业的集聚,形成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产业和人口的双集聚,会推动城市的发展,形成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没有工业化,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会出现过度城市化,这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没有产业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城市就会成为 “空城”,出现房地产泡沫,毁掉经济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只要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就将继续,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会结束,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工业化不仅包括完成传统工业化,而且还要实现新型工业化。这就意味着,仅仅以人口红利是否消失来断定经济高速增长是否结束,依据是不充分的,甚至可以说丢掉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要素或者灵魂。
第二,城市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枯竭被看做是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分水岭,这也是许多学者判断经济高速增长是否结束的依据。实际上,这是陷入了刘易斯理论的误区。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存在着几个错误的或者被忽略了的重要假定。一是刘易斯忽略了农业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进行了修正,认为只有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时候,劳动力无限供给才会持续。也就是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断增加的。二是刘易斯忽略了城市需要就业人口的存在。托达罗对这一理论缺陷做出了修正,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增加过剩人口。因此,不能简单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少来判断剩余劳动力的多少。三是刘易斯的工业化是假定数量的扩张,而没有技术的变化。实际上,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更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实施自主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减少对过剩劳动力的吸纳,相对增加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会对劳动力的质量提出要求,因而人口红利不一定继续表现在简单劳动力身上,而会表现在受过一定训练的劳动力身上,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替代。四是刘易斯将工人工资的上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干联系起来,但忽略了还有许多因素会引起工人工资的上升,比如生活成本的上升,所以,不能看到工人工资上升就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干了。将以上这些因素纳入刘易斯的理论框架,用扩展的刘易斯理论就不会仅仅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静态多少,甚至仅仅根据工资上升就得出高速增长已经结束的结论。
第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化,进入发达经济体。一国通过推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就是要实现现代化,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因此,理应把是否进入发达经济体也列入判断一国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进入发达经济体这个单一指标来判断经济高速增长是否结束,因为一国进入发达经济体可以有多种原因,那种脱离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地位是不稳固的,如利比亚就是一个人均GDP过万美元而出现社会动荡的国家。这就是说,必须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三位一体来判断一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限。
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国际经验验证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均达到9%及以上,但在高速增长之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下滑,大约跌至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一半左右。这被称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30年大限”。
日本从1956年到1973年的18年间,年均增长率超过9.2%,其中有7个年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人均GDP也迅速攀升,从1956年的1 558美元上升到1973年的7 785美元。但到1974—199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降为3.8%。1990年后的21年间,年均增长率跌至0.99%。韩国从1963年到1991年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如果剔除因为国内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1980年①1980年,由于爆发 “光州事件”,韩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率为-1.9%。,年均增长率高达10.4%。1991年韩国名义GDP达到3 150亿美元,是1963年的116.7倍,人均GDP达到7 288美元,是1963年的72.9倍。1992年后的20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速降为5.2%。我国台湾地区从1961年到1989年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7.69亿美元增长到1 527.4亿美元。1990年以来的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降为5.2%。新加坡从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其中从1965年到1973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名义GDP从9.742亿美元增长到42.275亿美元。1995年至今,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速为5.9%。
从上述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限来看,最长没有超过30年的,似乎 “30年大限”是成立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限与它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时则会发现,它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时间上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它们经过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都在高速增长结束前后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迈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从工业化来看,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韩国1965年为21.3%,处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到1975年提高到29.3%,进入加速工业化阶段;1985年达到39.1%,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1991年达到高点的42.6%,韩国的高速增长也恰好在这一年结束,与工业化的完成非常吻合。①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日本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55年为33%,处于工业化启动阶段;到1960年提高到40%,进入加速工业化阶段,并一直维持在40%左右,到1970年达到最高值44%,1971—1973年均保持在43%,然后持续下降。1973年日本高速增长结束,也与工业化的完成非常一致。②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整理。中国台湾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63年达到28.1%,首次超过农业,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22];1975年达到39.4%,工业化加速;1980年和1981年达到最高值,均为45.3%,此后几年一直维持在41%~44%的高位,直到1989年,才首次下降至40%以下,恰恰是在这一年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同样表现出与工业化完成的高度吻合。[23]
从城市化来看,日本城市化率从1947年的33.1%提高到1965年的68.1%,年均提高1.94个百分点,到1970年,进一步提高到72.2%。韩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期是1961年到1987年,与韩国的高速增长阶段完全重合,1985年的城市化率达到77.3%。到1990年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结束时,城市化率提高到82.7%。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化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的24.07%上升到1978年的63.8%,80年代达到70%的水平。如果以城市化率70%为城市化完成的标志,那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之前均完成了城市化。刘易斯通过跨国实证研究也反证了以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他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很少有国家的人均GDP能达到1万美元。
从现代化来看,日本1978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73年高速增长结束;韩国1995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91年高速增长结束;中国台湾地区199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89年高速增长结束;新加坡198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94年高速增长结束。高速经济增长结束的时间与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时间基本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不是因为到了30年就结束的,而是因为他们经过20~30年的高速增长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了。这一结论验证了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由此看来,“30年大限”的假说就成为似是而非的结论了。
此外,我们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的经济增长表现还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征:(1)即使在它们结束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同期的其他经济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的10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虽然仅有3.6%,但仍高于同期美国的1.8%、联帮德国的1.6%、法国的2.3%和英国的1.0%。(2)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都进入了一个较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而且与先期的日本相比,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日本在该阶段共持续了17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3.8%;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分别持续19年、21年和17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5.2%、5.2%和5.9%。
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假说的内在机理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高速增长阶段与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高度吻合,说明工业化、城市化对经济高速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机理就在于工业化、城市化为投资和消费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城市化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大规模的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
(一)工业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推进工业化高速增长的阶段,投资是重要的拉动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主导特征。日本在1956—1964年围绕重化工业化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相继出现了“神武景气”(1956—1957)和 “岩户景气”(1959—1961)两次经济发展高峰。1956年,日本的私人设备投资比1955年猛增54.6%,投资的70%集中在钢铁、机械、电力、化学等行业,使日本很快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重化工业体系,体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对投资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日本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的时期,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日本大量投资于电机、电子、汽车、合成纤维、合成树脂、石油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为其提供机器设备和原料的机械、钢铁等基础工业部门的投资。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高速增长时期不断提高,1961年超过30%,到1973年高速增长结束时,达到历史最高,为36.4%,呈现出与高速增长阶段的同步性。韩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也是通过大规模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 “三五”(1972—1976)、“四五”(1977—1981)两个五年计划为中心,韩国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加大对造船、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这对当时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台湾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了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标志的十个重大项目建设,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
上述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将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化工业的做法表明,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从而能够带动更快的经济增长。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发展重化工业,到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大约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日本从1963年开始重化工业化,到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也有10年的发展期,占日本高速增长阶段的一半时间。投资重化工业之所以能够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是因为重化工业具有产业链长、附加值大、技术含量高、消费升级周期长等产业特点。实际上,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其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也都高于轻工业发展阶段。根据霍夫曼、张培刚、盐谷佑一、钱纳里和泰勒等实证分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重化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就是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就意味着:一国完成了重化工业化,也就实现了工业化,从而也标志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
(二)城市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
城市化推动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实现高速增长的机理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一是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二是劳动力的低廉提高了企业利润,为吸引大规模投资创造了条件。
韩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63年高达63.1%,1970年开始实施新村运动,1975年下降到37.1%,1985年下降到20.1%,向城市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这个时期韩国的失业率也大幅降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韩国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为3.2%,但失业率却从1962年的8.2%峰值逐步下降到了1975年的4.1%。[24]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 “人口红利”。
与其他国家相比,此间韩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据统计,1964—1970年韩国的工业日工资水平,最低时为0.48美元,最高时也只有1.24美元。这一水平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半导体工业为例,1970年美国工资是韩国的10.2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的工资水平则是韩国的1.2倍。[25]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
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产业的集聚会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产业投资和进一步的产业集聚。产业的集聚会带来人口的集聚,产业和人口的双集聚就会带来城市数量的增加和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扩大,从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这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日本在城市化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和55%的工业生产,目前进一步提高到约2/3的全国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0%。韩国仅有4 800万人口,但却发展出277座城市,其中有7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人。首尔1960年城市化加速初期人口仅有200万人,1970年达到400万人,1980年超过800万人,到1990年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结束时,人口已超过1 000万人。目前首尔地区的人口占韩国总人口的50%以上,对持续GDP的贡献率高达24%。
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假说的中国价值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经验,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图景做出如下描绘:
(一)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还应持续20年左右,再创世界经济发展的 “奇迹”
既然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完成时间高度相关,那么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的国家发展水平分类标准,我国2011年人均GDP为5 400美元,处在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在 《2030年的中国》一书中的预测: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按此预测,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入高收入社会大约还需要20年的时间。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也就是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根据有关测算,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大约完成60%以上。按照发展规划,到2020年才基本实现工业化。我国城市化率2011年为51.27%,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如果剔除在城镇居住和工作但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城市化率还不到40%。按照发展规划,我国到203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0%,即使按此计算,我国仍有4亿人口在农村。根据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进程来看,两者相差约10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未来10~20年,城市化将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从三位一体的判断依据来看,我国还应有潜力再来近20年的快速增长。如果再来20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就可以创造出无论是在高速增长持续时间上还是在国家类型上全面的世界经济发展的 “奇迹”。
而且,根据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在结束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还将进入一个次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所谓次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是相对于高速增长阶段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经济体而言,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这个阶段还要持续大约20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完成高速增长阶段后,在不发生大的政治、军事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该经济体的经济突然减速甚至陷入崩溃是不现实的。依据这一历史经验,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就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在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和不发生与他国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将快速发展,不可能崩溃!
(二)城市化将继续创造 “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活力
加快推进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继续贡献 “人口红利”。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但仅减少了345万人,占总劳动人口93 727万人很低的比例,而且这种下降趋势到2030年前都是逐步的,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使出现减少,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完全可以保证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更应看到的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将有越来越大的需求。我国现在每年有近700多万大学生毕业,2013年内地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699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学研究生172万人。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红利开始出现增长,而且未来增长得会更快。人力资本红利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转型,从而通过转型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动力和活力。
(三)城市化将带动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空间
基本实现城市化,我国至少将有3亿~4亿人口进入城市,这将对城市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城市化也会因收入增长和商品化率提高而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根据马晓河的测算,假定到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0%,将会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资约20万亿元,增加消费5.3万亿元。[26]25.3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将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报告甚至认为,城镇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27]
(四)人口的集聚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2008年,我国拥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座,但其中人口超过200万人的城市仅有41座,人口集聚程度较低。因此,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将主要不是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多,而是既有城市规模的扩大。据预测,2025年,99座新城市有望跻身全世界最大600座城市行列,其中72座来自中国。[28]另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结构改变最明显的证明将是城市的繁荣,尤其是目前人口少于150万人的中小城市,它们将为中国城市贡献40%的GDP。人口的集聚,不仅会促进中国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而且将有力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马晓河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为1.13,这意味着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29]
(五)人口的集聚要求产业的集聚,而产业的集聚将提高经济的效率
与人口的集聚度不高相对应,我国的产业集聚度也较低,目前在全国GDP总量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贡献还不到40%,与日本三大经济圈70%和美国三大经济圈68%的水平有很大差距。按照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的基本规律,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和前提,因而人口的集聚必然要求产业的集聚。根据麦肯锡的预测,中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这意味着产业越来越向城市集聚。产业在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向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集聚。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三大经济圈。有人考察了美国1900—1990年期间城市的变化,发现在此期间出现的新城市,如果邻近其他城市,则发展较快,而且与相邻城市的增长率紧密依存。二是产业的集聚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才会出现集聚效益。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弗农·亨德森认为,如果中国一些地级城市的规模扩大1倍,可以使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产出增长20%~35%。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这就要求产业将向几大经济圈集聚,并随着产业的集聚,人口也将随之集聚,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最终打造出若干个经济增长极,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1]Paul Krugman.“Will China Break?”.The New York Times,2011-12-18.
[2]Michael Schuman.“Why China will Have an Economic Crisis”.Time,2012-02-27.
[3]张军:《邓小平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载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4]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The New York Times,2013-01-18.
[5]夏斌:《当前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载 《京华时报》,2013-07-15。
[6][16]孙学工、刘雪燕:《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分析》,载 《经济日报》,2011-12-12。
[7]《专家: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或将消失 第二次人口红利可能再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24/c1001-18820528.html。
[8]祁京梅:《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载 《中国金融》,2013(15)。
[9]《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载 《中国经济时报》,2011-11-29。
[10]刘世锦、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载 《比较》,2011 (3)。
[11]《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了吗?》,载 《人民日报》,2011-11-21。
[12]《中国社科院春季经济蓝皮书: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载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4-25。
[13]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http://www.ftchinese.com/story/1001052200?full=y。
[14]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载 《国际融资》,2008(1)。
[15]黄泰岩:《中国经济还能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吗?》,载 《中国能源报》,2012-12-10。
[17]张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载 《深圳商报》,2013-11-04。
[18]彭文生:《中国经济:改革驱动下的长周期》,载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02-25。
[19]Michael J.Silverstein.“Ten Predictions for China's Economy in 2014”.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log Network,2013-11-21.
[20][2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2]楼勇、阎桂兰:《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载 《海峡科技与产业》,2013(8)。
[23]彭百崇:《台湾经济转型与就业 M型化问题》,载 《台湾劳工》,1997(13)。
[24]徐建平:《韩国的劳务市场》,载 《国际经济合作》,1999(3)。
[25]张玉柯、马文秀:《比较优势原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载 《太平洋学报》,2001(1)。
[26][29]马晓河:《积极推进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载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 (2012)》(讨论稿)。
[27]《“城镇化”或将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1226/c1004-20016174.html。
[28]《美媒:2005年全球最具活力城市四成在中国》,载 《环球时报》,2012-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