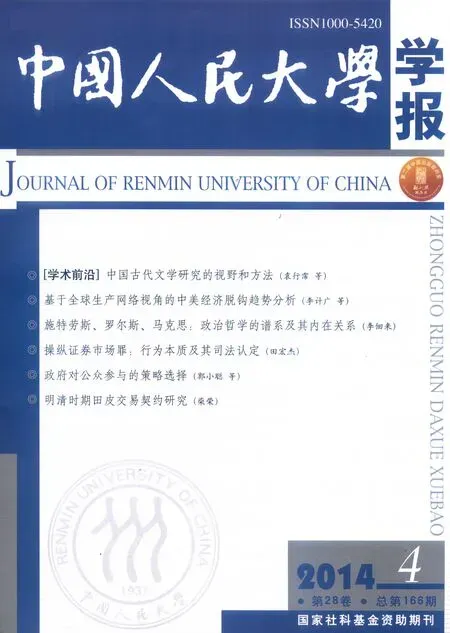明清时期田皮交易契约研究
2014-08-08柴荣
柴 荣
明清时期田皮交易契约研究
柴 荣
明清时期,田皮交易是土地买卖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各级官府对其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在分析明清时期契约中“一田二主”的表现形态并厘清其中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可得出结论,朝廷正式法典从未对田皮交易作出过调整,省级官府出于税收和社会稳定的考量,反复调整有关田皮交易的法律规范,逐步从默认转到禁止;同时,田皮交易在基层官府的放任和支持下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而且基层官府通过授权乡村基层组织的方式实现了对田皮交易的参与和监管。各级官府对田皮交易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制定法常常需要让位于非正式制度的民间习惯法,这也是明清时期田皮交易非常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田皮;田骨;“一田二主”
明清时期一份地权可能分成田骨权和田皮权,有的地方称其为田底权和田面权,这样在一份土地上就有两个主人,其一为田骨业主,其二为田皮业主,这就是所谓的“一田二主”现象;田皮业主对土地享有独立于田骨业主的占有、耕作、转让等权利。从历史渊源考据,早在宋代就出现过田骨的字眼,宋代文献中有这样的表述:“广都人张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几,其人欲加质,嘱官侩作断骨契以罔之。”[1](P223)田皮、田骨分离,分别作为土地权益的一部分而成为交易“标的物”的现象从明代开始在民间盛行,正如杨国桢先生所言:“自明中叶以后,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则已蔓延全国,在若干地区甚至成为主要的租佃制度和土地制度。”[2](P70)葛金芳先生也认为:“明清时期,随着永佃制的逐步普遍化,一田二主之惯例遍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江南各地,台湾亦有。”[3](P242)
傅衣凌先生于1939年发现了福建省永安县文书所包含的关于买卖典当田皮的契约,对这批文书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研究明清时期田皮的源流之一,之后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从历史、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解读。这些研究用永佃、田皮、田骨、“一田二主”等传统民间习惯法术语,以土地所有权分离或分割,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现代理论为路径,揭示了中国明清到民国时期土地交易形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原因。笔者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个时期一些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造成“一田二主”如此活跃的原因远非土地交易本身使然,其中一个重要的、未被前辈学者所提及的原因是,不同层面的官府基于不同的考量对有关田皮交易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有不同的适用态度。明清时期,从国家制定法层面而言,对“一田二主”问题始终没有在国家律典中予以明确的规定,省级政府对田皮、田骨分离交易,曾经历了从默认到禁止的过程。从民间习惯法的角度而言,基层州县级官府对乡村习惯中的田皮交易一直持放任的态度,并且通过授权乡村基层组织,满足了田皮交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签约到解决纠纷的自力救济需求。结果是作为国家正式制度的省级政府田皮交易禁令往往形同具文,而民间习惯法中田皮交易行为却大行其道。这正印证了樊纲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与实施‘理性化’的正式制度;一切正式成文的法律,都可以随时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写和放弃,从而使得所谓成文的正式制度,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等同于非正式的制度。”[4]
一、契约中的“一田二主”及其法律关系解读
我们今天要想知晓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实际状态,最主要的资料数据来源是当时的土地交易契约。因为“它(契约)是一种法律文书和私家档案,又是特定事情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私法规范”[5](P1)。田皮交易契约作为私法规范的一个独立系统,它所反映的是基层社会日常生活民间习惯中的种种现实行为。奥地利法律社会学家埃利希(Eugen Ehrilich)曾将契约中所包含的规则称为活法(Living Law),并认为活法支配着实际生活,尽管它并没有被作为法规规定下来,却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契约文书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6](P542、547)
(一)明清时期田皮交易契约情状描述
从一些资料分析,一份地权分割成田骨(田底)、田皮(田面)不同层次,均可以独立流通于市场的现象大约在明朝嘉靖以后开始流行。田面(田皮)交易的契约格式被绝大多数的明代日用类书收录,这表明“一田二主”在民间非常普遍。从现有资料分析,万历年间刊印的民间日常用书《万锦全书》所载“赔田契式”,就是买主支付“赔价丝银”直接取得田面(田皮)的契约格式:“今来不成业次,情愿托得知识人为中说谕,即将前项田土出赔与某里某人耕作。当同中见三面言议,时值赔价丝银几两正。当时立契之日,价银一并交收足讫,外不欠分厘。自赔之后,某田且某人仍从前去耕作管业。”[7](P699)笔者赞同一些学者的说法,也认为“某类契约的格式化代表着这一类交易行为的普遍化流行度”[8](P75)。与“一田二主”相对应的土地交易契约中,有田骨或田皮活卖与绝卖等各种不同的形态,即便是仅仅买卖田皮的契约,在各地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名目各异,例如称为“田皮契”、“小苗契”、“税田契”、“质田契”。*这个时期有关田皮契约的来源主要得益于以下学者的整理研究:傅衣凌先生早在1939年于福建永安县发现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百余件并进行了整理研究;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搜集了大量田契,并以田契为中心做了较系统的研究,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日本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曾编有《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东京,日本东洋文库,1975,还有王钰欣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田涛、宋格文、郑秦主编:《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到清代,土地交易过程中田骨、田皮分离的现象更加频繁,名称也更为繁多。例如,江西省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告示中有这样的表述:“江省积习,向有分卖田皮田骨、大业小业、大买小买、大顶小顶、大根小根,以及批耕、顶耕、脱肩、顶头、小典等项名目,均系一田二主。”[9](P80)再如《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中收集到165件租佃契约,其中田根、田面分离者达151件,占总数的95.52%。[10]中国经济史学者章有义先生在整理清顺治至咸丰年间徽州休宁县朱姓家族的置产簿提及的100件田地契约时,发现田骨权与田皮权分离的现象十分明显,如图1所示。[11](P82)

图1 顺治咸丰年间某朱姓地主置产薄田地契约
(二)田皮契约法律关系解读
关于永佃与“一田二主”以及田皮、田骨分别交易的关系,学界从不同的学术视野做出了很多种阐释*梁治平认为“永佃与一田二主系历史上相关然而形态各异的两种制度”,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8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以杨国桢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一田二主”是由永佃制发展而来,在原有的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使用权——永佃权和分割出部分所有权——田面权,最终形成“一田两主”形态,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赵冈则认为永佃制包括初始、过渡、最终形态三个发展阶段,“一田二主”是永佃制发展的最终阶段,参见赵冈:《永佃制》,2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慈鸿飞认为永佃权的基本特征就是田面权,而不是什么“永远耕种”权,并认为江南永佃制在民国时期的流行情况可能要比人们所了解的更为广泛,永佃制在近代并没有衰落,参见慈鸿飞:《民国江南永佃制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分析它们的关系,所有的学者都认可永佃与田皮交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实际上,作为民间习惯法层面的“永佃权”,常常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权利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田二主”的法律关系作了阐释。日本学者认为:把同一地块分为上下二层,上地(称田皮、田面等)与底地(称田根、田骨等)分属不同人所有,这种习惯上的权利关系就是“一田二主”。田面权(地上的权利)与田底权(底地的权利)并列,也是个永久性的独立物权。[12](P411—416)杨国桢先生认为:“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俗例’,它就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这时,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这样,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一田两主乃至一田数主的形态。”[13](P77)明代历史资料中曾描述过这种“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受田之家,后又分为三主:大凡天下土田,民得租而输赋税于官者为‘租主’。富民不耕作而贫无业者代之耕,岁输租于产主,而收其余而以自赡给,为‘佃户’……当大造年,辄收米入户,一切粮差,皆其出办,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买田契券,大率记田若干亩,岁带某户大租谷若干石而已。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和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14](P3073)
从这段史料分析,在田皮交易的过程中,会涉及“大租主”、“小税主”、“佃户”三者的法律关系:“大租主”即田骨业主;“小税主”即田皮业主;“佃户”是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实践中在缔结田皮交易契约关系时,买主支付了“粪土银”后(粪土银是指田皮权的价值),就变成了田皮主,他可以不限年月永远耕种土地,甚至直接以质典等交易方式处分该土地,其实质上拥有了对该土地的独立用益物权。嘉靖年间《龙岩县志(卷之上)》所提到的“佃丁出银于田主,质其田以耕”[15](P46),也是指如果佃户直接把田皮的价款交给田骨主,就获得了田皮权。当佃户拥有田皮权便“私相授受”,以“质典”这种交易形式出让田皮权(粪土田),收取“小租”(即小税)时其身份就发生了转化,成为“小税主”,也就是所谓的“二地主”,加上土地的真正使用者(佃农),于是这块土地上便出现了“一田三主”。同时在“一田三主”的法律关系中,意味着田皮主取得了稳定的耕作或转让权后,即使田骨业主出卖土地,也不影响田皮主的权利,田土仍归原主使用。田皮主这种稳定的耕作使用权在光绪《周庄镇志》中是这样表述的:“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虽易而田主不易。”[16](P538)
这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围绕着田租如何承担以及田赋差徭如何分担问题而形成。就田租而言,习惯上大都由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即佃户农交付,实践中一般有两种交付方式:其一,佃户交两份地租,一份交田骨主,另一份交田皮主。如江西宁都县的做法,佃户“既交田主骨租,又交佃人皮租。”[17]其二,佃户交给二地主(田皮主),田皮主再转交田骨主。福建《南平县志》:“赔主向佃收谷,苗主向赔收租。”[18](P219)(赔主是指田皮主,苗主是指田骨主)例如,广东惠来县,尤廷烈父亲在日承耕方荣伍田五亩,每年纳租谷三石八斗。后尤廷烈父故,无力耕种,便将田转批与温必兴承耕,递年租谷都是温必兴交与尤廷烈,尤再转交方荣伍的。[19]
田赋差徭是承载在田土之上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其情况更为复杂。实践中有田骨主承担的,有田皮主承担的,有佃户承担的,由于田皮交易的盛行甚至还有专门的“揽户”来代理承办田赋差徭。其一,田骨主(苗主、大租主)承担,如《漳州府志》记载:“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米兑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20](P3073)。其二,皮主(小纳主、小业主、小税主)承担,如福建平和县“买田者为田主,买租者为租主。其田原载粮米,租主全不收入户,只将田租之内抽出三分,付与兑米人户,代办条差”[21](P3122)。其三,佃户承担,例如江西南靖县,“佃户则出资佃田,大租、业税皆其供纳”[22](P3120)。上文提到的“揽纳户代为办纳”、“代办条差”均是指收取一定的费用代为办理缴纳田赋差徭。
二、朝廷与省级官府对“一田二主”态度衍变之解析
中国古代正式法典中关于土地交易的规定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集中在与国家公权力相关方面,尤其税收和社会稳定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徐忠明教授在分析明清法律文化时,提到这个时期的官员也认为:“民生之本,莫若钱粮、刑名二事”[23](P226—227)。西方观察家对此也有类似的评价:“他们(指中国)的立法者的主要努力,都用在制定镇压骚动及保护税收的法律方面,而把民法、商法或契约法的问题交给地方政府去处理。”[24](P44)国家的正式法典体现了朝廷的立场,对朝廷直接负责的省级政府对田皮交易的态度受其左右,基于税收和词讼的考量,经历了从默认到禁止的过程。
(一)朝廷与省级政府之态度:从默认到禁止
有学者认为,《大清律例》中,“在通常被西方学者译为‘民事法’的‘户律’里面,与现代民法有关的事项多半是因为与户部的主要职能——税收有关才被排列在一起。此外,律典中有关土地交易的规定甚少,而且完全没有系统性”[25](P128—129)。尽管法典层面有关土地交易的规定非常简单,我们仍然能够从明清时期法典层面的规则体会出来。就朝廷最高层而言,一直是坚持“一田一主”的土地法律理念的,而且有资料显示,一些官员也认为:“一田一主才是合法的土地制度,田主是占有田底的土地纳税人”[26](P238)。具体做法是国家通过确立土地契税制度和钱粮过割手续对民间的土地交易契约活动进行宏观控制。地籍是国家税收的重要依据,所以,明清时期均对脱逃地籍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制裁。例如,《大清律例》的“欺隐田粮”条规定:“凡欺隐田粮(全不报户入册),脱漏版籍者(一应钱粮,俱被埋没,帮计所隐之田),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7](P190)
但是,明清时期的土地政策和法律中的一些规定还是为田皮交易和“一田二主”的滋生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明代政府对民田的政策是“民所自有,得买卖之田”[28](P18),可见到明代土地自由买卖已经得到朝廷的认可。清代《户部则例》明确规定:“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户仍旧,地主不得无故增租夺佃。”[29](P206)在永佃关系下,明清律例均规定:佃户虽有交租的义务,但却取得了世代承耕的权利;田主在收取地租的条件下,也不得自行转佃。[30](P114)对地主“增租转佃”行为的法律限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读,只要佃户履行了交租的义务,就可以永远耕种或者使用业主的土地,即使地主出卖土地,永佃人也不丧失其权利,除非佃户自愿退佃。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土地的真正占有者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久佃成业”非常容易演变成对土地的处分收益权(田皮权)。
明清时期地方省级政府对田皮交易现象的态度有较大的差异性,大致经历了明代默认其合法到清代乾隆年间多次颁布禁令的过程。关于明代政府对田皮交易的态度,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省级政府对“一田二主”现象有明显禁止规范的证据,相反,我们推测这个时期官府基本上是默认田皮契约的合法性的,不过这种契约不是以买卖田土的形式而是以转让佃权的形式出现,交易者应该去官府缴纳一定的契税。这样既规避了法律上转让土地必须要过割户籍的规定,又保证政府的税收不受影响。《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有许多明代佃农转佃的契约,其中还有经过官府验证的赤契。[31](P1775—1781)杨国桢先生在分析明代一份判词时也认为:这些祀田通过“田骨”、“田皮”的分割,以交易的方式落入外姓手中,已经不是当时之事,而知县竟捐俸代为买回“田骨”,说明官府已经承认这个“俗例”的合法性。[32](P80)清代土地买卖更加频繁,田骨、田皮分离交易的现象更加常见,民间土地交易实践中回赎惯例和田皮转移而税粮并未过入买主户内以及逃避契税等等事例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地权分为田骨、田皮引起的产权纠纷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甚至引发刑事人命案件也不在少数。
从清代开始,尤其是乾隆年间,一些省级政府屡次“发布告示”对田皮、田骨分离交易予以“禁革”。例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福建)省府颁布了第一部省例,宣布区分田面权利和田底权利的“恶例”为非法行为。[33](P240)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省府两次采取“勒石(其表现形式为在交通要道刻石立碑,这是传统社会政府向民众传达法令告示等国家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34](P127)和“刊刻告示”的方法下发禁革章程,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再次“申明禁例,严加整饬”,“在于城乡处所一体勒石禁革”,比较偏僻的地方也要“照式竖立石碑或刊刻木榜,一体示禁,务使家户谕晓”。[35](P446—447)葛金芳先生根据《福建省例》卷十五《田宅例》的记载也认为:“雍正、乾隆年间,福建省级官府为了理顺租税关系,企图调整‘一田二主’的关系,具体举措包括:取消皮租;禁止买卖不随田骨的田皮;佃农没有向皮主交租之义务;皮主欠租时,骨主可收回耕地,转佃他人;乡绅对骨主欠租,立即严惩;命各乡村以此勒石树碑。”[36](P245—246)
与省级政府田皮交易禁令相呼应,清代朝廷也曾试图从立法的层面规制土地交易所有权的清晰度和肯定性,以此来杜绝田皮交易大多不卖绝而可能回赎的现象。乾隆十八年(1753年)发布的一条新例规定,契约必须明确是否允许回赎,同时法例规定在订立契约三十年内,可以回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37](P203)。
(二)“从默认到禁止”之原因分析——税收与社会稳定之考量
当田皮、田骨分离交易并未影响到明清时期国家公权力时,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其均采取默认的态度。我们在很多资料中发现,“一田二主”对整个政府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税收减少和诉讼量增加,甚至是刑事案件的增长,这成为这个时期中央和省级政府试图禁止田骨、田皮分离交易的主要动因。顾炎武对“一田二主”的弊端有过这样的评价:“钱粮逋负,词讼日兴,皆此之由。”[38](P3077)美国一些学者也认为:“乾隆三十年(1765年),福建省布政使重新审查了过去35年间省府意图宣布一些习惯行为是非法的,其中包括一田二主行为,认为其一方面造成有些佃户公开不交纳地租或者擅自将田面权卖给他人,另一方面造成田底所有权人既不能支配自己的土地也无法缴纳国家的税收,甚至常常因此而引发词讼,一田二主在两个方向上的滥用恰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紧张、词讼以及岁入的减少。”[39](P239—240)
就税收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程度上“一田二主”,田骨、田皮分离交易是规避国家苛捐重税的产物。所谓“赋役之重,至明而极矣”[40](P105)。《大明律》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41](P55—56)清初赋税政策沿袭明例,赋税依然繁重。总之,在国家苛重的税收政策下,一些有田之家便采取了不转移赋役和规避契税的办法,于是在民间田皮大多私自交易,采用“白契”*明清时期土地买卖,按照法律规定,要向官府办理登记手续,向政府办理纳税、粮差过割手续,并在契约上加盖官印。由官方认可的契约,加盖官印红章,称为红契。白契实际上是未登记纳税的民间私人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形式。历史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福建《漳州府志》亦称:“惟是漳民受田者,往往惮输赋税,而潛割本户米,配租若干石,以贱售之。其买者亦利以贱得之……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和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42](P3073)
就社会稳定而言,田皮、田骨的分离使得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身份变得模糊,两者的身份常发生某种重叠,使主佃双方的关系变得复杂,因争夺土地权益引发了很多纠纷,由此影响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得不关注的问题。首先,因争夺地权引发人身伤害在史料中多有记载。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浙江仙居县佃农张锡文和周桂芳在田皮权的争夺中未能如愿,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初三日,张锡文见周桂芳的田内谷已成熟,就叫了儿子张富松到周桂芳田里割谷子,遂发生冲突。周桂芳举扁担向张锡文打来,张锡文用拄棍格伤他左胳膊,并打周桂芳头上一下,不料伤着他头顶”[43](P666)。更为关键的是,官府最担心“民间细故酿成人命大案”,当田皮交易纠纷引发双方纠纷,甚至人命案时,就需要由各省督抚将案件提交给中央的刑部,最后由“三法司”作终审判决。一般情况下在交易田皮时,各方是想不到会有纠纷诉至官府的,这时官府也没有办法介入他们的交易。但是,田皮交易的灵活性、复杂性很容易引发词讼,此时中央政府又成为无数土地纠纷的最终解决之处。中国第一历史研究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收有乾隆刑科题本中“永佃权类”和“转租类”的命案共118件,《刑科题本》中未录或未酿成命案的冲突事件应更多。田骨、田皮分别交易过程中转手过于频繁、手续又过于简便势必为日后彼此之间的纠纷埋下隐患,很多时候甚至酿成人命大案,典型的案例如:“乾隆五年(1740年),江西安远县蔡友习被殴身死一案,其起因也正由于佃农蔡相叔父子将转顶来的田面,顶耕年久,田成膏腴,从而引起原佃蔡友习的嫉妒,欲图谋夺耕”[44](P493)。
三、基层官府与乡村民间组织对“一田二主”的态度:支持并参与
在对待“一田二主”的问题上,我们发现明清时期基层官府的主流态度是默认其存在或主张其合法化,在实际的田皮交易过程中,从契约的签订到纠纷的解决,乡村民间组织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得到了基层官府的授权。
(一)基层官府对上级“一田二主”禁令之态度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挖掘,我们发现,明清时期即便是上级省政府多次颁布禁令,试图“禁革”田皮、田骨分离交易,但是这些禁令并未得到下级基层官府的执行和配合,相反,基层官府对田皮交易大多持默认甚至主张其合法化的态度。例如,如前所述,福建省三十几年间先后数次用立石碑、刊刻告示等方式试图“禁革”田皮交易行为,省级政府“禁革”田皮、田骨分割交易的官方立场是坚定的,但全省州县一级基层官府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多是置若罔闻、敷衍了事。
乾隆时期福建省政府多次颁布禁令,但是因在基层官府并没有得到落实而收效甚微,以至于被省政府认为“地方官奉行不力,以致日久废弛”[45](P447)。乾隆三十年(1765年),福建省布政使司公告指出,“一田二主”的惯例自雍正八年(1730年),历三十余年,屡被禁止,却毫无成效。[46](P242)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江西宁都州仁义横塘塍茶亭所立的碑中,更以法律的形式把田皮买卖规定下来。碑文称:“查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上流下接,非自今始,不便禁革。”[47](P244)在推行第三次“禁革”20 年之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建闽清县令甚至还认为田皮、田骨名目“牢不可破”,要求皮骨共同纳税,承认田皮权的合法地位。他说,鉴于田皮、田骨分离交易在该县“相沿已久,势难禁革”,呈请省府将皮骨“一体报税”,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平息纠纷又可以增加税收,但因为“与叠奉禁例有悖”而没有得到批准。[48](P27)
为什么基层官府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这些禁令?一方面,民间现实经济生活中田皮交易盛行是其有令难行的实际困境;另一方面,上级省政府禁令背后不同的声音,也常常让基层官府对这些禁令熟视无睹有着潜在的托辞。即便是出于税收和词讼的考虑,一些省级政府多次发文禁止田骨、田皮分割交易,但在同时期省级官员中对政府的禁令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禁令的效果并不看好,对绝对禁止的措施也并不赞同。例如,雍正末期乾隆初年,江西按察使凌燽以立法方式,承认田皮买卖、转退的合法性,他在公文中写道:“田皮、田骨名色,相沿已久,故属习俗难移。”[49](P173)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那苏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江南之陋习”,农户租田时“有送上首佃户顶首钱名色”,业主打算更换佃户时,佃户“必索取他佃之顶首钱”,“如不遂欲,即霸占不容耕种”,“江南大概业主之苛刻者少,佃户之刁黠者多”。他建议,地方官应该“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虽然他认为农户交纳押租获取永佃权会产生诸多弊端,但却没有建议“禁革”,而是认为可以因势利导,逐步消除这些所谓的“陋习”。[50](P11)
(二)基层官府参与支持田皮交易——以授权乡村民间组织为路径
基层官府通过对乡村民间组织的授权,管理参与着民间的土地交易过程。实践中从土地交易契约的签订、过割到纠纷的解决整个环节都有基层民间组织参与主持,而且基层官府授权乡村组织管理土地交易是有国家正式法律依据的。例如,明代法律规定:“今逢前因,相应刊印契纸,编订上、中、下号簿,呈送巡按御史印钤。给发该州县。责成现年坊长、里长,凡遇典买房产、田、地、山、滩、荡等项,无论乡绅士庶,该坊里长一人,将所领契纸转给受业人户,使出业人将价值数目,眼同填注,随同受业人赴州、县照例纳税。”[51](P353)意思为:官府认可的官方土地交易的契纸由省政府印制,加盖巡抚御史的印章,发到各个州县,州县再发放到基层的坊长、里长手里。有田土交易时,由基层的坊长、里长负责将之前从州县领取的印好的官方契约文书发给买方,填好价格等各种信息之后再陪同买方去州县纳税。可见,即便缴纳了契税,经过官府认可的“赤契”的签订最终也离不开民间基层组织的参与管理。
按照明清时期法典的规定,田产一经换主,地籍税粮也应随即相应过割,而且买主要使土地交易契约具备合法效力,还得向官府亮契纳税。在《大明律》中就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凡是民间典买田宅,均须订立契约,并要到官府加盖完税印章。[52](P55—56)前面已经论及“一田二主”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规避国家赋税的产物,田赋和契税征收过重,使得民众纷纷避税。于是,“一田二主”在交易过程中,民间大多采用“白契”的形式,实际处于田不过户的状况,使得在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能而且不必求助于官府,他们常常在乡村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在这个范围内,田骨、田皮分离的白契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体现了“官有政法,民从私契”[53](P135)的价值追求。这也证明了章有义先生的观点:“未经官府盖印但符合当地通行买卖惯例的白契实际足以保证买主的产权。对一切制度包括土地买卖,起支配作用的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传统习惯。产权纠纷的解决往往不是仰仗官府,而是倚靠邻里士绅的公断。”[54](P80)
普通百姓民众因“一田二主”而产生的纠纷大多也愿意求助乡村民间组织,明代,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倡设老人制度,基层社会管理中呈现出部分自治的倾向,这种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政治体制不足,同时也可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他们不必再远途跋涉到州县打官司。在明代,里老(耆老)的义务是“劝民为善”和“听一里之讼”,所谓“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55](P709)。据《闽书》记载:“老人之役:凡在坊在乡,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此正役也。”[56](P961)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很多地方的乡村民间组织调处纠纷的范围均包含了田土纠纷。如山东诸城县“村置乡约,亦名甲长。土田、婚姻、命盗、殴置之事,惟保长、甲长是问”[57](P47)。
即使求助了官府(主要指交纳了契税和过割了田户的情况),官府的做法也是先发回原处让民间的地方乡保等进行调处。因为,明清时期,州县一级的司法权高度集中在州县官一人之手,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大量的民间纠纷完全由州县官一人直接、具体去管,势必既管不了,也管不好,通行的做法就是赋予基层组织司法功能,也就是由官府据情批给乡保、族长调处。清代乡约调处的诉讼纠纷范围与明代情况相同,但清代州县官将词讼批转乡约调处时,往往要求里长保甲将其调处意见和结果向州县官汇报,这方面的史料在清代巴县档案中比比皆是。如乾隆年间如有百姓告状,知县往往将其批与“约保邻证查理复”[58](P305)。史料也证明,在关于这些“一田二主”纠纷的解决机制上,如果不涉及人命,农民们常常求助于基层组织中的里老或保甲来调解。例如:“乾隆三年(1738年),广西武宣县佃农韦扶穷和皮主罗扶元因田皮权纠纷在田间争闹,罗要拉韦去告官,韦的叔子走来,劝不要去告官,有话到村中去说。于是他们到村中投知村老理论。”[59](P490)
为什么基层官府会将土地交易管理这部分权力下放给乡村基层组织?其一,基层政府的某些职权下放给民间是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政府以及法律的运行模式密切相关的。“由于帝国的巨大扩展以及相对人口规模来说官员的数量较少,中国行政在一般统治者的治下既不精细也不集权。中央机构的指令均被下属机构拿来便宜行事,而不是当做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在这种环境下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官员必须重视宗族长老和职业行会体现出来的传统主义的抵制,只有设法与这些势力达成谅解才有可能履行公务职责。”[60](P1192)明清时期由于基层政府的人力与财力严重不足,国家对基层乡里社会的管理和调整一直处于典型的粗放式状态,主要关注钱粮赋税的征收和严重危害统治根基的刑事案件,而对户婚田土斗殴等纠纷,大多交给基层乡里处断。其二,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府很重视民间基层组织职能的发挥,宗族势力一直在政治上发挥着作用,在民事与轻微刑事案件中充当着调解人的角色,这样既能收到较好的治理效果又减轻了基层官府的压力。“他们和官府相互补充,包括解决民事争端和维持社会治安、逮捕和惩办罪犯、发放灾荒救济和进行其他福利活动、发展教育事业和监督科举考试机构、建造和维护工程,以及批准和管理某些半职业人员和商人。”[61](P395)甚至在明太祖的《教民榜文》中明确规定有些民间纠纷必须先经过“里甲老人的理断”,即“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62](P639)。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基层官府的诉讼压力。其三,就明清时期官吏的考课制度而言,词讼的多寡是考核州县官政绩的重要标准,如果将案件批付民间调处,既可以销案,显示自己任内结案率很高,又可以收到相对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政和人平的评价。[63](P564)
四、结语
“一田二主”在明清时期各级官府的默认、禁止、支持的纠葛中反复着、继续着,它从未得到法典的明确认可,但是在明清民间的经济生活中却一直生机勃勃地存在着。田皮、田骨以分离的状态交易是明清时期土地流转活跃的需要,在基层官府的授权下,从田皮交易契约的订立到有纠纷时的解决,大多都有乡村组织的管理参与,以乡村民间习惯法独有的方式实现着田皮交易的自力救济功能。正如奥地利法律社会学家欧根·埃利希指出的那样,法律概念的本质要素并非在于其必须由国家加以创制,而是平常的活生生的法律规范着人群的生活。[64](P25、127、183)所以我们可以说,“一田二主”在明清时期一直以“活生生的法律”形式存在着,基层民间习惯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家高层从中央到省级的多次禁令。这也说明中国法律具有极强的灵活变通性,基于不同的问题考量,国家正式法律规定与非正式民间习惯法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效果的差异极其明显。
[1] 洪迈著,何卓校注:《夷坚志·乙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9][13][30][32]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36] 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樊纲:《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载《二十一世纪》,1994(4)。
[6][64] 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7] 《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新刊天下民家便用万锦全书,第1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 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0] 江太新:《明清时期土地所有制萌生及其对地权的分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11]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2] 仁井田升:《明清时代的一田二主习惯及其成立》,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20][21][22][38][4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五),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5] 汤相、莫亢纂修:《龙岩县志(卷之上)》,民物志第二·土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明嘉靖间刻本二册,缩微号DJ0798。
[16] 陶煦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一,上海,上海书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成都,巴蜀书社,2013。
[17] 黄永纶修,杨锡龄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18] 福建省南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平县志(上)》,卷五·田赋志第八,福州,福建省南平市志编纂委员会,1985。
[19] 《题为广东惠来县民尤绍相喝阻毁田放枪伤毙温广珍案依律斩监候等请旨事》,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2-01-07-06070-010。
[23] 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6][33][39][46] 梅利莎·麦柯丽:《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7]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九·户律·田宅,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8][41][52]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五·户律·田宅,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9] 史尚宽:《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1]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34] 安涛:《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5][45]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福建省例》,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九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
[37] 薛允升著,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律存疑点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40] 黄厚本等撰,崔廷镛、龚宝琦修:《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10·光绪金山县志,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
[43][44][5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北京,中华书局,1982。
[47]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8] 保成六法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六法全书·民法》,台北,保成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2。
[49] 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50]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
[51] 蒲坚:《中国古代法制丛钞》,第四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53] 郭建:《獬豸的投影——中国的法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54]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5] 范忠信主编:《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6] 何乔远编撰,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第1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57] 李文藻等撰,宫懋让等修:《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乾隆诸城县志,第38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刻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8]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60]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1]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
[62] 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洪武法律典籍,第一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63]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八条察吏·牧令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
(责任编辑张静)
Onthe“FarmingLand(LandRentTenure)SaleContract”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
CHAI Rong
(Law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transaction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land trading style.And yet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adopted vast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uch a transac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 transaction con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its legal relationship of“a piece of land having two owners”and conclude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tatut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transaction all over the time,bu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hanges their attitude from acquiesce to prohibit for the sake of tax and social stability .Meanwhile,“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transaction is quite popular,supported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privately.The local governments accomplish the goal of supervision to the“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transaction by way of authorizing to the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 transaction of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utes and the customary law,which more often than not requires the statutes to give way to customary law,and this is one of the crucial reasons why“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transaction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ownership of land;“One Piece of Land Having Two Owners”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中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法律机制研究”(NCET-12-063);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法律问题研究”(2012WZD12)
柴荣: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