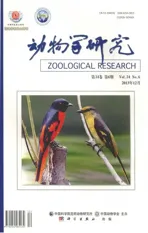扁颅蝠(Tylonycteris pachypus)和褐扁颅蝠(T. robustula)理毛行为比较及其与体表寄生虫的关系
2013-12-17张礼标张光良唐占辉洪体玉
张礼标,张光良,唐占辉,洪体玉
1.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广州 510260;
2. 东北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吉林省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 130024
体表寄生虫通常降低宿主存活和生殖成功的适合度,这些适合度代价反过来促进了宿主对体表寄生虫的行为防御进化(Hart, 1992)。回避和清除是动物减少体表寄生虫的两种行为策略。宿主可以通过选择生活在不适合寄生虫生活的生境来回避寄生虫,许多研究都证明动物可以通过生境选择来防御寄生虫感染(Hart, 1992, 1997; Reckardt &Kerth, 2007)。特定生境对动物产生的生活利益和代价会影响其行为特征,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在寄生虫较少的生境中的动物用于理毛的时间相对较少(Mooring & Samuel, 1998; Mooring et al, 2000;ter Hofstede & Fenton, 2005)。理毛行为是另一个防御体表寄生虫的行为策略,通过清除能有效地减少寄主的寄生虫负荷量。以往有研究表明,理毛行为的增加与体表寄生虫的增加步伐一致,即体表寄生虫增加伴随理毛行为的增加(Clayton et al, 1999;Eckstein & Hart, 2000)。虽然理毛行为能有效控制体表寄生虫负荷量,但也是一种高代价的行为:包括水分散失、降低警惕性、脱毛、能量消耗等(Giorgi et al, 2001; Mooring & Hart, 1995; Mooring &Samuel, 1999; Ritter & Epstein, 1974)。因此,理想的理毛水平(包括频率和时长)应该是理毛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体表寄生虫的负面代价或至少二者达到一个平衡。
在蝙蝠理毛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理毛行为存在种间差异,推测是由于寄生虫负荷量不同引起的;但在种内理毛行为和寄生虫负荷数量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结论,有学者认为高寄生虫负荷量增加理毛行为,寄生虫负荷量的增加显著影响宿主理毛行为的频次、持续时间及能量投入(Giorgi et al, 2001);也有学者发现蝙蝠是否携带寄生虫对理毛行为的时长、频率没有影响(ter Hofstede & Fenton, 2005)。
扁颅蝠(Tylonycteris pachypus)和褐扁颅蝠(T.robustula)为同域分布的姊妹种,主要栖息在村庄周围竹林的竹筒内,雄性倾向于独居,而雌性喜群居且通常为一雄多雌;两种蝙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轮流使用相同的栖息竹筒(Zhang et al, 2004),但是其各自的体表寄生虫不同(Tian et al, 2009),寄生虫表现出对各自宿主的专一性(Zhang et al, 2010;Zhang et al, 2013)。扁颅蝠与褐扁颅蝠的体表寄生虫负荷量是否有差异,它们各自的理毛行为又是否不同,寄生虫负荷量与理毛行为之间是否有关系?本研究通过实时监控录像,观察分析两种扁颅蝠的理毛行为,进而分析理毛行为的种间差异,以及体表寄生虫负荷量对其理毛行为的影响,试图探讨这两种扁颅蝠理毛行为的调控机制。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实验于2010年8月—10月进行,研究地点位于广西龙州县(区域自然地理概括见文献Zhang et al, 2013),扁颅蝠和褐扁颅蝠均栖息于村庄周围竹林的竹筒内,白天捕捉蝙蝠后按栖息群分装于布袋内,带回临时实验室进行理毛行为观察。对捕捉到的蝙蝠记录物种和性别,选择雌性个体(扁颅蝠21只,褐扁颅蝠 15只)进行实验,测量体重和前臂长,计数体表寄生虫数量(即为该个体的寄生虫负荷量)。扁颅蝠体表寄生虫为拟雷氏巨刺螨(Macronyssus pararadovskyi),褐扁颅蝠体表寄生虫为雷氏巨刺螨(M. radovskyi,Domrow, 1963)(Tian et al, 2009)。螨类主要寄生在蝙蝠的翼膜上,特别是腹部靠近体侧的位置,极少寄生在身体的毛发等其它部位;计数寄生虫时,对蝙蝠全身进行排查,统计所有的体表寄生虫。用体表寄生虫数量除以该蝙蝠体重做为该个体的单位体重寄生虫负荷量。
从野外采回两根分别栖宿过扁颅蝠和褐扁颅蝠的竹子,将小型红外视频监控摄像头放入竹筒底部,并调节好成像距离以保证观察时能清晰看到蝙蝠的行为。将进行实验观察的个体放入对应的竹筒(扁颅蝠放入栖息过扁颅蝠的竹筒,褐扁颅蝠放入栖息过褐扁颅蝠的竹筒),封上竹筒裂缝进出口防止蝙蝠逃出竹筒(预留一些缝隙保证空气流通)。红外视频监控摄像头连接到 Sony DV机上记录蝙蝠的理毛行为。预实验时发现两种扁颅蝠只有在傍晚18:00—19:00时段理毛行为比较频繁,其它时间段相对比较安静。因此我们只观察记录实验个体在18:00—19:00时段的理毛行为。记录的理毛行为参数包括理毛方式和时长(一次理毛行为回合的持续时间)。将蝙蝠整个躯体分为左翼、右翼、尾膜、胸腹、后背、头部等6个部分;理毛方式分为舔拭(licking,即蝙蝠使用舌部、吻部对身体其他部位的舔拭行为)和抓挠(scratching,即蝙蝠使用拇指或者后足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梳理行为)两种;一次理毛行为回合定义为采用一种理毛方式对同一个躯体部位连续理毛的过程,如果对同一部位的同种理毛方式间歇时间超过3 sec则记为另一次理毛行为(Mooring et al,2006; ter Hofstede & Fenton, 2005)。扁颅蝠和褐扁颅蝠的舔拭行为主要是用舌头清理其自身体表,通常是翼膜、尾膜及后足,偶尔针对拇指区域;抓挠行为主要是用后足爪似梳子快速重复地清理皮毛区域。为尽量避免其它因素对理毛行为的影响,参与理毛行为观察的蝙蝠个体在体型数据测量及放入竹筒的过程中,实验操作人员戴一次性的塑料手套;且这些个体都在下午17:00以前放入竹筒,使其有一段适应时间;并于18:00—19:00进行理毛行为取样,每只个体的理毛行为取样时间为1 h。
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独立样本t-test分析两种蝙蝠单位体重寄生虫负荷量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以及种内两种理毛行为之间的频次和时间的差异、种间理毛行为频次和时间的差异;使用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寄生虫负荷量与理毛行为频次、时间之间的相关性。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mean±SD)表示,显著性水平设为α=0.05。
本研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所有蝙蝠在完成行为观察后在原捕捉地释放;整体实验方案获得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 结 果
扁颅蝠和褐扁颅蝠的理毛行为均包括舔拭和抓挠行为。种内不同理毛行为对比发现,扁颅蝠和褐扁颅蝠舔拭行为的频次均比抓挠行为的要高(Tp:t=10.1, df=20, P<0.001; Tr: t=3.2, df=14, P<0.01,respectively),每次舔拭行为的持续时间也均比抓挠行为的要长(Tp: t=11.0, df=20, P<0.001; Tr: t=11.7,df=14, P<0.001)(图 1)。

图 1 扁颅蝠与褐扁颅蝠两种理毛行为的平均时长(a)及其平均频次(b)Figure 1 Durations (a) and frequencies (b) of licking (blank bars) and scratching (grey bars) of Tylonycteris pachypus and T. robustula
种间理毛行为对比发现,扁颅蝠舔拭行为的频次比褐扁颅蝠高(t=5.3, df=35, P<0.001),但抓挠行为的频次比后者低(t=3.8, df=35, P<0.05);扁颅蝠与褐扁颅蝠的舔拭行为和抓挠行为的持续时间差异均不显著(t=0.7, df=35, P>0.05; t=1.3, df=35,P>0.05, respectively)(图 1)。
扁颅蝠单位体重体表寄生虫负荷量(1.2±0.7只/g, n=21;范围 0~11只)比褐扁颅蝠(0.5±0.3只/g, n=15:范围0~4只)高,差异显著(t = 6.9,df=35, P<0.01)。两种蝙蝠体表寄生虫负荷量与理毛行为的总时长(Pearson correlation: Tp: r=0.23,P>0.05; Tr: r=0.18, P>0.05)和总频次(Tp: r=0.21,P>0.05; Tr: r=0.15, P>0.05)均没有相关性。
3 讨 论
包括翼手目在内的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许多体表寄生虫的天然宿主。体表寄生虫通常对宿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理毛行为是减少寄生虫感染较为有效的防御策略之一。由于不同动物类群携带不同密度的寄生虫,所以理毛行为有可能表现出种间差异。本文研究表明,扁颅蝠比褐扁颅蝠携带更多体表寄生革螨类,前者理毛行为(舔拭)的频次更高。
舔拭和抓挠是蝙蝠最主要的两种理毛行为,抓挠是对有皮毛覆盖区域的梳理,舔拭是对翼膜和尾膜区域的清理行为,这种差异是由寄生虫在蝙蝠体表寄生的位置决定的。蝠蝇类主要寄生在皮毛覆盖区域,而革螨类主要寄生在翼膜和尾膜区域,抓挠行为主要是针对蝠蝇类,而舔拭主要是针对革螨类的理毛行为(ter Hofstede et al,2004)。扁颅蝠和褐扁颅蝠体表都只有革螨类而没有蝠蝇类寄生虫,本文研究结果证实,它们投入到两种理毛行为方式上的时间和频次均呈现差异,舔拭是它们防御革螨类的主要理毛行为。但是,这两种蝙蝠虽没有携带蝠蝇类寄生虫,也呈现出一定频率与时长的抓挠理毛行为,且存在种间差异,这可能说明理毛行为不仅仅是针对体表寄生虫的一种行为反应。
关于动物理毛行为的生理学机制主要有两种:中枢调节理论(Colbern & Gispen, 1988; Fentress,1988; Spruijt et al, 1992)和外部刺激调节理论(Riek,1962; Willadsen, 1980; Wikel, 1984)。本文研究的扁颅蝠和褐扁颅蝠种内不同个体的体表寄生虫负荷存在变化,但是其理毛行为没有表现出种内的个体差异,即在种内水平看,寄生虫负荷量对其宿主理毛行为没有影响,说明这两种扁颅蝠理毛行为可能受到中枢调节。对新热带地区蝙蝠的研究也表明,体表寄生虫的叮咬并不能引起宿主皮肤的疼痛反应(Fritz, 1983; Overal, 1980);ter Hofstede & Fenton(2005)发现,鼩形长舌叶鼻蝠(Glossophaga soricina)与黄肩蝠(Sturnira lilium)无论个体是否携带寄生虫(最大寄生虫负荷分别为3和5),种内不同个体都表现出相近的理毛频次与持续时间。但是,Giorgi et al(2001)对携带不同寄生虫负荷水平(无寄生虫、20只、40只3个梯度)大鼠耳蝠(Myotis myotis)理毛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寄生虫负荷量显著影响宿主的理毛时间和能量的投入,且两者呈正相关;另外一些学者也发现寄生虫负荷量与理毛行为存在正相关性(Møller, 1991; Mooring,1995)。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可能与研究对象本身及其携带寄生虫的种类、数量的多少等有关。携带较大数量寄生虫时,寄生虫数量剧烈变化可能显著影响宿主的理毛行为,可能表现为外部刺激调控机制;而较少数量的寄生虫对宿主理毛行为产生的影响有限,理毛行为主要受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从而表现为中枢调控机制。
不同动物理毛行为调节机制的差异,可能与理毛行为的启动机制有关,即理毛行为不是单一调节机制控制的结果,它既受寄生虫负荷的影响(外部刺激理论),也受遗传调控(中枢调节理论)。在本文的实验观察中,扁颅蝠和褐扁颅蝠种间理毛行为存在差异。但是,两种蝙蝠种内携带寄生虫与否以及寄生虫负荷量对理毛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进一步说明理毛行为不仅仅是外部刺激引起,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性(或者遗传)的行为,受遗传与寄生虫负荷的共同作用。
致谢:感谢丽水学院韦力、研究生张伟和叶建平在野外调查中给予的帮助,感谢研究生杨剑、谭梁静、陈毅、刘奇、沈琪琦和赵娇在稿件修改中给予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