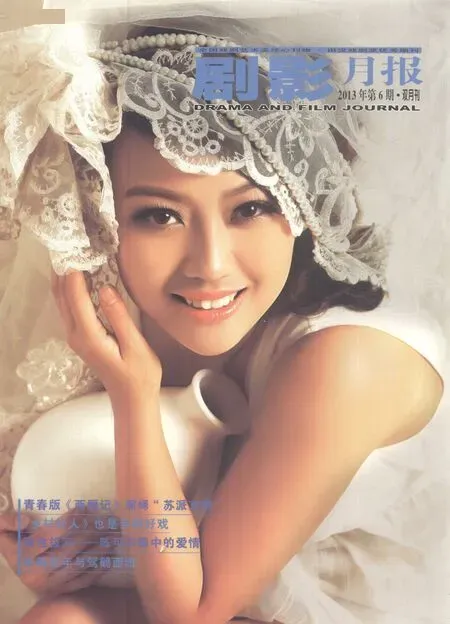柳琴戏的俗中之雅
2013-11-21李庆凯
■李庆凯
柳琴戏的俗中之雅
■李庆凯
柳琴戏原名拉魂腔,流传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受到黄淮文化的浸润和风土民情的濡染,在艺术特质中蕴涵着大俗大雅的风韵。大俗主要表现在故事俗——家长里短,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人物俗——凡夫俗子,呼之欲出;语言俗——本色机趣,生动活泼。俗中见雅,家长里短展现生活的真实与情趣,凡夫俗子给人们留下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生活化的语言更是让人难以忘怀。剧作家应在深入生活、感受时代律动中把握其俗与雅,创作出艺术精品。
柳琴戏 拉魂腔 民间戏剧 大俗大雅
当今世界的戏剧艺术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一些曾经热闹一时的剧种却衰亡了,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曲艺术却生生不息、跌宕起伏地发展、繁荣着。究其根本原因是她不脱离人民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时在艺术表现上总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清代中叶以后,也有一些戏曲走上一味嘲风弄月的道路上,遂为人民群众所抛弃而渐趋衰落;而那些充满俗味的来自民间的地方剧种,如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等花部乱弹,却受到观众欢迎而现勃勃生机。当时花雅之争的结果,也以花部崛起,雅部失败而告终。
匈牙利出生的著名艺术理论家豪萨,在其《艺术社会学》中将艺术分为三类,即文化精英的精英艺术;城市中受过一半教育的人们的通俗艺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的民间艺术。这种划分方法主要是着眼于接受者的文化层次。我国的戏剧专家借用豪萨的艺术分类法,将戏剧艺术划分为精英戏剧,通俗戏剧和民间戏剧三类。
通俗戏剧具体地表现为通俗性和地方性等等。构成通俗性和地方性的因素,包括选材、立意、表现方式和手段、语言习惯、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等,只有这些因素巧妙而有机地结合,才能产生一部好的地方戏剧。
如果把昆曲比做雍容华贵的牡丹,那么柳琴戏就是在农村田野中绽放的石榴花,就连过去老百姓给她起的名字拉魂腔也是土得掉渣、俗得到家。试问如果不土不俗能拉住乡亲们的魂吗?正如郭沫若先生说的“俗到家时自入神”。
柳琴戏的俗味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故事俗,家长里短,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第二是人物俗,凡夫俗子,呼之欲出;第三是语言俗,本色机趣,生动活泼。
第一是故事俗。郭沫若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吃故事”。我国元代中叶市民文艺出现,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拍案惊奇》为代表,把当时商业繁荣下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的社会众生态作了多方面的描绘。多种多样的人物故事、情节都被揭示展览出来,尽管充满了小市民某种庸俗、低级、肤浅,甚至无聊,尽管远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却是充满艺术生命活力的,是对封建专制的讥讽和鞭挞,所以话本能长期流传。话本也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
今天观众看戏,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故事情节。古人把戏曲称为传奇,“传奇传奇无奇不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戏剧的本性。清代戏剧家李渔说“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优秀的传统柳琴戏无不如此。如《孟姜女》、《张郎休丁香》、《白罗衫》、《泪洒相思地》、《四告》、《五女兴唐传》等等,都是引人入胜的好剧目。那种“淡化情节”、“淡化主题”、“淡化人物”的新潮戏剧往往不太受观众欢迎。现在许多剧作家编故事的本领大大减弱了,因此有识之士又在呼唤“故事”,要求“戏不惊人誓不休”。戏要有强烈的感情,一下子戳到观众的心窝子,叫人哭,叫人笑,叫人揪心,叫人看了上场想看下场。
实践证明,令观众百看不厌的戏剧总是有一个好故事。如《白罗衫》,《灵堂花烛》、《状元打更》、《小燕和大燕》、《梁红玉醉审皇案》、《三赐御匾》、《龙泉夜雨》、《解忧公主》等,无不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状元打更》写忘恩负义抛妻弃子的状元沈文素在妻子刘婵金帐下当了运粮官,因为任务没完成被妻子打了四十军棍,赐更锣一面,令箭插背,罚他打更。当然最后承认错误,夫妻重归于好。把一个文状元弄去打更,必然笑话百出,引人入胜,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梁红玉醉审皇案》讲一个领兵元帅击鼓战金山的巾帼英雄,如何当了“青天大人”的故事。她审问皇家御案,把太后、皇帝、正宫娘娘都当成了被告,为受冤屈的西宫娘娘平反昭雪,最后查出害死太子的真凶竟然是大补的药物人参与鹿茸。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情节跌宕之中常常出现陡转,所以演出时很受观众欢迎。上海唱片社灌制唱片录制盒带后,销售到海内外。所以,我们说“俗”中有好故事,“俗”到尽头成大雅。
第二是人物俗。写凡夫俗子,活灵活现,戏剧中的人物不是“高大全”式的,不是神,而是可以平视的“凡人、俗人”,是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使观众感到亲切可爱。这些人物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是群众化的。即使是表现帝王将相的故事,也是以下层民众的视角来想象加以艺术化的。那神圣的金銮殿在农民眼中和庄稼大院差不多。皇帝老儿“吃的是玉米,喝的是香茶”。正如林彪折戟沉沙时,一位老乡纳闷说:“林彪一家子都是非农业,天天早上吃烧饼夹油条,为什么还要叛国投敌呢?”《王华买爹》中,王华登基后依然是农民的思想和做派,《打金枝》郭子仪和唐王处理小夫妻纠纷就和平民百姓、儿女亲家一样。《梁红玉醉审皇案》中,皇后可以去找梁红玉送礼、走后门,以便能打赢官司。在《戚姬怨》中,第二场“刘邦登基”中来自睢宁农村的戚夫人去寻找刘邦时,不满刘邦的讲排场,借用睢景臣《高祖还乡》的意境唱出了“你得天下摆的什么谱?这里外都显得财大气粗,多好的绸缎胡糟蹋,弄成旗子迎风舞。还有这红漆叉、银铮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头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大晴天还打一把黄油伞,莫非你出门还怕那太阳毒?”每演到此处,观众总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当戚夫人在皇宫中思念家乡梦幻中唱出“又闻野花香,又听百鸟喧,又采幽谷草,又戏水潺潺,又吃家乡饭,满口香又甜。香椿调豆腐,盐豆炒鸡蛋,凉拌金针菜,糖醋泡苔干,家乡水,家乡山,怎不叫人忘忧烦,家乡情,家乡恋,欢欢乐乐长寿百年。”这段唱词配上睢宁民间小调,唱得委婉动人,趣味无穷,真是大俗中见大雅。
第三是语言俗。本色机趣,生动活泼。戏剧是在舞台上演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你总不能让观众带一本辞典,一边听一边查吧!因为戏剧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反复阅读,仔细品位。曹禺先生说:“我们写的东西,文学上要注意,一方面要通俗,一方面要有味道,有诗意,含蓄无穷。”高尔基说:“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十分朴素的,因为朴素就是美。”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贵浅显”,要求台词一定要通俗易懂,明白如话,而不可“艰深隐晦”,好的戏剧创作能将街谈巷议的大众口语、俗语进行提炼加工,从而创造出通俗优美、词浅意深、脍炙人口的戏剧语言,充分体现了现实生活中语言本身的鲜亮、活泼、生动且富有表现力,即所谓“能于浅处见真才”。
戏剧语言要俗中见雅,既要有俗味,还要有诗味。因为雅和俗既相互独立,又可相互转化,两者存在着某种互动互律的关系。如果把“雅”理解为高雅的品格,“俗”理解为亲切而会心的微笑,那么柳琴戏就是两者的统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情,一方情出一方戏,一方戏的精神就是一方人的魂。京剧姓京,秦腔姓秦,柳琴戏姓柳。所以有人说:“艺术越有地方性,就越有民族性,越有民族性,越有国际性。”戏剧要想“打出去”,先要“走下去”,得到这一地域观众的认可。一部戏剧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剧种特色,让观众欣赏艺术的美,道德的美,思想灵魂的美,风物色彩的美,从而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柳琴戏流行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受故黄河、大运河的滋润,有着独特的地域特点。柳琴戏的编剧们大多出身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艰苦的岁月磨砺他们的意志,丰富的生活给他们营养,他们与这片热土有割舍不断的亲情,所以他们作品中的乡土味特别浓烈。愿柳琴戏这朵地方戏奇葩,在大俗大雅中绽放出时代精神的绚烂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