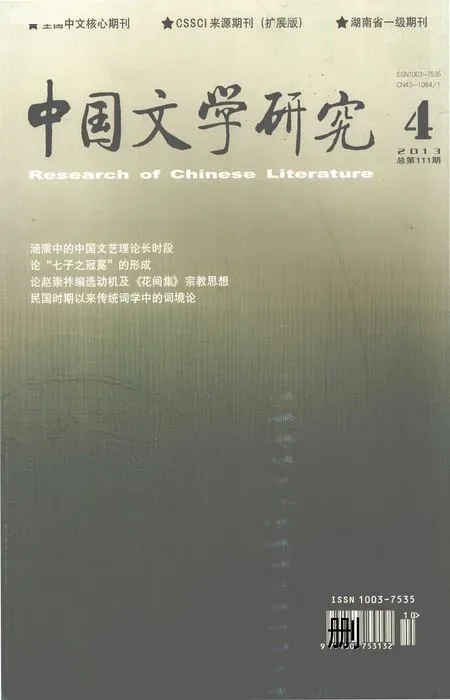艺术的魅力是细节: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细读分析
2013-11-15周茜
周 茜
(同济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092)
张爱玲的小说重视“传奇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传奇的情节最能俘获读者,细节则极易为读者所忽视。然而,缺乏细节描写的作品,终将失去生命力。耐人咀嚼的好小说,让人难以忘怀的往往是那旁支横逸、杂花生树的细枝末节。《半生缘》自有“传奇的情节”蛊惑人心,但是,如果不能细读品味作者丰富细腻的用笔用意,那么,这部张爱玲摒弃了艳异、冷酷又尖锐的招牌风格,而以平淡自然却极富意味的细节写实来铸就的苍凉而凄美的悲剧便会大大失去它的魅力。
一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几乎全是市井男女的婚恋生活、两性纠葛。那男女之间的无言细节、微妙感应、隐晦心理她一一绘来,舒卷自如,浑然天成。《半生缘》中三对男女的情感,就如同一轴工笔长卷画,细腻精微,不可不心明眼亮、细读深究。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小说在回忆中拉开序幕,那回忆中咨嗟感叹的语调以及渐渐弥漫开来的淡漠的悲哀,总是使读者在进入文本的第一时间便心生凄迷、期盼,于是“他和曼桢”有待追忆的情感故事诱惑着我们:
一进门的一张桌子,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
她是圆圆的脸,圆中见方——也不是方,只是有轮廓就是了。蓬松的头发,很随便地披在肩上。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
这是沈世钧第一次见顾曼桢时的印象。那是在一个小饭馆的初见,世钧和许叔惠出来吃午饭与曼桢相遇相识,平淡无奇。然而,描绘细节和心理的高手张爱玲怎么可能在这样的重场戏中没有妙笔呢,请看:
那饭馆里的餐具太脏,曼桢便替他们涮洗,替叔惠洗了之后:
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世钧忙欠身笑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等她洗好了,他伸手接过去,又说“谢谢”。曼桢始终低着眼皮,也不朝人看着,只是含着微笑。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依旧搁在桌上。搁下之后,忽然一个转念,桌上这样油腻腻的,这一搁下,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我这样子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人家给我洗筷子倒仿佛是多事了,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他这样一想,赶紧又把筷子拿起来,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而且很小心的把两只筷子头比齐了。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因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
小饭馆脏兮兮、油腻腻而曼桢早坐在那里不以为意,叔惠抱怨时就帮他们涮洗,可见曼桢的出身不会是娇贵的小姐。曼桢始终低眉含笑,又足见她面对陌生男子是有一份矜持的,或许还有一丝微妙之情。而世钧虽然对女人没什么分析力,但一见曼桢就笼统地觉得她很好,也许说不上一见钟情,但绝对是颇有好感的。至于他接筷、搁筷又拿起筷子的一系列动作和心理,则立刻见出世钧拘谨、憨厚又羞涩的性情,不仅如此,作者还一箭双雕地写出了男女初识又心生好感时那种常见的小心翼翼、拘束窘迫的情状。如此细腻、精湛地刻画男女之情,对于作者是手到擒来,对于读者则妙不可言。而男女主人公追忆前尘往事时,以下的几个重要场景一定是他们曾经单纯而美好的恋情中难以忘怀的,也是我们读者千万不可忽略的。
交往之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三人去郊外拍照,曼桢丢了手套。傍晚世钧去找寻手套——那昏黄雨夜让人感觉异样的环境,找到手套时那踌躇懊悔的心理,第二天归还时那冤屈的神气及曼桢拿到手套时的发怔发窘,不可不细读。实际上,关于小小手套的种种细节,表明他已经对曼桢情不自禁了,但在环境细节描写的阴郁冷寂中,在他心理状态的压抑两难中,使原本应该明朗、欢快的初恋笼罩着一层阴影。
确定恋情。在两人关系有了微妙进展的过程中,世钧回了一趟老家南京。在家那几日世钧心神不定,只求赶紧脱身,“仿佛他另外有一个约会似的”。时间空间的距离最能消磨感情同时也最能证明感情,仅仅几天的小别已让世钧感到他心心念念的都是曼桢,他再也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了。于是回到上海的早晨,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曼桢,“一看见她马上觉得心里敞亮起来了”,不过几天工夫,两人都有“一日三秋”之感。此时的世钧有满腹的心里话要说,满心的爱恋要表白,但却语无伦次,欲言又止。为此,张爱玲不惜笔墨用了十几页的工笔细描来写这天早上到夜晚,世钧为了这真情告白而受的煎熬:等待、猜测、兴奋、希望、失望、又希望……最后终于“他握住她的手”。
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跟别人的都不一样。
从前他跟她说过,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星期六这一天特别高兴,因为期待着星期日的到来。他没有知道他和她最快乐的一段光阴将在期望中度过,而他们的星期日永远没有天明。
如此纯情、真情,不掺杂任何物欲、情欲的恋爱是张爱玲小说中绝无仅有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琉璃瓦》等等,男女之间的恋爱好似斗心计耍心眼,进行一场不吃亏的财色交易,完全是“言情”中的无情,有笔尖扎进人性至深至痛处的尖锐和冷酷,却全然没有青春爱恋的诗意和真情。世钧和曼桢的恋情原本是那样的普通平常,自然的相识、正常的交往,正当的相爱,但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却是异乎寻常的,她总算让我们看到了人世间的希望和美好,尽管那是短暂的——自认为与人家的“闹恋爱”都不一样的世钧,没有逃脱与相爱的人失之交臂的命运,他一生都在期望和等待中……“他们的星期日永远没有天明”——在张氏忍不住所发的议论中已经暗示着没有光明的未来。
谈婚论嫁。真心相爱的男女因为爱而希望有个相依相伴的家庭,是极其自然的。有一天世钧照例去曼桢家里,两人围着火炉谈天,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没有鲜花、没有戒指、没有精心的求婚设计,就这样自然这样直白这样平常地求婚了,一切仿佛水到渠成。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婚恋生活都不过如此!这就是张爱玲的普通人的“传奇”。在她第一部小说集《传奇》上卷首题辞:“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可以说抒写普通人寻求一份安稳生活最终却不可得,是张爱玲艺术的根底。因此,我们以为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已然顺理成章,却不想被张爱玲无奈地打碎了。哪个女人不希望与自己深爱的人早日成婚?可是曼桢却因为自己家庭负担太重,不愿意把世钧拖进去而影响他的前途,所以她让世钧等一等,等她的家累减轻些。
相较于张爱玲笔下个个自私的男女而言,世钧和曼桢真的是异类。他们顾虑对方的感受,压抑自己的情感,他们不过是想给对方一个平实而安稳的生活而已,没有奢望、没有强求、没有争取。越是这样善良而美好的愿望,越是这种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最终都不能实现,就越是让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和凄凉。
紧接着求婚之后,这一回的末尾,作者以一个卖豆腐干的叫卖声细节作结:
他们在沉默中听见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逝了。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时间老人。
这是作者对岁月的感慨,颇具象征意味。也是世钧和曼桢对岁月的感慨吗?毕竟这一天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极其重要的一天——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毫无结果、悬而未决。可是岁月无情,“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逝了”,消逝的不光是这一天的光阴,消逝的其实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最明亮的一段光阴,在未来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过了。身处其间的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十四年后追忆往事的他们呢?
此外,还有许叔惠与石翠芝,顾曼璐与张豫瑾的一段情也是我们不能不体察的。
叔惠陪世钧回南京,在世钧家第一次见到翠芝:
那石翠芝额前打着很长的前刘海,直罩到眉毛上,脑后却蓬着一大把卷发。小小的窄条脸儿,眼泡微肿,不然是很秀丽的。体格倒很有健康美,胸部鼓蓬蓬的,看上去年纪倒大了几岁,足有二十来岁了。
叔惠聪明漂亮,善于言辞和交际,自信满满的他见到陌生女人并不局促,因此初见时他便多看了两眼的翠芝形象较为写实详细,与世钧看曼桢“笼统的好”自是不同。
翠芝是世钧嫂嫂的表妹,她与世钧从小认识,长大后两家大人有做亲的意思,但两人彼此都看不上对方,却不料翠芝和叔惠一见就相互吸引,心生好感。因为世钧讨厌翠芝,竟给了翠芝和叔惠单独游玄武湖和吃晚饭的机会。游湖划船时叔惠想道:
他也觉得像翠芝这样的千金小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当然交朋友是无所谓,可是内地的风气比较守旧,尤其是翠芝这样的小姐,恐怕是不交朋友则已,一做朋友,马上就要谈到婚姻,若是谈到婚姻的话,他这样一个穷小子,她家里固然是绝对不会答应,他却也不想高攀,因为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
由于翠芝是位富家小姐,叔惠不过是个城市平民,更何况翠芝是作为世钧的女朋友与叔惠相识的,所以叔惠有极大的心理障碍。张氏此处的心理细述,见出叔惠对翠芝感情的复杂微妙。
叔惠回南京后翠芝先后给他写过二次信,虽然叔惠常常想起她,但却顾虑重重,都没有什么表示,后来得知翠芝已经与一鹏订婚后内心却非常难过,当晚便在家里借酒浇愁。
叔惠表面上看起来随和热情、开朗外向,骨子里却有一颗人穷志不短的骄傲之心。他对翠芝的确是有爱慕之情的,但每每面对翠芝的情意,他总是有着种种现实的考虑和顾忌,以理性压抑情感,做冷处理。
总之,叔惠与翠芝彼此有情却无缘,他们游离于一种若即若离、隐隐约约、终未有一语道破却又挥之不去的“地下情”中。
再看顾曼璐与张豫瑾。曼璐是曼桢的姐姐,请看她的出场:
她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
曼璐和曼桢是家里的老大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小弟弟,在她们少女时代父亲就去世了,于是中学未毕业的曼璐只好出来做了舞女,挣钱养活一家老小。出场时的曼璐已经不再年轻,沦为了一个二路交际花,作者用了一大段文字从妆扮、声音、举止、姿态等方面为我们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个过气舞女的形象。
其实为了全家而牺牲自己的曼璐是令人同情的,她也曾经青春美丽过,那时她老家的亲戚张太太就看上了她,让自己的儿子张豫瑾跟她定了婚,男女双方也都十分愿意,还常常见面约会。后来她做了舞女就主动解除了婚约。如今她找了个已婚的投机商人祝鸿才,做了他不合法的姨太太。
无论是曼桢与世钧的真情,还是翠芝与叔惠的隐情,抑或是曼璐与豫瑾的绝情,无一不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
张爱玲写情得心应手、体察入微。毕竟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中外古今都述之不尽,咏之不绝,读者似乎亦见惯不惊。而张爱玲写恨、写人性、写扭曲则是她的“绝活”,那些微妙隐秘难言的“内心曲折”被她剖示得炉火纯青,往往令人惊叹不已,又惊诧莫名。
前六回中爱情的自然平顺终究随风而逝,此后便是暗潮涌动、波诡云谲,几位主要人物都各怀难以启齿的绵绵长恨。
曼璐的幽恨。曼璐嫁给祝鸿才,原本打定主意跟定他了,只想做个平平常常的家庭主妇,过一份哪怕是粗茶淡饭的安稳日子,但那个“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的鸿才是个吃喝嫖赌的混混,竟然发了财,整日不着家,年大色衰的曼璐则落下一身病,不能生育,备受奚落冷落。
女人结婚嫁人求的就是一份安稳保障,即便是孤傲卓绝的张爱玲在与胡兰成结婚时,双方在一纸婚书上所写不也是“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吗。后来,风流成性的胡兰成移情别恋,张爱玲的责问竟也是:“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安稳”不可得,天才独立的张爱玲便毅然与丈夫绝交绝情。而曼璐那个时代平凡又渺小的女性又能怎样呢?卑微不幸的曼璐只能在不安稳中自寻“安稳”了。
一天曼璐又生病了,曼桢前去探看,早就垂涎曼桢美貌的鸿才特意回了家,对曼桢大献殷勤。当晚鸿才竟向曼璐表示,如果他有了曼桢就听曼璐的话,不出去鬼混。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鸿才竟然打起妻妹的主意,曼璐自然不依不饶与他大闹了一场。两个月以后,一次曼璐回娘家,向母亲哭诉鸿才的不是,顾太太给她支招,不过是老一套的“妈妈经”——要有一个自己的儿子,哪怕是借腹生子。当晚回家后:
曼璐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她追溯到鸿才对她的态度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一天,她妹妹到这里来探病……
她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她忽然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个孩子就好了。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还最好是她妹妹,一来是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
如此奇思怪想!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详尽铺陈了曼璐设计陷害亲妹妹的心理轨迹。这一丧心病狂之念让曼璐自己都觉得“真恨”、“非常恐怖”,更让读者感到惊悸痛恨,期望这只是曼璐的一时之想,却不想旧情人张豫瑾的出现让曼璐坚定了罪恶之念。
已经成为曼璐生活中前尘幻影的豫瑾,竟然从老家安徽六安来到了顾家。三十出头的豫瑾如今是县医院的院长,尚未娶亲。顾太太和顾老太太都觉得现在的豫瑾跟曼桢倒是理想的一对儿。豫瑾也确实喜欢上了曼桢,在他看来曼桢以一己之力支撑全家而没有怨意,真是坚强又充满了朝气,因此他向曼桢委婉地表达了他的心意。
豫瑾的到来让曼璐惊怔不已,母亲和祖母竟毫无顾忌地告诉她豫瑾对曼桢有意,她们也希望曼桢嫁给豫瑾,这更让曼璐又惊又气。豫瑾临走时,曼璐不顾一切要见他一面,相见时豫瑾的反应则是:
一抬头,却看见一个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的瘦削的妇人……豫瑾吃了一惊,然后他忽然发现,这女人就是曼璐——他又吃了一惊。他简直说不出话来,望着她,一颗心直往下沉。
她今天穿这件紫色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偶然的。从前她有件深紫色的绸旗袍,他很喜欢她那件衣裳……豫瑾有一个时期写信给她,就称她为“紫衣的姊姊”。
作者别有用心地让曼璐穿上“紫色”,她内心多么渴望唤回些许“紫衣姊姊”的温情回忆啊,可是豫瑾却说:
我现在的脾气也跟从前两样了,也不只是年纪的关系,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笑。
从前的事被豫瑾一句“非常幼稚可笑”一笔勾销,全然否定。这样的打击对曼璐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她惨淡人生中仅存的那么一点儿青春美好的初恋记忆被彻底粉碎了,她恨不得将身上那件紫衣撕成破条。
豫瑾匆匆道别而去,只留给曼璐无尽的眼泪和满腔的怨恨。她恨曼桢!“曼璐真恨她,恨她恨入骨髓”,她认为豫瑾如此轻慢自己而移情于妹妹,都是因为妹妹卖弄风情,她愤愤地想道:
我没有待错她呀,她这样恩将仇报。不想想从前,我都是为了谁,出卖了我的青春。
如果说曾经有过的借妹妹生子的怪念头还让曼璐感到恐怖、于心不忍,而现在曼桢“恩将仇报”,那么曼璐的心理恐怕就是: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于是在曼璐的精心策划下,曼桢被祝鸿才强暴,并被关了起来。当曼桢意识到是姐姐和姐夫合谋害了自己时“她实在恨极了,刷的一声打了曼璐一个耳刮子”。
刚才这一巴掌打下去,两个人同时都想起从前那一笔账,曼璐自己想想,觉得真冤,她又是气忿又是伤心,尤其觉得可恨的就是曼桢这样一副烈女面孔。她便冷笑了一声道:“哼,倒想不到,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撒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
此时此刻,本是同根生的姐妹各有各的辛酸凄惨,各有各的幽恨愤恨啊。曼璐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但作者还是对她存有悲悯之心的。“我写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是的,只有哀矜。毕竟普通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都是弱小无力、微不足道的,他们不是强者、不是英雄,他们只能屈辱苟活,自我挣扎却无奈无望。
曼桢的遗恨。如果说曼桢悲剧的直接责任人是曼璐、鸿才,那么世钧和她自身的性格弱点则是造成悲剧的内在因素,由此铸成了他们人生中永久的遗恨。
此前曼桢、世钧的情路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们含蓄压抑、秘而不宣的性格和感情表达方式实际上已暗藏着信任危机,而第三者豫瑾的到来使双方的感情开始出现隔阂,由此引起了一场误会。后来曼桢向家人作了解释,消除了误会,两人和好如初,世钧再次提出结婚一事,曼桢仍然说再等两年,虽然随后她的心里终于有点动摇起来,想先结了婚再说,可是就在当晚世钧因为父亲病重,马上要回南京。“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两人都感到一种凄凉的况味”,于此,作者对夜的寒冷空寂进行了环境细节的描写,加重了凄凉的意味,因篇幅所限,此不赘引。最后“她站在街灯底下望着他远去”,作者越是写他们的难分难舍,就越是让人心生不祥之感。果然,回家后的世钧替父亲打理事务、生意,渐渐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倚重他,母亲依赖他,劝他辞掉上海的工作。经过考虑,世钧未跟曼桢商量就辞职了。就这样没有沟通、没有商议,这件对双方都非同小可的大事就仓促而定了。
曼桢、世钧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都爱着对方,可是他们的性格里都有着隐忍不发、委曲求全、沟通不良的一面,这不能不说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父亲常常是缺席的,要么是去世,要么就是无行为能力者。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无父,《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丈夫二爷残疾卧床。而《半生缘》中曼桢和世钧的家庭也都是“父亲缺位”(世钧的父亲一直住在姨太太家)的,缺乏男主人的家庭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世钧胆怯懦弱顺从,曼桢保守戒备顾虑,无疑都是成长环境给他们性格投下的浓重阴影。所以,即使曼桢和世钧是真心相爱的,但他们又都有着保留、不坦白。
辞职后的世钧很快回到了南京,他写信让曼桢和叔惠去南京。没想到世钧的父亲见了曼桢觉得眼熟,原来他年轻时在上海风流过,认识曼璐。世钧只是向家里说曼桢是他的同事,他父亲则很鄙夷:“就算她现在是个女职员吧,从前也还不知干过什么——这种人家出身的人,除非长得真丑,长大了总是吃这碗饭的。”随后他母亲又是对他一番提醒叮嘱。家人的态度对世钧无疑是沉重的一击。
外在的压力——来自父母的、社会的、世俗的……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象一张无形的网无法挣脱,使人渐渐丧失自我。尽管世钧一再地说他不介意曼璐身份,但一旦面对压力,他终究还是只能以社会大众的“他者”眼光来看待此事,以致于他对曼桢说“我就根本否认你有姐姐”,曼桢当然无法接受,最后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世钧屈服于压力,是软弱的,我们对此抱有理解之同情,因为作者向来肯定既非“英雄”也非“完人”的“软弱的凡人”,“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道出了她的创作心声。
就在闹矛盾的那晚,却发生了曼桢被强暴被关闭一幕。顾太太得知后,“急得眼睛都直了”,但在曼璐的一番巧言开导下也无可奈何,最终同意了曼璐让她们都搬到苏州的安排,以避免世钧来找寻。顾太太终于做了暴发户女婿女儿的帮凶!母爱、亲情,这些历来被赞颂的伦常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遭到了颠覆。疯狂的曹七巧把报复发泄到自己的儿女身上(《金锁记》);离了婚的白流苏回住娘家,受哥嫂欺负,向母亲悲啼求助,却发现是一个错误(《倾城之恋》);女儿川嫦生命垂危,川嫦的母亲不愿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为女儿治病(《花凋》)……天下竟有这样的母亲!张爱玲的描写让我们感到震惊绝望。其实这何尝不是她本人生命历程中缺亲少爱带来的心灵创伤之投影——母亲多数时候都仅仅是张爱玲生活中一个美丽的幻影,父亲则差点把她打死并监禁。曼桢被关的描写与张爱玲被监禁的场景何其相似。
此后世钧两次去到祝公馆想见曼桢皆被拒绝。这期间又碰巧听说安徽六安的张医生来上海结婚,于是他相信曼桢嫁了豫瑾,离开了上海。他彻底绝望了。
几个月之后春天来了,与世隔绝的曼桢发现自己有孕了,她的窗外:
春天,虹桥路紫荆花也开花了,紫郁郁的开了一树的小红花。有一只鸟立在曼桢的窗台上跳跳纵纵,房间里面寂静得异样,它以为房间里没有人,竟飞进来了,扑喇扑喇乱飞乱撞,曼桢似乎对它也不怎样注意。
这样的环境细节描写让人欲哭无泪。《半生缘》中的景物环境多半都是阴郁荒寒、灰暗多雨的,而此处的景象则是那样的鲜活,充满生机。春天越是美好,小鸟越是自由欢快,就越发反衬出曼桢被隔绝的悲哀与麻木。
她现在倒是从来不哭了,除了有时候,她想起将来有一天跟世钧见面,要把她的遭遇一一告诉他听,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好像已经面对面在那儿对他说着,她立刻两行眼泪挂下来了。
世钧绝望了,曼桢也绝望了。曼桢与世钧的情缘就此划上了句号。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翠芝的憾恨。叔惠陪曼桢去南京,在世钧家再次见到了翠芝。此时的翠芝是在未婚夫一鹏的陪伴下前来的,他们一行共六人到清凉山玩,后来竟不见了叔惠和翠芝,直到天都黑了两人才回,“翠芝一直没开口,只是露出很愉快的样子。叔惠也好像特别高兴似的。”就在当晚,一鹏送翠芝回家时,翠芝与他解除了婚约。
后来世钧告诉叔惠,翠芝毁了婚,叔惠震了一震,回想到清凉山上的一幕:
天色苍苍的,风很紧,爬到山顶上,他们坐在那里谈了半天。说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话,但是大家心里或者都有这样一个感想,想不到今日之下,还能够见这一面。所以都舍不得说走,一直到天快黑了才下山去。可见翠芝的任性退婚还是因为叔惠的缘故,但翠芝写信向叔惠提起她解除婚约一事,而他一直没有回信,翠芝为此郁郁寡欢,恨不能走出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到大上海去求学做事,她甚至都出逃过一次,但被家人严防死守,不能如愿,最终委屈地嫁给了世钧。
婚礼当天,“叔惠远远的在灯下望着她,好久不见了,快一年了吧,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向她道贺因为她和一鹏订了婚,现在倒又向她道贺了”。自己钟情的女子却一直都是别人的女人!叔惠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向新人敬酒时,大家起哄要他们当众搀一搀手,两新人却僵在那里:
还是叔惠在旁边替他们解围,他硬把翠芝的手一拉,笑道:“来来来,世钧,手伸出来,快。”但是翠芝这时候忽然抬起头来,向叔惠呆呆的望着。叔惠一定是喝醉了,他也不知怎么的,尽拉着她的手不放。世钧心里想,翠芝一定生气了,她脸上颜色很不对,简直惨白,她简直好像要哭出来了。
酒席散后叔惠便悄悄离去,不久去了美国。新婚之夜翠芝后悔莫及,又想到了退婚,但,木已成舟、憾恨终生。
三
张爱玲一方面津津乐道于世俗人生,把其中的凡人小事、情天恨海迂回细腻地盘写而来,有着现时现刻的具体可感、“庸俗”可观;另一方面则哀哀戚戚于人生无可奈何的虚无,以苍凉荒凉的手势打造“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的哀情。如果想在张氏作品中找寻花好月圆、诗情画意的欢喜浪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美好童话,无异于痴人说梦。沙特曾指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叫人不舒服的”,张爱玲的《半生缘》如此,张爱玲的小说都是如此。
曼桢不明不白地从世钧的生活中消失了,自卑的世钧就糊里糊涂地自认了曼桢与豫瑾的婚事。“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那个春天,曼桢被关几个月后的春天,世钧已是心灰意冷,而他的父亲也在那年春天去世了。世钧处理完丧事、家事后,照例到亲戚家“谢孝”,翠芝家也去了一趟。翠芝向他问起曼桢,世钧感觉“好像已经事隔多年,渺茫得很了”,心里无限悲哀。而翠芝毁了婚,此后又没有叔惠的音讯,便一直郁郁不乐,消瘦沉静了许多。于是,这两个原本就被家人促成一对儿的男女,如今各怀伤痛之心,同病相怜,终于走到了一起。
世钧平常看小说,总觉得小说上的人物不论男婚女嫁,总是特别麻烦,其实结婚这桩事真是再便当也没有了,他现在发现。
是的,如果人生都是按照既定的路子、长辈的安排来走,便会省却许多麻烦。世钧和翠芝的婚事不就是走了一圈后回到原地吗?回到他们从小所生活的那个圈子,那里早已预设安排下了他们常规的人生。而世钧与曼桢的婚事特别麻烦,好事难成,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世钧的父亲认出了曼桢有个舞女姐姐,而这舞女姐姐又暗害了曼桢,然而真正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于他们的门第和性格,“门当户对”、“性格即命运”几成定律。因此,《半生缘》绝不仅仅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姐夫合谋暗害亲妹妹的“传奇”而已。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设想,如果曼璐没有变态的仇恨,如果世钧不辞职回南京,如果顾太太不对世钧隐瞒实情……又会怎样呢?即使这些假设都成立,世钧的父母也是绝不可能答应他娶曼桢的,父母不答应,顺从懦弱的世钧能不顾一切地反抗吗?世钧别无选择。
那个夜晚,那个本该是人生大喜事的“洞房花烛夜”,一对新人竟是各自后悔。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和她一样的茫茫无主。他觉得他们象两个闯了祸的小孩。
这才是世钧真正的悲哀——堂堂男子竟象小孩儿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常常要孤注一掷地抓住一种“依靠”,曹七巧是“金钱”、白流苏是“婚姻”、顾曼璐是“儿子”。但“男性则连‘依靠’也没有,他们的自卑则体现为深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种种无形力量的驱使下做出违反自己意愿的事。”无依无靠、茫茫无主的世钧,总是被动、顺从的世钧只能如此。我们“哀其不幸”,却很难“怒其不争”,因为他毕竟是个好人,是个凡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曼璐的梦想——借妹妹替自己生儿子,终于实现了。而曼桢则因为难产才终于得以离开那魔宫似的禁闭屋。曾经在祝公馆、在医院,曼桢想到世钧:
她在苦痛中幸而有这样一个绝对可信赖的人,她可以放在脑子里常常去想想他,那是她唯一的安慰。于是逃出后的曼桢想方设法联系世钧,未果。后来从叔惠那里曼桢得知世钧和翠芝结婚了,叔惠对于这件事不愿多说,因为翠芝的缘故他自己也是满怀抑郁。
曼桢从叔惠家出来,只觉得天地变色,不敢相信还不到一年,世钧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不管别人对她怎样坏,就连他自己的姊姊,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的使她伤心。……那天晚上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但是人既然活着,也就这么一天天的活下去了。
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也会是最伤你的人。对于曼桢来说无情的姐姐、母亲早已不是她的亲人了,在那囚禁的日子里,唯一能够让她熬过漫长的痛苦,心存希望的人就是世钧了。可如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还有什么打击比这个更大呢?如果那晚曼桢在回家的路上因绝望而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是一般悲剧的惯例和高潮。可是张爱玲偏不这样写,她要“反高潮”。“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如《封锁》中,在“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时刻,两个陌生的男女竟相爱了,读者期待着进一步的情事展开,然而,“封锁”突然开放了,一切又跌回到“封锁”之前,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再如《倾城之恋》里,白流苏颇费周折都未能成为范柳原的“妻子”,又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似乎即将发生,突然,香港倾覆了,由此成全了她。而此处曼桢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那晚在外滩的桥头上想到“跳下去也不知是摔死还是淹死”,但是她终究熬了过来,依然活着——虽然活着仅仅是活着罢了。
后来曼璐去世了,鸿才也开始走霉运,独自拖着原配妻子的女儿和曼桢生的儿子。因为儿子发高烧,曼桢前去照看,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曼桢为了孩子竟然决定要嫁给鸿才了。
她现在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确切的信念,觉得无一不是渺茫的。倒是她的孩子是唯一的真实的东西。尤其是这次她是在生死关头把他抢回来的,她不能再扔下不管了。
她自己是无足重轻的,随便怎样处置她自己好像都没有多大关系,譬如她已经死了。
哀莫大于心死!以前那个充满朝气、勇挑重担、沉毅又娴静的曼桢的确已经死了,现在的她只有麻木、呆滞地活着,在不能忍受中忍受,只有唯一的愿望——为了孩子。
人生真是无可奈何、如诉如泣。诚如作者所言她小说的人物只有“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如果说曼璐对妹妹的谋害让人不可思议、惊恐扼腕,那么现在曼桢这样的选择更是出乎意表。她的活着已是一次高潮的跌落,而她嫁鸿才的决定则是一次更大的突兀的跌落,让人措手不及。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则让我们更加“觉得无限的惨伤”,生何异于死!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鸿才发了战争财。豫瑾则在战争中失踪,不知去向。
战争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通常只是作为背景来虚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半生缘》也不例外,战争只是一笔带过,作者着力表现的仍然是那兵荒马乱的时代里的平凡夫妻,因此,十五回里张爱玲花了不少琐细的笔墨来叙写曼桢与鸿才的婚后生活。那是怎样的生活可想而知,曼桢“只觉得她现在过的这种日子是对不起她自己”,“这是她自己掘的活埋的坑”。
傅雷先生以笔名“迅雨”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有曰:
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而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赚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
虽然曼桢生不如死般的生活并非“情欲主宰”下的选择,但这的确是她“自己掘的活埋的坑”。如果说以前的苦难是他人的罪过,而今的不幸则是她自己难辞其咎的,更加令人痛心不已。这的确是最大的悲剧,作者如此写来使得作品愈显高明深刻、彻骨寒心。
当初她想着她牺牲她自己,本来是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象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好在有一天曼桢终于醒悟,下定决心离婚。
战后,去美国已十年的叔惠回国。
此时的世钧已在上海某洋行工程部任职,一家人迁到了上海,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翠芝有时候跟他生起气来总是说:“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起来会结婚的!”这样的抱怨何尝不是世钧的心声。那时他因为曼桢的事非常痛苦,父亲也刚去世,为了排遣,其实当时很可能跟有所接触的几个女孩子中的任何一位结婚的。为了排遣也好,为了逃避也罢,照世钧的性格,他都只可能被家庭、被命运牵着鼻子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成家生子,过一种安稳却同床异梦的生活。人生的悲哀无奈正是在于多少人寻求“安稳”却不可得,又有多少人有了“安稳”却虽生犹死。对于翠芝来说,尽管朋友说她有福气,丈夫老实可靠,不玩不交际,对女人也没有兴趣,但是,世钧从来不曾喜欢过她,他们彼此格格不入、漠不关心,因此她心中的不满失望、委屈哀伤也是可以想见的,而这次与叔惠的久别重逢自然让她兴奋不已。
叔惠、世钧、翠芝三个人终于坐在了一起,“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这不能不令世钧想起曼桢,“他们好像永远是三个人在一起,他和叔惠,另外还有一个女性。”世钧当初就是通过叔惠认识曼桢的,现在再次通过叔惠得知了曼桢的电话号码,但他顾虑重重,好不容易找个机会鼓起勇气打过去以后又懊悔地把电话挂了。后来他去叔惠家,叔惠不在,倒意外地:
一眼看见里面还有个女客,这种厢房特别狭长,光线奇暗,又还没到上灯时分,先没看出来是曼桢,就已经听见轰的一声,是几丈外另一个躯壳里的血潮澎湃,仿佛有一种音波扑到人身上来,也不知道还是他自己本能的激动。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到真发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
辞别叔惠家,他们象当年初识一样走进了路边的饭馆。
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
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一样。
往事不堪回首,是悲哀。重逢,不过是伤痛的揭秘,也是悲哀。而未来,则是永别,“就跟死了一样”,无可挽回,更是悲哀。大团圆的皆大欢喜从来就不是张爱玲的本色,所以《十八春》那迎合时代及市民情趣的牵强结局,终于在《半生缘》中得以改正。死亡的悲哀其实早已注定:
在《半生缘》中,死亡的形式是结婚,结婚是“想象中的死亡”。在肉体的衰败之前,死亡穿着结婚的礼服找到芸芸众生的男男女女。……世钧在与曼桢结不了今生因缘之后,便与他原本不喜欢的石翠芝结了婚,过着貌合神离、虽生犹死的生活。而曼桢更不堪,嫁给原来奸淫她的祝鸿才。历尽沧桑的曼桢了解他们各自走过死亡的幽谷,所以她在与世钧久别重逢时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的确。他们这壁厢生离死别,叔惠与翠芝也难分难舍。
叔惠回国,为了好好在家款待他,翠芝兴兴头头地忙里忙外,因为买酒,翠芝“不禁想到叔惠那天喝得酩酊大醉,在喜筵上拉着她的手的情景。这时候想起来,于伤心之外又有点回肠荡气。她总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他那时候出国也是为了受了刺激,为了她的缘故。”
不管叔惠出国是为了什么缘故,也不论叔惠在国外结婚又离婚,但对于叔惠来说“不过生平也还是对翠芝最有知己之感,也憧憬得最久。”
然而,不管憧憬得多么长久,叔惠与翠芝十年前失之交臂,十年后也同样无可挽回。作者最后以无声的景致、象征性的细节来暗示双方“过门不入”的错失,“虚度此生”的悲哀:
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
〔1〕胡兰成.今生今世〔A〕.张爱玲,胡兰成.张爱胡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2〕来凤仪.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3〕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A〕.子通,亦青.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4〕讯雨.论张爱玲的小说〔A〕.子通、亦青.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5〕胡锦媛.母亲,你在何方?——被虐狂、女性主体与阅读〔A〕.杨泽.张爱玲阅读〔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