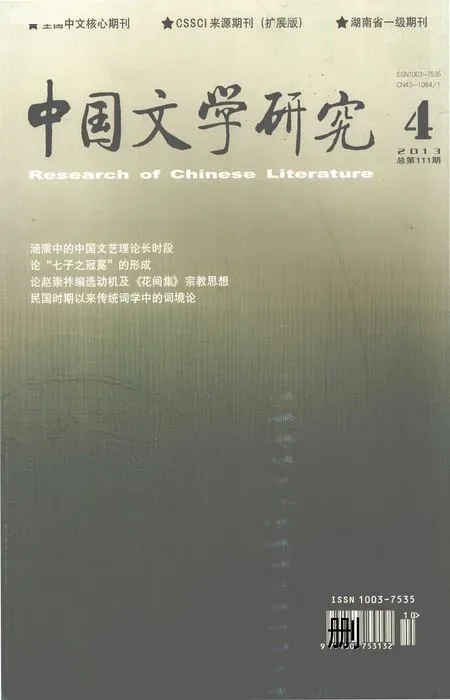从张贤亮、阎连科、王小波的创作来看政治视域的身体叙事
2013-11-15胡艳
胡 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 湖南 娄底 417000)
身体与政治是天然的密友。权力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尽全力拉拢身体,加强对身体的管理和控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如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视为自己社会理论核心的福柯发现的一样:各种权力技术都围绕着身体而竞相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对其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试探着它,挑逗着它,控制着它,生产着它,正是在对身体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权力的控制,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以及对它们的安排与征服。卷入政治领域中的身体,“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对于现代中国尤其如此,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政治与身体如此亲密地接触着。正是通过对身体的恐吓、限制,政治实现了对它的管辖,当身体试图对政治稍有叛逆时,政治便以摧残甚至消灭它的方式来达到对身体驯服的目的。借助这种方式,政治得以大行其道。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政治对身体的控制更是达到耸人听闻的地步,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便是权力对身体通过极端手段控制的典型例子。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指出,社会主义的革命伦理(他又称之为“人民伦理”)是敌视个体身体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表达——“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剥夺了个体身体的价值。“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然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每个个体都有基于自己身体的自然感觉、价值偏好,却掩盖在“完美理想”的革命伦理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个体的身体在政治书写的文本中基本上是缺席的。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两具被符号化了的公共躯体:革命者(包括革命群众等一切正面形象)的身体――反革命者(包括压迫者等一切反面形象)的身体。这两具身体以固定的外形特征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正面形象必定是一脸正气,体格健壮;而反面形象则必然是獐目鼠脑,行动猥琐。在身体的欲望方面,正面人物几乎没有七情六欲,他们拥有极为强大的意志使自己不受身体欲望的左右,将自己作为绝对服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工具;相应地,反面人物则往往屈从于低级的身体感觉,他们的生活作风腐败,往往荒淫无耻。这种类型化、脸谱化的创作,自然无法表现出有着不同身体感觉的个体。无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遮住了他们真实的身影。
在当代中国政治事件中,文革无疑是一个影响力最为巨大的负面坐标。它不单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更是一个危及整个民族和灵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它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作家叙事视野中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许多作家都曾以文革时代的政治氛围、文化环境作为创作的基本背景或重要参照体系。对文革反思程度的深浅也是衡量一个作家精神空间是否博大的重要标尺之一。以叙述文革、反思文革为核心的“伤痕——反思”文学,尽管在其出现初期获得了眩目的辉煌,却因其陷入单一的政治视角的叙事陷阱,极大地削弱了反思的力度,至今为后人所诟病。以张贤亮、阎连科、王小波为代表的作家努力突破纯粹的政治视角,将视线投向与政治纠结的身体,将叙事重心从“政治中的人”转向“人在政治中”,在特定的处境中关注人的可能性。身体与政治的结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历史的反思,完成了对政治的深刻书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这一系列创作中较为典型的作品。
先来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篇小说在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史上只具有过渡性意义。作为自然存在的欲望个体,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章永璘自然也希望能与异性融合,实现自我的完整。弗洛姆指出:“人,不论其性别如何,只有在把自身中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相融合的前提下方可实现人格的整合。个人身上的两极性乃是一切创造性的根基”。然而,这种基于人性的正常需求,却因他身处一个极端荒谬的时代而难以实现。由于长期的思想改造和禁欲主义的盛行,一方面,章永璘少有机会接触女性,客观上使他处于被“阉割”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政治对人身的绝对控制下,作为一个被改造者,章永璘深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丧失了作为独立主体存在的权力,这种危机使他在主观上也自觉地“阉割”了自己。由外而内的控制,使章永璘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主宰自己身体的力量。因此,当他与黄香久结合后,便发现自己已然阳痿。这种由政治造成的生理缺陷,章永璘无力解决,直至他在抗洪中成为人民的英雄,重新获得一种社会命名,才使他摆脱了历史的缺席感和无名状态,恢复了对黄香久的欲望支配权,实现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身体是嵌入政治中的,它受到政治的迫害,被迫抑制了自己的欲望,当政治稍稍给予它一点喘息的空间时(在文中表现为政治以国家的名义对章永璘进行肯定),它又恢复了自己部分的本能,政治身份的变化使章永璘的个体生命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变化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对身体的控制与异化。
尽管小说对身体的正常生理诉求予以肯定和关注,在八十年启蒙话语盛行的大背景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依然有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语),对身体欲望抱着欲迎还拒的犹疑态度。章永璘不仅仅是作为受压抑的身体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潜在的人文主义者。对他而言,释放被压抑的欲望是一种自然需求,但这种释放却必须与自我超越相联系才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身体的解放依然从属于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与现代性话语,对它的思考与描写无法逾越新时期的“文化思考”“思想解放运动”,它依然承载着沉重的政治与精神负担。就章永璘而言,身体的复活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这便导致章永璘的身体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分裂:一方面,他享受着与黄香久的欢爱,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忧国忧民的精神负担。他无法调和这两者的尖锐冲突: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身体的绝对价值,它拒绝给属己的身体欲求留下丝毫空间。刘小枫曾指出:“启蒙意识形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性。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是最高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进步。它的道德律令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身体”。在这种启蒙意识的指引下,章永璘极力抵制代表肉欲与日常生活的身体性的黄香久,将其视为限制自己自由的约束和羁绊,认为“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的发展,我要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因此将黄香久所代表的日常生活贬为“令人窒息的”、“令人消沉的”。人民伦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取消了个体日常生存的合理性。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小说中,张贤亮大胆地采用“政治——性”的视角,揭露文革极左政治权力对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的生命阉割,给当时“伤痕——反思”文学贡献了新质,但并没有使政治记忆的书写获得质的飞跃。章永璘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对于政治的荒谬,他有一定的认识,因此他能勇于面对自己的欲望,可他却在另一种更为宏大、更为隐秘的意识形态前又迷失了自我,自觉放弃了身体的独立存在,将身体置于国家、民族之下,重新撕裂了身体的灵肉统一性,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历史主体,完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神话。既定政治视角的拘囿,使张贤亮超越政治的努力无法最终实现。
这种局限,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却得到了极大突破。它主要表现在作者以彻底的批判意识,呈现了“身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荒唐遭遇,并深刻揭示了荒谬时代导致的人性扭曲和道德伦理的虚伪性与蒙昧状态。《黄金时代》中,王小波用幽默、玩世不恭的语言构建了一个荒诞世界。荒诞浸淫在整个生存环境中,谣言、污蔑、暴力、混乱、政治话语、荒唐逻辑无处不在,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因为王二“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队长便认定是他打瞎了自家的母狗,从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王二与三闷儿因小事吵架,却被上纲上线为知青殴打贫下中农;由于陈清扬结了婚后居然“脸不黑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违背了众人对已婚妇女的既定设想,所以大家认定她是破鞋;王二到缅甸边境赶街被人保组说成越境勾结敌对势力。如此种种,无所谓事实,无所谓理由,无所谓对错,人们以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这个荒谬的世界,甚至连原本确定无疑的人的存在也成为一个不确定的事件。上山养伤的王二究竟存不存在成了一个可疑的“问题”。知青们希望找到王二,证明“大家在此地受到很坏的待遇,经常被打晕”;领导认定王二不存在,因为可以“说明此地没有一个知青被打晕”。
处在极权社会,任何“出格”的外在行为都可能导致危险,王二无法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实际存在,他惟有借助自己的身体。于是,他选择了在性行为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在性欲与生存之间,有一种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生存在性欲中扩散,那么反过来性欲也在生存中扩散”。在一定意义上,生存与性欲是等同的,性欲的实现证实了现实的生存。因此,当别人在讨论他是否存在的时候,他在作爱;而在做爱的时候,是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否存在的。“当我的价值被他人的欲望承认的时候,他人不再是我希望被他承认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受到迷惑、失去自由的人”,王二以这种方式征服了陈清扬,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在相互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中,性欲成为一种更深刻地确认身体存在的方式,个体的身体与存在都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王二的纵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价值。
王小波说:“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在作者看来,人的性欲是存在之本身,毋须大惊小怪。只有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成为主题。对王小波而言,身体/性爱是对抗荒谬时代最有力的武器。通过这个“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与其说王小波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的非常性爱,不如说他所关注的是权力的轮盘——它的永恒运转和它的无所不在。在王小波的笔下,性爱场景,性爱关系,并非一个反叛的空间或个人的隐私空间,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萎缩的权力格局,一种有效的权力实践。权力一方面以“不正当关系”千方百计限制身体/性,设置了许多条条框框约束它,同时又以“今后主要的任务就是交代男女关系问题”喋喋不休地挑逗性话语、性行动。这种病态的权力管理使得原本健康正常的人性活动畸形发展。王二与陈清扬轰轰烈烈的男欢女爱,以变态的方式还原了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就如李银河所评价的,对他们来说,“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他对变态的性的叙述中,性有时是隐喻的,影射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在这一点它进入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域”。
王二与陈清扬的出现,意味着文革叙事中增添了两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语)。他们拥有不随大流的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一方面,他们是周围环境中带破坏性的、变形的、瓦解性的、压制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实际上反抗着既定的生存境遇,把个人的生活建立在另一种道德基础上。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什么也不能证明”的时代,他们以荒诞对荒诞、非理性对非理性,凭借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与庄严,使自己由被动的历史捉弄者获得了主体的提升,在与荒谬逻辑的对抗中,最终确立了自我。
文革作为作家重要的精神矿藏,以受害者身份记叙文革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通过受害者身体的压抑来反衬时代的冷酷无情也成为顺理成章的创作潮流。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却摆脱了道德审判的惯例,反其道而行之,以造反派的身份再现了历史的荒诞不经,以身体/性爱狂欢书写了政治的疯狂,从而颠覆了一般人的审美惯性和思维惰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态度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政治事件。男主人公高爱国的政治身份是一名退伍还乡的造反派,作品摒弃了同类题材常用的谴责、批判、嘲讽、荒谬或忏悔的叙事伦理态度,而尽可能地保持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心态,塑造了一个至死依然豪情满怀无怨无悔的反革命形象。女主人公夏红梅则是一位患有“革命臆想症”的狂热崇拜者,是一位被革命权力异化的畸形儿。对她而言,革命与爱情是等同的,革命就意味着光荣的献身。在失控的、狂颠的革命叙事中,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另一面。其次,阎连科竭力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回复当时的历史情境。文中大量出现的“三句半”、语录歌、对联、演讲、报告、样板戏、“两报一刊社论”、快板书、流行的标语口号等等,不啻建立了一座小型的“文革语言”博物馆。昔日的话语蜂拥而至,让人应接不暇,喘不过气。狂欢突进的语言不仅是构建作品的物质材料,也是情节本身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人物行动的必要工具。这种夸张、疯狂的文革语言既激发了高爱军和夏红梅革命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是他们情欲的催化剂和性爱的伴奏音乐。这种革命式的语言不仅把持了话语霸权,而且也以无形的力量操纵了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控制了他们的灵魂。它在文中形成了某种隐喻,提供了我们时代曾经历过的一种情绪和症侯:抒情的激情取代了日常的生活用语,暗示着一个民族走向思维的疯狂与失控。
在特定人物设置的基础上,贯穿在高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行动中的是身体和性爱的渴望与纠缠。故事开始于一次意乱情迷的相遇,英俊的革命军人令夏红梅心生爱慕,激昂的革命歌曲撩拨着夏红梅情欲的神经,使她情不自禁地解开上衣纽扣,几近失控。而夏红梅的美丽性感也激发了高爱国的革命斗志。此后,情欲的高涨与革命热情如胶似漆地交织在一起,高爱国在权欲满足和失落中寻求性的慰安,夏红梅则在情欲的高潮中满足了对革命和权力的向往与膜拜之情。他们的情爱,在革命火焰的炙烤下,燃烧得蓬蓬勃勃,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革命越发展,他们的身体交流就越狂热。高爱军看到夏红梅的裸体时,他表达的是革命的决心:“为了你,我死了都要把程岗的革命搞起来,都要把程岗的革命闹成功”,而高红梅表达的同样是与革命相关的爱情誓言:“高爱国,只要你把程岗的运动搞起来,把革命闹起来,我夏红梅为你死了,为了革命死了我都不后悔”。
在《坚硬如水》中,爱情的誓言交织着革命的誓言,性不是革命的附属和衍生物,而是与革命共时的、一体的和互为因果的。性的压抑诱发了革命,革命又使性成为现实。高爱国与夏红梅无法餍足的情欲,导致了政治上的疯狂;而疯狂的权力欲,又更大的刺激了他们的情欲的放荡。他们一方面疯狂地闹革命,夺权,抄家,打人,逼得高爱国的妻子上吊,岳父发疯,亲手杀死夏红梅的丈夫,炸毁程寺和“二程故里”牌坊,将程天民葬身于寺庙的碎砖破瓦下。与此构成同声部的是他们疯狂进行着的情爱。墓穴、麦秸垛、地道甚至刑场处处回响着他们海枯石烂的誓言,留下了他们无数次灵肉交融的颠峰体验。
王蒙在《狂欢的季节》中曾这样形容革命:“革命就是狂欢,串联就是旅游,批斗就是摇滚乐、霹雳舞”。这种对文革的智慧洞察化成了阎连科作品中的感性显现。阎连科用纵欲般的身体叙事替换了政治叙事,那着了魔的身体和陷入疯狂状态的政治思想如出一辙。它既是隐喻,又是颠覆。它暗示了正是在疯狂的红色恐怖年代极度的政治压制和性压抑下,才导致了夏红梅与高爱国的性欲狂欢。同时,失控的、狂飙突进般的性欲狂欢又强行穿越更为荒诞、恐怖的历史情境,从而完成了对非理性的社会革命的一次独一无二的颠覆。在这种反差极大的叙事情境中,阎连科呈现了身体的压抑和狂欢,凸现了被特定境遇激发的人性恶魔因子,完成了对革命神话的解构。
波德里亚指出:“在意识形态的历史里,那些与身体相关的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对以灵魂或其他某种非物质原则为中心的唯灵论、清教、说教类型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批判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处于这样极权和禁欲的时代,章永磷和黄香久的结合、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高爱国和夏红梅的狂欢,才显示了最强烈的政治颠覆意义。
〔1〕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弗洛姆,陈维岗译.爱的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此处借用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M〕.中国新诗集序跋选(一九一八—一九四九).陈绍伟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M〕.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
〔7〕王小波.黄金时代〔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8〕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王锋.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A〕.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0〕李银河.王小波笔下的性——常态与变态.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11〕阎连科.坚硬如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12〕王蒙.狂欢的季节〔J〕.当代,2002.
〔13〕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