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对张爱玲《半生缘》之电影改编
2014-07-20徐付美智
⊙徐付美智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70]
许鞍华对张爱玲《半生缘》之电影改编
⊙徐付美智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70]
1996 年许鞍华导演改编拍摄了张爱玲的同名长篇小说《半生缘》。影片对原著在情节上进行了大量的增删与改写。在拍摄上,影片运用了大量的红色构成画面,这些红色的运用有的起到遮掩和对比的作用,有的用来暗示情节的转折;同时,许鞍华导演也十分注重镜头的运用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作为一名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对《半生缘》的改编有她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她对影片原本政治意识的改编和对结局的女性化改写方面。
《半生缘》 红色 蒙太奇 香港 女性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长篇小说,1996 年许鞍华导演将其改编为电影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展现了曼桢、世钧等人的悲剧性人生,尤其是其中的爱情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契阔,而是像她与胡兰成的婚书上写的那样“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像许鞍华导演所理解的“我们现在这样处理是想符合曼桢当时的心理——她其实是不太想嫁世钧的,她自己亦有很多疑惑”①。这种淡淡写来、淡淡写去的表现手法,同样运用在了许鞍华导演改编的电影中。整部电影以灰色为基调,加入许多大红的元素,以缓慢的速度“哼唱”过来。
一、电影对原著的增删与改编
《半生缘》是一部长篇小说,把二十二万字的情节浓缩为两个小时的电影,势必要对原著进行大量的增删与情节的改编。
(一)曼桢与世钧
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场景是曼桢、世钧、叔惠三人去小树林拍照,在这个过程中曼桢丢了她的红绒线手套,这也是与世钧情感纠葛的开端。电影中三人两两合影,到曼桢与世钧合影时恰巧相机没有底片了,这也暗示着两人的感情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没有走在一起,小说中是没有这一情节的。电影中曼桢桌下压着的是三个人的合影,曼桢生病时她姐姐看到了说站在她右边那个还不错。影片的后面有一个镜头是世钧把剪掉了叔惠那一部分只剩他与曼桢的合影藏进了钱包,与影片前面相互呼应,这也是许鞍华导演的高明之处。小说中看到合影的是曼桢的母亲,桌下压着的是与叔惠的照片,并没有曼桢与世钧的合影。
小说中造成世钧与曼桢矛盾原因之一的豫瑾,在影片中与曼桢的感情发展也并非像小说中一样细腻。影片没有表现出小说中的豫瑾因为曼桢的热情、上进而对她产生好感。造成世钧与曼桢矛盾的另一个原因世钧的家庭在影片中也是略微概述。世钧父亲病重急需他赶回南京老家是通过世钧的口述表达出来的。世钧在家中与嫂子的矛盾、与姨太太的矛盾、与翠芝的矛盾的情节影片中都略去了,世钧父亲与其舅舅聊曼璐的情节也一并略去了。
多年后世钧与曼桢的碰面省去了小说中曼桢一次次的电话的情节。世钧读完曼桢当年写给他的信提到去叔惠家听他父母讲世钧的事后,决定去叔惠家,恰巧碰见了从叔惠家出来的曼桢,这是许鞍华导演的精彩之处。用一封信的前后穿插连结两人的感情线索,使得删减掉大量情节后的故事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二)曼璐的刻画
电影中增加了对曼璐的刻画,可是有一些增加的情节造成了电影的冗余,对曼璐在细节上的刻画也是不够的。比如祝鸿才在曼璐家翻旧照片把年轻时的曼璐认成了曼桢,这对曼璐造成了一种刺激,小说中的描述是“曼璐也不作声,依旧照着镜子涂口红,只是涂得特别慢。嘴唇张开来,呼吸的气喷在镜子上,时间久了,镜子上便起了一层雾。她不耐烦地用一排手指在上面一阵乱扫乱揩,然后又继续涂她的口红”,这是小说中的一个大特写,强烈地突显出曼璐心里或多或少的对曼桢年轻的嫉妒,对自己为家庭付出这么多年的内心的酸楚。但是电影中的这一画面是通过一个中景简单略过,而用增加其他情节的方式造成了影片的冗余。影片中增加了王老板有了新宠后曼璐去麻将场找王老板的情节和曼璐回忆豫瑾年轻时为她打架的情节。这两个小说中没有的情节集中在影片前半段突兀地出现,不但没有鲜明地突显人物性格,还造成了曼璐形象在影片中前紧后松的问题。
(三)叔惠与翠芝的感情线索
影片中叔惠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因为翠芝的鞋跟断了,世钧去翠芝家帮她取鞋,所以翠芝陪世钧划船游湖。小说中的情节相对较长。雨天三人去看电影,翠芝的鞋跟断了,世钧不甘愿地去给翠芝取鞋,落掉了半场电影,气得又买票重新看了一场。这些在影片中进行了改编,翠芝与世钧的关系也没有小说中那样恶劣。
影片中叔惠第二次去南京的时候是陪曼桢一起去见世钧父母的,但是影片并没有像小说中那样交代叔惠为什么要去,而是在曼桢决定去南京以后,镜头出现了叔惠,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这一次到南京听说了一鹏和翠芝订婚了,在大家一起爬山后的第二天,又取消了婚约。叔惠与翠芝的通信影片里没有交待,翠芝在叔惠回上海后一起吃饭流泪被世钧大嫂撞见也没有交待。信件在电影中是不好表现的,若是把电影中出现的每一封信都读出来会显得太嗦,除非是像张艺谋《归来》中陆焉识读信是故事的一个重要情节,否则难以表现出小说中每一封信的内容。
电影中的叔惠比小说中的要主动的多,比如在影片结尾在翠芝家叔惠把头帖了下翠芝的额头说:“我都是被你害的。”许鞍华导演这样的安排,包括结尾去掉原著中世钧在背后默默祝福豫瑾与曼桢,可能是想改编小说的结局,凑成叔惠与翠芝、世钧与曼桢的结合。
二、《半生缘》的拍摄手法
许鞍华导演的《半生缘》中包含了颜色的运用、镜头的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拍摄手法。
(一)红色的运用
很多导演在电影中都擅长用红色来发展情节或代表某种意义。如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辛德勒的名单》中全程黑白色,影片唯一彩色的地方就是那个穿了红色衣服的小女孩;许鞍华导演在《半生缘》中也大量地运用了红色。

曼桢的橘红色的毛衣、叔惠和曼桢他们去树林里照相时戴的红色围巾、曼璐去和王先生与祝鸿才打麻将时围的红披肩、世钧南京老家的一路红砖房子、世钧第一次去曼桢家里吃饭时曼桢妈穿的暗红的衣服、曼桢第一次去曼璐家时祝鸿才围的红围巾等等,这些都是许鞍华导演在红色上的大量运用。不仅仅是服饰上,灯光上也有很多红色的运用,如:世钧和曼桢刚刚牵手的时候,曼桢去给学生补课、世钧在楼下等她时,路边的灯光照在世钧脸上呈现的是红色。这与世钧终于牵了曼桢的手的心情是相映衬的。这部电影的灯光是暗暖色的,整部电影给人以灰蒙蒙的感觉。张爱玲的小说原著中对于服饰的描写大多是暗色调。许鞍华导演为避免整部电影因暗色给人以单调阴沉感,用红色造成视觉上的冲击。
翠芝的着装多是红色的。翠芝第一次出场是穿的红色呢子大衣,第二次出场虽穿的是黑大衣,但是一排扣子是红色的,翠芝家是红砖洋房,众人去爬山时翠芝穿的是红色的大衣,世钧与翠芝的婚礼上也布满了红色。而翠芝的红与她性格的闷是不相称的。她不是曼桢那种热情洋溢的性格,可在着装上却是最艳的一个。曼桢在生活上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她在衣着上却以灰暗为主。

曼璐每次在说谎时都习惯穿红色的衣服。曼璐骗曼桢说祝鸿才对他好,她不喜欢冰箱的颜色就送去换了,恰巧碰见祝鸿才回家骂曼璐“贱货,买个冰箱也要换来换去的”,这时候曼璐穿的是白面儿红领子红里子的睡衣。曼璐穿这个颜色的睡衣一是因为年龄大了,老王抛弃曼璐找了更年轻的舞女,曼璐用这种颜色的搭配来掩饰自己年龄上的心虚;二是想给曼桢一种她过的很好的感觉,来掩饰生活上的不尽如意。曼璐骗曼桢自己生病了的时候装出一副病态穿的是红色的丝绸睡衣。曼桢被祝鸿才强奸后,曼璐去楼上看曼桢穿的也是红色睡衣。曼桢逃离祝家后去了一所学校当老师,曼璐这次去学校找曼桢穿的是一身白色,而这是曼璐跟曼桢讲真话的一次。也许是由于舞女的身份,红色能够让曼璐在做不想做的事情时有一种心理安慰。
除了能用来掩饰,红色还能用来做对比。曼桢在逃出祝家后不久去叔惠家听说了世钧和翠芝结婚的消息,她备受打击而去影院看喜剧。两个女观众在后排穿的红色的衣服和荧幕里放映的喜剧电影与曼桢止不住的眼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红色不仅可以体现在服装、灯光、人物心理的掩饰与对比上,还能够表现在暗示情节的转折上。
世钧第一次回南京坐火车的时候,导演给了火车红色轮子的一个大特写镜头。这是世钧与曼桢感情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回南京以后,世钧和曼桢的感情间就加入了世钧家庭的因素,在这里开始了从感情最高点的下降趋势。之后发生世钧父亲病重辞去工作,曼桢觉得世钧向家庭妥协、世钧家里怀疑曼桢是舞女,曼桢退还给世钧戒指等一系列事情。红色的火车轮子象征着有一系列矛盾冲突激烈的事情的发生。另一次红色暗示的情节的转折体现在招弟的红衣上。曼桢本来已经逃出了祝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儿子病重,不得已她又回到了祝家。刚到祝家时看到的是穿着红色衣服的招弟。这一次的红色,是曼桢从自己新生活到回到祝家嫁给祝鸿才的转折。
(二)镜头的运用

影片的开始是一副空镜头,高高的烟筒冒着青烟,显得空旷肃静,这时出现画外音。曼桢的出现伴随着长镜头,曼桢在隧道与世钧擦肩而过时,镜头推到了世钧的背影。世钧的出现是在电车上,伴随着画外音。
片中特写的镜头不多,运用最多的镜头当属长镜头,开始曼桢三人到树林照相,世钧和叔惠在树林里打闹,这些都是通过长镜头加移的手法表现出来的。长镜头更能表现出故事的真实感,叙事性强,刻画出的人物更加深刻。当曼桢和曼璐在床上谈话时,没有用正反打来回的切换姐妹俩人的视角,而是用了长镜头,更加突显出了曼桢和曼璐之间存在的隐隐约约的矛盾。世钧和曼桢在街上牵手散步也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豫瑾将要离开上海,从曼桢家离开的前一天,曼璐回家了。她想告诉豫瑾不要再傻傻地苦等她了,却不知此时豫瑾已经爱上了曼桢。导演用了一个大大的长镜头表现二人,这样更能让人感受到曼璐对于少女时的怀念和豫瑾知晓了曼璐误会后的尴尬。

影片的主线镜头是手套,同样也是曼桢与世钧两人感情的线索。曼桢丢了手套,世钧冒雪为曼桢找手套。曼桢为世钧买手套,让豫瑾试戴,又让叔惠试戴,最后在找到手套时却因为两人吵架决心分手并未拿出,到结尾回放世钧是如何为曼桢找到的手套。整个影片都被手套这条主线所贯穿着。手套既是曼桢与世钧爱情的开始,又是他们爱情的结束,也是曼桢委婉拒绝豫瑾的理由。从相识到相知,相恋到相爱,手套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出现时都伴随着剧情的重大转折。
曼桢的红绒线手套既是红色的运用,又是许鞍华导演对张爱玲《半生缘》原著改变的关键所在。原著的结尾本是曼桢、世钧、翠芝三人去了东北为解放事业奋斗,后来世钧和翠芝遇到了豫瑾并告诉他曼桢已经离婚了。豫瑾去找了曼桢,世钧在背后默默地祝福他们。而许鞍华导演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结尾。她把世钧是如何为曼桢重返小树林寻找手套的回放放在了影片的结尾。去掉了原著中把曼桢与豫瑾凑到一起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安排也许更符合广大读者对曼桢与世钧爱情的期待。
(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
许鞍华导演在《半生缘》中擅长用门缝、窗子、栅栏等建筑意象来表现情节的发展、暗示人物的内心。这些意象象征着曼桢与世钧的感情状态。
曼桢与世钧相识后到饭店吃饭,许鞍华导演采用的镜头是从窗外隔着铁栅栏拍摄屋中的二人,这是一种蒙太奇的象征,象征着两人互有好感暗生情愫,隔着铁栅栏拍摄,象征着两人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被禁锢,也暗示着世钧和曼桢在此时交换内心的秘密。世钧送曼桢回家,镜头依然采用隔着铁门拍摄的手法,世钧望着曼桢的离去,被隔在铁门之外,象征着他无法完全走进曼桢的世界,曼桢这时还不愿把家里的情形让世钧看到。世钧第一次在曼桢家吃饭后,曼桢送世钧离开,这时采用远景的拍摄手法,镜头内除了两人,还有敞开了一半的大铁门,象征着曼桢的内心对世钧敞开了半扇门。世钧和曼桢从南京回到上海,在曼桢屋子里因为世钧家人介意曼璐是舞女的事情争吵,曼桢给世钧找为他买的手套,这时镜头透过铁栅栏似的壁橱拍摄曼桢,象征着两人的感情再次被禁锢,敞开的半扇门又重新闭合了。当世钧与曼桢多年后重逢时,他们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感情,表现得非常客气而且疏远,但当他们走进饭店的那刻起,两人紧紧拥抱,此时镜头依旧是隔着障碍物拍摄,但隔的不再是铁栅栏,而是透明的玻璃窗,玻璃完全占据了整个画面。如果说之前的铁栅栏象征两人的感情状况,那玻璃窗就象征着两人之间的感情只能透过玻璃观望,不再像能来回打开的铁门。两人在隔着玻璃窗的小空间里享受着,镜头从两人恬静的状态摇到了大厅当中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一静一动,一喜一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用人物自述交代小说中的人物心理与情节发展
小说可以用心理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可以用叙述的方法几句话交代完一段时间内的情节变化,而这些在电影中是无法用同样的方式呈现的。许鞍华导演在本片中采用了让曼桢与世钧交替自述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节的发展变化。
影片开始是以曼桢的视角自述与世钧的四次见面,曼桢关注到了世钧,而世钧没有在意曼桢。镜头转到世钧在公交车上坐下后世钧开始自述。第一次去曼桢家世钧自述三天没有见面,用叙述的方式表达心里对曼桢的思念。一次世钧送曼桢回家留在了巷子门口,曼桢进去后心里想的内容通过自述的方式表现出来:“世钧那么开心,就知道他是好介意姐姐的职业,否则他要送我回家都没说要进来坐,大概就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吧。”因为有了曼桢这样的自述,才能让人知道曼桢心里会因为世钧介意曼璐的职业而感到一丝难过,才能更好地解释曼璐与曼桢之间的矛盾。张爱玲的原著中交代了很多世钧南京老家的情况,这些在影片中以世钧从家回到上海以后的自述略过。在世钧的自述后曼桢自述了到南京见世钧父母一事。曼桢在医院生小孩求助金芳一事也以曼桢的自述一带而过。多年以后世钧自述还是不能忘了曼桢,接着转换到曼桢的视角自述。
三、香港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
港台导演翻拍张爱玲小说的很多,许鞍华导演在拍《半生缘》之前就拍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但汉章(台)导演在 1988 年拍摄了《怨女》、关锦鹏(港)1994年拍摄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李安(台)2007 年拍摄了《色·戒》。作为唯一的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在她的拍摄上具有其独特性。
(一)政治无意识
《半生缘》上映于 1997 年,拍摄在 1996 年,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大陆,香港人甚至现在的香港人对新中国的解放也是不甚了解的。《半生缘》由香港东方电影公司与天山电影制片厂合制,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且影片会在大陆和香港同时上映,在香港没有回归之时许鞍华采取中立态度,不表明任何政治立场,不讨好各方,也不激怒各方,避开矛盾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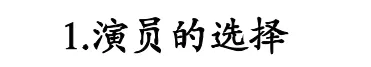
许鞍华在一次访谈中说:“考虑到之前所说的危险性,其实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用一些较年轻、有魅力的演员,便能够把上海拍的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模样,令它不至那么‘老套’。”②《半生缘》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知名演员,如黎明、吴倩莲、黄磊、葛优、梅艳芳、吴辰君、王志文等,年轻化是许鞍华导演的一个手段,但不可否认陆港演员的集聚是有意而为之。
角色的选取也考虑到了每个演员身上的角色特征。黄磊回忆说:“正如我可以扮演许叔惠,却演不了‘红高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生活中的‘许叔惠’,是复杂的人。以复杂的心态去面对周遭,只是那是不同内容但本质一样的复杂——就是无奈——或言是能做的远远不如想做的那么多。”③

影片中对叔惠改动最大的就是他的去向问题。原著中是叔惠受到翠芝的打击,思想上又有了一定的觉悟,决心去东北为解放事业奋斗。而在电影中叔惠变成了去美国。小说结尾处世钧想要逃离翠芝身边,同曼桢一起去东北考会计,在电影中也取消了这一情节。
影片拍摄于 1996 年,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大陆。许鞍华导演同张爱玲一样是一个政治意识不明显的人,或者说是避而不谈。若安排叔惠去了东北,或许1996 年的香港观众会不太愿意接受。
(二)港台导演的上海情结
上海这样一个最具特色的从历史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却又身姿袅袅的城市,在港台导演的眼中是极具魅力和神秘感的。上海的每一个巷子都有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张爱玲出生在 1920 年的上海公租界,1939 年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被伦敦大学录取,但因战事转入香港大学就读。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吸引着许许多多的港台导演。
影片《半生缘》中表现了许多老上海特质,比如夜晚路灯下的街道、翠芝家的洋房、曼桢家带铁门的巷子等等。和许多人印象中的纸醉金迷不同,许鞍华导演表现出来的正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隐隐啜泣。
(三)女性导演的特殊期望
《半生缘》有两个编剧,第一个编剧萧貌,因太过忠于原著,被许鞍华舍弃,最终她选用了对原著大幅删减的陈健忠编剧。
影片结尾是对原著动刀最大的地方。小说中世钧和翠芝、曼桢一起去了东北,世钧和翠芝遇到了豫瑾,并告诉他曼桢已经离婚了。豫瑾去找了曼桢,世钧在背后默默地祝福他们。也许是作为《半生缘》女性读者共有的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许鞍华导演对结尾进行了大手笔的改动。首先是删去了几人一同去东北的情节,让故事结束在上海。第二是影片中世钧与曼桢相见的时候,叔惠和翠芝在家中游走在偷情的边缘。而小说中的叔惠是更加怯懦的,从一开始就不敢面对与翠芝的感情到后来从东北回来后翠芝与他吃饭时哭泣,他便开始回避与翠芝的接触。小说中的世钧也是始终恪守着对家庭的责任,即便他嫂嫂和他说翠芝的小话,他也是十分信任翠芝的。
这些安排大概都是为了凑成原本的“有情人”,让因误会和差错分开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让本不该在一起的错误婚姻回归正轨。即使影片最后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还是给了人能够回去的遐想。
许鞍华在采访中说:“有一样东西要考虑的,便是在片中要放进多少时代背景,是否需要贴招纸表明那是战争的时期?是否需要有炸弹声?我觉得不需要。”④这也是许鞍华作为一个女性导演的特殊安排,无须过多表现战争,只需用一个个人物的命运去表现时代。
许鞍华导演本身就是一个张爱玲的书迷。她在日本生活期间就开始读张爱玲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到《半生缘》。纵观《半生缘》的拍摄,尽管有少许情节上的冗余,但从大部分改编、拍摄手法的运用等方面来看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是对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敬礼。
①②④ 黎肖娴:《半生缘的世界观 许鞍 华访谈 录》,《书 城》1998 年第 6 期,第 9 页,第 8 页,第 9 页。
③ 黄 磊 :《影 片 〈半生 缘〉 拍 摄 心得》,《新 世 纪 电影 表 演 论坛》(上),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 页。
[1] 名导许鞍华访谈:电影不是唯一表达方式[J].广州:南方周末,2002:10-24.
[2] 孙尉川.论 90 年代香港电影导演[J].当代电影,2002(2).
[3] 孙尉川.论许鞍华电影中的两性形象及其性别意识[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2).
[4] 周潞鹭.无法回避的“十四年”——试论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影视改编[J].名作欣赏,2009(3).
作 者:徐付美智,内蒙古大学 2011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