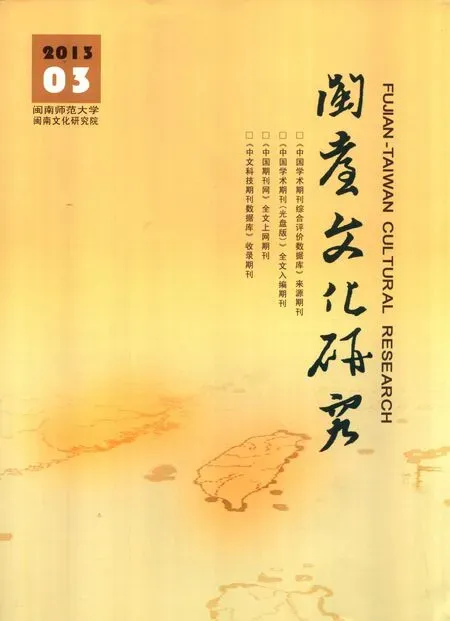从保生大帝及其庙宇传说看民间信仰的正统性
2013-11-14谢贵文
谢贵文
(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系,台湾 高雄)
一、前 言
“正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其形成与宗法制度有密切关系。宗法制乃一庞大复杂又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其规定社会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既为天下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诸侯及卿大夫亦依循此例。宗法制度作为一种统治制度,虽在西周之后逐步瓦解,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却随着宗法家族的存留而继续发挥作用,秦汉以后的王朝即利用此一制度及其意识来进行统治,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一套伦理政治学说,将“国”家族化,又把国家统治关系渗入“家”中,“家”与“国”紧密结合,家庭即国家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忠”、“孝”成为最重要的两大道德。
在此宗法制度的作用下,中国社会形成一种“正统”的观念,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代表国家的皇权乃天帝所授,是崇高神圣而不可侵犯,具有“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的权力,故凡国家或皇权认可者即是正统,反之则为异端,此即政治的正统性。其二,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其强调人在宗法关系中所应尽的伦理义务,而形成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符合儒家之伦理道德即是正统,反之则为离经叛道的异端,此即文化的正统性。其三,宗法制度强调家族的血缘关系,通过血缘来团结家族、区别人我关系,并以父系血缘的谱系决定
权力地位的高低,而有嫡长子为大宗,拥有继承权力之规定,故与我有血缘关系之嫡亲为正统,旁支、庶出则非正统,无血缘关系则为外来的异端,此即血缘的正统性。
民间信仰深植于中国下层社会,与广大庶民的生活紧密结合,被视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小传统文化,也成为后现代史学“由下而上”看历史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关民间信仰之政治与文化正统性的研究,美、日汉学界及中国史学界已有可观的成果,本文即拟在此研究基础上,以保生大帝及其庙宇的传说为材料,探讨民间信仰中的政治与文化正统性,并扩及至血缘正统性,期能扩展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并与国际后现代史学研究潮流相接轨。
保生大帝本名吴夲,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白礁乡人,生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三月十五日,卒于仁宗景佑三年(1036)五月二日,享年五十八岁。根据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进士杨志所作的青礁慈济宫碑文,首见对吴夲生前形象的描述,曰:“弱不好弄,不茹荤,长不娶,而以医活人”;而其医术尤获时人之推崇肯定,曰:“枕中肘后之方,未始不数数然也,所治之疾,不旋踵而去,远近以为神医”。吴夲死后,高超医术仍为后人传颂,甚至逐渐予以神化,曰:“既没之后,灵异益著,民有疮疡疾疢,不谒诸医,惟侯是求,撮盐盂水,横剑其前,焚香默祷,而沉疴已脱矣。乡之父老私谥为医灵真人,偶其像于龙湫庵。”
此一逐渐形成的保生大帝信仰,在地方士人的积极推动下,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分别在白礁、青礁正式兴建庙宇,并于乾道元年(1165)获宋孝宗赐庙额“慈济”,又于庆元元年(1195)敕封“忠显侯”、嘉定元年(1208)敕封“英惠侯”等爵号,纳入国家祭祀的体系。明、清时期,保生大帝虽未获王朝敕封,但在地方信徒对南宋封号的重温与新封号的伪造、士人对保生大帝形象的“儒化”及地方官府对其正统性的适度肯定下,保生大帝不仅逃过王朝打击淫祠的冲击,且获得进一步的传播与发展。迄今保生大帝已成为福建漳州、泉州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当地的同祀庙宇至少在两千座以上。而随着闽南地区的商人与移民,保生大帝信仰也传入台湾、香港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皆设有同祀宫庙,尤其台湾更高达三百座以上,已形成一个跨越闽、台两地,并扩及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广大信仰圈。
保生大帝信仰流传近千年,也累积不少的传说,大略可分为三部分:一为南宋时期杨志、庄夏分别为青礁、白礁慈济祖官所作的碑文,此为记载保生大帝信仰最早的文字,碑文中也留有多则传说,包括吴夲显灵治病、退贼、建庙,以至于“黄衣行符,景光照海;挽米舟而入境,凿旱井而得泉;秋涛啮庐,随祷而退”等。二为明、清时期记载在方志、文人作品与民间文本中的传说,如 “真人降生”、“泛槎昆仑”、“王母传法”、“神方活骨”、“江张从游”、“米舟济急”、“袪疠击魔”、“白礁飞升”、“揭榜医太后”、“露幡救驾”、“鄱阳助战”、“丝线诊脉”等。三为闽、台两地保生大帝庙宇所留传的传说,内容包括庙宇的香火缘起、建庙、神像及其神明治病、降雨、降妖、退敌、平息天灾等神迹。
这些传说虽与史实有明显的差异,但能在民间形成并广泛流传,实反映常民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及社会制度,由此来观察民间信仰的正统性,并解读其背后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了解某些民间信仰行为形成及运作的心理机制,亦可一窥传统宗法制度、皇权政治、儒家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以下即从政治正统性、文化正统性、血缘正统性等三方面分别讨论之。
二、政治正统性
民间信仰中的政治正统性,最明显表现在国家对祠庙的赐额与赐号上。这种制度形成于唐代,完成于宋代,日本学者松元浩一曾透过《宋会要辑稿·礼制》有关民间祠庙的记载,指出授予庙额、封号表达对祠庙崇敬、保护之意的方式,乃北宋中期以来政府对民间祠庙剧增的因应对策,藉此认定对民有功的“正祀”,以重新整编秩序及国家祭祀体系,并对未赐封的“淫祠”加以弹压。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的研究也指出,宋代由于赐封制度已深入民间,民众普遍认为封号会影响神祇的灵力,这使得赐额、赐号成为南宋时期地方势力藉由替他们所支持的神祇找寻头衔,以提升自身地位的方式;而在地方官员才有权力向中央请求,而地方官员又需要士绅来协助统治的情况下,两者常维持非正式的合作关系。由这两位外国学者的研究可知,赐封制度主要来自国家由上而下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以赐封与否决定正统或异端、崇敬或弹压;这种制度深入民间后,地方又会透过官员、士绅由下而上争取国家的赐封。在此上下的交互作用下,民间信仰常带有政治正统性的色彩。
在南宋杨志与庄夏分别为保生大帝东、西祖宫所作的《慈济宫碑》中,都特别强调保生大帝曾受王朝赐额、赐号的政治正统性。如杨志记载青礁慈济宫受封建庙的过程,曰:“绍兴间,虔寇猖獗,乡人奉头鼠窜,束手无策,委命于侯。未几,官军与贼战,毙其酋李三大将者,残党皆就擒。今之庙基,即贼酋死地也。阖境德侯赐,益以竭虔妥灵,岁在辛未,乡尚书颜定肃公奏请立庙。……庙既成,四方之香火,来者不绝,士祈功名,农祈藩熟。”庄夏亦记载此一显灵事迹,并进一步说明赐额、赐号的过程,曰:“岁在辛未,肇轫祠宇,于是精爽振发,民讠雚趋之,水旱疾疫,一有欸谒,如谷受响。时梁郑公当国,知其事为详,达部使者,以庙额为请,于是有‘慈济’之命。越庆元乙卯,又有忠显侯之命。开禧三年春夏之交,亢阳为沴,邻境赤地连数百里,独此邦随祷辄雨,岁乃大熟。会草窃跳梁,漫淫境上,忽有忠显侯旗帜之异,遂汹惧不敢入,一方赖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绩转闻于朝,于是有英惠侯之命。”由两人的记载可知,民间信仰的神明要获得朝廷的赐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护国佑民的显灵事迹,二是有如颜师鲁、梁克家等地方缙绅的协助推动。前者说明朝廷在赋予民间祠庙之政治正统性时,也在巩固自身的政治正统性;后者则显示国家与民间在建立政治正统性时,士绅阶层在两者间扮演重要的角色。
明、清时期,保生大帝虽未获王朝敕封,但地方士绅仍透过护国佑民传说及新封号的编造,来延续及强化保生大帝的政治正统性,以逃避王朝打击淫祠的冲击,并获得进一步的传播与发展。尤可注意的是这些编造出来的传说,大多与皇室有关,如明代何乔远《闽书》所载:“皇朝永乐十七年,文皇后患乳,百药不效。一夕梦道人献方,牵红丝缠乳上炙之,后乳顿瘥。问其居止,对云某所。明遣访之,云:有道人自言‘福建泉州白礁人,姓吴名夲’,昨出试药,今未还也。既不得道人所在,遂入闽求而知之。皇后惊异,敕封‘恩主昊天医灵妙惠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仍赐龙袍一袭。”这段事迹自非史实,但由于明代以后的地方文献及通俗读物皆有所转载,而成为广为人知的“揭榜医太后”传说,“保生大帝”也成为信众对吴夲最普遍的尊称。
清初颜兰《吴真君记》除记载上段传说外,又增加保生大帝“露幡救驾”、“鄱阳助战”等两段显灵事迹,曰:“高宗久质于金,思归中原,夜步月至崔子庙,不得马,虑其难脱。闻廊下马嘶,遂乘去。至江,金将追之将及,高宗仰天祝焉,忽见神兵阻御、露幡拥护,高宗乃知其为公,绍兴二十年颁诰立庙,祀公于白礁,盖公之祖庙也。明太祖、陈友谅战于鄱阳湖,飓风大作,友谅练舟流压太祖,战北,舟将没,见公于云间,旗幡森布,天遂反风回浪,太祖得安。及即位,感公之德,洪武五年敕封昊天御史医灵真君。”这些传说进一步编造保生大帝直接显灵解救南宋、明代开朝君主的事迹,以突显其不仅有功于皇帝一人,更对整个王朝的建立有所贡献,而将其受封建庙及赐号的正统性推至最高,实为保生大帝信仰在未受明、清王朝承认下,仍能在民间成功发展的原因之一。
由这些保生大帝与皇室有关的传说可知,代表国家的皇帝是政治正统性的最高象征,地方信仰的神明及其庙宇要快速提升地位、扩张信众范围,则展现与皇帝有关的显灵事迹是一快捷方式,即使这些事迹是编造出来的,但在民间仍有明显的影响力,也因此各地庙宇常流传着与皇帝有关的传说,甚至有文物为证。例如在台湾有不少民间寺庙,即流传有“嘉庆君游台湾”传说,指清嘉庆皇帝任太子时,曾来台游历,在台南普济宫;云林北港的妈祖庙、义民庙;彰化的清水岩、虎山岩、法水岩、宝藏寺、鹿港龙山寺、田中干德宫;嘉义东门福德祠、民雄大士爷庙;南投竹山连兴宫等,皆留有足迹,甚至有许多寺庙迄今仍高悬嘉庆皇帝御赐的匾额。当然这些传说与文物,都是民间虚拟附会的,但这种现象说明即使处于边陲的台湾,民间社会依然存在着政治正统性的观念,皇权仍具有一种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神圣力量,因此无论皇帝曾经亲临、敕封或颁赐文物,都可赋予该寺庙神圣的力量与正统的地位。
同样的,位在南投草屯的龙德庙,有一块清代台湾道丁曰健所献的“刑期无刑”匾额,其背后也流传一则与皇帝有关的传说,内容描述丁曰健冒功杀害戴潮春,皇帝令其领军剿办北势湳的洪欉,在龙德庙保生大帝的显灵相助下,顺利完成使命,将功补罪。这块“刑期无刑”匾本与皇帝无关,但匾上所书“曰健奉天子命……”等文字,提供地方创造与皇帝有关传说的有利条件,而有皇帝令丁氏来台围剿洪六头,以求将功补罪,后来在保生大帝的显灵相助下,顺利完成使命,皇帝下诏“刑期无刑”,丁氏再将此四字制成匾额等情节。此一情节无非在强调“刑期无刑”匾虽为丁氏所立,但这四字却来自于皇帝,如同是御赐文物一般,可证明龙德庙的保生大帝具有国家认可的“正统性”。
综上所述,历代王朝透过统治的力量,将政治正统性的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给予民间祠庙赐额与赐号,即是其渗透的手段之一。这种渗透的工作显然颇为成功,以致于在民间社会形成根深柢固的正统观念,视皇帝为政治正统性的最高象征,地方透过士绅阶层争取王朝对其信仰之神明与庙宇给予赐封,以扩大地方的影响力,提升神明的地位与灵力;即使无法如愿,也会藉由编造与皇室有关的传说及伪造新封号,来创造政治的正统性,以获取民间百姓的认同。
三、文化正统性
民间信仰的文化正统性,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员及文化菁英对神祇“儒家化”形象的塑造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代表一种正统的文化,也被用来改造纳入祀典的神祇。美国学者沃森(James Watson)在《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一文中,即提到国家或文化菁英为接受并塑造如天后般神祇的形象而有意识做出努力,如明代出使南洋的郑和曾在表彰妈祖的碑文上,记载祂“镇定”、“教化”海上民族的传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一文中,也指出清代在刻划关帝的神话时,对关帝的孔子化做出巨大的努力,尤其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禀监生卢湛所编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中,将关羽塑造成忠孝两全之人,并说他熟读儒家经典《春秋》,将其忠诚归之于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是一个“守经达权”的儒家智者。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究刘猛将军时,也指出清初曾将该神视为淫祠,在江南流传祂是南宋末年抗金名将刘锐、刘锜或刘宰,但到了雍正年间将其纳入祀典后,直隶总督利瓦伊钧重塑一个全国性的传说版本,刘猛将军成了元末指挥有功、殉节而死的刘承忠。这些研究都说明国家将民间信仰的神祇纳入祀典后,会由官员或文化菁英就其原有形象进行“儒家化”的改造,以符合儒者的特征,或具有儒家所强调的忠诚性格与教化功能。
即便是未为国家认可的神祇,文化菁英仍会顾及百姓的信仰情感,而藉由与儒家有关的连结或论述,赋予其文化的正统性。如陈春声研究三山国王信仰所指出,元代翰林国史院编修刘希孟撰写潮州三山国王的庙记时,即特别强调韩愈的祭祀,藉由他于当地被塑造成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及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将三山国王信仰与具代表性的儒者相连结,而为此边陲地区的民间信仰披上文化正统性的外衣。
在前述南宋杨志与庄夏的碑文中,记载保生大帝因护国佑民的显灵事迹而为王朝所赐封,不仅具有政治的正统性,也有意突显其具有儒家“忠君爱民”的表现。庄夏于碑文中又记载吴夲生前“尝业医,以全活人为心,按病投药,如矢破的,或吸气嘘水,以饮病者,虽沉痼奇恠,亦就痊愈。是以厉者、疡者、廱疽者,扶升携持,无日不交踵其门,侯无问贵贱,悉为视疗,人人皆获所欲去”,亦在强调其具有儒家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赋予其文化的正统性。明清时期,保生大帝“揭榜医太后”、“露幡救驾”、“鄱阳助战”等传说,除藉由解救皇室的事迹来强化其信仰的政治正统性,也在突显其忠君的表现,体现儒家的伦理道德。
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的文人与地方士绅,也积极为生前仅是布衣医者的吴夲塑造“儒家化”的形象,赋予其文化的正统性,以避免地方官员的弹压,并获取更多士绅及百姓的支持。如明万历三十年(1602)的《吴真人世修道果碑》记载:“至丙子年五月初三日,上帝闻其道德,命真人捧诏召夲。夲乘白鹤,白日升天,衣则道,冠则儒,剑在左,印在右,计在世五十八年。”这段碑文虽在呈现吴夲白日飞升的道教形象,但其“冠则儒”,则又肯定他具有儒者的身份。
清初大学士李光地在《吴真人祠记》中,更进一步强调吴夲的儒者本质。其曰:“卒之日,鹤雁蔽天,道服儒冠而化。……呜呼!此余所谓生为神人、殁载祀典者与。惟其不遇明王,使之理幽明、和上下,故托于仙老之伦而以真人称,而非夫世之怪神者比也。”他认为吴夲本是具有道德功业的儒者,但因“不遇明王”,无法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只能“道服儒冠而化”,而被民间以道教神奉祀,但绝非一般怪神淫祀之属。李光地虽与前段碑文同样提及吴夲“道服儒冠而化”的传说,但他身兼理学大儒与朝廷重臣,自然强调是以儒者为本、道者为末,藉此赋予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正统性,并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
至清末颜清莹《保生大帝传文序》,更直接将吴夲塑造成经世济民的儒者。其曰:“自古羽化登仙者众矣,求其有学问、有经济、有事功,超出乎凡俗,不流于凡俗,而为凡俗所爱戴,传诸天下后世而不忘者,未有若大帝之道大而德洽群生者也。帝氏吴讳夲,泉之同邑白礁绅士也。少而颖异,长博经书,凡天地之理靡不究,歧黄之艺罔不稽。生平以护国庇民为主,济人利物为先。由贡举登御史,赫赫名显一时,岂不伟哉。”这段序文以学问、经济、事功来推崇吴夲,甚至谓其具有功名,并且曾经为官,此皆与传统儒者无异,实已彻底将吴夲“儒家化”。
在保生大帝信仰的发展历程中,南宋杨志、庄夏等士大夫阶层,及明清时期的文人与地方士绅,都曾透过传说塑造吴夲“儒家化”的形象,这代表一种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渗透与影响。即使后来此一信仰逐渐“民间化”、“地方化”,传说也多着重于保生大帝的神异形象与灵验事迹,但在民间仍可看见富有儒家道德教化的故事。例如白礁慈济宫所编之《真人灵光》一书,记载两则吴夲生前的传说:一为“舍身救世”,谓吴夲为了制药救人,攀爬悬崖摘取“金不换”药草,不幸失手坠崖而亡。一为“竹仔枝炒肉治疯癫”,谓有一媳妇常谩骂夫家,口出狂言,状似疯癫。吴夲前往诊治,知其为偷懒、不孝而故意装出来的,故佯以“竹仔枝炒肉”治之,实以竹枝鞭打教训,使媳妇坦承装疯,并从此勤理家务、孝顺公婆。
另在青礁慈济宫所编之《圣山春秋》一书,也记载一则“重贫轻富”的传说,谓泉州知府为巴结吴夲,曾派花轿延请他赴寿宴。但吴夲以忙于治病,不愿上轿,并在得知有一贫农之子遭蛇咬伤,即匆忙赶去医治。后人为纪念他重贫轻富,乃在花轿停留处建一“花轿公府”,即今花桥慈济宫。这几则传说或宣扬吴夲救人济世、不慕富贵的伟大人格,或劝诫世人应勤勉孝顺,都具有道德教化的意义,
显见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的观念,仍保存于民间信仰的传说之中,继续发挥教化世人的功能。
四、血缘正统性
民间信仰的血缘正统性,主要表现在祖宫之争,及地方庙宇与原乡祖宫的香火关系上。陈春声在台湾三山国王信仰的研究中,曾以彰化溪湖河婆仑霖肇宫的香火缘起传说为例,指出庙宇的“正统性”是多方面地通过其与原乡的关系来证明的,包括带香火来台的是原乡河婆人、霖肇宫所在地命名为“河婆仑”、为该庙雕刻神像的师傅来自原乡河婆墟等;而其庙名“霖肇”有霖田祖庙在台肇基之意,该庙在道光年间又曾漂洋过海到霖田祖庙进香,这都在多方面呈现其与原乡祖庙的香火关系,此一信仰的正统性也让台湾许多同祀庙宇愿意承认自己是从霖肇宫分香出来,并以此为荣。翁佳音的研究也指出,台湾妈祖庙争相以赴大陆祖庙进香或全台绕境等活动,来证明自身才是“正牌”的妈祖庙,其背后目的在夸示本地的正统与优越地位,也用以增加香油钱的收入,这正反映出民间宗教意识中的正统观。
对于民间信仰的血缘正统性,人类学者则以“系谱权威”来说明。Maurice Bloch分析传统或祖先之所以有权威,乃因现存的人有时间性、空间性与个体性,故其权威有限;而死去的祖先进入“永恒的过去”,取得一种“无时间性”、超越时空与个体的权威。Sangren则分析妈祖“灵”(ling,有灵验之意)的原因来自历史,妈祖庙之所以要追溯早期历史,或宣称自己是历史上那尊“开台妈祖”,均是为了显示妈祖在早期移民的小区移垦、小区意识的功劳。张珣则在前两人的基础上,加入中国人的人观与亲属观,探讨台湾妈祖庙在两岸开放后争相回湄州祖庙进香的原因。她认为“认祖归宗”是妈祖信仰中“进香”的深层文化意涵,争取系谱时间上、上位的、高层的位置是建立在“系谱权威”的要求。如同人的系谱,后代的层次越多,开基祖的权威越大;湄州妈祖是开基祖,是系谱上的第一点,后代分香庙一辈接一辈,其权威也堆积越高。这种妈祖系谱来自中国父系继嗣的社会结构,神明世界也有嫡系旁系及祖孙世代的辈分;而向湄州妈祖认祖归宗,具有嫡系的意涵,因此各庙热衷到湄州进香,且不论真假都要声称其香火来自湄州。
保生大帝信仰中最能表现血缘正统性者,便是白礁与青礁两地的祖宫之争。
根据杨志与庄夏的碑文记载,吴夲辞世之后,青礁与白礁同时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兴建慈济宫,一般称为保生大帝信仰的东、西祖宫。自建庙以来,由于涉及到地方意识、信仰的正统性及进香添油的经济利益,青礁与白礁的祖宫之争未曾停息。前述颜兰《吴真君记》所载保生大帝“露幡救驾”的传说,特别书明“绍兴二十年颁诰立庙,祀公于白礁,盖公之祖庙也”,即刻意将白礁建庙年代往前移一年,制造其早于青礁建庙的假象,以在祖宫之争中占得“第一庙”的先机。
明、清时期,白礁所在之泉州由于经济、人文地位皆领先青礁所在之漳州,加上地方士绅积极透过传说、方志及各式文本的广为传播,白礁逐渐在祖宫之争中取得优势,而形成“西宫—祖宫”的历史记忆。这种祖宫记忆也影响台湾的保生大帝庙宇,常藉由香火缘起传说来突显与白礁慈济宫的关系,如嘉义市三台宫即强调其香火缘起,曰:“其肇建源自清康熙年间,先民林耀宗及林耀烈二兄弟,由祖家即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之白礁慈济宫,恭迎保生大帝金身一尊,护航地海来此。”高雄湖内区长寿宫也谓其香火乃缘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当其时市街日渐繁盛,本庄林姓善士乃自故乡白礁祖庙迎奉保生大帝尊像来台,卜七星坠地之灵穴,择吉建庙,以供信众朝夕膜拜,慰藉思乡情怀。”
屏东枋寮乡北势寮的保安宫,则传说其香火缘起乃当地临海,船只来往频繁,曾有人上岸提取淡水,因内急将保生大帝香火挂于树上,匆忙间未带走。夜深之时,当地居民杨开山在海上捕鱼,见陆上一盏灯火光芒四射,久久不灭,心感有异,乃上岸查看,发现一方木造香火,上书“白礁保生大帝香火”字样。杨氏遂将香火迎回自宅供奉,后因非常灵验,乃正式兴建庙宇。这些传说皆强调其宫庙香火直接源自于白礁,乃祖宫之嫡系子庙,具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藉此强化自身的正统性。
另外,台湾的保生大帝庙宇也有藉由神像来历的传说,来强调自身的血缘正统性,从而建立在此一信仰的“谱系权威”。例如目前被公认是台湾保生大帝开基祖庙——学甲慈济宫,其缘起于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之军民于学甲西方四公里处之头前寮登陆,先民建简屋奉祀保生大帝,因香火益盛,乃于康熙四十年(1701)改建宫庙。建庙之后,每年学甲十三庄居民皆于登陆日的三月十一日,组成香阵前往登陆地的头前寮“请水”谒祖,遥祭大陆白礁慈济宫祖庙,即是台湾知名的民俗祭典“上白礁”。
学甲慈济宫有则传说曰:“吴夲辞世之初,因屡有显灵事迹发生,乡民感念其神灵显赫,乃恭塑大大帝、二大帝、三大帝等三尊神像,大大帝奉祀于白礁慈济宫,三大帝供奉于青礁,二大帝则于明永历十五年,由李姓信徒迎奉来台,奉祀于台南学甲慈济宫,神像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这段传说除重申该庙于明永历年间在台建庙的历史外,更将其神像年代大幅提前至“吴夲辞世之初”,且与白礁、青礁祖庙同时雕塑,藉此暗示其香火年代更为久远,并与两大祖庙具有同等的地位。尤可注意的是,这三尊同时雕塑的神像,白礁、学甲、青礁分别奉祀大大帝、二大帝、三大帝,显示白礁的位阶最高,学甲次之,青礁最低,显然有意矮化青礁的地位,这与学甲慈济宫尊白礁为祖宫有关,故藉此在祖宫之争中助白礁一臂之力。
另外,台南西港开仙真宫近年来也出现一则神像来历的传说,谓荷据时期青礁海沧吴厝先人渡海来台,随船奉请三尊神像,大祖辗转奉祀于该庙,二祖由凯达格兰族人迎奉至大龙峒保安宫,三祖则在大寮保龙宫;该庙还曾依此传说推动三庙同袍认亲的活动。这则传说除将开仙真宫的香火缘起提早至荷据时期,且宣称神像来自于青礁祖宫,并与大龙峒保安宫系出同门而位阶较高,显有深层的用意。自1980年代随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划归厦门的青礁在经济与人文上反而超越划归漳州的白礁,加上两岸开放宗教交流,为争取大批台湾保生大帝信众前往进香谒祖,青礁乃重启祖宫之争的战火,且挟着丰沛的政经资源而渐占上风。而台北大龙峒保安宫董事长廖武治自2005年接任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会长后,在推动两岸及东南亚的宗教交流、岛内同祀宫庙的联谊与互助上,都有丰硕的成果,也俨然成为华人世界保生大帝庙宇的领导者。因此,开仙真宫藉由神像来历传说,将其香火血缘与青礁祖宫、大龙峒保安宫相互连结,隐然有利用这两间新“正统”宫庙来提升自身地位的企图,诚可谓用心良苦。
无论是白礁、青礁的祖宫之争,或是台湾庙宇与大陆祖庙的连结,其目的都在追求血缘的正统性。白礁、青礁各自强调与吴夲的地缘关系,又在建庙年代上大作文章,都在拉近吴夲的时空距离,以站上保生大帝信仰系谱的第一点,拥有最高的灵力与权威。而台湾各地庙宇透过进香及传说的编造,连结与大陆祖庙的香火关系,则在证明自身属正统嫡系,具有更高的辈分位阶,亦同样在建立“谱系权威”,提升在台湾同祀宫庙中的地位。
五、结 语
本文透过保生大帝及其庙宇的传说,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性,发现“正统”的观念影响民间信仰的运作甚深,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国家运用赐额、赐号的制度来管理民间信仰、拢络地方势力,并藉此巩固王权;民间则透过官员及士绅阶层争取将地方性的信仰纳入国家祀典,赋予神明及其庙宇正统的地位,并视皇帝为政治正统性的最高象征。在文化正统性方面,文化菁英积极塑造地方神明“儒家化”的形象,以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民间也流传神明护国佑民、慈悲济世的神迹传说,展现忠孝仁爱的精神,而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最佳典范。在血缘正统性方面,民间相信神明祖庙的地位最高、灵力最强,因此常有祖宫之争的现象;祖庙经由分香、再分香而衍生出许多子庙,祖庙与子庙之间具有一种拟血缘关系,依祖庙的分香谱系决定子庙的地位与灵力,也因此各庙常透过谒祖进香、分灵神像或编造各种香火缘起传说,来拉近与祖庙之间的关系,以提升自身的地位与灵力。
虽然现代社会以政府取代皇权,国家权威大幅降低,儒家思想也不再定于一尊,但政治、文化的正统性观念仍持续影响着民间信仰。例如民间庙宇喜好悬挂政府官员所颁赠的匾额,也以官员来访参拜为荣,甚至汲汲争取将庙体建筑与庙会活动指定为官方认可的文化资产,都突显对政治正统性的重视。另庙方或信众在讲述神明的生平或神迹时,仍常会强调其忠孝节义的道德表现,甚至将此精神转化为推动社会教化及公益慈善活动,则可看出带有文化正统性的色彩。尤为明显的是,现今各庙宇为提升神明的灵力及在同祀宫庙的地位,以获取更大的香火利益,常运用各种手段来争取祖庙名衔,或连结与祖庙的关系,更表现出血缘正统性的作用。因此,这种因传统宗法制度而形成的“正统”观念,显然已深植于民间社会,并未因时代及外在环境的改变而式微,这也是研究民间信仰及各种民间文化所不能忽略的课题。
注释:
[1]许庆玲、李世龙:《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特定社会模式》,《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总64期,2009年7月,第76~77页。
[2]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8卷2期,1997年6月;《评介近年来明清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的三本新著》,《新史学》15卷4期,2004年12月。
[3][7]杨志:《慈济宫碑》,收入陈锳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艺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清乾隆27年刊本影印,卷22,第256页。
[4][25]范正义:《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69~204 页、206~283 页。
[5]松元浩一:《宋代の赐额、赐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辑稿》にみえて史料から》,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中央政治地方社会》1985年度科研费报告,1986年。
[6]韩森(Valerie Hansen)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8][17]庄夏:《慈济宫碑》,收入陈锳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艺文志》,卷 22,第 258 页。
[9]何乔远:《闽书·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卷 12,第 275 页。
[10]颜兰:《吴真君记》,收入林学增等修、吴锡璜纂:《同安县志·祠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卷 24,第 656页。
[11]林文龙:《嘉庆君游台湾》,《台湾掌故与传说》,台北:台原出版社,1992 年,第 40~71 页。
[12]南投县草屯镇月眉厝龙德庙编:《保生大帝吴真人传》,南投:龙德庙,出版年不详,第7~10页。
[13]沃森(James Watson):《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 年)》,收入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7~92 页。
[14]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收入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114页。
[15]滨岛敦俊:《江南刘姓神杂考》,《待兼山论丛·史学编》24 号,1990 年,第 1~18 页。
[16]陈春声:《正统化、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期,2001年,第124~125页。
[18]李光地:《吴真人祠记》,《榕村全集·续集》,道光九年利瓦伊迪刊本,卷5。
[19]颜清莹:《保生大帝传文序》,收入林廷璝,《保生大帝实录》;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20]王加福编:《真人灵光》,福建:龙海市白礁慈济祖宫管理委员会,1999 年,第 46~47、55~58 页。
[21]青礁慈济宫编:《圣山春秋》,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22]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80期,1995年,第69~72页。
[23]翁佳音:《民间宗教意识中的正统观》,《台湾风物》37 卷 4 期,1987 年,第 93~95 页。
[24]张珣:《文化妈祖: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2003年,第79~90页。
[26][27][28][29]“全国”寺庙整编委员会编:《“全国”佛剎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上)》,台北:桦林,1986 年,第217页、157页、178页、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