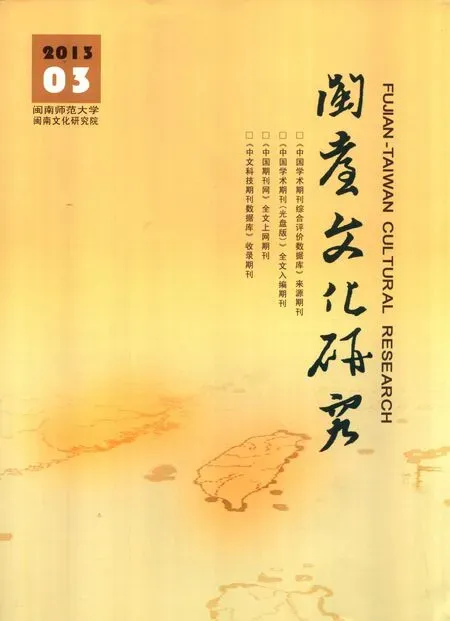从福建南安的“炉内潘”到新加坡的“潘家村”:南洋华人宗族村落的个案研究[1]
2013-11-14曾玲
曾玲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361005)
从福建南安的“炉内潘”到新加坡的“潘家村”:南洋华人宗族村落的个案研究
曾玲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361005)
近现代以来,当一批批华南移民南来东南亚拓荒,在移居地重建社会结构与组织,是华南移民在海外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是否存在宗族,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本文以个案研究方式,透过具体考察新加坡一个在殖民地时代建立的聚族而居的华人村落“潘家村”的建立与运作,进而思考和讨论近代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东南亚华人的宗族社会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而是一个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是在移民社会初期,华人宗族组织和宗族社会的重建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不同于祖籍地的社会环境下,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使之能适应新的人文条件,由此也在宗族结构、组织形态、以及祖先崇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形态。
华南移民;新加坡;潘家村;宗族村落
前言
近现代以来,当一批批华南移民南来东南亚拓荒,在移居地重建社会结构与组织,是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面对的共同问题。在19世纪的新加坡,由于殖民地政府实施半自治的社会政策,华人移民必须建立自己的社团和组织,方能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本文以个案研究方式,透过具体考察新加坡一个在殖民地时代建立的聚族而居的华人村落潘家村的建立与运作,进而思考和讨论近代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
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后,南来的闽粤移民建立了一些华人村落。例如在今天新加坡的义顺地区,华人移民曾在此建立财启村、黄梨山村、泽光村、直鲁殊村、柑仔园、合春格村、海南村、苏家村等村落。这些由华南移民建立的华人村落有不少是聚族而居的单姓村,“潘家村”亦是其中的一个村落。
清末民国初,一批批来自福建省南安县乐峰镇炉内乡的潘氏族人因各种原因南来新加坡,并聚集在一起。经数次的迁移,20世纪初他们逐渐定居在新加坡东北部的义顺兴利芭。二、三十年代后,聚集在兴利芭的潘姓族人愈来愈多,逐渐形成一个以横山庙为中心的聚族而居的村落,该村落被称之为“潘家村”,其村民则被称为“炉内潘”。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国家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期。从7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实施市区重建计划,建造大量的公共组屋,有计划地进行打破种族、方言等隔离的全国人口大迁徙。到了80年代,潘家村所在的社区被规划为义顺新镇。受发展计划影响,潘家村大约160个家庭迁居到宏茂桥和义顺两新镇。1997年底,因政府修筑快速公路涉及横山庙所在地段,“潘家村”族人开始在义顺工业区内重建新庙。重建工作历经一年时间,1998年底,新庙落成,横山庙由潘家村迁入。
潘家村从建立到消失,在新加坡历史上存在了近八十年之久。潘家村的历史虽然短暂,但作为一个个案,它对华人社会历史研究却可以有许多重要的启示。从中国南安炉内的“潘家村”到新加坡义顺兴利芭的“潘家村”,移民海外的“炉内潘”族人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艰难历程,也经历了在移居地重新建构华人社会的历史过程。而聚族而居的“潘家村”在新加坡社会文化脉络下的运作,更为研究华人运用祖籍地的血缘纽带在海外建立的家族组织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个案。
本文主要根据新加坡殖民地的一些档案和田野调查、访谈等口述资料,考察来自南安的“炉内潘”族人,如何运用祖籍地的血缘纽带和文化资源,在新加坡重建血缘、地缘、业缘三结合家族社会“潘家村”的历史过程,进而讨论海外华人建构家族组织与社会的有关问题。
一、新加坡实里达流域种植经济的发展
义顺区兴利芭位于新加坡实里达河流域。实里达河全长九哩,是新加坡最长的河流。它发源于新加坡北部实里达蓄水池一带的森林地区。在中游地带与其支流新邦干南河及新邦基里河汇合,向东北注入柔佛海峡。
根据资料记载,实里达河流域在19世纪40年代仍属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地带,河流两岸既无人烟,也没有栽种任何农作物。只有一种原始人叫实里达原住民常在该河出没。50年代开始发展种植经济。从那时起至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前后,实里达河流域种植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1850年至1880年的三十年间以发展甘蜜业和胡椒业为主。在河的下游以东、以西以及河的上游地区,形成东实里达、北实里达和中实里达三大种植区,是当时新加坡甘蜜与胡椒主要出产地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马来半岛上的柔佛南部甘蜜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与新加坡形成竞争的局面。而新加坡的甘蜜业却在70年代以后逐渐走下坡路,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种植园主放弃种植甘蜜与胡椒,实里达流域的甘蜜胡椒业没落了,园地也荒芜了。直至本世纪初黄梨与橡胶种植与加工业的出现,才使实里达河流域的种植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19世纪80年代,陈齐贤、林文庆在马六甲大规模种植橡胶成功后不久,橡胶种植便移入新加坡。九十年代因欧洲工业革命、欧美汽车工业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橡胶的需求增加,促使世界胶价急剧上升。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发现橡胶工业有利可图,便在1908年至1911年间开设实里达河以北约2000英亩的保护林。并施行地租回扣制,鼓励橡胶种植,以满足国际市场对橡胶的大量需求。于是,实里达流域原有的甘蜜园纷纷改种树胶,还未开垦的土地也陆续被辟为胶林胶园。实里达树胶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前后。当时日本南侵新加坡,粮食极度缺乏,于是大多数胶林改种粮食作物。昔日园丘处处,胶林密布的景象从此不再。
橡胶业和黄梨业的发展在该地区几乎同时出现。因树胶树的生长期较长,从种下树种到能割胶大约需要五到七年。在树胶树未能割胶之前,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树胶园多在胶园中套种黄梨。黄梨生长期短,一年可有三熟。由黄梨制成黄梨罐头,在当时的欧洲市场上很畅销。所以当时橡胶种植园主都普遍兼种黄梨和发展黄梨罐头加工业。
经营种植经济的先驱者中有不少是华人企业家。他们从海峡殖民地政府领得地契,获得土地开发权,便雇工开垦。同时设置工厂加工甘蜜,胡椒,黄梨和树胶,输往国外。这种种植业与加工业一体化的经营方式随着种植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促进实里达市镇和乡村的出现。
由于加工业生产产品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商品流通需求,在当时交通要道实里达河上游形成商品集散地——“港脚”。“港”在华语闽南方言中指水道,“脚”指尾端,“港脚”即指上下船的所在地。港脚多以开发当地的地主命名。例如实里达河上游的港脚,当时称为曾厝港(chan chu kang),因1850年曾阿六获东印度公司发给他44英亩土地的地契,在此发展甘蜜、胡椒业而得名。今天新加坡的许多地名,如杨厝港,林厝港,蔡厝港、云峰港,都是当时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脚”。
随着种植经济的发展,港脚日益繁荣。尤其是黄梨和树胶加工业的兴起,华人企业家将工业引入港脚,在此建宅设厂,从事加工生产,造成港脚人口的增加和各种服务、消费行业的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港脚大路两旁的商店已经象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为了及时将原料从乡村运往港脚的工厂加工,他们注重修建沟通港脚与周边地区的道路桥梁。港脚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而大大增强,周边地区便成为港脚的腹地。港脚便由早期的商品集散地逐渐变成繁荣的商业市镇。
与此同时,为加工业提供产品原料的种植业的发展则促进了乡村区的形成。在原为原始森林覆盖的实里达开垦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开发实里达两岸的种植园主多采用承包的经营方式,他们将园丘包给工头,由工头雇佣劳工来从事生产。劳工们在原始森林垦辟土地,种植甘蜜、胡椒或黄梨、树胶。由于树胶生产期长,在种好树胶树苗后,有些工人离开了园丘,有些则留下来继续作为园丘工人,住在园丘内园丘主用亚答叶及木板建的简陋宿舍万栅(bangsal)里。以万栅为家的劳工多是单身汉。有家眷或准备回中国娶亲的华人,则在胶园边缘用亚答叶和木料搭建房屋安居下来。这些有了自己简陋安身之处的华人,除了在胶园与胶厂做工,也种些果树蔬菜和畜养家禽,称为“做芭”。当时的华族企业家多欢迎劳工在靠近工厂和园邱的地方定居,以保证劳动力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青劳工成家立业,定居下来,逐渐形成许多主要由华人劳工组成的村落。
从事经营实里达河流域种植经济的华人先驱者多喜欢雇佣来自自己故乡的,与自己具有同一地缘、方言缘的华族移民,这就使因种植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乡村聚落具有浓厚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
早期在实里达河经营甘蜜和胡椒业的多为潮州人。在他们园丘内工作的劳工多来自潮州。20世纪初,树胶与黄梨取代了甘蜜和胡椒。许多潮州籍企业家如林义顺(因其对开发实里达地区贡献甚大,20世纪40年代后,实里达地区以其名命名,称为“义顺区”)、苏添富等都改种树胶和黄梨,继续执实里达流域种植经济之牛耳。与此同时,福建闽南籍的陈泰,陈嘉庚,李光前等也跻身新加坡黄梨、树胶行业,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897年殖民地政府开放港脚以南三百多英亩的地段发展种植业,福建同安籍企业家陈泰在该地区合春格获得约150多英亩地段,创合春号黄梨厂生产黄梨罐头出口。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也在这里拥有100多亩地段,引进农户,进行黄梨种植。1904年,陈嘉庚在实里达河边设立新梨川黄梨厂,并买下福山园,广植黄梨,生产大量的罐头出口到英国及其他国家。1906年,陈嘉庚又斥资购买十八万粒树胶种子,播种在福山园的黄梨园。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他在20年代末30十年代初收购了林义顺的通益树胶厂,将其改称南益树胶厂,大力发展树胶的种植与加工。与潮州帮企业家相似,这些闽帮企业家多雇佣来自故土的劳工。在陈嘉庚与李光前的胶园和胶厂工作的多是福建闽南人,特别是李光前祖籍南安,他更偏爱南安籍移民劳工。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里达流域存在对福建尤其是南安籍劳工的需求。
实里达流域种植经济尤其是树胶和黄梨的迅速发展,造成大片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不仅唤醒了这片沉睡千万年的原始土地,改变了实里达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奠定了河流两岸最初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
二、福建南安潘氏族人的南来
与实里达种植经济发展和新加坡其他地区的开发基本同时,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动乱、经济凋敝、人民向海外大量迁移之时。实里达种植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社会的建设,给中国南移新加坡的拓荒者带来希望和机会。中国福建南安的潘氏族人便是在上述自然与人文背景之下,离乡背井汇入移民潮,来到新加坡这片亟待开发的实里达流域。
潘氏族人的祖籍在中国福建南安乐峰乡炉内村,该村村民绝大部分都姓潘。据笔者见到的不完整的荀江炉峰潘氏族谱,其内有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年)五月的序言:“吾潘开基于晋江旬水,分派于南安炉山……自开基祖迄今已三百余年……”,可知这是一个经由晋江分支到南安、并已有五百年多发展历史的中国传统宗族。另据笔者1995年在当地的调查,经过数百年的繁衍,潘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是一个被称为“万儿丁”的大姓宗族。据一九九四年的统计资料,“炉内潘”所在地区约为90平方公里,后裔在海内外共有85000多人,其中在祖籍地的“炉内潘”已达三万四千多人,分布在厚洋、炉中、福山、霞厝、炉山和飞云等六个大村庄。福建省内1万多人,浙江等地26000多人,海外的星(新)、马、菲、印、港澳台等地共15000多人。
根据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华族村史调查报告,南安炉内潘氏族人(以下简称“炉内潘”)的海外移民与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习习相关。那一时期的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天灾人祸、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福建南安炉内的“潘家村”也不能免受其害。他们遭受地主官僚横征暴敛、高利贷剥削、土匪横行、天灾人祸等的折磨,纷纷向海外移民寻找生路,故当地人称:南安不安,乐峰不乐,村民过番来求活。
调查和访谈资料显示,至晚在19世纪末叶,已有“炉内潘”人南来新加坡谋生。初到新加坡时,他们聚居在当时汤申路七英里的牛胆湾。1904年因政府扩建贝雅士蓄水池,征用了牛胆湾,这些“炉内潘”人便迁徙到位于牛胆湾东北杨厝港十一条石大伯公口的地方,与潮州人的洪姓家族同处一地。“炉内潘”住芭头,潮州洪氏住芭尾。潘洪合处的局面大约维持了十年。1914年,大伯公口卖给日本人,“炉内潘”再次迁徙,来到兴利芭。
兴利芭位于实里达河上游附近,因港主潮州人苏文兴在此买地种植甘蜜经营兴利公司而得名。在“炉内潘”未迁入之前,这里杂姓共处,其中有几户南安籍的潘姓。“炉内潘”集体迁入之后,盖了横山庙,来此的“炉内潘”逐渐增加到二十几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混乱,军阀为患,社会动荡。福建南安土匪横行,兵荒马乱。这种情形迫使更多“炉内潘”族人移民海外,过番投奔已先到新加坡的潘族人。此时也正是陈泰、陈嘉庚、李光前等福建籍华商经济实力增强的时期。他们在实里达发展种植经济,兴办树胶和黄梨加工工厂,修筑道路桥梁,拓展市镇和乡村,吸引了大批华人移民的到来。于是一批批南来新加坡的“炉内潘”族人移进兴利芭,逐渐形成了新加坡的“潘家村”。
三、潘家村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一)“潘家村”的村民构成
“潘家村”存在的近八十年历史中,其村民构成基本可以二战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二战前,兴利芭内的村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炉内潘”人。二战以后情况开始改变。但直到政府征用该地,兴利芭内“炉内潘”人的比例还是占了村民的四分之三。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炉内潘”移民聚族而居的“潘家村”。
“潘家村”所在兴利芭的大部分土地原属在实里达发展种植经济的潮籍企业家苏添富。苏添富在兴利芭的树胶园多雇佣潮籍和海南籍劳工。这些劳工大多数是单身汉,住在苏添富所盖的“万栅”里。苏添富的事业到第二代就衰弱了,他的后代将土地出卖,其中部分卖给“炉内潘”。当“炉内潘”购买了兴利芭的土地,原居住在该地“万栅”里的单身劳工,属海南籍的移到兴利芭西南部另建家园,后来逐渐形成海南村;属潮州籍劳工移到兴利芭的西北部一个叫三百浔的地带,靠在实里达河捕鱼为生。1934年,“炉内潘”购置族产供族人居住,迁入兴利芭的潘氏宗亲愈来愈多,为数不多的外姓更感难以此立足,纷纷连人带庙搬离兴利芭。因此,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利芭内几乎是清一色的“炉内潘”人。在日本南侵新加坡时期,虽有一些来自安溪、晋江等非南安籍的潘氏移民搬入兴利芭避难,但兴利芭内仍以“炉内潘”占绝大多数。
二战结束后,实里达的种植经济衰落,新加坡社会变迁开始冲击聚族而居的潘家村,一些“炉内潘”氏子弟陆续搬离“潘家村”,向外寻求发展机会。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随着都市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吸引更多潘族年青一代离开“潘家村”到都市建立新家园。与此同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非潘姓者通过姻亲、朋友等关系在“潘家村”安家落户,逐渐打破了“炉内潘”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据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资料,1969年他们调查了居住在“潘家村”的72户村民,其中“炉内潘”58户,占76.3%,安溪卓姓3户,占3.9%,黄姓4户,占5.2%,其他杂姓7户,占9.2%。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潘家村”的四分之三以上村民仍具有紧密的血缘联系。
(二)“潘家村”村民的经济活动
来自南安炉内的潘族移民,在兴利芭新建的“潘家村”操持着基本相同的职业。此种情形在二战以前尤其明显。具体说来,“潘家村”民从事的工作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当园丘工人。兴利芭及其附近地区在1905年后都改种黄梨和树胶,需要很多劳力来从事园丘工作。当初兴利芭很少华人移民,不足应付树胶和黄梨园丘的工作。自从1914年“炉内潘”迁入后,其族人多从事割胶或锄黄梨草的工作。每当园丘扩展缺乏工人,他们便介绍家乡的亲属亲戚来填补,兴利芭内的“炉内潘”人因而不断增加。
其二、在黄梨厂或橡胶厂工作。随着种植业的发展,港脚的黄梨厂和橡胶厂愈来愈扩展,对工人的需求量也愈来愈大。特别是陈嘉庚的新利川黄梨罐头厂和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厂都喜欢雇佣闽裔劳工,许多潘氏族人就在他们的树胶厂和黄梨厂工作。
其三、种植果蔬与饲养家禽。兴利芭的东部为盆地,适宜种植黄梨和树胶。中部有许多低地可种植果蔬或饲养家禽。当时不少种植园主鼓励劳工在他的胶园黄梨园里饲养家禽。这些劳工义务为园丘除草。同时将饲养家禽的排泄物作为园丘的肥料。所以在兴利芭,除了胶园黄梨园和胶厂黄梨灌头厂的工作,种植果蔬与饲养家禽也是“潘家村”民基本的职业之一。兴利芭所生产的果蔬、鱼、肉、蛋之类的农副产品,自用者为小部分,绝大多数是运往当时新加坡的市区大坡小坡出卖。
二战以后,由于树胶黄梨园在战争中都遭摧毁,种植果蔬与饲养家禽成为许多潘家村人的主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蔬菜种植和禽畜业生产采用现代化大农场的经营方式,以机械化取代传统的手工操作。“潘家村”民紧跟时代潮流,出现不少以农致富的企业家。还有一些村民开鱼塘饲养热带观赏鱼,种植胡姬花。在那一时代,实里达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义顺区成为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禽畜和果蔬供应基地之一。
从上述“潘家村”村民构成和经济活动状可以看出,移民海外的“炉内潘”人,在新加坡兴利芭重新聚族而居,并建立了一个兼具地缘、血缘、业缘三结合特色的新社区,对这个新社区实施管理的则是作为“炉内潘”人凝聚中心的横山庙。
四、横山庙的建立与运作
(一)横山庙的建立
“潘家村”的横山庙,是经由南安炉内的横山庙分炉(香)而建。
在兴利芭“炉内潘”人的祖籍地有一座庙宇称为横山庙。该庙因建筑在走势横向的山脉上而得名。横山庙里供奉有主神潘府大人和配神陈、李两将军。“炉内潘”人认为,潘府大人即明朝的工部尚书潘季驯。不过,潘府大人并非南安炉内潘氏的开基主,而是被尊称为“祖叔公”的祖神,因而并不进入“潘氏宗祠”,只被供奉在横山庙内。
19世纪末,潘春膑南来新加坡,在实里达石仔山经营石场。与此同时,他也将横山庙分炉来新加坡。所谓分炉,即启程前他从故乡横山庙的香炉里捧了一包香灰带来新加坡,在住家附近搭一间小小的茅屋供奉潘府大人。当南移新加坡的“炉内潘”族人聚居在牛胆湾时,他们居住地盖了一小庙,把潘府大人从潘春膑的茅屋中请到此供奉。后来“炉内潘”二迁到大伯公口外,潘府大人再从牛胆湾的小庙里被请出,迁回潘春膑家。1914年“炉内潘”族人三迁至兴利芭定居,潘府大人便随之来到兴利芭。初到兴利芭时,“炉内潘”族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建庙宇,只能建一间亚答屋来供奉他们的祖神。1931年,“炉内潘”从中国故乡聘请专业庙宇建筑师,在兴利芭建立了一座横山庙,供奉潘府大人。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潘家村”内的横山庙所仿照的不是祖籍地的横山庙,而是“潘氏宗祠”。1957年,“潘家村”再次聘请故乡的庙宇建筑师翻建了横山庙。
(二)横山庙的管理机构
在兴利芭,管理“潘家村”的机构是横山庙理事会。根据存留下来的理事会会议记录和调查资料,横山庙理事会的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二战以前,理事会的理事来自由各房推举的族长。各房族长的人数由各房人口比例决定。南安炉内潘族有四大房支,四房之中,以二房人丁众多势力最大。到兴利芭来的“炉内潘”也分为长房、二房、三房、四房,其中也以二房人数较多。在兴利芭各房推举族长的人数中,二房在比例上总多占一些。这些由各房推举出来的理事组成横山庙理事会。
理事会会长在理事中推举产生,他也是潘家村的族长。在兴利芭潘家村存在的近八十年历史里,共产生过两个族长,就是潘春膑和潘南山父子。他们属二房。不过,房头大并不完全是他们成为族长的主要原因。潘春膑较早移民,离故乡前受过一些教育。来新加坡后曾在实里达石仔山开石场,早期一些南来的宗亲曾投靠他,在他的石场工作。横山庙便是由他分炉去石仔山。潘春膑对家族的贡献还在于他以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维护“炉内潘”人的利益。潘春膑过世后,其子潘南山继任为族长。潘南山因承包殖民政府市政道路建设工程,在经济上颇有实力。他也秉承父志,热心于家族事业,故能为族人接受为族长。
二战之后,横山庙理事会实行董事制。董事会设主席,下设总务、财政、文书、查账、交际各股、各股设正副股长各一人,另设十二人评议员。董事会职员由理事会投票选举产生。横山庙管理机构最大的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1年因政府征用潘家村和横山庙,横山庙决定重组理事会。理事会选出新的正副主席,同时聘请义顺区国会议员高立人博士及当时担任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的潘巴厘为顾问。1982年1月18日,横山庙理事会成立一个横山社有限公司,负责处理赔偿金问题以及照顾族人的福利事务,原有的理事会则“只负责横山庙之庙务”。
横山庙组织形态的演变表明,当中国人移居海外,曾力图遵循祖籍地的传统重建其社会结构,尤其是在移民社会早期。从来自中国南安的移民在新加坡所建立的“潘家村”内四大房支的构成,族长的存在,以及由各房支族长组成的横山庙理事会实际上是一个宗祠委员会等等情况,显示了中国移民在海外对持中国农村传统家族组织基本特色的坚持。然而,在不同于祖籍地的社会脉络下,华人移民也必须调整传统的文化原则,以适应移居地的人文环境。横山庙组织形态的演变正反映了华人移民在新环境下的调适。
首先,潘家村族长的产生取决于他在潘家族人中相对经济实力以及他对家族的热心与贡献,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族长的基本条件,如辈分、名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董事制是近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来自中国传统家族社会以务农为生的潘氏族人从战前的理事会到战后采用商业社会的董事制来组成自己的管理机构,是他们在重商主义的新加坡,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适。
(三)横山庙的经济功能
横山庙具有经济功能,主要因为它是潘家村族产拥有者与管理者。
横山庙的资金来源,始于初迁兴利芭之时。当时“炉内潘”与卓姓人发生纠纷闹上法庭。潘春膑为替家族打官司,自捐了一百元,同时发动宗亲集资三百元来支付律师费。官司结束后,潘春膑将余款捐给横山庙。横山庙将钱出借,利息二分半。后来横山庙理事会为寄钱回祖籍地帮助修理故乡宗族祠堂,在庆祝潘府大人生辰时向宗亲募捐。所募款项大部分寄回故乡,余下小部分留在横山庙理事会。这两部分款项由理事会属下的基金会管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南安兵荒马乱,很多“炉内潘”人来到新加坡的“潘家村”。为了应付这种形势,1933年9月11日,横山庙理事会召开全体理事及南安炉内乡侨居新加坡之潘氏宗亲大会,讨论集资购买地产以供分居各处的宗亲集中在一起守望相助的问题。会议决定以认捐与劝捐的形式聚资购买族产。三个月后,横山庙理事会收到族人捐来的2464元,后以2794元5角买下了两块地皮(不敷部分由庙基金填补)约为11.6公顷,委托六名宗亲为地产信托人。理事会也决定,购置的地产以每年12元的租金租给族人。租者可以在租地上盖房建屋,亦可在房屋周围的空地上种植蔬菜果木和饲养家禽,但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如有迁移或售于别人,须俟地主(横山庙)凭准之后始作有效”。
横山庙的地产给新来乍到的一批批“炉内潘”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使他们可以较快地安定下来,这是吸引“炉内潘”人来兴利芭的经济原因。有了族产,“炉内潘”人便可以聚居在一起。因此,族产为新加坡“潘家村”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购置族产是潘家村建立的标志,而管理族产的横山庙理事会则成为“潘家村”实际的经济管理中心。
横山庙的经济力量对于维持这个由“炉内潘”人在移居地建构的“潘家村”的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横山庙的地租等收入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提供潘府大人生辰庆祝费用。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潘家村人都要举行庆祝潘府大人生辰的活动。这是“潘家村”每年最为重要与隆重的庆典。其内容包括上演酬神戏,标福物等。
其二、提供杏墩学校运作费用。在新加坡移民时代,华人社团兴办华校是很普遍的现象。“潘家村”也不例外。为了承担教育“炉内潘”族子弟的任务,1937年横山庙在潘家村兴办了一所杏墩学校,从中国聘请老师来教育村中的潘族子弟。杏墩小学的费用主要来自横山庙的地租收入。
其三、照顾“炉内潘”族中老人和扶持需要帮助的族人。并非所有南来过番的“炉内潘”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有些人穷困潦倒,终老时连回故乡的盘缠都筹不起。横山庙便负起照顾这些老人的责任。横山庙盖了两间简单的宿舍,让这些孤苦老人在此吃住,终老时送他们返故乡。类似于今天的老人院。另一方面,横山庙也照顾南来的“炉内潘”新客移民。当这些过番新客一时找不到工作,也可先在横山庙内的宿舍里免费吃住,直到他们找到安身之处为止。
(四)横山庙的社会功能
在“潘家村”,横山庙是这一社区的中心,横山庙理事会则是管理与执行“潘家村”运作的最高机构。理事会定期在横山庙举行,讨论与处理村内外或与村民相关的各项事务,议决各项重要的决定。例如购买地产、兴办杏墩学校等。
在移民社会,不同社群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械斗是常有的事。每当“炉内潘”人与外姓发生冲突,便由族长潘春膑、潘南山代表横山庙出面与外姓人谈判解决。“炉内潘”人曾因为地界问题与南安黄姓族人发生冲突,横山庙便找新加坡华社重要侨领之一、也是南安黄氏族人的黄亦欢交涉,经过双方族长的谈判,终于得到解决。
在潘家村,村民间也会因事发生冲突。每当此时,村民们就到横山庙找族长,让理事会来仲裁。二战以前,村民对横山庙潘府大人极热爱,族长和理事会在村中威信很高,由他们做出的仲裁村民一般都能接受。
横山庙还是潘家村的教育与文化中心。据南洋大学历史系的调查,潘家村的“炉内潘”父老在南来以前有60%为文盲,30%只受过很少的私塾教育。他们希望在新加坡成长的下一代能有机会受教育。随着拓荒生活的渐趋稳定和兴利芭第二代潘氏子弟逐渐长大,教育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但是兴利芭地处一隅,远离市区,潘家子弟很难就学于城市学校。于是横山庙便在1937年兴办了杏墩学校,从中国聘请老师教育潘家子弟。学校实行董事制,董事均为“炉内潘”族人。该校于1938年向政府注册。
一年一度的庆祝潘府大人诞辰活动是潘家村村民最重要的文化娱乐。这是一项全体“炉内潘”人共同参与的活动。整个活动持续三、四日。在此期间,横山庙上演南音、高甲戏等传统福建地方戏。
此外,横山庙也从中国买来一整套锣鼓设备,组织了一支村锣鼓。平时让村民练习娱乐。如遇乡村附近举办神赛会或族人家中出殡,横山庙便出动锣鼓队沿街表演或送行。大锣鼓队为远离市区的潘家村村民提供了一个娱乐的机会。
总之,二战前的横山庙承担了社会组织的功能,维持了潘家村内外社会的稳定。
那么,一个祭拜潘府大人的横山庙,又是如何能作为“潘家村”政治中心、承担起管理和执行潘家村运作的功能呢?
1、整合新加坡“炉内潘”人的横山庙。
如上所述,潘家村在二战前,其村民基本上都是“炉内潘”人。然而,这些 “炉内潘”人来自不同的宗支和房头。如何使他们重新整合并建立起对新社区的认同感,是潘家村能够正常运作的重要关键所在。而能够扮演整合南来的“炉内潘”人角色的正是横山庙。
对于南来新加坡的南安“炉内潘”人来说,横山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与居住条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与凝聚的中心。这是因为横山庙内供奉着“炉内潘”人的祖神潘府大人。根据“炉内潘”人的诠释,潘府大人兼具祖先和神明两重身份。潘府大人的潘姓,可以视为“炉内潘”人的远祖。但他并非南安“炉内潘”人的开基祖先,所以只能是保护开基祖先的神明。对潘府大人兼具祖先和神明两重身份的诠释,非常适合建构“炉内潘”人对潘家村新社区认同的需要。由于南来新加坡潘家村的“炉内潘”人来自祖籍地不同的宗支和房头,潘府大人的远祖身份能够让他们跨越宗支和房头的差异而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在这个意义上,横山庙在潘家村扮演了“潘氏宗祠”的角色。事实上,当南安炉内潘氏族人离开祖籍地,在新加坡兴利芭重建他们的新家园“潘家村”时,横山庙就是这些跨越宗支和房头的“炉内潘”人的宗祠。在潘家村,“炉内潘”人祭祖是在横山庙,曰“在庙里祭祖”;对横山庙购置的地产,“炉内潘”人称之为“族产”;横山庙理事会主席则被称为“族长”。而横山庙的建造也是仿造祖籍地“潘氏宗祠”的样式。
横山庙所扮演“宗祠”角色,在潘家村于二战后两次面对重大社会变迁的挑战时,都发挥了凝聚“炉内潘”人的重要功能。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社会发展和二战后实里达种植经济的衰落,曾经冲击了聚族而居的潘家村。为了加强“炉内潘”人的凝聚力,1957年4月28日,横山庙召开特别董事会议,研究修建横山庙的问题,并在接下来的几次特别董事会上讨论庆祝叔祖圣诞与修建庙宇的工作。这样频繁地召开董事会议,在横山庙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并不多见。横山庙的理事们希望通过发动宗亲认捐,修建庙宇,庆祝祖叔公圣诞等活动,重新唤起族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家族的认同,以此加强“炉内潘”人的凝聚力。1981年,潘家村族产被政府征用。在政府搬迁计划下,村民们将迁移到政府组屋居住。潘家村与横山庙很快就要从兴利芭消失。当潘家村解体后,如何继续维系“炉内潘”人的联系与凝聚纽带?面对这一重大挑战,横山庙理事会的理事们和“炉内潘”人艰难奔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重建横山祖庙事务中。为了重建横山庙,理事们和许多潘氏族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因土地赔偿问题上法庭与政府有关部门打官司。但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这个祖庙是我们潘姓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我们族人)有共同信仰的地方。”。现在,“炉内潘”人已经在义顺工业区内重建了横山祖庙。潘府大人作为维系“炉内潘”族人的凝聚力量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出来。
然而,潘府大人虽被新加坡的“炉内潘”人视为远祖,但毕竟他不是在祖籍地“潘氏宗祠”和各房支供奉的祖先。为了使潘府大人与祖籍地的血缘祖先相区别,潘家村人以对待神明的方式来祭拜横山庙里的潘府大人。横山庙在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庆祝是潘府大人的诞辰以及陈李二将军,同时上演酬神戏。80年代以后,潘家村内的“炉内潘”人虽然已经陆续搬迁到新建的义顺新镇和全岛的各个地区。但到了九月二十七这一天,散布在新加坡各处的“炉内潘”人都会回到横山祖庙相聚,参与祭拜祖叔公潘府大人的仪式和聚会。与早期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庆祝活动,除了“炉内潘”人及后代和他们的朋友外,还邀请国会议员和各地潘氏宗亲参加。上述内容显示,横山庙在扮演“宗祠”角色的同时,它也具有如一般华人庙宇的形态。
总括以上所述,新加坡的横山庙把来自祖籍地不同宗支、不同房头的“炉内潘”人重新整合起来,聚集在潘府大人的旗帜下,为潘家村的建立与运作奠定了重要的认同基础。
2、维系潘家村与周边社区纽带的横山庙。
二战前,潘家村内的外姓很少。二战以后,外姓村民逐渐增加。另外,潘家村周围还有财启村、黄梨山村、海南村等其他的村落。因此,横山庙所要处理的不仅有潘家村内部潘族人之间、潘族人与外姓村民之间的事务,还有潘家村以外、与别的村落村民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潘家村存在的历史时期,“炉内潘”人曾与外姓或外村人发生过矛盾和冲突。横山庙理事会作为潘家村的管理机构,曾处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然而更多的时候,潘家村与睦邻村落和其他姓氏的社群都能友好相处。而横山庙对于维系潘家村与周边社区和其他姓氏社区的睦邻联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虽然横山庙里供奉的潘府大人是“炉内潘”人的祖先,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神明。民间信仰在意识形态上是超越祖籍人群之分别的。寺庙神唯有附着在不同祖籍移民的分类意识上才构成一种排外的认同标准。正因为横山庙虽然具有“潘氏宗祠”的功能,但它同时也是一间华人庙宇,具备一般庙宇的功能。所以即使在潘家村内几乎是清一色“炉内潘”人,在二战前,横山庙也从未规定外姓人不得入内祭拜。只是由于当时外姓人惧怕潘族人多势壮,加上地界、孩子吵架等纠纷与潘族人结怨,故不敢或不愿前来。二战以后,潘家村的外姓人已逐渐增加,外姓人对潘府大人的祭拜便多了起来。1996年笔者曾参加横山庙庆祝祖叔公潘府大人诞辰活动,在现场访问了一位正在烧金银纸的陈姓老人。他今年已七十多岁,祖籍福建安溪,他说他祭拜潘府大人至今已四十多年了。另一位同样是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告诉我,二战以后,别的神明做大日子,可来请潘府大人当贵宾。如果别的村落有灾祸也可来请潘府大人去驱鬼消灾。潘家族人潘扬会老先生也说,战后,潘府大人的祭拜多了起来,不仅南安“炉内潘”人拜,“海南潘”,“潮州潘”也来拜,从而减少潘家村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和冲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整合。
横山庙在维系兴利芭社区睦邻友好的功能,充分体现了“神明是不分姓氏”这一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
五、结论与讨论:海外华人宗族社会的建构与特征
潘家村是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建立的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它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因政治经济的变动而产生海外移民问题和十九世纪新加坡实里达流域经济开发的直接产物。虽然潘家村在新加坡社会历史发展中仅大约存在了八十年之久,但它的发展与演化,为研究海外华人的宗族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
关于东南亚华人社会是否存在宗族组织与宗族社会的问题历来有争论。Freedman从其对华侨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东南亚不存在华人宗族社会,因为“宗族是不能移植的”。陈其南根据台湾汉人社会的研究结果,认为“并不是宗族本身的不能移植,主要是华侨的观念中不积极加以移植”。比较Freedman和陈其南两种看法,虽然他们讨论东南亚华人宗族的角度不同,前者讲的是客观环境,后者注重的是华人主观愿望,但他们都对东南亚存在华人宗族持否定态度。潘家村短暂的历史显示,上述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聚族而居的潘家村建立和运作的情况看,宗族组织是华南移民在东南亚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所建构的社会形态之一。这应是可以肯定的事实。那么,是否华人移民在主观上不愿意移植宗族?从潘家村这个个案,显然也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因为如前节的研究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需要移民新加坡实利达的“炉内潘”人,在兴利芭建构一个聚族而居的新“潘家村”。在主观愿望上,来自“炉内潘”族移民,也在尽力运用祖籍地的文化传统以建立他们的新家园。例如,潘家村通过认捐与劝捐等形式,力图建立新加坡“炉内潘”族人的族产;横山庙理事会扮演宗祠的角色,按照宗祠的组织原则,由四房成员组成潘家村的管理机构等等。这些都显示出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对传统家族的坚持。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宗族能否移植?从潘家村的建立和运作的历史,很清楚显示东南亚华人宗族社会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这是因为一般说来,中国人缺乏举族迁徙的传统,除非面临不可避免的威胁。在无法举族迁徙的情况下,祖籍地家族社会形态便难以完整地移植到移居地。换言之,海外的华人宗族社会是重建而非移植。以新加坡的潘家村为例,虽然它主要由祖籍地的“炉内潘”族人所组成,但它并非故土宗族的移植,“炉内潘”人在祖籍地的宗祠、宗支、谱系、祖先牌位、族产、族田,以及与潘氏宗族社会相适应的宗族关系与宗族制度等无法完整地移植到新加坡。因此,新加坡的“潘家村”是由部分“炉内潘”族人在新加坡社会文化脉络下重新建构的宗族社会。
那么,华人移民是如何在海外重建家族社会?潘家村历史亦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本文的研究显示,来自福建南安的“炉内潘”移民,运用传统中国社会祖先崇拜与神明信仰的文化资源,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社会文化脉络下,重建了一个聚族而居、具有血缘、地缘、业缘三结合特征的“潘家村”。
“炉内潘”移民对传统中国祖先崇拜与神明信仰文化资源的运用,集中地体现在祖籍地分炉而来的横山庙的社会功能上。在新加坡“潘家村”的重建过程中,横山庙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炉内潘”人南移新加坡时,横山庙以“炉内潘”人的祖神潘府大人作为认同象征,把来自故土宗族的不同宗支和房头的“炉内潘”人重新整合起来,为重建“潘家村”奠定了重要的认同基础。在潘家村建立之后,横山庙又以其双重功能维持这个新移民社区的运作:一方面横山庙承担宗祠的功能,透过沿袭自祖籍地的四房宗亲组成的理事会,管理潘家村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另一方面,横山庙又透过民间信仰体系承担庙宇的功能,维持潘家村内部和潘家村与周边社区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社会稳定。横山庙对于潘家村建立与运作的重要意义与功能,说明了祖籍地传统的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社会重建宗族组织结构的重要意义。
上述横山庙的社会功能,也显示了华人在海外建构宗族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即华人移民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调适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使重建的宗族社会表现出与祖籍地不尽相同的特征。就中新两地的“潘家村”而言,其最大的差异亦体现在横山庙的社会功能上。由于“潘氏宗祠”不可能从南安炉内搬至新加坡兴利芭,新加坡的“炉内潘”人便以供奉祖神潘府大人的横山庙替代。这样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中新两地“潘家村”祖先崇拜的形态。
第一,祖先崇拜对于中新两地的“潘家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在“祖先”的认定上,两地的“潘家村”却差异很大。祖籍地的“潘家村”,“祖先”来自开基祖,是一个自然的形成过程;而新加坡的“潘家村”,“祖先”来自人为的认定,由一个据说是潘季驯的“祖神”的潘府大人充当。
第二、由于祖先来源与祖先认定上的差异,两地的“潘家村”在不同的地点祭拜祖先。在南安炉内的“潘家村”,潘族子孙在开基主的“潘氏宗祠”和各宗支、各房头的宗祠里祭祖;新加坡的“潘家村”则在横山庙里祭祖。
上述差异表明,与华人祖籍地由自然血缘延续而形成的宗族社会相比,海外华人的宗族社会具有人为建构的特征。尤其是在移民社会初期,这一特征更为明显。这些海外重建的宗族,“祖先”不是自然产生,而是人为的选择,而且祖先与子孙之间不一定要有明确的谱系可寻,甚至可以如新加坡的“潘家村”,以亦祖亦神的“潘府大人”作为共同祭拜的祖先。事实上,以人为的方式重建宗族在移民社会早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它不仅发生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也存在于台湾汉人社会。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早期曾出现 “合约式”宗族。这类宗族以祖籍地祖先、即“唐山远祖”为祭祀对象。透过宗族成员间虚拟的血缘关系而建立。“合约式”宗族多采用自愿的方式,通常是以契约认股的方式组成。宗族内部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祖籍地传统宗族组织的“照房份”,而是采用“照股份”。
最后,笔者要讨论华人宗族组织或宗族社会在当代新加坡的状况。“炉内潘”移民在新加坡兴利芭重建的潘家村,在20世纪80年代因新加坡的市区重建而被拆除了。这并不仅仅是潘家村的命运。事实上,新加坡所有的华人村落,都在新加坡建国以后因城市建设而消失了。当这些村落尤其是那些姓氏家族村落,如兴利芭的潘家村、兴合园的苏家村等消失后,他们是如何处理祖先崇拜、家族凝聚等问题?从潘家村的情况看,“炉内潘”宗族关系的延续与宗族成员间的联系是通过横山庙的再次搬迁和重建。1999年笔者曾在义顺新镇工业区的新建横山庙,就潘家村消失后横山庙的功能问题再次访问时任横山庙副理事长的潘扬会老先生。潘老先生告诉笔者,潘府大人是新加坡所有有“炉内潘”血脉之人所共有的祖先,只要横山庙在,“炉内潘”人世世代代都知道自己的根源所在。所以,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聚族而居的潘家村,但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居住在新加坡四面八方的“炉内潘”人还是会扶老携幼来这里参加潘府大人诞辰的活动。所不同的是,横山庙搬到义顺工业区后,它已经成为新加坡众多华人庙宇中的一座,潘府大人的崇拜者更为增加。不过,“炉内潘”人及其他们的后代与这些信徒不一样,对他们来说,潘府大人不是一般的神明,而是他们的“祖叔公”、“祖神”。
值得提出的是,在潘家村消失后,不仅作为“神明”的潘府大人有了更多的崇拜者,作为“祖先”的潘府大人也受到更多子孙后代的祭拜。成立于1938年、由来自不同地缘的潘氏组成的“南洋潘氏总会”,其会所现在就设在新横山庙的二楼。该总会在横山庙里举行祭祖仪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热潮的推动下,1989年10月南洋潘氏总会举办了世界潘氏宗亲恳亲联谊大会。四十多位来自港台与大陆各地的潘氏宗亲专程来横山庙祭祖,以示慎终思远,饮水思源的心意。由此可见,虽然潘家村消失了,但作为“炉内潘”人及其子弟仍坚持他们在新加坡潘家村时代形成传统方式祭拜祖先:在横山庙里祭拜祖叔公潘府大人,显示出在祖先崇拜上问题上,他们与祖籍地不尽相同的本土特征。而与此同时,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潘府大人也从“炉内潘”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成为全世界潘氏宗亲认同的“虚拟”先人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透过对新加坡潘家村短暂历史的考察,以一个具体的个案讨论了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社会文化脉络下,华人宗族社会的建立与运作的状况。本文认为,东南亚华人的宗族社会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而是一个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在移民社会初期,华人宗族组织和宗族社会的重建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不同于祖籍地的社会环境下,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使之能适应新的人文条件,由此也在祖先崇拜的形态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形态。伴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在新加坡社会形成的新形态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当地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些传统的内容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华人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发展起来的本土特色。
注释:
[1]笔者在任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期间,对福建南安乐峰镇炉内乡潘氏宗族和新加坡义顺的“潘家村”进行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在研究和写作本文期间,得到新加坡林孝胜、林源福、黄雅辉等多位学者和中新两地“炉内潘”族人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笔者特别要感谢新加坡横山庙副理事长潘扬会先生。他抽出宝贵时间多次接受访问,不厌其烦为我解答中新两地“潘家村”的有关问题。笔者也要感谢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和新加坡横山庙理事会资助的研究经费。
[2]林源福:《义顺社区发展概述》,《义顺区村落图》,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1987年出版(非卖品),第36~39页。
[3]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显微胶卷,编号:ROD26。
[4]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显微胶卷,编号:ROD 8。
[5]林源福:《义顺社区发展史》,第39页。
[6]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出版,第133页。
[7]杨进发:《陈嘉庚 1874~1961》载《怡和轩俱乐部9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1995年出版(非卖品),第49~50页。
[8]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页197。
[9]据“炉内潘宗庙董事会”1994年12月23日资料(未刊文)。1969年9月,由当时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师生组成的华人村落调查小组曾在潘家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撰有调查报告(油印本)。该调查报告保留了不少七十年代以前有关潘家村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教育诸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以下所提调查报告均出自上述调查报告内容。
[10]“苏成庆录音访谈”,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录音卷1~2》,1985年。苏庆成是苏天富的儿子,生于1897年。
[11]有关“炉内潘”构买族产一事,见下节的讨论。
[12]横山庙理事会1957年3月31日、4月7日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为手抄本,现存横山庙董事部)。
[13]横山庙理事会1981年7月8日、8月22日、9月24日、11月15日会议记录。
[14]横山庙理事会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五日会议记录。
[15]有关内容将在下节讨论。
[16]横山庙理事会1957年4月28日、7月28日、12月1日的会议纪录。
[17]潘扬会访谈资料。载《潘家村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第78页。
[18]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出版,1987年,第125、117、141页。
[19]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年出版,第141页。
[20]陈其南:《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台北,第433~348页。
[21]庄英章:《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台湾,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897年出版,第478~479页。
〔责任编辑 吴文文〕
From"Lunei Pan"in Nanan Fujian to Singapore's"P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n Nanyang Chinese clan village
Zeng Ling
In modern times,a group of frontiers immigrated from southern China to Southeast Asia.After emigrating,they faced the common problems on rebuild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broad.The 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cla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debate in academic field.This paper specifically studies the Chinese village clans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Pan village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in a case study approach,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cent immigrants'clan society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The Chinese clan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n is not simply a transplantation,but also a reconstruction in a new social environment.Especially in the early immigrant community,the Chinese cla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s depend on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ancestral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resources.In places different from ancestral home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e Chinese must also adjust these cultural rules,so that it can adapt to new cultural conditions,which also have some variationsin the clan structure,morphology and ancestor worship.
migration from south China,Pan village,Hengshan Temple,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曾玲(1954~),女,山东济南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