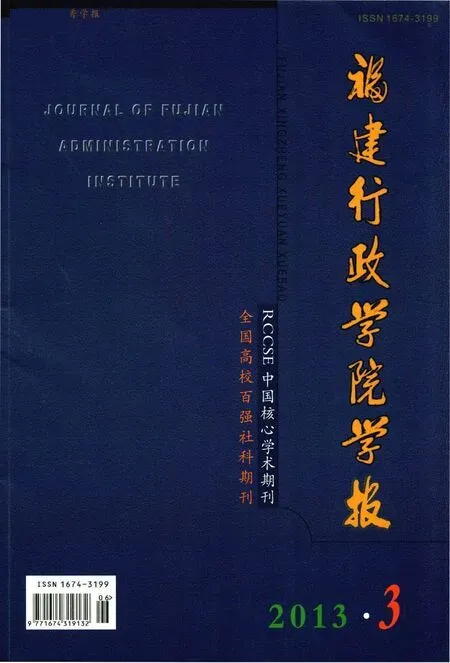行政裁量的司法控制研究——基于79个经典案例的实证考察
2013-11-04史意
史 意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一、研究缘起与样本说明
每一个政府都是兼有法治和人治的,行政裁量权无疑是两者的结合体。其作为法治国家的特性,已经完全渗透到行政法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作为政府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来源之地,裁量权扭转了传统行政的“传送带”定位。然而“每有讴歌裁量的事实,就会伴有裁量危险的事实:只有当正确运用的时候,裁量方才是工具,就像一把斧子,裁量也可能成为伤害或者谋杀的器具。”[1]27面对浩浩荡荡的裁量之势,如何规制其使用已经成为行政法的核心问题。
“法无授权即禁止”,从这个角度看,通过立法授权的限缩似乎能够从本源上控制行政裁量的空间。然而,从行政实践活动来看,之所以存在自由裁量权,正是因为立法者不知道如何针对各种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则。“立法机关看到问题之所在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则屡见不鲜,于是,就授权他人解决这个问题,告诉被授权人其希望的是真、善、美,公正合理的结果或者促进公共利益。然后被授权人通过逐案的考量,逐渐啃噬该问题,并且为大问题的每一小部分找到有限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思维往往处于最佳状态。”[1]21这种立法本意与我们希冀的立法控制相冲突,因此,将裁量控制的主力置于立法机关似乎显得力有不逮。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裁量基准则受到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大力追捧,这种“自我断臂”式的控制模式无疑对处于迷茫途径中的裁量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通过细化和量化规则,裁量基准将大量的散漫裁量收归囊中。但是,近年来,学者对此也提出一些反思,比如,“关于同一个事项,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裁量标准;这些裁量标准,设定主体与发布时间各异,各裁量标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等等。”[2]“实践中试图大规模地制定裁量基准并通过基准的普遍适用来控制自由裁量的做法,除了可能带来裁量的格式化甚至僵化,也存在着合法性方面的问题。”[3]这些异议,无疑对“飞蛾扑火”式的裁量基准控制方式泼了一盆冷水。受制于权利竞争的本位意识,我们认为,行政裁量基准只能过滤部分裁量滥用,其他溢于基准范围之外的裁量行为却不能受到任何有效规制。因此,为了最大化个案正义的实现,从而契合行政裁量的本位功能,行政裁量的司法控制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所在。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将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却认为“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泛泛地谈合理问题,尤其是在违背了合理性要求的时候,却不能够在诉讼上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那么,这样的合理性要求与其说是法律上的,倒不如说更像是道德上的要求。”[4]77而将合理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放在一个层面上,就使得“不合理”构成合法性审查的一个标准集合体。这种理解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滥用职权”标准相契合,也为行政裁量的司法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法律依据。
然而将行政裁量控制放置于司法审查的角度,也并非无可争议。其受到了司法有限性观点的诟病,后者认为前者会导致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僭越以及司法权的极度膨胀。这种担心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值得我们深思。审查强度由此也成为行政裁量司法控制的问题所在。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所言:“行政行为中的裁量,是法律作为专属于行政权的判断的事项予以委任的领域是否存在以及其范围的问题,即法院在何种程度上必须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厅的判断为前提来审理的问题。于是,裁量在实务上成为问题的,是以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的形式出现的。”[5]81在此问题上,有的学者引进了日本的“判断过程审判方式”,即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陈述,对行政机关以何种方式考虑何种事项作出行政行为进行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对裁量过程的妥当性进行评价。[6]有的学者则认为“审查标准日渐抽象化,将能逐渐推动行政裁量的‘原则之治’,从而实现‘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的转换”[7]这些学说对于丰富行政裁量司法控制理论、指导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中国本土化的行政裁量司法控制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对本土司法经验与智慧的总结和提炼。
本文以行政裁量为观察对象,主要通过对《人民法院案例选》和《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所刊载的典型行政裁量案件的阅读整理,试图展现行政裁量的多样性以及司法控制的灵活方法,进而提炼行政裁量审查对象及标准的本土司法经验。通过检读我们发现,截止到2011年底,《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公布的近900个典型行政案例中,涉及行政裁量的有74个;《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上公布的典型行政案例中,涉及行政裁量的有3个;《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中涉及行政裁量的有2个。这79个典型行政裁量案例涉及政府、交通、公安、环境、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会保险、工商、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林业、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海事、水产、卫生、税务、医药等24类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公开、行政征收、行政赔偿、行政合同等13类行政行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司法实践中行政裁量案件的现状,构成了本文的基础性研究资料。
在构成本文基础性分析样本的79个案件中,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观上意见一致、行政机关最终胜诉的案件有29个,占所有案件的36.7%,且其中包括大量由用人单位提起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观上意见相左、行政机关最终败诉的案件有48个,占所有案件的60.8%。这些行政裁量案件具体的判决形式及比例如表1所示。

表1 行政裁量案件结案形式和比例表
这一结果不仅显示出行政裁量不合理运用的情形大有存在,也反映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典型案件中得到了充分维护,从侧面展现出司法能动主义的现实图景。在下文的研究中,笔者将通过对这79起典型行政裁量案件的解读,试图剖析出进入司法审查视野的行政裁量种类以及法院审查行政裁量所动用的智识资源,从而提炼出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本土经验,为行政裁量理论提供司法治理的窗口。
二、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对象
传统的二元论认为,法律领域和裁量领域是相区分的,在裁量领域,行政机关是绝对自由的,因此法院只能审查行政机关在法律领域的活动。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裁量一元论大有取代二元论之势,其认为:裁量问题与法律问题并非各自独立的二元,裁量问题不过是法律问题中的那些不重要的问题;所有的行政裁量都是法律授权的结果,根本不存在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8]本文即是根据一元论的学说,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探析行政裁量。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司法文本中的行政裁量权包括行政主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就事实认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法律适用、行为与否、做出何种行为以及程序选择上的权力。
(一)事实认定裁量
从证据的种类到取证的方法,从证据的收集到证据的认定,从行政程序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到证据量的充分性,从行政推动和行政认知到证据与待证事实间的关系,从根据已有证据自由心证获得事实结论到对事实的定性,行政主体享有广泛的裁量权。[9]这种通过证据还原事实的过程中存在的裁量即是事实裁量。关于事实裁量是否属于裁量范围,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在日本,传统学说和司法实践对于事实裁量一般不予承认,但是近年来随着行政裁量领域的扩张,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承认在要件认定上存在裁量的趋势,“裁量问题在与法院审查的关系上采取这样的形式,使裁量和羁束的范畴区分已经有困难了,而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审查密度的程度如何成为问题。”[5]85-86我们认为,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任意地认定其偏好的事实,那么行政机关就可能改变法律目的的运作,事实认定也极有可能成为裁量滥用的庇护所。因此,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将事实裁量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例如,在“何希光不服汕尾市工商局查扣其随身携带外币的行政处罚决定案”[10]中对于何希光主张其所携带的外币是其母经向海关登记申报携带入境的事实到底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又如在“费列罗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确认案”[11]中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能不能证明申请商标经长期和大量的使用在消费者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认知度成为“显著性”事实认定的关键。
(二)法律适用裁量
行政机关必须以适用法律的方式活动,因此在庞杂的法律体系中如何进行法律筛选成为行政裁量的应有范围之一。不同的法律适用往往对利益衡量的取舍起着关键作用,法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无疑是对法律的“二次适用”。例如在“慈溪市掌起镇经纬汽车配件厂诉慈溪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12]307中,在上位法对未报批环评文件但项目已经投入生产的情况下使用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无任何规定,而下位《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却对此责任明确时,该不该适用此地方性规章成为当事人争议的核心所在。在“樊秀芝等63名退休教师不服南宁市人民政府不予接收随校归口教委管理案”[13]418中,“国家经贸委等五部委184号文”并未确定企业自办学校的移交时间以及人员范围,而南宁市政府通过147号文件以“企业提交分离申请前三个月正式在岗职工名单为基础”限定了移交时间及人员范围,在审理案件时,能不能适用147号文件成为当事人的主要争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中,《行政处罚法》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而苏州盐务局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实施了处罚,这种处罚依据是否合法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
(三)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
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的关系,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在德国和台湾,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严格区分,认为“裁量的客体是法律后果,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判断余地的客体是法定事实要件”[14]132-133“行政机关通过裁量授权获得活动空间,通过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获得判断余地。”[14]124但是近年来反对之声越来越强烈,认为“二者虽非毫无差别,惟不构成本质上之截然不同。在从事概念运作之际,尤其难作理性类形式之区分。”[15]我们认为,由于法律语言本身的缺陷和事物的复杂性,不确定法律概念也存在滥用职权的空间,因此有必要纳入司法控制的领域。比如在“佛山市永发贸易有限公司诉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案”[16]中,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为设立国际交流学院而申请划拨土地,政府由此批准因而征收了永发贸易有限公司的土地,此征收行为到底合法与否就涉及到对“公共利益”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在“南通顾艺印染有限公司诉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17]中,职工王云海未沿最短线路回家,而是绕道稍远的路线陪同妻子一起下班,期间出现车祸,在工伤认定时就涉及到对“下班途中”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又如“王齐双诉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履行法定职责案”[18]中,对于“6个月”到底指的是以“日”为标准的180天还是跨度达到6个“月”即可,成为本案原告领取医疗保险金数额的争点。
(四)决定裁量
决定裁量指的是行政机关在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所做的合理选择的权利。一般立法常常用“可以”“得”等模糊的词语,这就使得行政机关在是否做出行政决定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裁量权。比如,在“张志发申请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行政赔偿案”[19]475中,行政机关在发现张朱明醉酒后并未将其带到派出所救治而是打电话通知其家属,其是否尽到救助义务成为本案的争点。相反,在“陈小青不服隔川乡人民政府撤销离婚证案”[19]469中,行政机关在确认陈小青和李桂明离婚协议合法的基础上,仅给陈小青一方离婚证书,后又以“当事人在申请离婚登记时未能及时地提供法定的离婚材料,造成工作人员失误”为由做出撤销离婚证书的决定。在此案中,行政机关撤销离婚证的此种行为是否合理成为案件的焦点所在。
(五)选择裁量
选择裁量包括法定方式的裁量和法定幅度的裁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如果公民违反此规定,那么行政主管部门就可以在“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或“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并处以罚款”之间择一决定,若选择并处罚款,那么罚款的数额就属于行政机关的幅度裁量。如在“石六少不服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分局治安行政拘留决定案”[20]316中,在石六少与工商所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并彼此造成轻伤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给予石六少7日拘留的处罚决定是否合理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法院最后判决将其变更为200元的罚款。这就是行政机关在处罚方式上的裁量。又如,“顾维诉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红桥支队放行事故车辆行为违法并行政赔偿案”[21]中,交管局在收取35000元担保金后就放行了肇事车辆,顾维以其担保金收取过少远达不到其应得的民事赔偿金为由请求行政赔偿。此案中,交管局收取担保金的数额大小就属于行政机关的幅度裁量。
(六)程序裁量
行政程序指的就是行政行为的步骤、顺序、时限、方式共同构成的过程。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沿袭加之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方面拥有较大的裁量权。但是,随着程序观念的兴起,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俨然已经成为行政法前进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程序由此也取得了自身的独立价值。而站在司法机关的角度,“考虑到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法院转而试图审查行政机关所履行的程序或者其判断过程的适当性及合理性。”[22]例如在“阳山县灰沙砖厂诉阳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认定纠纷案”[23]269中,被告在给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时,只给予其一天的举证时间,此时间裁量的确定合理与否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代学平等诉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公安行政确认案”[12]284中,公安机关为了控制代鹏跳楼自杀,向其面部喷洒了辣椒水,此行为合理与否即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又如,在最高人民法院第6号指导案例中,工商局在没收何伯琼33台电脑主机时是否应告知当事人享有听证的权利成为案件的争点。
三、行政裁量司法控制的标准
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裁量进行审查时,既要坚守司法的底线,避免对行政权的僭越,又要充分发挥能动性。那么,人民法院在夹缝中究竟动用了哪些智识资源呢?换言之,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裁量案件中究竟采用了哪些审查标准?仔细研读这79起典型案例,在有限的“审判”主文和相对详尽的“评析”的字里行间中,大体上能够管窥到司法机关的审判智慧:其不仅沿袭了行政裁量规范主义治理模式,即结合“滥用职权”的明文规则标准来控制行政裁量,还通过行政法原则的阐释实现行政裁量的功能主义治理模式。总体而言,法院的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滥用职权”标准的运用
1.符合相关法律目的和政策。如前所述,立法者将裁量权授予行政机关,就是希望行政机关能够真正地将裁量权用在刀刃上,从而达到“真、善、美,公正合理的结果或者促进公共利益”。因此,实践中,立法目的和政策也就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裁量选择的方向和途径,以保证个案正义的最终实现。例如在“刘庆、吕维峰诉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24]中虽然一审和二审法院都只用了隐晦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来表明行政机关的程序违法,但是在评析中明确指出“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只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准备作出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而并不告知准备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处罚,这将是一个不完全的公开,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将得不到完全实现,这是不符合立法目的的。”在“介付超诉舞阳县林业局行政处罚决定案”[25]450中,就是否给予当事人听证权利的问题,法院即是将立法目的作为评判行政行为合理与否的依据。该案评析中明确指出“舞阳县法院在解决这一步遇到的问题时,把听证目的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听证首先是为了查清案情,在此基础上才适用处罚,而案情的查清直接关系到介付超八人的处罚结果”,从而保障了当事人的听证权利。上述两案,法院都是通过立法目的来寻求审判标准。而在“广州贝氏药业有限公司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滥用职权案”[26]的评析中则引入了政策因素,其行文中指出“对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开展政府定价工作,是药品价格管理的重大改革措施,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生产政策及医疗卫生政策有密切联系,是应该从全局角度综合考虑的问题。”因此,行政机关未举行价格听证会并不属于程序违法行为。在上述“樊秀芝等63名退休教师不服南宁市人民政府不予接收随校归口教委管理案”[13]418中,法院同样是引入了政策依据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该案中,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南宁市人民政府确定企业自办学校的移交时间和人员范围并不违反184号文的政策性规定。评析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本案中,由于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自办学校的分离事项未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关于企业改革方面的有关规定都是政策性规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对南宁市人民政府对樊秀芝等60名老师不予接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只能以政策为依据。”我们认为,通过立法目的和政策来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控制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2.考虑相关因素。相关因素是从行政裁量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言的,指行政裁量各环节和要素之间有着某种合理的关联性。相关因素对作出行政决定的推理质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能够保证行政行为基本上按照法律设定的目标方向做出有助于推进和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特定的目的和政策。[4]102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运用两种标准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控制:一为“未考虑相关因素”,二为“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例如在“肖子勇诉濮阳市公安局治安处罚案”[27]466的评析中,明确指出“从危害后果看,原告只拔了两棵树,事后又主动将拔掉的树栽到第三人的杏园中,且存活一棵,故原告具有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情节轻微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被告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不分责任大小,不论情节轻重,对三名违法行为人一律裁决治安拘留5日的处罚,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有关‘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的要求。”此案即是运用的“不考虑相关因素”标准。相反,在“上海东兆化工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静安分局行政处罚案”[28]中,一审法院明确指出“本案东兆公司无违法所得却被罚款40万元,静安工商分局对此辩称,该处罚还考虑到东兆公司成立之前的违法经营,静安工商分局对法律上不同经营主体的违法行为,采取合并处罚的方法,显属不当,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该案中,法院即运用了“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来作为判断选择裁量合理与否的标准。上述两个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相关因素”的适当性要求,也对行政机关合理行政提供了指引。
3.“显失公正”标准。“显失公正”标准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赋予司法机关的裁判标准。在此,行政机关不合理的选择裁量会变成实质违法,司法机关也可以变更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例如在“覃仕琼不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工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29]中,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称其所购28套‘南极人’保暖内衣一套也未售出,未给社会造成危害,被上诉人处罚款数额过大显失公正的理由基本成立”,因此作出了变更判决,将5000 元罚款变更为200 元罚款。又如在“郭佳诉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治安管理处罚案”[25]461中,法院判决明显指出“被告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给予其治安拘留15日之最重处罚显失公正,应予变更。”并将15日的拘留改为200元的罚款。再如上述“石六少不服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分局治安行政拘留决定案”[20]316中,评析认为“本案原告因第三人违法行政而与之发生争执,进而互殴,互致对方轻微伤,都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治安行政责任,受到相应的治安处罚。被告单处原告,且给予最重的一种治安处罚,即限制人身自由的治安行政拘留处罚,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没有超过法定幅度,但该处罚明显不符合理性、公正、客观、适度的原则,应属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从而将行政拘留7日改为治安处罚200元罚款。
(二)比例原则的援用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裁量行为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之间要合乎相当的比例关系。这其中又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即妥当性、必要性和法益相称性。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量的时候必须要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若采取的行政行为将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应该将其控制在最小损害的范围内,并且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标的追求之间也要合乎一定的比例关系。法院也正是通过比例原则来审查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例如在上述“慈溪市掌起镇经纬汽车配件厂诉慈溪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12]307中,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是否要告知原告限期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成为本案的实质焦点,一审法院对于告知程序只是一笔带过,认为“被告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经立案调查,并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后……该行政行为并不违法”,而评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案原告与慈溪市掌起镇五金厂位于同一经营场所,从事同样的五金加工生产,虽挂着两块牌子,实际是在统一从事生产经营。在执法过程中,被告已向慈溪市掌起镇五金厂发出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补办环保审批手续,并告知了逾期不补办的法律责任。原告负责人在被责令改正签收栏签字。故被告事实上已经告知原告限期补办手续,原告对其行为的违法性及补办环评手续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原告拒不办理补办手续,被告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不存在违反比例原则的障碍。”该案即是法院灵活运用“妥当性”要求的例证,虽然责令通知书的对象是五金厂,但是汽车配件厂与其处于同一经营场所,且由汽车配件厂的负责人签字同样能达到告知的效果,在该行政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目的时候,法院充分尊重了行政机关的裁量决定。而在“王丽萍诉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交通行政赔偿案”[30]89中,评析明确指出“中牟县交通局扣押车辆行为违反比例原则,属于滥用职权,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这种片面追求单纯执法效果,无视由此给相对人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在相对人提出合理预防措施请求时仍置之不理,是一种严重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为。”该案中,人民法院即是从“必要性”的角度来审查裁量行为的,虽然该执法手段能够达到惩罚违法行为的目的,但是仍然存在其他使相对人受损更小且同样能达到行政目的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法院最终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又如,在“陈宁诉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案”[30]94中,人民法院认为“气焊切割车门的方法虽然会导致车门破损,甚至造成轿车的全部毁损,但及时抢救韩勇的生命比破损车门或者造成轿车毁损更为重要。相对于人的生命而言破损车门或者造成轿车毁损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明显较小,交通警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气焊切割的方法强行打开车门救韩勇的行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该案则将重心放在“法益相称性”的合理性阐释中,将相对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相较衡,认为虽然行政行为造成了当事人的财产毁损,但却维护了价值位阶更高的生命权,符合“法益相称性”的意旨,法院也最终维持了行政机关的决定。
(三)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原则的援用
《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明确了行政诉讼的价值所在,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无疑即是该价值的题中之义。在行政裁量案件中,法院也始终贯穿了该项基本价值,其表现如下:
1.宪法基本权利至上——基于公民角度。宪法基本权利是自然权利的法定化,是公民自我生活、参与社会和国家管理的必需品,因此在基本权利行使期间,公民享有较大的豁免权。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审判时也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例如,在“邵宏升不服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案”[19]23中,法院在审理中认为“检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保障公民充分地行使这一民主权利,公民在行使检举权时,对其行为应享有充分的豁免权。因此,并不应强求其所检举的情况一定属实,国家机关亦不能仅因检举人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所出入便对其科以处罚,否则,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会丧失殆尽,亦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背道而驰。”该理由充分赋予公民检举权以对抗性,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样,在“成都蜀汉园林有限公司诉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纠纷案”[23]262中,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民工再就业应否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这一争点,案件评析从休息权和劳动权这两个基本权利的关系着手,认为“国家实行退休制度,劳动者达到一定的年龄可以离开工作岗位而回家休息。由国家或企业给予一定的生活费,或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是国家依照法律给予劳动者的一项权利,而并非直接规定为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后必须终止劳动的义务,既然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那么,劳动者则可以放弃这种权利的享受而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服务,《劳动法》没有禁止的即为可为。”该案从侧面展现了休息权和劳动权的互相兼容性,在超龄农民工放弃休息权而继续从事劳动时,其仍享有劳动权并属于《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
2.信赖利益保护——基于利害关系人角度。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但是其内容却显现在法条内容之间。基于法安定性的基本理念,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受到自身行政行为的约束,即使做出了不合法的行为也不能随意撤销,而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予以维持行政行为或者撤销后给予一定的补偿。例如在上述“陈小青不服隔川乡人民政府撤销离婚证案”[19]469中,评析认为“本案中,陈小青取得离婚证后即已取得了重新与他人结婚的资格,隔川市人民政府认定原离婚登记机关行为违法而予以撤销,并未考虑人民因信赖离婚登记的合法性并因此而产生的诸多的社会关系。”又如在“张正雄、王建群诉泸州市纳溪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征收社会抚养费案”[27]494中,评析认为“本案被告确定的社会抚养费计征基数,虽然略低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但是该基数的确定是经过当地政府讨论决定的,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同时也说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与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无正当理由再来提高原确定的计征基数,是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该案超越了规范主义路径,从司法角度明确提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充分展现了司法能动性及灵活性。
3.维护弱者群体利益——基于弱者角度。法律的生命离不开适用,而法律的适用更离不开社会。维护弱者利益体现了法律的社会关怀。如在一些工伤认定案件中,法院判决普遍偏向于劳动者,这就是法院对弱势群体特殊关照的体现。“北京易美易家家具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31]即是典型,针对劳动者超出本人工作岗位主动从事单位的其他工作而受伤是否应属于工伤的争点,该案评析并没有直接从事实认定角度出发,而是将工伤案件类型化分析,认为“对于单位和职工这两个主体而言,显然职工属于弱势群体,很多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给职工上工伤保险,不签订劳动合同,出事以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给点看病的钱就想不再承担责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不违反工伤认定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保护职工的利益”。同样,在“杨庆峰诉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予受理工伤申请案”[32]中,对于工伤认定的申请日期以“事故伤害发生之日”为准还是“事故发生之日”起算,法院认为“据医生介绍,铁锈沉着综合性具有特殊性,应根据伤害部位决定患者平时有无不适感觉及病变时间,若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明。由于本案中杨庆峰从发生事故到伤害发生病变间隔两年多时间,无锡市劳动局以2004年6月来确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不利于保护受伤害职工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而在上述“成都蜀汉园林有限公司诉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纠纷案”[23]262中,法院则将农民工列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该案评析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占很大的比例,其人均纯收入低,生活不富裕,且大量家庭中还有需要供养的学生、医治的病人。因此每家的富足劳动力通常都会选择到城市通过劳力挣钱补贴家用,其中不乏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而大多数省市将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安排排斥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外,这直接影响对超龄农民工在再就业时对受损权利的救济”。
(四)程序正当原则的援用
囿于司法机关的宪政定位,法院在对行政裁量进行审查时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及行政机关的主观判断问题。如果说行政机关在裁量时“戴着镣铐起舞”,那么法院在进行裁量控制时即是在“针尖上起舞”。从这个角度看,法院绕过实体问题,对行政机关的程序进行审查无疑为明智的选择,既尊重了行政机关的实体裁量,又促进了行政程序理念的深入发展。如在“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30]99中,在法律无规定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时行政机关是否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复议程序成为本案的争点,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行政复议机关拟作出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行使复议权利。行政机关未履行通知义务,属于程序违法。”又如在“何廷凯不服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治安处罚决定案”[33]中,在《行政处罚法》只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前必须告知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的前提下,还是否应告知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二审法院认为“未告知上诉人将受何种、何幅度范围内的行政处罚,其行政处罚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评析中也指出“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治安行政拘留5日处罚决定前,只履行了告知原告违法行为、处罚依据的义务,未履行告知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即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义务,且未对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进行复核,违反了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在“北京创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处罚案”[34]中,法院认为“海淀区人防办向创基物业公司送达了听证告知书,明确告知当事人可以在三日内提出听证申请,意味着自行选择适用听证程序,是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海淀区人防办对其自行选择适用的行政处罚程序,负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履行的义务。海淀区人防办在告知创基物业公司听证权的当日,在没有证据证明创基物业公司表示放弃听证权利的情况下,即向其送达了处罚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公正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司法判决中法院或通过“法定程序”或通过“公平公正原则”的用语来表达“正当程序原则”的观念,这种“中国特有的语言方式”成为审判理由的一大亮点,也需要我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仔细甄别。
四、结 语
行政裁量的泛化要求政府具有战略性的眼光和灵活处事的方式,这就必然与依法行政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裁量的边界由此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受制于权力制约的理念,法院无疑成为行政裁量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对79个典型行政裁量案件的分析,可以为中国法院面对行政裁量时的立场和功能提供一个窗口。我们认为,在行政裁量合理与否的判断基准上,法院展现出难得的司法能动主义姿态以及巧妙的司法审查技术,为行政裁量的控制提供了可鉴之材。
第一,审查标准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法院在对行政裁量案件进行审判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法律规定,而是不断拉伸“法”的菜单,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内能动地扩大了行政裁量案件的判断标准,有效克服了现行法律规范滞后性的负面影响。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不仅仅从立法目的、政策方面寻找审判理由,也将程序元素、基本权利元素、社会元素等等都置于法院判决中,丰富了裁量规制的素材。
第二,法院否弃机械式合法性审查的同时,并没有僭越行政权,而是在独立判断的同时,对行政机关的裁量自由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比如在上述“王丽萍诉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交通行政赔偿案”中法院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在“陈宁诉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案”中法院判决行政机关胜诉。虽然审判结果不同,但法院都运用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裁量司法控制的依据,这充分说明了司法机关在行政裁量控制中的公正独立性,而非一味的受制于权利竞争意识乃至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1]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M].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27.
[2]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J].浙江学刊,2006(6):124.
[3]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J].法学研究,2008(5):36.
[4]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77,102.
[5]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1,85-86.
[6]王天华.行政裁量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J].清华法学,2009(3):96.
[7]顾大松,周佑勇.论行政裁量的司法治理[J].法学论坛,2012(5):56.
[8]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J].行政法学研究,2006(1):24.
[9]朱新力.法治社会与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则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97.
[10]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223.
[1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4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433.
[1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2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284,307.
[1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418.
[14]毛雷尔.行政法[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4,132-133.
[15]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3.
[1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3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426.
[17]佚名.南通顾艺印染有限公司诉南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EB/OL].[2013-04-17].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Display.asp?RID=1242349.
[18]佚名.王齐双诉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履行法定职责案[EB/OL].[2013-04-17].http://www.fsou.com/html/text/fnl/1178029/117802917_3.html.
[19]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23,469,475.
[20]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年第4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316.
[2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306.
[22]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J].法商研究,2003(1):63.
[2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10年第4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262,269.
[2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6年第3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434.
[25]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50,461.
[2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3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71.
[27]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6年第2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66,494.
[28]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6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27.
[29]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2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382.
[3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89,94,99.
[3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460.
[3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3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453.
[3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年第1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303.
[3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4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