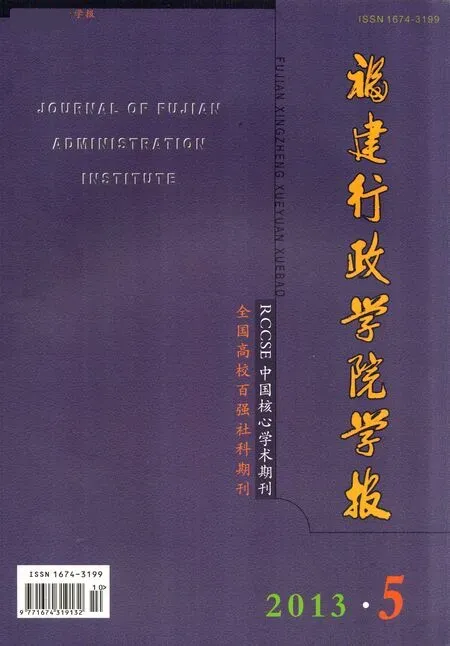制度、家庭策略与半工半耕型家庭生计策略的形成
——兼论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
2013-10-24罗小锋
罗小锋
(福州大学 社会学系,福建 福州350002)
一、研究缘起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小农经济仅能解决农户的温饱问题,无法解决农户的富裕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深深地被市场化大潮所裹挟,农民的生产生活严重地依赖于市场与货币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农业生产资料到柴米油盐等日用品都已经市场化了。诚如徐勇所言,农民已经成为社会化小农,农户已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1]社会化小农的货币化支出压力大。小农经济所产生的推力以及城市工商业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所产生的拉力共同将一批又一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到城市。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2]从年龄结构看,进城的农民以青壮年为主;从性别结构看,进城农民以男性为主。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进城的农民以青壮年和男性为主?从农户的角度看,这种安排如何作出的?这种安排对农户的生计有何影响?
学界对农民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下述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农民外出流动的动因;二是探讨农民工的状况,包括就业状况、城市适应状况、身份认同状况、权益受损及维护状况;三是研究农民外出流动的影响,包括对农村的影响、对城市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四是探讨农民工的阶级形成。
纵观已有文献,我们注意到已有研究甚少关注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生计安排。鉴于此,本研究拟从制度与家庭策略的两个角度考察农民工家庭的生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农户如何通过有效的分工来扩大家庭的生计来源,分析农户是如何作出部分家庭成员务农工、部分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决策?根据研究问题,笔者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
文中所用质性资料均来源于笔者于2008年暑假、2009年春节、2010年暑假在东莞、福州、厦门、龙岩、长汀等地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所做的调查。在调查中,笔者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所有访谈时间都在1小时以上,所有访谈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访谈结束后对访谈资料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誊写。
三、制度化的半工半耕
从制度层面看,农户半工半耕根源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有研究指出,进入改革时期,出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动机,同时结合均分土地的原则,我国创建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村庄按照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对土地的使用权。[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依然非常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每人平均分配土地2.4亩,每户平均9.2亩,每个劳动力耕种7.3亩土地。[5]众所周知,与从事工商业相比,务农的比较收益低。为谋求个人以及家庭的生存,农民在农业之外寻求出路。而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为农民外出提供了空间。
从市场层面看,改革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大批外资企业在东南沿海兴起。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这为农业剩余人口的外出就业提供了可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我国东南沿海的多数企业是加工企业,这些加工企业缺乏自有品牌、缺少知识产权,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底端和边缘。受制于此,这些企业本身能获得的利润不多。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外资企业不可能给农民工开高工资。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农村人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减少,这些国家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大多转变为市民。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不同步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受制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农民虽然在城市务工,从职业上看与城市市民没有差异,但身份上他们依旧是农民。农民工这个符号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具有讽刺性。城市政府发展经济,需要农村劳动力,但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城市政府出于自身治理的需要,维持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并阻止农民工成立工会。如此,分散的无组织的农民工处于被资本剥削的境地。农民工无法完成市民化的过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户半工半耕的形成是有制度根源的。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务工,而外出临时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作为保险。这样使得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6]
四、家庭策略的半工半耕
家庭策略概念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7]家庭策略是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旨在寻求家庭资源、消费需求和替代性生产活动方式之间的动态平衡。[8]新迁移经济学认为,外出流动的决定不是由独立个体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关人群组成的更大单位如家庭或家族做出的。在家庭中人们集体行动不仅是为了最大化预期收入,而且是为了最小化风险。不像个体,家庭可以通过对家庭资源(如家庭劳动力)分配的多元化来控制对家庭经济状况的风险,一些家庭成员留在当地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其他成员可以到其他劳动力市场工作。[9]
在本研究中笔者把家庭策略定义为:农民家庭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家庭的各种货币需求以及拓展家庭的收入来源,根据家庭的人口结构及家庭经济状况能动地作出部分家庭成员外出、部分家庭成员留守的家庭安排。调查发现,农民的外出决定是由家庭做出的,为了使家庭经济收入多元化以及家庭经济风险最小化,农民家庭会让家庭的部分成员外出。[10]由于农民家庭的人口结构不同,因此在人口外出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生计安排,有的家庭形成了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有的则形成了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下文我们从家庭策略视角分析农户如何作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职业、部分成员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的安排。
(一)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这种分工模式包括两种类型:男工女耕和女工男耕。许多研究注意到农民跨区域流动中出现了性别差异这一现象,表现在当外出的大环境相同时,外出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分配是有选择的。一般情况下,农民家庭会选择让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之所以让男性成为外出的首选对象,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
1.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思想的影响。帕森斯就认为,男人主要表现工具性角色,而女人扮演表达性角色。[11]谭深认为,这是源于许多家庭依旧保持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家务农、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结婚成家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12]李实的解释是:女性劳动力在结婚成家之前因为承担的家庭责任要小得多,因而有较多的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机会。当她们结婚以后,承担的家庭责任不断多起来,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家庭责任的增加意味着面临更多的选择,也意味着更有可能在赚取收入方面作出牺牲和放弃。[13]已婚女性迁移的最大约束是作为母亲的责任。已婚女性受传统分工格局的影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是合理的,教育子女、家务和照料老人的责任等都落在她们肩上,这降低了她们外出的可能性。[14]笔者认为,男人外出打工挣钱,女人留守料理家庭符合传统社会性别规范,此举表现了社会性别。
2.基于家庭效率的考虑。相对而言男性文化程度高,有手艺,能力比女性强,出门较能找到工作,更能挣到钱,而妇女在家里更会做家务事。这其实与贝克尔关于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致的。在贝克尔看来,虽然市场和家庭部门性别的明显分工部分地归因于从事专业化投资的获益,部分地归因于男女性别的内在差异。源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妇女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提高家庭效率,尤其是生儿育女的人力资本上投资,因而与男人相比妇女在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男人把大部分劳动时间用于提高市场效率的人力投资上,因而他们与女人相比在市场部门拥有优势。因而当人力资本投资相同时,一个有两种性别的、有效率的家庭,就会把妇女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家庭部门,而把男子的主要时间配置到市场部门。[15]类似地,有研究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因而被大量配置于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的报酬率高于男性劳动力,相反在非农业领域其报酬率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两种的收入差异主要源于他们在获取非农收入方面的差异。
3.男工女耕的家庭安排可以拓展家庭的收入来源,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般而言,男性拥有较多社会网络资源,男性工作可以实现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农民外出最初多是通过熟人介绍,做工做熟悉后老板会介绍活给他们做。
个案一:来自闽西某县的罗先生,一家四口,2004年以前,他一个人外出做工,妻子留守在家务农和照料家庭。
罗先生的妻子张女士认为,一个人外出一个人在家这种安排有利于改善家庭经济,“家里只有这么多田,一个人也是这么做,两个人也是这么做,外出做工的钱是多余来的。”与丈夫打工相比,尽管自己在家里负担更重,但从家庭整体着想她没有觉得夫妻之间的分工是不公平的。她说:“为了挣钱,这有什么办法,自己会更辛苦些!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更累,因为一个人出去挣钱,一个人在家等于钱会更多。”
个案二:彭女士,初中文化,30岁,与江先生于2002年冬结婚,一家八口。
访谈中彭女士告诉笔者,结婚后有两三年时间是这样的:上半年夫妻都在家里种烟,多的时候十多亩,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亩。烟叶收成后,八月中秋节左右他出门做工,老婆和小孩留在家里。彭女士在家里一方面带小孩,一方面负责农作物收成。 彭女士觉得丈夫上半年在家种烟,下半年出门做工这种安排还可以,因为丈夫外出打工可以多挣点钱,而自己与公公婆婆在家可以保证农作物的收成。她说:“春天在家里种烟叶有收入,下半年我跟大人留在家里干农活也应付得过来,他作为男人可以到外头挣点钱回来。”丈夫外出挣钱履行作为男人的工具性角色,自己留守在家带小孩和照顾家庭扮演的是表达性角色。烟叶收成后彭女士支持丈夫出门,关于丈夫的外出,夫妻会协商。彭女士说:“下半年出去打工,外头有活干,他亲戚会邀他去做,提前一个礼拜会告诉我。”江先生也觉得出门做工比在家效益好,“老板也知道我上半年家里比较多农活,走不开,下半年老板会打电话叫我去做工(指帮忙带工)。在外面做工的效益比在家里更好。家里需要钱的时候我会寄一部分钱回家,买肥料,做人情,买其他东西。”
(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代际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是指,家庭中年龄较大的老人在家务农,年轻人则外出务工,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务工,这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家庭因此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使小农经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在年轻人进城务工,耕地不用流转出去,而是由年老的父母耕种;父母耕种小块土地,虽然收入不多,但可以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16]
如上述个案二中江先生夫妻俩决定2007年正月一起出去打工,部分是因为夫妻外出打工使家庭经济有了新的来源,部分是因为小孩的照顾问题得以解决,部分是出于体谅公婆,部分是为了摆脱务农的艰辛。她说:“小孩可以送去幼儿园了,在家种烟很辛苦,自己出来的话公婆可以不用种烟会清闲些,经济有来源了。虽然在家里种烟更自由,但雨淋日晒,比较辛苦。在外面更不自由,但更单纯,事情少,毕竟是上下班。在家里雨下再大都要出去摘烟叶,工厂管理比家里严。”彭女士的看法得到了丈夫的证实。江先生说:“在家里种烟很累,但是能照顾到家里人。我们在家里种烟,多种是这么点收入,少种也是这么点收入。收入分为两路比较好:我们在外打工挣钱,父母在家里种田。我们在家里种田也只有这么多田,我们出来这里挣钱的话可以多积累点钱,如果不出来在家里的话就只有偶尔帮人做点小工,收入比较少。我们出来打工粮食不会减少,而收入增加了。我们出来后两个老人还是有这个能力去种那些田,只不过是没种烟,负担重点,累是跟从前差不多。”
2007年以前,江先生上半年在家与妻子和父母一起种烟叶,烟叶收成后他出门打工,而妻子则留守家里,一方面带小孩,一方面负责农作物的收成。这种安排既保证了家庭农作物的收成,在此之外还有打工的收入,家庭收入多元化了。2007年以后,江先生夫妇决定出门打工,而后弟弟一家及妹妹也在厦门进厂打工,而父母则留守老家种田。家庭成员部分留守部分外出打工使得家庭收入多元化的家庭策略得以有效实施。
个案三:严先生,初中文化,一家七口,子女三个,父母二人。父母在家种田,严先生比较早就出去打工,先是一个人出去做,妻子留守家里与公公婆婆一起种田,当上小包工头后才把妻子带出来。妻子跟随他外出后,家里的农田交给父母管理。他说:“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老婆都跟我出来了。”严先生告诉笔者,当上小包工头后,出于增加利润的理性考虑,他把老婆带出来给工人做饭。他说:“装修要请工人,有时请五六个,有时请十多个。如果去外头吃快餐,最低六块,一餐六块,十个人就一百多块。自己做饭不仅吃得好,而且不会像快餐那样吃得很厌,还可以节省一点钱,这样利润就会更高。而且我老婆出来,假如时间多的话,她可以去收购破烂,挣到的钱她可以存起来作为自己的私己(房)钱,她可以自己买些衣服,减轻他的负担。老婆收破烂一个月也有千来块钱收入。”
作为三个孩子父亲的严先生家庭负担很重,为了孩子上学,他选择出门打工。刚开始他一个人出门给别人打工,妻子则留守在家,一边带小孩,一边与公婆一起务农,这种安排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后来严先生自己组建了一个装修队伍,当上了小包工头,才把老婆带在身边。妻子出来给工人做饭节省了成本,另外,妻子利用空闲时间收购破烂,客观上增加了家庭收入。无论是最初一方外出一方留守的安排还是夫妻共同外出都是为了多挣钱,供应子女上学,显然这两种安排都拓展了家庭的收入来源。
五、余论:半工半耕与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隔
上文笔者从制度和家庭策略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家庭在面对人口流动的情境下如何合理地安排家庭成员,拓展家庭的经济来源以满足家庭的货币需求。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农民家庭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民家庭由原来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转变为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调查对象普遍反映,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家庭成员的外出并没有影响农业收成,而务工或经商的收入是家庭新的收入来源。半工半耕的家庭安排有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支出压力,但这种安排同时也造成了家庭成员空间上的隔离。伴随人口的流动,一个个完整的家庭被撕裂,农民工难以与其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外出务工人员和留守家庭成员饱受相思之苦。
谈及外出打工的原因时,许多访谈对象不断提及“在家里务农没什么收入,出来看能否发展”、“外面比家里挣钱容易”、“农村落后没什么好发展的”、“出门更能挣到钱”、“这里更好,家里那么累,在家里没什么出息”、“在家里积蓄不到钱”、“种田没有效益”等等,农民的句句质朴语言流露出他们出门的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
上述农民的质朴语言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再现了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结构性差距。外出从事工业或者商业的效益比在家从事农业高,理性的农民当然会作出外出的决定,诚然,经济上的差距不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唯一原因。必须指出的是,外出丈夫在城市从事工业和商业生产活动,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大部分留在了当地城市[17],少部分以汇款的形式返回到农村,而留守妻子在农村从事家庭再生产活动,家庭再生产的成本由农村和农村家庭来承担,因此生产性活动与再生产性活动在空间上分隔开来。
Michael Burawoy认为,流动劳工系统再生产的条件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包含的两个过程在空间上的分离,即劳动力的维持过程和更新过程在不同的地方进行。[18]调查发现,我国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所包含的两个过程在空间上也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反映在家庭上就是家庭成员跨区域的劳动分工,在男工女耕这种分工模式中,丈夫负责生产活动以及自身的生计,而留守妻子则负责家庭的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更新。在壮工老耕这种分工模式中,留守老人负责家庭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更新,年轻人负责生产活动和自身的生计。
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之所以会出现空间上的分离,主要是受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以及体现此结构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影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通过工作和消费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城市政府仍然不欢迎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定居下来,城市政府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农民工无法成为市民,无法摘掉“农民”这顶帽子。没有市民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有学者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具有分配社会资源的功能。国家通过将国民分为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从而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根据户籍来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相应的生活资源分配额。在目前农村人口跨地区流动频繁且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人口流入地政府可以设法免去为流入人员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和制度性社会保障及其他各种社会服务、社会支持的职责。[19]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维持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制度性地排斥农民工及其家庭定居城市,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甩给农村和农民家庭。
诚如潘毅等所言,国家在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是缺位的。[20]进城农民由于各方面资源的不足,他们只能进入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在非正规经济中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如建筑工、装修工、保姆等等,这类工作工资低且缺乏保障。受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农民工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收入因此也不稳定。城市高昂的房价以及生活费用,使得农民工难以将家庭安在城市,不得已他们将家庭的部分成员留在家乡,依托家乡来进行家庭的再生产。
中国的土地制度一方面束缚着农民外出流动,另一方面也为那些难以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农民工提供了后退之路。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当农民工因年纪大了,无人聘请其务工时,他们可以选择回家务农。经济危机时,农民工也可以回家务农。调查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都没有放弃家乡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或者留给妻子耕种,或者留给父母耕种,或者流转给亲戚种。虽然耕种土地无法富裕起来,但足以解决温饱。农民家庭让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务农、部分外出务工,一方面可以拓展家庭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可以分散家庭经济风险。这种安排也有助于家庭的再生产。不少农民工家庭将家庭的主体留在农村是有原因的,农村生活成本低、教育成本低、医疗成本也相对较低,这有助于降低家庭再生产的成本。
[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8.
[2]国家 统 计 局.2011 年 我 国 农 民 工 调 查 监 测 报 告[EB/OL].(2012-04-27).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3]陈向明.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2.
[4]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6.
[5]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31,135.
[6]黄宗智.经验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77.
[7]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5):100-105.
[8]Pessar.P.A.The Role of Househol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Case of U.S.Bound Migration from the Dominican Republic[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2,16(2):342-364.
[9]Douglas S.Massey,Joaquin Arango,Graeme Hugo,Ail Kouaouci,Adela Pellegrino,J.Edward Taylo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3,19(3):431-466.
[10]Yuen-fong Wong.Circulatory Mobility in Post-Mao China:Temporary Migrants in Kaiping Country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3,27(3):578-604.
[11]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3.
[12]谭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社会学研究,1997(1):1-7.
[13]李实.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3):56-69.
[14]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9-43.
[16]贺雪峰.组织起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3.
[17]王西玉,崔传玉,赵阳,等.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73-82.
[18]Michael Burawoy.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s of Migrant Labor: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Vol.81,No.5:1050-1087.
[19]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20]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