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瑶挑花服饰的认知图式及其文化时态
2013-10-10谢菲
谢 菲
(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附于所属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实践、认知、观念而存在。文化主体既是名副其实的传承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最具权威的表达者。换而言之,基于主体诠释下的文化内涵是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在整体性学科视野下,人类学主位研究旨趣不谋而合地契合了这一主题,成为窥探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最佳视点。
同时,从技术人类学的发生角度而言,“只有制作与使用手工艺品,才能产生手工艺品文化意义的洞察力”。[1]与经典性手工艺以生产支撑技艺的生长形态不同,习俗化手工艺一般为特定群体的民俗生活之物。从制作到使用,深嵌了个体日常生活的经济理性与族群心性的文化张力,负载了个体表现自我,形塑社会结构的主体能动性。因此,在视觉表达上,基于主体表述下的服饰制式、图案、颜色等艺术符号,无疑成为考察群体文化谱系与时态的现实表征。以下关于花瑶挑花服饰的研究以及阐发便是基于以上思考的结果。
一、挑花服饰:“花瑶”他称的缘起
花瑶(自称模岚)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该族女性擅长挑花,且服饰色彩鲜艳斑斓而盛名,主要聚居在湘中邵阳市与怀化市接壤的海拔1500多米的白马山一带,人口约八千余人。“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对面喊得应,走路半天多,要想得生活,全靠自己做。”由于花瑶居住地为中原高寒山区,境内峰峦起伏,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生产方式以山耕农业为主,以山林树木套种金银花、杜仲等为辅。
论及花瑶挑花,与其族群称谓有着一定的关联。众所周知,瑶族本是一个支系较多,分布较广的民族。一般而言,瑶族称谓可分为自称与他称。花瑶这一他称正是源于该族女性擅长挑花且服饰色彩多样而得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和一些旅游背包客的陆续踏访,花瑶这支人口较少族群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一些文人学者以及地方官员便以一种直观方式将这一服饰独特的瑶族支系称为“花瑶”。而据当地的长者介绍,这一称呼最初来源可追溯至民国期间。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一月,时任县长的徐君虎得知小沙江瑶民生活困难,便亲自筹款筹粮,专程入瑶山体察民情,成为第一个进入瑶山考察的县长。之后,徐县长热情邀请花瑶人走出大山进城做客。由于当时对这支人口较少族群没有固定、统一的称谓,难以宣传。于是,徐君虎便以其服饰艳丽为由,称之为花瑶。[2]
随着花瑶与外界商业贸易和社会信息交流的频繁,“花瑶”这一直观称谓愈来愈为本族人所接纳。在他们看来,在众多瑶族支系中,花瑶服饰独特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花瑶所在地的虎形山瑶族自治乡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并成为周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后,逐渐为外人熟知。其中,可视性强的民族服饰景观常被初至花瑶的游客津津乐道。长期以往,“花瑶”这一源于局外人对该族女性服饰感官意义上的称呼便流传开来。
二、花瑶挑花服饰的认知图式
“物本身不能言说文化,但与物相关的言词却能最大化地表达文化的洞见(insight)。”[2]在花瑶,挑花技艺并无确凿的文字资料记载,唯有依据收藏与时下流行的挑花服饰,通过花瑶人的自我阐释,深描挑花服饰的色彩与图案,展现其技艺演变的文化图式与谱系。
1.挑花色彩的自我彰显
“远看颜色近看花”。从空间距离感知与视觉可视程度的关系而言,颜色与图案是花瑶服饰显性的两大构成要素。在挑花服饰中,“花”隐含两个方面的指喻:一是花瑶挑花服饰颜色种类多,给人在视觉上“花”的意象。二是花瑶挑花裙以花样繁多、复杂而闻名。
“服色不仅仅是民族的某种徽记,还强化着特定人群的集体意识。从颜色本体上而言,它并无善恶贵贱之分,但经过族群意识的投射后,便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3]在花瑶人日常生活服饰色彩构成中,红、黄、绿、黑、白为使用频率较高的五种色彩,瑶语分别称为“告”、“拔”、“桂”、“茂”、“巩”。其中,红色是挑花服饰最常见的颜色,如女子服饰中的头帕、上衣滚边与袖口边、腰带、挑花裙的前褡和滚边、绑腿花边。问及缘由,因花瑶聚居区——虎形山地处梅山文化的上峒,梅山教盛行。在梅山教的仪式中,红色象征着生命,而白色喻示死亡的征兆。在花瑶人生礼仪活动中,与结婚和诞生、丧葬礼仪式有关的“钉铜”①“钉铜”实为花瑶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通鬼神、安置亡魂的仪式。(瑶语谐音)仪式则分别称为“红事”与“白事”。这种二元对立的颜色结构在花瑶女子参加仪式的服饰颜色上逐一得到印证。如参加婚礼和“打三斗”(花瑶诞生礼)都必须穿上艳丽而隆重的节日盛装。即便在夏季遇上类似的喜庆场合,花瑶女子也不得不避穿夏季常穿的白色短装,改穿黛蓝色的长衫,以图吉利。
如果系统地将花瑶人服装色彩体系、内涵以及呈现场域予以总结,可以发现其色彩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区分,如红色和白色则分别直指“吉”和“凶”之意,而黄色、绿色和黑色则为中性色彩,并无特定的规范与禁忌。如图1所示。
不过,疑惑的是既然白色为凶色,但花瑶服饰的精髓——挑花裙却以黑布为底,用白色纱线挑制而成。问及缘由,她们给予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挑花裙不是白色的本布,而是用白色纱线挑成的花。”尽管挑花图案用白色涤纶线挑绣,但经过花瑶妇女的构思与布局,赋予自我意识与体验,完全转变成由图案组成的“花”布,与丧葬礼所穿的素白色本布有所区分。

图1 花瑶人色彩认知图式
除了红色外,在花瑶挑花服饰中,黄色、黛蓝色与绿色是比较常见的配色。“在我们花瑶,红黄相间的花斗笠就像那火红的太阳,绿色的盛装上衣就像崇木凼的古树一样葱绿。”[4]显然,在当地人的色彩感知中,黄色与绿色被赋予了生命,如金色的阳光、郁郁葱葱的古树,通过附着身体的方式感染个人,喻示个体生命力的旺盛。的确,以农耕为主的花瑶人总能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寻绎到自然之物美的力源所在。唯有深居密林、与自然之物朝夕相处的花瑶人,将生产与生活的切身感悟衍发于身体饰物中,不言而喻,不明自显。
至于花瑶人偏爱黛蓝色长衫的缘由,一些当地的民间文化人自觉地将其附会于族群迁徙遇难的叙事中。
“天禧元年,吾族又被赵鲁二督统造反,围战古。七月初二,追剿不放,逼吾族逃命,各散五方,快者远之,慢者到鹅颈大五黄瓜、白瓜棚下躲藏途中,怀胎妇女受惊,个个血淋生子,追兵见之,寒情凛凛,啼哭惊天。蒙军官丢插令旗,赦留此处,不准斩杀,幸免于难。当天集会誓愿,过此日方可食黄瓜、白瓜,永传后代,违者子孙不昌,并定每年农历七月初二至初四为罹难纪念日——讨僚皈”[5]。
历史上,花瑶人在反抗外族的压迫过程中,黄瓜与白瓜偶然充当了挽救族群的英雄角色,被奉为族群的庇佑神,严禁在特定日期进食,更有甚者禁种黄瓜与白瓜,以示敬意。这种行为的践行与尊崇弥散出花瑶人对黄瓜与白瓜助其族群躲避灾难,繁衍生存的感恩之情。因此,在琳琅满目的挑花服饰图案中,黄瓜与白瓜因与族群关系的特殊性,被排除在外,与其他普通动植物相区别。但因黛蓝色与黄瓜、白瓜外表颜色接近,花瑶女子选择黛蓝色上衣作为冬季日常服饰,以示护佑。对于这一解释却缺乏多数当地人的认同。大多数花瑶妇女特别是年龄稍长者,却给出了一个自以为比较客观而合理的解释:
“以前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钱买布,都是自己纺纱,制土布衣裳。后来,有人发现瑶山的深山老林里有一种‘比龙’(瑶语谐音)的野果,将果实压榨后可以将白色土布衣服染成靛蓝或者红色,颜色很鲜艳也好看。就这样,大家都学会了用野果染色。”[6]
“暗示(suggestion)和期待(expectancy)视为对图案艺术来说是活动和静止的作用力”[7]。在花瑶服饰颜色的自我阐释与叙事中,或隐或现的暗示与期待,凭附于族群迁移历史与集体记忆中,寻绎花瑶服饰主体颜色选择的当下性与合理性。在叙述中,悲怆族群迁移史的复调和诗意般栖息生存的高扬便成为了花瑶人表达自我的两大主题与旋律。
其实,除了服饰单一颜色选择的策略外,“花”色对比形成的强烈反差与色彩搭配的统一和谐同样反映了花瑶人色彩布局的独具匠心,即在强调红、黄、绿、蓝等醒目颜色的视觉冲击时,利用黑、白、青等颜色予以缓冲和调和,同时充分利用色块之间大小和空间距离的穿插与经营,实现色彩的搭配统一,产生富有节奏感的韵律,“花”而不腻,清新明快。
2.挑花图案的自洽
如果说色彩是花瑶挑花服饰最直接的感官元素,那么图案无疑以花样与布图为具象,具有“第二性”的感官特征。
总体而言,花瑶挑花纹样的母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自然类题材。“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交往的、人的身体。”[8]对于一个崇尚自然、亲近自然的族群而言,将花草与动物作为审美对象,挑绣在衣裙上装饰身体是他们亲近自然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些自然类题材的图样尤以花草树木与动物居多,如花草纹样主要有干杯约、南瓜纹、蕨叶纹、勾勾藤纹、牡丹纹、“乖子花”、十字花、海棠花、包谷花、“打纸花”;动物纹样包括狮、龙、虎、蛇、马、鸡、狗、羊、鱼、凤等种类,是挑花图案的主体部分。

“打纸花”① “乖子花”:顾名思义,以挑花图案隐喻新娘乖巧、伶俐的秉性,常见于新娘服饰的头帕。

苞谷花

“乖子花”② “打纸花”:在花瑶社会,一直流传着“嫁郎要嫁十七八,挑花要挑打纸花”的说法。所以,在新娘服饰的图案中,打纸花是比较常见的花样。
在挑花裙中,尽管花草类纹样在整体图案的布局中充当辅助性角色,但其勾勒、迂回与曲折的视觉线路,却挑动了整个挑花图案的灵活性与活泼性。并且,至今每一种花草纹图样仍然在花瑶人生活的深山密林中找到原型。正如苏珊·郎格所言,每一种艺术形象,都是对外部世界某些个别方面的选择和简化,……;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再现外部现实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为了将主观经验和情感对象化而服务的,当外部世界中的各个方面被人类逐一选择和注意的时候,艺术便产生了[9]。
二是传说故事类。据可查的历史资料记载,花瑶为只有语言,没有固定文字的迁徙性民族。许多本民族的历史都依靠一代又一代花瑶人口传,或使用手中的纱线与靛蓝色土布挑织而成的图案,忠实地记录本民族的历史传说,如“乘龙过海”、“盘王升殿”、“朗丘(瑶语,意即头人)御敌”等挑花作品。
三是日常生活类。这类题材场景宏阔、人物众多,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对歌定情”、“打蹈成婚”等花瑶婚俗的场景。遗憾的是,由于此类作品挑花技艺难度很大,大都已失传。
以上各纹样母题并不独立成篇,往往以动物类、传说故事类与日常生活类为主题,以花草纹样补白,构思而成。除了花草纹样外,一些几何图形也是旁补与边饰的主要内容,如菱形、三角形、矩形、万字符、回字符、井字符、十字符、“V”字符、圆点符、“U”形符。这些图形以两两组合和重复的形式勾勒于挑花图案的边框上。在视觉效果上,“几何图形的制作和重复,就像声音或动作的重复和模仿一样,似乎是能够提供把握感、安全感和摆脱焦虑的愉快情感的一种基本的人类生物心理倾向”[10],使欣赏者生理与心理上获得富有节奏感与安全感的视觉愉悦。
其实,除了花瑶挑花边框独具匠心的设计外,挑花图案的布局与表现手法也彰显了花瑶人表达自我的良苦用心。
在花瑶挑花中,对称是图案布局的主要方式。与湘绣以及其他机绣不同,花瑶挑花不用事先描图为底,也不用模具做刺绣架,全凭花瑶女子的腹稿,循土布经纬线进行徒手操作,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聪慧的花瑶妇女却擅长对称的手法,以化解花瑶挑绣无章可循的难度,增加其美观度与精细度。从制作者的技艺手法而言,对称表现形式可以将花样“杂乱无章”的走向变得“有章可循”,驾轻就熟,掌控自如。其次,从花瑶挑花生存的语境而言,其制作者与欣赏者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花瑶人,“它的完成与享用,既是生产又是创作,既是艺术作品又是生活用品,生活的实用与艺术的欣赏没有文化上的分割。”[11],凝聚了作为生活主体——花瑶人的体味与感悟。自然,其挑花图案的对称法则也渗透了花瑶人崇尚“好事成双”的迂回表达。
《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在日常生活中,秉承“物我同一”理念,诗意般栖居的花瑶人依照个体对生存空间的认知与体会,投射于生产与生活对象中。如在挑花形式布局上,花瑶人井然有序地将宇宙空间、自然之物与现实生活分割成上、中、下三个层次,并挑绣于一块三尺见方的挑花裙上,层次分明,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这种对生活空间物象的提炼与浓缩不仅表述于花瑶挑花图案的布局中,也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直白的表达力蕴含于挑花对象中,如虎图。在瑶家女子针线下,虎可谓形态各异,千姿百态:或雄姿勃勃,威武豪放;或温文尔雅,静若处子。不过,妙趣横生的是花瑶女子挑绣的老虎腹中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虎崽”,或仰或卧,情趣横溢。在“虎崽”的周边使用各种花草填充。问及原因,花瑶人解释说,“老虎要怀崽,还要吃东西。这样绣出来的才是活老虎。”原来,在花瑶人的审美感知中,物象的生命力才是挑花技艺追求的精髓。这种对生命直白而纯真的礼赞并不是对自然之物表象的简单模仿,而是对于生命深层意蕴的领悟与阐释。
其次,追求事物的完整与圆满也是花瑶挑花图案布局的另一视觉特征。在图案设计中,挑花裙可谓见缝插针,密密匝匝地布满各式各样的图案,看似毫无章法,稍显杂乱。花瑶女子却并不以为然,“花满而全才热闹,才好看!”这种“全”而“满”的往往以花套花、几何纹样与花纹相饰等方式,层层相套,环环相连,完全不拘泥于花纹与几何图形的束缚,流畅而闹腾。至此,在花瑶服饰的意象中,“花”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指喻:颜色种类的多样和图案布局的全、满。
“人的活动并不是由于客体对象的存在并单纯作用于主体的结果,而是主体根据需要对客体对象进行选择的结果”。[12]在花瑶挑花颜色与图案的主体表达中,“花”的意象与特征得以不断突显与强化,与族群称谓颇为贴切与映衬。富有意义的是这种“花”的选择与强调,积淀并阐发了花瑶人对宇宙空间结构的认知与建构、族群历史记忆的复述、物我同一的表达。这样,挑花服饰不仅仅是花瑶女子日常生活穿用的普通之物,而是与民族心性、族群历史以及个人生命连缀在一起。这种维系既是花瑶人坚守自我、表达自我的归宿,也是花瑶女子制作、穿着民族服装的源动力。
三、花瑶挑花服饰的文化时态:“现在的过去”与“过去的现在”
论及花瑶服饰文化时态的变迁,一般通过不同时期服饰图案、材质、内容的比对可大致反映一二。这种调试和渐变是在社会情境变迁下,花瑶服饰主体通过形成与内容的考量与选择而表现的一种主动适应,兼具“过去的现在”与“现在的过去”[13]两种时态。总体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莫过于服饰制式的简化:缠头帕改为戴花斗笠;老式腰带修改为挂扣腰带;缠绑腿化约为绑腿套。在穿着上,改变了过去耗时长、以“缠”的方式固定服饰的方法,取而代之是更为省时、轻便、快捷的替代品。尽管花瑶服饰在形式上发生了些许改动,但仍然保留原服饰颜色搭配、图案布局与穿着功用的整体效果。这种对传统持续性的眷念与坚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花瑶人的适应与创造:“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14]身受现代化气息晕染的花瑶人仍依赖传统挑花服装中过去时态的内容,如颜色、图案与功用,寻找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感,以维持其作为花瑶族群合法性存在的依据,保持自我。这种既成性内容持续使用于现时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过去的现在”之意味。同时,现时对制式渐变性的改造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传统花瑶服饰历史的、既定框架的限制,并在此框架下寻求现时服饰定位,成为“现在的过去”。
如果说花瑶服饰制式上的改变是花瑶人基于生活方便的需要,而挑花裙底布、挑线材质的变化则大多源于实用经济学的考量。从当地老人收集与保存的挑花裙来看,时下流行的挑花裙与老式挑花裙无论是挑线还是底布都有明显的差异。据当地花瑶老人回忆:“大概是九二年左右,我们就开始用尼龙线、尼龙布做挑花裙了。这样一来,省了不少工。原来白色棉线与土布不耐洗,穿一年就烂了,而新式挑花裙可以穿四、五年,有的更长。”[15]
此外,摒弃白色棉线和土布等旧材质还在于新材质提升了挑花裙的美观度。除了耐磨性差,靛蓝色的土布无论是色彩选择的多样性还是光泽度难以与涤纶布相抗衡。加之,随着上个世纪初,农村家庭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花瑶妇女用于挑花劳动时间骤减。自然,花瑶妇女挑花时间的锐减与新式挑花材质的优势,两者的因缘际会触发并耦合了她们对材质经济而理性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新式材质以结实、牢靠、不易褪色的特性占据了上风,成为花瑶妇女挑花材质的首选。如果说,花瑶挑花材质的更新与替换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的结果,而挑花图案简笔化倾向相当程度上蕴涵了花瑶人挑花技艺的自决性。
为了节省工时,保持挑花裙的制式,花瑶妇女在图案布局上试图改变以往繁复的花样,将主体图案的外廓简单勾勒出来,并大面积地使用白毛线为底填补空白。相较传统挑花裙的图案,制作简笔画图案的挑花裙工时大为缩减,由原来一年左右的时间缩减为三个月左右。构图上,简笔画式的挑花裙已完全摒弃了传统挑花图案抽象性、想象性以及“花包花”的表现手法,寥寥几笔,勾勒成型。观看者勿须费神,一瞧便知图案的实体,且这种实体图案以孔雀、熊猫、狗和兔子等常见动物为主,传统花草纹样和几何纹样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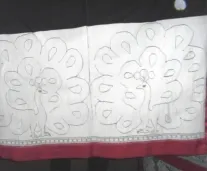
简笔画图样

老式图样
显然,尽管花瑶社会深居一隅,独处一方,但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锋中,花瑶人不再独善其身,而是不由自主地融入到更为深入的社会空间生产中。这种生产不仅让花瑶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比传统材质与性能更为优越的替代品,接受更为简略的艺术表达形式,同时也让她们渐渐丧失自我特色的坚守与表达。鉴于花瑶挑花技艺所凭附的物质与文化空间的蜕变以及穿着主体选择变化所引发的濒危性,2006年,花瑶挑花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步入名录体系保护时代。
然而,花瑶挑花进入名录体系后,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的指导以及地方实施文化旅游经济策略的吸引下,2009年后花瑶人却又逐渐放弃简笔画图案,重拾老式图样,恢复了传统花瑶挑花服饰的制作与穿着,在“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中重新审视并寻找自身存在的痕迹。
四、余论
以上花瑶主体表述下服饰制式、图案、颜色等艺术符号的历史演绎,清晰展现了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推动下,花瑶人利用服饰表征族群历史生存与现实选择的自觉性。
进入名录制度以来,花瑶挑花保护与传承的主题始终逃脱不了“保护什么”这一关涉其本质性话题的追问与反诘。在名录保护体系的现实中,门类众多、形式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标准化、统一化的框架下,予以了整体式的关怀。然而,在民间手工艺的源发以及生长体系中,习俗化手工艺与经典性手工艺同属一个门类但分属不同脉络。在文化时空维度中,属于习俗化手工艺的花瑶服饰依托群体的社会公共空间,与族群的历史积淀、存在的现实感以及连续性交织在一起,成为该群体文化源源不断的内在创新机制。在文化间性、公共性和共享性的日常生活场域中,花瑶群体的日常服饰与仪式盛装成为其价值规范与行为体系“在场”的表达符号,并通过服饰的制式、色彩、颜色与布局予以彰显、凝聚与表达,并在时空流转中寻求“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的关联。因而,在不同文化主体交往下的日常生活中,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已属不可能,因为其本真性“体现在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15],处于持续的建构过程。唯有花瑶人自觉保持对其服饰文化制作、穿着的连续性与创造力,保护与传承这一关键议题便水到渠成。
[1] Tom G.Svensson.Knowledge and Artifacts:People and Objects[J].Museum anthropology ,2004(31):85.
[2] Tom G.Svensson.Knowledge and Artifacts:People and Objects[J].Museum anthropology ,2004(31):100.
[3] 奉泽芝.隆回瑶族简史[M]//隆回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隆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38.
[4] 居阅时,瞿明安.中国象征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93.
[5] 访谈对象:FXM,时间:2011年4月,地点:隆回县总工会。
[6] 奉锡联搜集整理 雪峰瑶族照文(清乾隆十年冬)[Z].溆浦县民族事务办公室翻印,2007年,第8页.
[7] 访谈对象:YLM ,时间:2011年7月,地点:隆回县虎形山瑶族自治乡虎形山村湘渝餐馆。
[8] (英)阿尔弗雷德.C.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M].阿嘎佐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9] 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
[10]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腾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6.
[11] (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8.
[12] 胡潇.文化的形上之思[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261.
[13] 赵铮郈.主体美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37.
[14] 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为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2):28.
[15] (英)E.霍布斯鲍姆 T.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2.
[16] 访谈对象:FYM ,时间:2011年7月,地点:隆回县虎形山瑶族自治乡虎形山村。
[17] 袁年兴.文化的人本寓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