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从波兰斯基的《死亡与少女》谈起
2013-09-21王永春
■王永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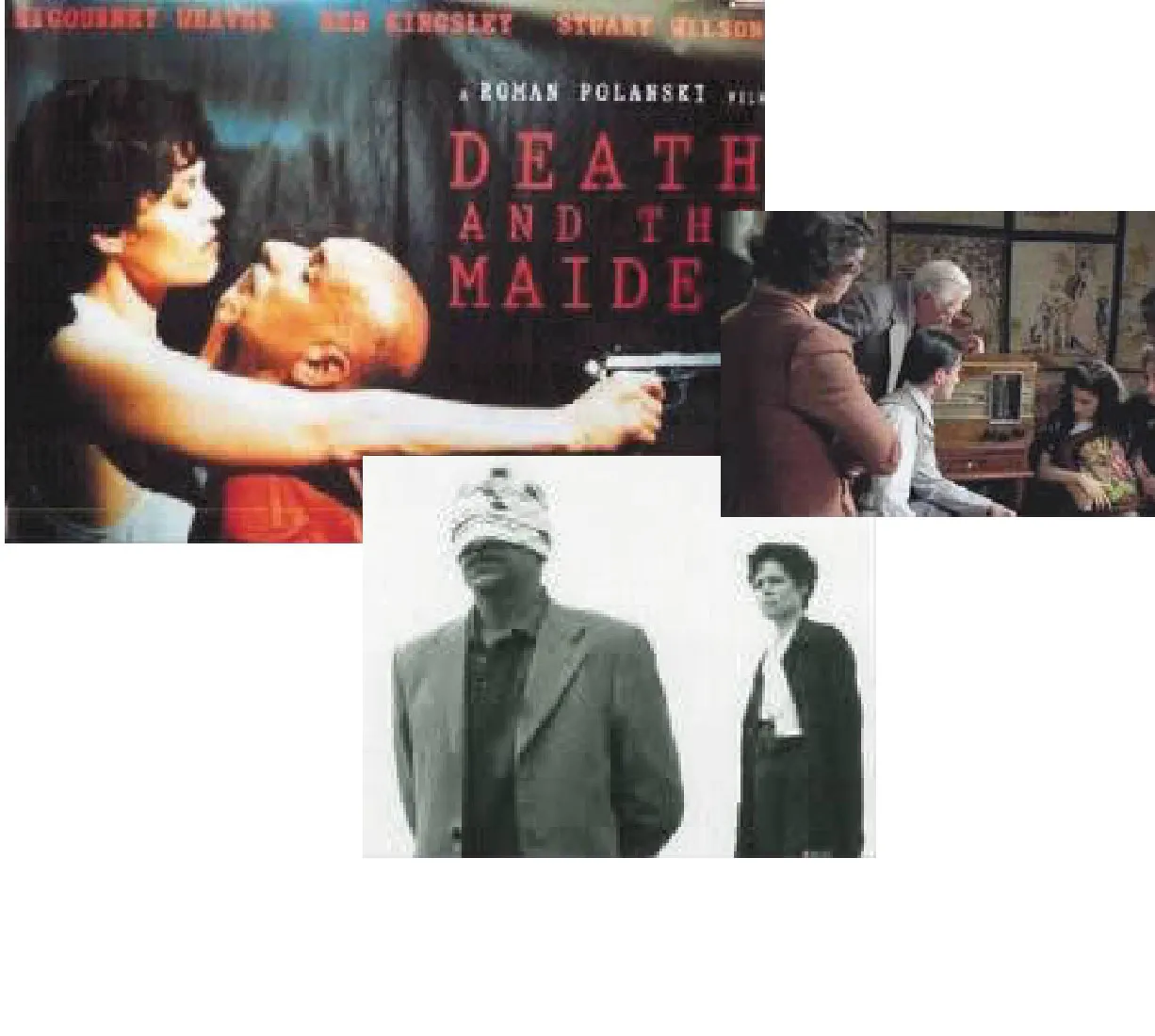
夜晚,海滨别墅,只有三个人,一个故事展开,紧凑的时间和局促的环境,不紧不慢又富有思辨色彩的言辞,看起来很是沉闷,但随着情节的展开,你就会在这一场审判中沉醉下去,获得一种心灵的共鸣与震撼。这不像是一部电影,倒是一部复杂曲折、高潮迭起的情节剧。被人强暴后有点神经质和情绪不安的受害者波利娜,无意中发现了施暴者就是邻居米兰达,于是通过以暴制暴在家中对他进行审判,丈夫埃斯科巴尔充做辩护律师;审判后,米兰达跪在悬崖边承认了一切。这就是《死亡与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又名《不道德的审判》,根据阿里夫·多尔曼同名戏剧改编,罗曼·波兰斯基导演,西格妮·菲佛、本·金斯利、斯图尔特·威尔逊等主演,1994年出品。
电影开始,几个提琴手演奏着舒伯特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死亡与少女》。波利娜在家中准备晚餐,焦躁不安。房间外,是暴雨,狂风大作;房间内,停电了,一片黑暗。这无疑就隐喻着波利娜的痛苦心境。她的这种情绪为何而来,那是一个阴暗的回忆。她试图忘却,苦痛却总是从骨髓里钻出,像一条条蛆虫,在脑子里蠕动,在全身蔓延。枪,作为一个暴力的象征,就放在身边。然后,施暴者出现,他却装作浑然不知或者俨然忘却,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审判在《死亡与少女》的音乐中持续展开。警察即将到来。天亮了,悬崖边,海水在奔腾,米兰达跪在那里,突然幡然悔悟,记忆中的黑暗铺开。音乐厅里,《死亡与少女》又一次响起,波利娜和米兰达互相关照,电影结束。
故事发生在南美一个极权独裁国家,青年波利娜和埃斯科巴尔是追求自由的民主战士。波利娜被捕了,暴力在身体和精神上持续展开,而米兰达就是其中的一个施暴者。在暴力发生的过程之中,米兰达既是施暴者,也是被胁迫者。他开始还对暴力感到不适应,最后就沉迷在暴力之中,在其中忘记了人性之善。他的施暴似乎有些克制,从另一种意义上使“罪犯”的生命延续,“一个人也没有在他手上死去”。显然,他不是救犹太人于苦难中的辛德勒,不是根本意义上的拯救,也不会为自己的罪恶痛哭流泪。独裁结束以后,社会看似恢复到民主的秩序之中,但历史的创伤仍残留在受难者的身体和精神之上,这时候该怎么办?

暴力发生以后,暴力所带来的残酷与伤痛成为既成事实。从受难者的角度来讲,是宽恕,还是惩罚;是铭记过去的灾难,还是去面向明天。而施暴者,是躲进社会的某一个角度,继续做人,而忘记了过去的暴行,还是在内心深处对暴行进行反思和忏悔,对受难者给予精神或者物质上的补偿;或者是换张脸皮,继续施暴。事实上,暴力之后,完善的反思和补偿机制很难出现也尚没有出现。
《倚天屠龙记》中,成昆杀死了谢逊的妻儿老小,却躲进了佛门净地,装作一个慈悲者,逍遥法外,继续施暴。作为受难者的谢逊,想到的只有报仇,以暴治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谢逊却由受难者一下子转变为施暴者,一十三拳打死空见大师。最后,幡然悔悟的谢逊遁入佛门,在忏悔中得到心灵的救赎;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的成昆也得到应有惩罚。在中国民间传统伦理中,一向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善恶观,这种善恶观给予了成昆严厉的惩罚。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胡汉山、南霸天、黄世仁等恶霸地主,一概接受了革命伦理的严酷制裁;而关敬陶等投向革命的起义者,也得到了革命伦理的宽恕。若如此,是否要给忏悔的谢逊与起义的关敬陶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选择“重新做人,改过自新”,从而完成自我的救赎及受难者的宽恕与谅解。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施暴者的宽恕,就是对受难者的不公平,或者说是对在暴力中牺牲者的背叛;或者说对施暴者的宽恕,将会对暴力行为产生一种漠视和纵容。因此,需要在制度建立一种惩罚的秩序,以儆效尤。所以,当崔英杰砍死城管队长李强后,无论他是否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无论他是底层小民被逼无奈,无论是他幡然悔悟痛哭流泪,无论是公众在为其唏嘘不已并对城管的合法性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还是要被送上法庭,接受制度的惩罚,以保持法律秩序的完整性。但任何秩序以整体的面目出现时,必将是对个体的压制和欺凌。在完整的秩序面前,不容你有任何闪失,否则你将无法改变被惩罚的现实。
暴力之后,要保持对施暴者的仇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在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革命电影人在战后获得了对革命战争叙述的绝对话语权。一方面作为胜利者,他们在战争中汲取了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争暴力所带来的惨痛则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必然和必须;另一方面,之所以保持着一种对革命他者(如日本鬼子等反面形象)的强烈仇恨意识,并在叙述中对他们施加暴力行为,是因为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渴望保持牺牲者的信仰,继续他们中断的事业,以此表达对他们的缅怀和崇敬”,这种对革命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创建什么新的记忆和重新阐释过去,都形成于老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情况下,过去的愤恨、苦痛和复仇的渴望会重新被激起。”由此,革命意识形态希望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象中的冲突继续下去,“拒绝让过去的记忆消逝,指责和平缔造者的所作所为是对那些为‘崇高事业’而献身者的背叛”。况且,“革命”在新中国革命道路上是不断前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要求意识形态之下的所有个体都保持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象中的冲突,使他们对革命历史中的反面形象保持着强烈的仇恨意识。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不能解决暴力之后的和解问题,而只能让暴力在文艺等其他领域得以持续的展开。
在某种程度上,对施暴者的仇恨记忆往往与受难者的苦难叙述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有把逝去的苦难一次次的拨开,让受难者一次次的接受“美丽”阳光的照射,才能更好的面对明天。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就此出现,受难者想方设法地想忘记阴暗的记忆,秩序的守护者却一次次的让它公之于阳光之下。《求求你,表扬我》中,欧阳花被歹徒凌辱,杨红旗救她与苦难之中。当杨红旗需要一种表扬的证明,欧阳花却矢口否认。或许,对灾难的矢口否认,是对施暴者的极度纵容;那么,把阴暗记忆的撕裂,莫不是受难者又一次的凌辱。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受难者都害怕阴暗的记忆,拯救他们心理阴影的路径,也并不是一味的忘却就能实现,即如波利娜,她心底的创伤,在施暴者米兰达的承认和忏悔中,淡淡飘去。其实,暴力之后,对仇恨的宣扬,对阴暗记忆的撕裂,对施暴者的卑污化或者小丑化(不去反思暴力产生的机制和原因),并不能有效的制止暴力的再次发生,而只顾报仇的谢逊更多的出现,暴力循环绵延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
暴力之后,或者虚妄的宣扬和平主义,要求受难者忘记历史,去期待明天,亦是对暴行的极度不负责任。各种欲望的压制下,和平不会自行产生。暴力的约束机制,与和平的期待机制,在技术上如何去操作,实在是一个难题。比如,在抗战题材电影中,对侵华日军的丑陋和妖魔化叙述,或者是人性化叙述(如《南京!南京!》),以及对中日人民友谊的过度宣传(如《烈火金刚》中的武男一雄),其实已经偏离了对暴力反思和约束的轨道,只能沦为某种外在的政治手段工具和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口号而已。空洞的口号,以及对细节的漠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具体人数),不能有效地去反思暴力,也不能有效地实现和平。
米兰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暴力行为的最末端的执行者而已。难道就因为他只是一个刽子手,就不需要承担,就可以无视或忽视曾经作出的恶的行为。即如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也没有亲手实施屠杀,就可以在暴力之后,安然自得;或者如《朗读者》里的汉娜,虽然文盲,却也在整个恶行的链条上实施着犯罪。在暴力来临之际,每一个没有起来抗争的人,他们的沉默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对施暴者的默许,他们自己也成为施暴者的帮凶而已。波利娜在被秘密警察逮捕时,为什么没有高呼“我是波利娜,我在被秘密警察逮捕”,因为如果她高呼,她将被射杀,身边就是默许的旁观者。
所以,重要的是,在暴行来临之际的抗争,以及在暴力之后的反思,每一个施暴者和纵容者都要进行着良心上的审判,并对暴力产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约束与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