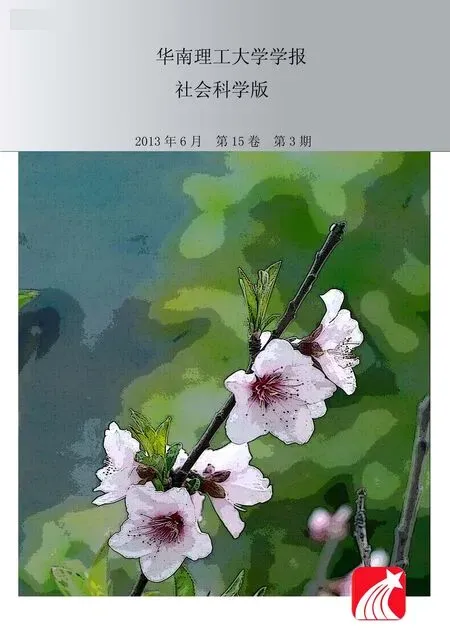历史内涵与现实认同:河源“客家古邑”的文化建构
2013-09-01吴良生
吴良生
(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0)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下称世客会)是客家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产物,这个大会又成为随后的客家文化建构的最大平台。各举办地在大会前后进行各项活动极大的增强了本地“客家”人的“客家”认同,把地区内几乎能够纳入的资源冠上了“客家”之名,建构起了“世界客都”梅州、“客家祖地”闽西和“客家摇篮”赣州等地方文化体系。
作为第23届世客会举办地的河源,在“客家古邑”文化形象下的地区文化建构亦初见成效,然而,如何更为深入和有效的文化建构仍然是河源文化界的最大课题。本文将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这个课题进行思考,希望对河源客家文化建构有所裨益。
一、“客”与“非客”:河源客家认同的困惑
康熙年间,广东紫金县的《永安县次志》和江西兴国县的《潋水志林》两本地方志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客家”二字①关于“客家”称谓起源的研究见:刘丽川《客家称谓年代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黄志繁的《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16-18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这是目前为止学术界能找到的最早的“客家”记载。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客家”并未成为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人们的普遍自称或他称,即便在最需要表明身份与认同的海外嘉应、惠州、汀州和赣州等属的华侨也极少见“客家”称谓。据颜清煌研究,南洋客家人一开始只有宗亲组织和地缘组织,并未冠以用“客家”、“客属”的字号,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新加坡客属总会、昔加客属公会、古来客家公会、泰国半山客公会等组织。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客家”不但在学术论著、报刊杂志中常出现,也成为一部分人的普遍自称。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有关“客家”的污名与反污名事件促进了“客家”人对“客家”问题的重视,而又以罗香林先生开创现代学术意义的客家研究为高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嘉应属外迁的人多,“客家”认同的需求亦是最强;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一批以嘉应属为主的政治文化精英主导了“客家”正名运动,使梅州的客家认同开展的最早,扎根最深。解放后,大陆的“客家”问题停止了争议,而海外却不断掀起一个个小高潮,其中以20世纪70年代香港崇正总会创办“世客会”为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梅州人又最早打“客家牌”,以“客家”认同联系海外华人华侨。1992年,梅州成功举办第12届世客会,让梅州人的“客家”认同达到了顶峰,梅州成为了“世界客都”,梅州话成为了客家话的代表。随后闽西、赣南也进行了类似的“客家”文化建构与认同。由此,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一个中国汉族各“支系”中自我认同最强的“民系”(或族群)将自己的文化——客家文化成功建构。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认为所谓“客家”不过是客者们鼓噪起来的万建中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客家文化的建构的确是世界最成功的族群文化的“神话叙事”。[1]
公元前214年,龙川成为客家地区第一个建县的地方。然而,现代行政区划中的河源在历史上的地域管辖分多合少。在宋代,现在的河源地区就分属循州、惠州、梅州;在清代,又分属惠州、梅州、韶州等。统一的“河源文化”建构直到1988年河源建市才开始,非老河源县的连平人、和平人、龙川人、紫金人也慢慢习惯“河源人”这个自称与他称。但是,这种地域归属并没有解决河源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很少有河源人明确认为自己是客家人,靠近梅州的紫金、龙川有客家认同的人多点。90年代以来,河源的地方政府也在打客家牌,加上“客家”文化的旅游开发,进入21世纪,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的河源人越来越多,似乎河源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结果远非如此,河源人大多数人在回答自己是“客家人”时的声音并不那么响亮,而梅州人在这样的交流中通常显示出很强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河源到底是不是客家?这个问题的困惑在河源这样一个历史上多分治、建市不久而又缺乏客家学术研究的地方显得异常突出,尽管罗香林先生在其《客家研究导论》中已经将河源的大部分地区划为“纯客县”,河源也认为自己是99%的“纯客地区”,但少量的学术成果并不能为其提供实证。
事实上,河源的这种困惑是暂时的,因为在“客家建构”的过程中,梅州、汀州、赣州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困惑在客家研究较强的赣州还远未清晰。近年来学术界对传统的客家理论体系也有不少新突破,“多元一体”成为各地打破客家“梅州正统论”的有力武器。沿该路径,河源也将有可能建构自己在多元客家中的“一元”,而这条路径的主要内容就是历史定位和区域内的文化整合。
二、从“古邑龙川”到“客家河源”:地域文化建构的文脉梳理
客家尽管是一个较晚建构起来的族群与文化概念,但并非无中生有,确有赣闽粤边地区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厚实的建构基础。毫无疑问,秦代龙川建县并由后来成为南越王的赵佗任县令是河源最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资源,龙川因而也被称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2]应当说,龙川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获得这样的称号确实当之无愧,但用“古邑龙川”作为整个河源地域文化建构的主体显得有些偏颇。因此,河源地域文化的建构应完成从“古邑龙川”到“客家河源”的转变,也即是说“客家古邑”的内涵在于“客家”,而古邑则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品牌。
关于赵佗龙川建县的对河源乃至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影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论述,这其中不少可成就“客家古邑”之“古邑”说法。下面讨论“客家古邑”的之“客家”内涵。
唐代,俚人头领杨世略归唐而成为循州总管后,俚人进入了一个迅速汉化的过程。俚人“自隋唐以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缡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①《古今图书集成》卷1375《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循州也在同一进程中。古越人的后裔后来融入客家,罗勇教授在《客家赣州》一书中称其为“客家先民之先民”。客家文化中就有不少古越族的遗存。如汉开帝平定南越和东越后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帮衰耗。(汉武帝)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3]1399-1400而嘉靖《惠州府志》引天顺旧志云:(明代中期),惠州府属各县,“习俗多信鬼神,好淫祀。几有疾病,却医而用巫”,“常以鸡骨卜年”。“买水”浴尸亦是越人习俗之遗存。
经过唐中后期安史之乱等动荡后,粤东地区人口下降迅速,循州在天宝元年有9520户,但到元和年间,已经下降到2089户。②两个户籍数转引自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160页。王东教授由此认为:这样的人口数量,“与秦以来经两晋南北朝的移民无法对接”。河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客家先民的进入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客家民系在此孕育。

表1 宋元时期粤东梅循惠三州人口户数表
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虽循州当时还辖今梅州的兴宁、五华二县,但今河源市的河源县等属惠州管辖,但宋代河源的人口户数远超梅州却可以肯定的,这种较大的优势一直沿续至元朝。这一阶段正是客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谢重光和罗勇均认为“客家形成不迟于南宋”。而河源是这一时期客家形成的重要参与者。
宋代,盐为国家专卖,官府于建隆二年(961年)颁布《官盐阑入法》,赣南只能食用淮南盐,闽西只能食用福州盐,官府垄断加上路途遥远,盐价攀升而盐质低劣,赣闽粤边私盐贸易兴起,而运盐的主要路线就是循梅路。这场在赣闽粤三角地区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的私盐贸易带动了客家大本营间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流,王东认为“就赣闽粤边地域社会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而言,两宋时期私盐贸易的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指标意义”。[4]182这一地域社会结构过程的结果就是客家民系的形成,而河源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作用。
北方汉民的大规模进入,宋代的河源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农业较为兴盛,依托东江的水运发达。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诗中写道: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他在海南岛落魄之时典当衣物也想念河源之米,可见其在谪居惠州时,对河源之米已经有非常深入的认同了,也可见河源当时不但农业发展,而且东江水运发达,大米方能大量售往惠州。
南宋末至元初的客家人联合抗元斗争增强了客家内部的联系,而南宋至明代的几次畲汉大起义又推动了客畲融合。起义军转战赣闽粤湘,起义被镇压之后,王阳明在畲族和客家“流民”较多的地区设立县,其中就有和平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使畲族人不敢聚居于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族,畲族与此时居住在山区的北来“流民”一起成为了官府的“编户齐民”,以致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河源一直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发生地。
河源客家在明末清初大量向外移民,一是向赣南地区“返迁”。从赣州向西经南康过上犹到崇义,或经信丰至三南,我们发现不少从河源迁去的宗族村落。二是清初“迁海”与“复界”,官府颁布一系列招垦令,河源客民与梅汀客民一道向沿海、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深圳、佛山、江门、肇庆直至广西等地成为河源客民的目的地,也有“填四川”中迁往四川者,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客家分布格局。
据以上分析,大概可得出以下推论:河源自宋朝以来参与了客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客家的源发地之一,而在这过程中,河源客家文化不但具备了客家的基本文化特征,也形成了自已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客家古邑”之“客家河源”的真正内涵。
三、客家文化产业:河源地域文化建构的源动力和特色方向
纵观各地客家文化建构,笔者认为从动因而言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从“原乡”迁出者在与其它族群的挤迫下形成强烈的客家认同从而建构客家文化体系,估且称之为挤迫模式。赣闽粤边地区百姓在清代至民间外迁者受到当地土著居民之排挤和污蔑进行了迟日旷久的文字官司,在这过程中,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一批客家学者、政要和商界名流等对客家进行了系统的建构,梅州以此为基础成功成为客家地区第一个有着自己地域文化体系的“世界客都”。
二是经济利导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于经济发展需要,不少地区打起了客家牌,在本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本地的客家文化体系,赣南、闽西多为这种模式。
三是文化产业引导模式。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与地域文化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地区文化产业的基础就是文化认同与地域文化的建构,发展文化产业必然成为该地区文化建构的强大动力。同时我们观察到文化产业过程也是文化建构的过程,产业需求诱导促使文化生产出现了相应的、与学术建构不一样的体系,台湾以“桐花祭”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产业对台湾客家文化的建构是个典型。
这点河源自身也是个例子。河源利用自身地域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发展应是客家地区比较早的,影响也比较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旅游之初,当河源不少居民还知道自己的客家身份时,旅游部门即开始打客家牌。本世纪以来,随着河源与万绿湖旅游品牌的成长,苏家围客家乡村旅游区、南园古村等一批客家文化主题景区的开发和一系统河源特产的开发与热销,还有河源客家菜在广东的推展等,以旅游为主的河源客家文化产业可谓初具规模。而至今的一个高潮是“客家古邑”城市文化品牌的提出与建构。从提出“客家古邑”到申办第23届世客会的成功,河源仅用一年的时间,创造了大陆申办世客会的奇迹。政府组织媒体、相关企业和社团等开始了新一轮建构河源的客家文化,客家古邑文化研究会和客家文化学院的成立、电视台和报纸对河源客家的报道、网络对河源客家的争论,这对河源客家文化的挖掘与宣传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样建构起来的客家文化与有着较为深厚学术研究的梅州、赣州等地自然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产业是因需求而生产,河源的整个客家文化体系首要彰显的就是市场所需要的。因此,东江客家菜系、山歌、服饰、娘酒、诸如五指毛桃之类的特产等就成为比客家历史源流等沉重题材更鲜活的展示,这成为河源客家文化建构的一大特色。
河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在“客家古邑”的品牌引领之下建构起来,强化了河源人的文化认同,这是河源客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河源客家古邑文化建构的过程彰显了与其它客家地区不一样的特色,这种地方文化建设的路径或许也是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参考的。
[1]万建中.客家族制造神话叙事[J],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1):104-111.
[2]谭元亨.赵佗、中原文化、岭南文化与客家[M]//邹观林,吴良生.世界客属第23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9-11.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