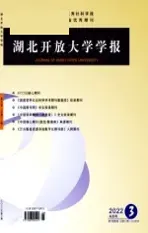不只是情爱——析苏伟贞《陪他一段》中的矛盾性
2013-08-15蔡榕滨
蔡榕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9)
据记载由于台风的作弄,沈光文(1612—1688)无意中成了台湾文学的开山老祖。[1]不论台湾文学是否真由此始,台湾文学终是发展并繁荣起来了,而在此过程中台湾文学也成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学界的关注点之一,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女作家的创作又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台湾女性文学发韧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上个世纪 80年代则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2]苏伟贞即是崛起于这个时期的新世代女性作家群中的一个。苏伟贞虽然出身眷村,后入军校(政战学校),也曾担任多年军职。况且也写作眷村情怀、袍泽之情、弟兄之爱,然而与传统女性作家相似,苏伟贞的小说作品亦多重于对爱欲疆界的探勘。[3]也正因其小说中多涉男女的爱情纠缠,于是苏伟贞亦被不少评论者冠以“言情小说家”之名。
《陪他一段》是苏伟贞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曾在台湾文坛引起较大的反响,时至今日还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给人以震颤。学界在对此作品进行评论时多涉其情爱层面。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是一篇有关爱情的小说,其间讲述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女子——费敏的艰辛爱情路。整个故事是在作者如散文诗般的柔美不拘,轻声慢语中缓缓开启的,阅读过后让人觉得如梦似幻般,悠悠忽忽,或许这也正是作家的自画般“我十分怕吵,说话像蚊子叫……”[4]不过,细读之下却不难发现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明的暗的矛盾、对立甚至紧张的对抗,如成熟与年轻,美与不美,生与死,真与假,恬静与炽热、温馨与寒冷、救赎与被救赎,乌托邦与俗世,传统与现代等,即纠葛于故事间的不仅是人,还包含了时间与空间。为此本文将试图阐释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情爱世界的真与假、人世间的对抗与依存、时空中的虚与实等多层面的矛盾,及其矛盾产生的因由。
一、爱情世界的真与假
《陪他一段》中的女主人公费敏是个悲情人物,在爱的不可得的情况下,她最终选择就死。对于费敏赴死的结局,文中所用的徐志摩的诗实在是早有所预示的。“当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我坟上……”[4]费敏的死是不争的,她的不幸亦是可见的。原因或许在于其手气的不佳,然而更在于其假戏真做的不该。虽然也有看似李娃般的决然,但是毕竟是没有得到李亚仙般的圆满情爱。不是谁的错,只是小说中的他不是郑元和。何况不是说好“陪他玩一段”吗?即是如此宣言,那“一段”自然亦注定不可长久,分离便是再所难免;更何况是“玩”了。当然,一个女子如此情爱宣言在那个封建势力仍有顽固的影响力,性别的歧视仍然存在的年代不知会引来多少嗔怪或惊奇的眼光。[3]然而,要是因着“陪他玩一段”的话语便觉得费敏是洒脱的,那自然是过于轻信了。果真如此,为何还要那么的独自儿用了五天时间来下个决心[4],最后还为何要死,不管怎样这个最早提出“玩”者最后却真真成了输家,不仅输了人更是连命也失了。但这却又该怪谁?那个看似真心要守护她一辈子的负心汉吗,“爱是不必说抱歉”[4]其实本来就没有真正地宣布要开始又何来结束,何况这本来就是明知的无果之恋,又何必太较了真。
二、人世间的对抗与依存
王德威先生认为“在苏伟贞最好的情爱小说里,竟有极阳刚的、军事化的精神贯注。”[3]在笔者看来,小说家的军人气质,除了体现于其小说人物的精神层面,即如费敏这种舍我其谁的抱负与从容,今生无悔式的牺牲奉献。作品中人物间的,即便是爱人也如敌人般的对抗是另一层面的,亦是更具有张力的表现。类似于“谁怕谁”“对手”“反击”“攻击”“坚守”“撤离”“如临大敌”“提防”等言语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着实不低。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就现出僵着的态势,不肯放松,不肯投降。即使是无望中,也只能“将自己完全亮在第一线,任他攻击也好,退守也罢,”因为“反正是要阵亡的”。[4]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消极之中,一如费敏却仍讲出了“我这辈子不嫁便罢,要嫁就一定嫁你!”[4]如此充满严重的对抗性话语。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小说人物多又是沉溺于自己的情感世界中的,他们总是如此的孤单,有着甚至令人无法承受的寂寞,即便是有了情人,有了爱的,却也是那般不可得救。甚至于连爱也是会冻死人的。于是为了存活,不论怎样地对抗着,尽管明知非属于对方却也只能靠在一起,因为只有人体才有温度。[4]就如费敏,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他的救赎者。初始的费敏确实是以基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似乎她对于他的得救是有义务的。况且“她过足了扮演施予者这个角色的瘾”[4]因为他说过自己需要很多的爱,因为他看上去是那样的孤独无依,于是为了怕他在孤独中死去,费敏便把自己视为了拯救者,如此地尽职尽责。即使她也不过是这么个平凡的小女子,却也甘心地苦着自己。而费敏自身,当她完成对他的救赎。其实,费敏的拯救也并未成功,他是一如既往的孤独,“他眼里仍然是寂寞的,看了让她愤怒,他到底要什么?”[4]当她自身要从圣坛走入俗世之中,从一个施予者欲成为索求者,从救世主而沦为需要被拯救者时,却因失恃而终于赴死。
三、时空中的虚与实
整个故事是在电影中开始亦在电影中结束,一切的死生存亡,真假虚实都在其间演绎,作品的叙事模式其实是老旧的,正如作者自言“这本剧本太老套”[4],然而剧情却又是实在的,曲终人散既在戏里亦在戏外。只是这戏里戏外不论情感世界真或假,不论人们是对抗着或是相互依存着,一切都无法逃脱于时空之外,即作品中所呈现的种种矛盾、对立甚至于对抗,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或最根源的便是在于这时空的纠葛。一如苏伟贞其他的作品,《陪他一段》中的时空纠葛是十分明显的。“现代”与“古老”的对立矛盾在小说中不断地被提示着,它们困挠着作品中的人物,即便是爱情层面“他们之间没有现代式恋爱里的咖啡屋、毕卡索、存在主义,她用一种最古老的情怀对他,是黑色的、人性的……”[4]只是不管怎样,人们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继续着生活,继续着爱。正如上文所述,小说人物多是沉溺于自己的情感世界中的,即真正“陪伴她自己(苏伟贞)的只有自己的心灵活动。”[5]即便是每天汲汲於名利,为人情世故而忙的他似乎更多地也还是沦陷于自己所营造的情感世界中,何况女主人公费敏,可谓 “以爱欲兴亡为已任”[3]。而作品人物的这种状态在笔者看来某种程度上或者即是陈芳明先生所言及的台湾女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世界”。[6]只不过,“乌托邦书写倾向”在苏伟贞这里在《陪他一段》中便已较鲜明地表现出来了。[1]然而,“乌托邦世界”毕竟只是“乌托邦世界”,于是不论南方澳、礁溪、大直等地是多么的幽静,多么的令人神往,处于现实之中的人们却总得回归世俗生活。正如费敏的终不可免俗,她一样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她再清明也不得不从圣坛上走下来成为需要被救赎者。一切的矛盾都是那么不可调和的存在着。而这其间纠葛毫无疑问是透露着某种历史的因缘。若深究,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正是当时处于内政外交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的台湾社会,人们普遍的无根无力、漂泊惶惑的心态在作品中的投射。正如现在印证的只能是对过去的怆然,俗世也只能衬得理想更显得易于幻灭。当“人的‘意识’与它所面对的‘现实’互相冲突,使人总是处于一种永无宁日的意识漂泊和自我放逐状态之中。这样‘灵魂’找不到‘躯体’,或者找到了却又无法在这个‘躯体’上安下心来,即无法彻底变同现实的矛盾态度。”[7]而或许正是历史变更所带来的不安,才使得苏伟贞笔下的《陪他一段》充满了这样重重的矛盾纠葛。
[1] 古继堂. 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2] 刘登翰,庄明萱. 台湾文学史(第三册)[M].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
[3] 王德威. 落地的麦子不死[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 苏伟贞. 陪他一段[M]. 洪范文学专书,1996.
[5] 苏刚. 女儿和她的小说[A]. 陪他一段[C]. 洪范文学专书,1996.
[6] 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
[7] 古继堂. 台湾小说发展史[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Not Just Love——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Su Weizhen’s “A Journey with Him”
CAI Rong-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