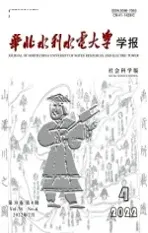试析中西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化遗产越南阮朝都城顺化——以顺化外城墙为例
2013-08-15王继东
王继东
(河南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河南郑州 451191)
1802年阮福映建立阮朝,定都顺化。顺化历经数十年修建,成现在规模。其以北京城为蓝本,结合法国沃邦式军事防御体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于1993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西方文化对阮朝都城顺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拟以顺化外城墙为例作一探讨。
一、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方型结构
“越南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建筑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形式,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供了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空间环境。中国的建筑技术传入赶制的历史很久远,深刻影响着越南。”[1](P45)越南修建都城时往往以中国都城为蓝本。“越南陈朝陈英宗兴隆七年(公元1299年),越南使臣邓汝霖到北京时,曾密画宫苑图本,以资建城时借鉴。”[2](P60)这一事例说明了越南在都城建设方面向中国学习的情况。至于顺化,更是如此,“其规模形式,大部分仿自中国的北京,为东方著名的中越合壁的都市”[3](P49)。据越南史书记载,阮朝曾多次派遣使节团到北京求封的同时,学习北京城的规划建筑。
顺化依香江北岸而建,呈京城、皇城和紫禁城三重方形结构。这种方形城池结构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都城建筑思想的影响。著名学者张驭寰先生曾说:“我国(中国)的古城,绝大多数,或者说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城池平面都做方形城池。”[4](P293)中国城池建筑接近方形的传统,是基本上按《考工记》里所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理念来建造的。总结了史前及先秦城池而形成的周王城图,于战国时期流传开来。秦汉时沿袭周王城图,建城也均为方形,于是周王城图逐渐成为了中国修建城池的标准,方形城池也成为中国都城建设的基本标准。
阮朝都城顺化,除去东北角镇平台,外城墙呈比较规则的正方形。外城墙周长约10公里,每边约2.5公里。如此标准的方形结构,显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筑城思想的影响。
通过考察嗣德本《大南一统志》①《大南一统志》曾前后修过两次。初修倡议于阮朝嗣德二年(公元1849年),实际工作始于嗣德十七年(公元1864年),至嗣德三十五年(公元1882年)编成草本,仅有抄本流传,是为《大南一统志》嗣德本。阮朝维新帝时,令高春育等人纂修安南本土的地理志书,于维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元1910年1月18日)成书,仍名《大南一统志》,是为《大南一统志》维新本。维新本于1941年3月由日本印度支那研究会据以影印出版,分为第一、第二两辑。如不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均出自《大南一统志》嗣德本。一书所附各省图可看出,阮朝各省城池也大都采用方形结构。在《大南一统志》所附26幅省城图中,有21个是方形或接近方形,占总数的80%以上,充分说明了阮朝修筑城池时方形是其首选。
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沃邦①沃邦(Vauban),名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Sebastien Le Prestre,1633~1707年),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军事工程师和建筑师,作为一名攻城术专家,沃邦被路易十四封为元帅。式棱堡造型
“由于百多禄②百多禄,法国传教士,即阿德朗主教,名皮埃尔·约瑟夫·乔治·悲柔·德贝埃纳(Pierre Joseph Goerges Pigneau de Behaine,eveque d’Adran.),越南人称他百多禄。的积极活动,阮映(即阮福映)终于投靠了法国资本家。”[5](P434)在顺化建造的过程中,那些帮助过阮福映的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筑城方面的人员参与其中,这就使得顺化城受到了西方筑城文化的影响。
阮朝顺化外城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棱堡式造型。除去东北角的镇平台,顺化外城墙共由二十四个棱堡组成,每一个棱堡均有名称,上可安放大炮,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的炮台。
这种类似于中国城墙中马面形式的结构,增强了顺化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属于沃邦防御系统,是当时法国人引入越南的。《大南实录》中关于“棱堡”的第一次记载出现于1792年。“壬子十三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春正月,筑美湫堡(其堡棱角如梅花状,周围四百九十九丈),发诸军营官兵应役,帝驾幸观之。”[6](P381)从“其堡棱角如梅花状”可以看出这是西方棱堡的典型特点。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及其门徒先后于1788年到越南,所以法国人参与美湫堡的修建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能正是因为它不同于越南本土的军事建筑,《大南实录》才会专门记录。
法国人的筑城技术在当时西方处于领先地位,恩格斯曾说:“在所有的筑城学派中,法国派享有最大的声望。”[7](P339)在法国派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沃邦式建筑,“使法国派成为欧洲第一的是法国的沃邦元帅”[7](P340)。“早在沃邦出生之前,半月堡、凸角堡、棱堡就已经面世了,他的天赋体现在更为精妙的工程中……对于这些讲究实用性的军事建筑,沃邦的设计将审美性和功能性很好融合在了一起,继而通过许多特别的方式将这种和谐之美表现了出来,并发扬光大。”[8](P74)《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③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01页。一书所附插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棱堡式造型,与阮朝都顺化的京城城墙如出一辙。
用沃邦名字命名的军事建筑——沃邦防御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大陆,甚至流传到了国外。阮朝建立和统一的战争中,以这种先进筑城理念修建的美湫堡等防御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阮朝建立后,沃邦式建筑得到进一步推广。从《大南一统志》附图可以看出,不仅京师顺化采用这种防御系统,其他省城如河内等城池也多采用这种结构。“他(嘉隆帝,阮福映)不仅不敢在升龙建都,而且还下令捣毁古老的京城,按法国沃班(邦)式样建立一个小城市。”[5](P442)
《大南一统志》附各省省城图26幅中,18个省的省城图都具有明显沃邦式棱堡城墙,占总数近70%,可见沃邦式棱堡造型影响之大。
三、中西文化共同影响下的顺化外城墙城门
欧洲沃邦式城墙的都市一般都呈圆形,这是因为“这些理想的城墙都市之基本平面,大部分是圆形,其周围是被星形棱堡与护城河所围绕。此乃因这种配置可拥有从圆心的都市核心——军事司令部到周边的最短联络道路”[9](P14)。顺化都城接近于方形,并非沃邦式棱堡都市的圆形,必然会影响到顺化城的城门。
顺化京城共有11个城门,南面4门是体仁门、广德门、正南门、东南门;东面3门是正东门、东北门、镇平门;西面2门是正西门、西南门;北面2门是正北门、西北门。如此城门开法是否完全按中国传统筑城思想开的呢?
元大都被认为是最接近于中国传统筑城理念的都城,和顺化城一样也是开11门。虽然元大都的营建最为接近《考工记》理念,但并不是按规定的每面3门共12门,而是南、东、西每面各3门,而北面只设2门共11个门。“推究其原因,就应与道家思想有关。按《周易》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取天数一、三、五、七、九,和地数二、四、六、八、十,这些数的天地之中和,即将天数的中位数‘五’,和地数的中位数‘六’相加之和为‘十一’。这取象为阴阳和谐相交,衍生万物,天地合和,自然变化之道尽在其中。大都城既是天子王位所在,众生所依,自当被视为天地之正中。其全城设计,共开十一门,即是取象为阴阳和谐相交,衍生万物之意。至于南墙开三门,为奇数,即天数;北墙开二门,为偶数,即地数。也就是说,在方位上,城南方向为天,城北方向为地,城南开三门,城北开二门,并用此二三错综之数,双示天地相交,万物相合之意。”[10](P12)这一解释说明了古代东方文化与哲学观念在城门设计上的反映。
顺化城表面上看同元大都城一样都是11个城门,但其设计却与元大都相去甚远。除去东北角的镇平台,顺化京城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方形。由于采用了沃邦式棱堡结构的外城墙,城门只能开在两个棱堡之间。除去四角,外城墙每边均有5个棱堡,如果采用对称的开门方式,各边开城门数为2或4。顺化东、西、北三面都是2个城门(之所以东边开3门则是因为有了镇平台而多开1门——镇平门),南边是4个城门。按中国的传统,城门一般以单数,特别忌讳用“四”这个数字。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城墙棱堡数目已定,不得已而为之。顺化城虽有明显的中轴线,但外城墙的南北城门却无法坐落其上。正是因为顺化京城方形的形状,加之吸收了法国沃邦式防御系统,二者共同作用才出现这些情况。阮朝具有棱堡城墙结构的各省城门也是如此,由《大南一统志》附图可以看到,这些省城外城墙所开城门也均在两个相邻棱堡之间。
四、顺化城棱堡形式城墙设计者
阮福映在建立阮朝统一越南的过程中,得到了法国资本家的大力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百多禄,由他出面动员法国在东方各殖民地的资本家出钱购买武器并招募人员帮助阮福映。其中有许多从事城堡建筑、造船等专业人员。“应主教(即百多禄)的劝告,多数的法国人(大部分是法国军舰的义勇兵)渡海来协助交趾支那国王(阮福映),其中最有名的是 Olivier de Puymanel、Dayot、Vannier、Chaigneau等人,他们从事要塞城堡的营造,以及造船、编组海路军队和工作,对于阮福映能够战胜西山党有很大的贡献。”[9](P12)“他们采用法国军事技师Vauban式的城墙工事,兴建城墙,河内因而产生重大的改变,规模也缩小了许多,变成了一边只有1公里正方的大小。”[9](P12)
《大南实录》对追随百多禄来越这几个人记载:“其徒有名幔槐者,名多突者,名吧呢者,名乌离为者(即名信),名黎文棱者,皆富浪沙人也。名耶悲者,名麻怒者,皆希波儒人也。”[6](P1322)
《越南史略》记载:“与百多禄同行的还有塞玉(越南史作车柔,法文全名Jean Baptiste Chaigneau,——译者)、阮文胜(P.Vannier,越文译阮文胜,从此,——译者)、维多·乌离为(Victor.Olivier)、戴福桑(De Forcant)、阮文震(Dayot,越文译名为阮文震,从此,——译者)。”[11](P292)这些追随者中“有专习机械工程者,为阮氏筑柴棍(即嘉定土城)、河内两城,并依富春江岸营炮垒”[12](P12)。霍尔认为,这个重要人物就是皮马尼尔。“法国志愿人员提供的帮助对阮氏的事业有着巨大的价值……奥利维埃·迪·皮马尼尔承担了训练新兵和设计、建筑防御工事的职务。”[13](P513)“奥利维埃·迪·皮马尼尔(Olivier de Puymanel)给阮朝训练军队,同时他也是将一个世纪前由沃邦在法国倡导的军事防御工事原理介绍到印度支那的人。”[14](P180)这里,阿尔斯太尔·蓝姆明确指出,介绍沃邦式防御体系建筑到越南的就是皮马尼尔。
通过对比,皮马尼尔即乌离为,但皮马尼尔并不是顺化棱堡形式城墙设计者。“在那些曾于阮映(即阮福映)的长期斗争中给与他以如此宝贵援助的法国志愿人员中,只有四人到1802年以后仍留在越南任职。他们是阮文胜(原名菲利普·瓦尼埃)、车柔(原名琼·巴蒂斯特·夏玉)、戴福桑和德斯皮奥医生。”[13](P517)据阿尔斯太尔·蓝姆对于皮马尼尔的生平介绍可以看出,皮马尼尔生于1768年,1788年到达越南,死于1799年①参见 Lamb,Alastaer,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é:Narrar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d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0,p.180.。查阅《大南实录》可发现,1799年后,便没有关于乌离为的任何记载了。所以,乌离为于阮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不可能参与阮朝都城顺化的建设。
虽然皮马尼尔是将沃邦防御系统介绍到越南的人,但他并没有参与顺化城的修建。参与修建的法国人只能是后来留在越南为官的四个人,即阮文胜、车柔、戴福桑和德斯皮奥。
此外,京城修建过程中,本土的越南人也参与了设计修建。“帝以天下既定,欲增广都城以为四方朝会之所,乃幸金龙至清河(俱社名),遍观形势,命监城阮文燕于富春都城外四面标度而加广之,帝亲定城制。”[6](P617)嘉隆帝阮福映自己不仅“遍观形势”,还“亲定城制”。监城阮文燕具体负责“于富春都城外四面标度”的任务。一些长期与法国人一起工作的越南人,如陈文学,曾先后参与嘉定城和美湫堡的修建工作。“学留从奉侍,率西洋通言与乌离为(洋人),翻译西洋言语文字及制造火车、震地雷兵器等项。庚戌(公元1790年)筑嘉定城,学标度土分及诸条路……壬子(公元1792年)筑美湫屯,学进图式。学工于画,凡筑屯堡、度里路、画图标志皆出其手。”[6](P1180)嘉隆五年(公元1806年),陈文学升至监城使。因此,在修建都城时,对于京城的棱堡式城墙的修建,陈文学也一定会参与其中。另外还有范文仁、黎质、阮文谦等具体负责修建工作的越南人,也必然在城墙的设计修建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顺化外城墙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影响,双方在相互妥协的过程中相互融合。为了符合中国传统的筑城思想,沃邦棱堡式的城墙没有按照西方传统建成圆形,而是围成接近标准的方形。同时,中国传统都城的开门方法又不得不适应这种棱堡式造型,以致于各边都为双数开门。也就是说,西方棱堡式的外城墙迁就了中国传统方形的都城形状,而中国传统都城城门的开法又迎合了西方棱堡式城墙的结构。当然,这两种文化还必须统一于顺化当地的实际地理环境中来。例如,由于皇城位置偏南有可能使得京城与皇城两道城墙重合,因此设计者将南面外城墙修筑成了弧形。正是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造就了顺化城独特的建筑风格。
[1]杨春雨.从明朝北京城和阮朝顺化城看中越建筑文化交流[J].东南亚纵横,2011,(6).
[2]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3]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张驭寰.中国城池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M].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张登桂.大南实录[M].东京:有邻堂,1951-198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Franck Lechenet-Dragonimage.沃邦与他的百变军事城堡[J].李亦萌,李弗兰,译.文明,2007,(6).
[9]黄兰翔.十九世纪越南国都(顺化)的城市规划初探[J].文史哲学报,1998,(48).
[10]侯仁之.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J].城市规划,1997,(3).
[11]明峥,范宏科,吕谷.越南史略(初稿)[M].上海:三联书店,1958.
[12]邵循正.中法越关系始末[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3]D·G·E·霍尔.东南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Lamb,Alastaer.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é:Narrar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d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