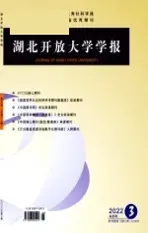从主权在民到公民权利——浅析卢梭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困境
2013-08-15魏银
魏 银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 江苏 南京 210046)
一、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内涵
(一)以自然法为社会契约前提假设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以“人,生来自由之身,却无处不披枷戴锁。”[1](P11)开篇,从自然状态下个人应然的自由与平等和社会状态下个人实然的束缚与等级之间的矛盾出发,通过订立他构建的社会契约使社会中的人重新获得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把自由和平等当作不容置疑的“天赋人权”而加以前提性的规定。但是,当个人遇到的生存障碍已经超过他的承受能力,那么人类只有改变这种离散的生存方式转而进行联合才能够避免灭顶之灾。由此可以看出,订立社会契约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是在订立社会契约之前,人是以独立的方式处于自由而平等的自然状态中,天然地获得各项自然权利,这种自然的状态是和谐的而非“战争的,野蛮的”;二是在自然状态下,由于各种妨碍生存的因素,人以独立的方式已经无法较好地生活,在不能创造新的力量的条件下必须进行联合。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论证范畴不涉及这两点,因为这两点自然而然地被他认为是前提条件。卢梭认定的前提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最早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的雏形。伊壁鸠鲁借用“原子”理论,以形而上的方法宣布了人的自由的本质、国家的起源的契约性。伊壁鸠鲁认为每个社会中的个人都可视为一个独立且平等的原子,可以自由平等地与他人发生关系,订立契约,进而结成社会。[2](P61)而这种以“自然法”为基础,以关于个人自然权利的形而上学假定为前提被卢梭认同并且也当作他构建社会契约理论的前提。
(二)以公意为核心具体构建社会契约
卢梭认为,每个人在订立契约时,必须将自己所有的权利和权力让渡出来,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交给联合的整体。[3](P27)这看似是“霸王条款”,实际上卢梭通过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公众意志——巧妙地让契约方认为是最平等的契约。“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4](P43-44)公意既然在卢梭的眼中是共同体的意志,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那么就名正言顺地为所有缔约方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共同体的意志即公意是绝对不可以分割的,因为公意是出于神圣的契约之下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分割自己的一部分就是自我伤害,是公意所绝对不允许的。[5](P355)因此,每个人都将自己所有的权利和权力交出去,置于公意的领导和统筹之下,就相当于自己也同等地拥有了对他人的权利和权力。在这场交易中,个人的权利和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削弱而只是转化了形式,但是每个人却获得了更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在此,卢梭通过公意将整体与个人融合为一体,服从整体就相当于服从了自己本身。
首先,卢梭认为抽象的公众意志通过主权表现,主权根据公意而形成。主权者是由全体个人结合而形成的有生命和意志的公共人格。主权是不可分割、不能被代表、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对主权体做出任何限制都不可以,没有法律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哪怕是社会契约本身。[6](P29-41)由主权的性质,卢梭指出主权属于人民——主权在民,而不赞同霍布斯的主权在君。他的出发点是人民只有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而不是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才能够真正通过社会契约获得自己可以做主的权利和权力。其次,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的联合整体,以国家或主权体命名,因此国家是一个具有公共意志的政治实体,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和本质。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在国家整体的分类上,卢梭只承认民主共和国,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由人民自己制定法律,由人民安排政府去存的国家。最后,卢梭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引入政府来建立臣民与主权者的中间桥梁。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卢梭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政府与主权者各自应遵守的权力分配。“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执政权则是指挥身体各部分运转的大脑。大脑瘫痪时,人仍然可以活下去。一个人成为痴呆,仍然能存活,可心脏停止作用,他就会死去。”[7](P125)根据哪种政体更适合实施主权者的意志而不使政府权力趋于专断和腐败,卢梭认为选举的贵族制最适合于运用主权者委托的行政权。[8](P191)
综上所述,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遵循这样一条理论逻辑: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拥有自然权利,但是平等自由的人在自然状态中遭遇威胁,因而有必要进行联合共同对抗。通过行之有效地缔结社会契约,使自然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而成为社会人。根据公共意志而形成主权体或国家,并且将主权归属于全体人民,人民通过制定法律让政府具体实施公共意志,最终让社会人获得道德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
二、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困境
(一)前提假设遭受质疑——功利主义挑战
卢梭身处18世纪封建君主专制的法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他从黑暗的现实社会出发,反其道而行,希望通过追溯到一个平等自由的原始自然状态,重新通过一种符合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联合方式使社会中的人再次获得自由和平等,而这种方式就是订立社会契约。也即,卢梭采取一种追本溯源的方式,试图找到一个起点,开始构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个起点就是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人拥有自由、平等,保护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利的自然状态。卢梭没有对这个起点做过多的论证,而是直接将其作为前提条件。
17、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自然法、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本质,政府的目的和运作,强调人的理性和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等等。17、18世纪著名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如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都站在自然法的角度主张天赋人权,以保护全体人民的自然权利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和目的。但是,到20世纪人们不再相信自然法,更怀疑任何天赋人权的形而上学,强烈要求在经验中验证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一旦被抽掉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置于经验情境之中,其内在矛盾必然暴露无遗。”[9]英国功利主义对用“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来解释国家起源和主权学说进行抨击,认为这是没有坚实根基的空想,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高效运作。休谟指出原始契约“在经历了政府和君主的不断更替后其效力已经销蚀殆尽”,其结果是“几乎所有现有的政府或任何有据可考的政府……不是建立在篡夺基础上,就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10](P61)边沁根据他的“最大幸福原则”,不仅否定自然法的存在,而且也否定由原始契约构成社会、成立政府的存在。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自然法,而只存在人定法,国家的产生或政治社会的形成源于人们服从的习惯。[11](P125)
(二)与其他社会契约理论比较——激进、难以操作
卢梭被认为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首先,他强调主权不可分割、是最高的、绝对的,因而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认为是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与之相对,洛克在《政府论》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分别从政府权力运作和法律的实质精神出发,论证了通过主权的分割和限制达到权力的相互制衡,最终保证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同时,由于主权不可代表、不可转让,致使卢梭在选择国体和政体类型时只能局限在民主共和国和直接民主制,而不能有更广阔的思维和视角。与此相反,同样主张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和政府起源的普芬道夫·塞缪尔则没有卢梭的激进性质。普芬道夫认为主权并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可以代表和转让。因为神法、自然法常常限制主权的运用,风俗习惯常影响主权者的行为,主权者只能就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方法达到主权目的作出决定。因此,普芬道夫·塞缪尔的理论表现出拥护开明的君主制度的倾向,在17、18世英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其次,社会契约理论既要求社会政治实体(国家或主权体)具有整体的权威以保障公意的实施,又坚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权利,这是一切契约论者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12](P189)与契约论的其他思想家不同,卢梭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虽然强调个人权利不可转让、不可剥夺,但是他更加认同个人与整体同一性的方面。他认为个人与整体发生矛盾时,“无论谁拒绝服从公众意志,整个实体都会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保持自身的自由。”[13](P31)他始终强调抽象的公共意志的核心领导作用,是国家起源、法律制定、政府构建等等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准则。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往往容易走向反面,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是一种极权的民主主义。当少数人因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不服从公意时,按照卢梭的说法,都会迫使这些人服从。个人权利在庞大的公意之下怎样可能实际得到保证,个人怎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的自由空气而不被公意笼罩,个人退出契约难道真如卢梭设想的那样简单,这一切都因公共意志而变得抽象。
三、结语:从主权在民到公民权利
卢梭社会契约理论被功利主义主要质疑的是其自然人的前提假设而不是社会契约的形式和效力或契约的必要性。后来主张社会契约理论者都试图针对功利主义的挑战进行完善以使社会契约理论走出困境。如康德明确把道德作为契约达成的最初要义和最终目标,使社会契约理论的贫困就不再是简单自然状态下对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拷问,而是对其道德基础的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则设计出一个“原初状态”区别于传统契约论的“自然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化解了功利主义对自然状态的批评。[14](P63)但是社会契约论者的各种理论仍然遭到各方的抨击,使得社会契约理论始终无法找到其假设前提的合法性。因此,跳出对社会契约理论假设前提无休止的怀疑,转而去分析社会契约的形成和效力或契约的必要性,或许更能够给现代政治生活以借鉴和指导。
卢梭强调人民的整体性和意志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则意味着将个人权利和自由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他认为整体意志坚决地得到执行,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得到最大的保障。实际上他的这种抽象的人民主权理论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成为少数人实施专制的口实。实质上,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要走出困境,必须放置在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生活的历史长河之中去审视。任何一个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无一例外都是时代背景和个人特殊经历的结合,当然应该关注卢梭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状况,以及特殊的人生道路。但是,往往正因为如此,也会不可避免地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使理论在以后的人类政治实践中受到挑战和抨击。纵观社会契约理论的发展路径,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达到了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顶峰,而也因此而存在着种种问题。要走出困境则必须追本溯源。社会契约理论的根本目的或者出发点应该是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害。因为自然人之所以愿意结束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能够使每个人拥有的自然权利和权力不受到损害。即使社会人在更多方面都优于自然人,比如:理性、道德等,但是人最根本的自然权利是不能够用任何其他东西代替的。主权在民并不意味着个人权利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公共意志的范围不可能是社会所有的人而只可能是绝大多数或者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直接民主制不能够在任何国家都高效实施是一个实践证明的事实。社会契约理论发展到现代,所面临的应该是公民权利如何切实有效地得到保障,这不仅是社会契约理论应该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理论共同面对的政治实践问题。
[1] [3] [4] [6] [7]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方华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2] 张秀.契约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J].求索,2009,(2).
[5] 任志军,欧佳佳.浅析《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与公意[J].法制与社会,2009,(4).
[8] [13]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9] 姚大志.国家是如何诞生的[J].开放时代,1997,(2).
[10] [14] 张秀.契约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J].求索,2009,(2).
[11] 边沁.政府片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