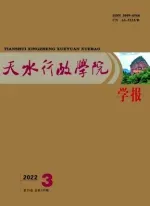府际合作: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的必由之路
2013-08-15冯海芬
冯海芬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陕西延安716000)
2012年3月2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我国第一部针对革命老区发展的综合性区域规划《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 (简称《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实施。历时4年编制的《规划》,国家从陕甘宁革命老区所拥有的能源、资源优势出发,将其定位为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现代旱作农业发展示范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即“一个基地四个区”。这是中央政府对老区发展导向、战略定位进行的规划,是从政策支持上对老区发展的扶持,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综合地、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陕甘宁三省(区)正积极抓紧策划项目,细化推进措施,争取尽快把政策机遇转化为现实发展成果。但是,陕甘宁三省(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占有等方面不尽相同,因而,在推进陕甘宁革命老区的振兴过程中,加强和优化相关政府主体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府际合作的内涵
William Anderson最早将府际关系定义为:美国联邦制度中所有类型和所有层次的政府单位之间所出现的大量重要活动或相互作用[1]。随着实践的发展,府际关系已不仅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还包括国际府际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国内府际关系。我国学者林尚立在其《国内政府关系》中,将国内政府间关系定义为:国内各级地方政府间和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各级地方政府间关系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关系[2]。学者谢庆奎在《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中认为,府际关系是政府间的关系,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3]。由以上定义可知,府际关系可以是同级或不同级政府间纵向、横向及斜向的网络式关系。有学者指出,府际关系的产生,是不同的政府行为体为了实现某一方面或某些共同的利益,在政府运作过程中发生的互动行为[4]。这种互动关系目前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交流与合作,竞争与摩擦,支援[5]。
府际合作作为府际关系的一种,是指不同政府主体为达到某一目标而以平等身份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对这一概念可做如下理解:府际合作的主体是不同的政府,它可以是同级的,也可以是不同级的;可以是正式的政府组织,也可以是经有关部门授权的其他组织;府际合作的目的是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如污染治理、打击犯罪、促进经济增长等;府际合作的参与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各参与者的要求;府际合作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形式可以有平行的和斜向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其内容涉及资源、人才、教育、工程、交通建设等。
二、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的必要性、条件和优势
(一)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加强陕甘宁革命老区府际合作是解决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维护区域公共秩序,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有效途径。与我国府际合作蓬勃发展相伴产生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许多跨区公共难题亟待各行政区政府解决,如流行病防治问题、环境保护、跨境犯罪问题、污染治理等。这些难题往往超出了以往单一地方政府独立处理的能力。由于缺乏跨区域问题处理的法理与制度层面的支持,单一地方政府面对此类公共管理事务时,表现为经常性的“缺位”或偶然的“越位”,致使区域内公共管理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利于区域公共秩序的维护,良好的公共服务便无从谈起。因此,开展府际合作是克服陕、甘、宁三省单一政府处理区域性公共事务力量不足的必然选择。
第二,从资源配置方面来说,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是克服“边界效应”的重要方面。虽然我国目前府际合作组织日益增多,但由于行政区划客观地存在,各地方政府作为本地域的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围绕政策、资源及公共物品等展开竞争,合作区内的“边界效应”日益凸显,导致各行政区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受阻,资源浪费严重,合作目标难以实现。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往往依托自身具有的资源来规划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道路,而陕、甘、宁三省(区)境内拥有着相似的能源、资源结构,在发展中极易形成相同的城市产业,出现产业同构现象,从而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因此,加强陕、甘、宁三省(区)间府际合作,建立积极有效的行政协调机制,有助于三省(区)资源效用最大化,有助于各行政区间实现资源互补,促进整个合作区的协调发展。
第三,从信息沟通方面看,开展府际合作是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之路的必然选择。良好的信息沟通是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助于各方准确理解政策,提高工作效率,化解矛盾。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自利倾向,会封锁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并且竞相出台地方保护政策和优惠政策,运用行政性力量干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各地方政府间经常出现信息不对称,导致“行政区经济”形成。行政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企业化;企业竞争寻租化;要素市场分割化;经济形态同构化;资源配置等级化;领域效应内部化等[6]。并且由于《规划》涉及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区)的8个地级市,9个县(市),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具有地域广、跨区多的特点。如此大跨度的范围,可能使陕甘宁三省(区)在具体合作过程中难以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创新等方面的协调统一。因此,为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陕甘宁三省(区)有必要建立及时、有效的区域性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各方面良好的信息沟通,为整个合作区域实现集体行动提供可能。
(二)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的条件和优势
第一,各省(区)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为陕甘宁开展府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陕、甘、宁三省(区)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即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前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基于这样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规划》提出要将陕甘宁革命老区建设成为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这就为陕、甘、宁三省(区)进行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其次,陕甘宁革命老区有着共同的现实背景。如《规划》中涉及的8市9县的共同点:均位于我国能源开发基地鄂尔多斯盆地境内。目前这一地区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39%,产量已达到3亿多吨;蕴藏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约占全国的35%以上;整体能源调出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且区域内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也非常丰富,具有发展百万千瓦级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自然条件等的限制,陕甘宁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整体脆弱,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经济社会一度发展较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支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和69%,城乡居民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和68%,55%的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7]。而国家为老区“量身定做”的《规划》,成为这一区域加快发展的绝好机遇。面对共同的历史文化、发展现实以及政策叠加机遇等优势,三省(区)只有进行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实现陕甘宁革命老区的振兴。
第二,明显的合作收益为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提供了拉力。促进本行政区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参与府际合作各主体的根本动因。我国蓬勃发展的区域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合作收益。再者,通过区域合作,还可以促进各参与主体治理水平的提高。一个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民众对他的认可与支持程度。对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来说,高效集约发展区、旱作农业发展区、生态环境修复区、生态环境保护区的建设,通过三省(区)的合作才能进行有效治理,才能降低治理成本,才能赢得民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这些明显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治理成本和较高的民众支持度等合作收益为各行政区政府提供了府际合作的拉力,它与各参与主体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发性动因一同促进了府际合作的形成。
第三,上级政府的规划为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提供了推力。进行区域合作,除了各行政区政府的横向合作需求及意愿,还需要来自纵向的更高级别政府的引导、规划、协调甚至强制。高层政府具有的权威比较优势对区域合作的推力作用主要表现为:能够有效避免过度竞争,保证合作的规范性和战略性,并在合作参与者之间无法形成公平博弈的情况下,起到调节作用,有效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8]。《规划》的制定和出台,立足于革命老区发展实际,着眼特色优势和资源禀赋,确立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促进旱作农业发展的战略,从更高层面上建立了老区跨越崛起的新坐标。《规划》还提出了2015到2020年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它对老区的发展导向、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对陕甘宁革命老区进一步加强规划的上、中、下游主体间的衔接和对接,积极开展实质性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助推力。
三、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的途径
第一,要加强和完善来自中央的调控。改革发展过程中对行政作用的强调,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政府层级运作的客观要求。陕甘宁革命老区开展府际合作,需要来自更高层级的政府或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推动。当政治权威持支持态度时,能够促使相关议案迅速提上政府的议程和促进各项政策的迅速执行。中央政府在财税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国土资源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次,在实践发展中,市场型协调模式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壁垒带来的恶性竞争,如“诸侯经济”和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因而,必须借助于高层政府干预型协调模式。为此,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老区宏观层面的支持、引导和协调,扮演好区域合作中重大事务的调控人角色、公益人角色、管制人角色、仲裁人角色、守夜人角色,通过承担这五种角色体现政府职能[9];西部开发司要及时跟踪了解老区规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做好督促者角色,并及时协调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第二,建立跨区域性的协调管理机构,并进行合理的权责机制设计,为府际合作提供组织保障。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构以各参与主体间相互认同和信任为基础,通过广泛的沟通、协商、谈判等方法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对于陕甘宁革命老区,其协调管理机构的领导班子可以由三省的相关负责人组成,负担区域内事务的协商、决策及领导;并根据社会治安、经济合作、公共污染治理等相关公共事务设置必要的部门,其人员可由三省相关部门抽调,分工负责,分类处理;协调管理机构还应根据《规划》要求设立统一的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市场竞争规则等,运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协调力对区域内工作进行协调、监督和引导来推动府际合作。
第三,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通过府际合作可以对区域资源重新整合,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体系,能为参与府际合作的不同主体带来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及各自发展定位不同,在参与府际合作时需要进行各种资源跨行政区整理、分类、合并、重组和开发,意味着有些参与方必须改变原来的收益格局,甚至有时候需要牺牲本地方的利益来保证区域公共利益,就会造成各主体在府际合作中的收益不均等,各种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再者,由于府际合作是平等主体政府间的活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约束,利益受损的主体缺乏更具有权威性的利益协调与调解平台,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极有可能采取地区封锁与市场垄断等办法,最终导致整个合作区域的目标实现缓慢或无法实现。显然,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是一种现实选择,它能够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减少合作摩擦等。对于陕甘宁革命老区,这种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内容要对利益补偿的方式手段、对象、内容、标准、实施,以及利益补偿资金渠道等均需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安排。陕甘宁革命老区虽然具有资源丰富的优势,但生态环境整体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则更难治理和恢复。因此,必须围绕生态补偿的重点、补偿的法律、补偿的形式和筹资渠道、补偿的监督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四,引入多元合作参与者。合作区域可以看做是一个小社会,它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区域内多种主体的积极参与。政府的参与可以保证开展府际合作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企业的参与能够促进合作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非盈利组织的参与则能确保合作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在实践层面,政府系统内部职能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合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直属性;相关企业、非盈利组织及个人是参与各种具体工作的第一人,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府际合作中的具体事项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协调管理机构进行工作纠偏、经验积累与科学决策等。因此,陕甘宁三省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参与到府际合作中,引导和促进其在陕北组团、陇东组团、宁东南组团发展中强化跨区域合作,如跨区域考查学习、举办论坛、签订协议及成立协会等;政府还应该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到对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项目、服务、质量和供给情况等的监督,以保证合作活动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1]赵永茂等.府际关系[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6.
[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4.
[3]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4]张志红.政府间纵向关系初探[A].南开政治学评论[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5]庄晓华.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浅析[J].理论与现代化,2006,(4).
[6]王健等.“复合行政”——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4).
[7]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8158087.htm.pid=baike.box.
[8]麻宝斌,李辉.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动因、策略及其实现[J].行政管理改革(京),2010,(9):63-68.
[9]沈荣华.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若干思考[J].政治学研究,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