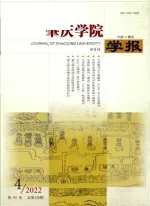从历代龙母信仰之禁看民间宗教的延续性
2013-08-15钟玉发
钟玉发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龙母传说在岭南地区广为人知,自秦代以来就获得民众的信仰,迄今仍受到整个岭南地区、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膜拜。历代统治者试图借助龙母种种“显灵”的“圣迹”和“母仪龙德”的道德权威形象加强对岭南统治,对之予以赐额与封敕,累加封号为“汉封程溪夫人唐封永安夫人又封永宁夫人宋封永济夫人加封普济崇福圣妃明封程溪龙母崇福圣妃又封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娘娘”[1],使其由地方性神明具有了正统色彩。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诸如龙母传说与信仰的起源、文化内涵、地域扩展、祭祀仪式、民俗活动以及历代赐额和敕封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相关论述参见:容肇祖《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载《民俗》第9、10期,1928年;陈摩人《悦城龙母传说的民族学考察——民间文学横向探索的实例》,载《广东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叶春生《龙母信仰与西江民间文化》,载《中国民间文化》1990年第2期;刘守华《关于“龙母”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载《荆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蒋明智《论悦城龙母传说及其信仰》,载《悦城龙母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颋《秦媪豢龙——“悦城龙母”的原始传说及流变》,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王元林、陈玉霜《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4卷第4期,2009年10月。不过,目前尚没有人注意到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主张禁止龙母信仰之事,甚至有人将之归入“淫祀”之内。实际上,这一问题牵涉到国家意志与普通民众宗教信仰自由之间的关系。同时,历史上虽然曾发生过禁止信仰与祭拜龙母的事,但是这一民间信仰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不使我们关注到民间宗教的延续性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与转向问题。
一
古代中国以神道设教,注意对各类神灵的管理和利用,形成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国语·鲁语上》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这里所指称的是所谓“正祀”,即纳入国家祀典之内的神灵祭祀行为。但与此同时,又形成了所谓“淫祀”之说。《礼记·曲礼下》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后代对所谓“淫祀”的界定又有所扩大,举凡扰乱社会治安、违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过度蠹耗民财的祭祀行为都被纳入其中。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将龙母及五龙子信仰看作“淫祀”并主张不予敕封的人是两宋之际的胡寅(1098—1156)。他指出:“臣窃以雨旸顺序,系乎政事。故汉明亲决冤狱,则甘雨应期;东海杀一孝妇,则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祷求福,非圣人之道、先王之法也。宣谕官以敷君德求民瘼为职,乃为龙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况封为夫人,爵称侯伯,施之于人,然后相称。龙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鳞,袭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礼,为后世笑乎?伏望圣断,特赐寝罢,仍降指挥,监司郡县当以爱民为急,若政平讼理,民无愁叹,和气所召,必有丰年。更不得陈乞庙额,崇修淫祀,以为不先勤民独致力于神者之戒。所有龙母五子封爵词命,臣未敢撰行。”[2]显然,在胡寅看来,所谓“政事”得失与“天人感应”密切相关,故人事重于神事;龙母封夫人为越分之举,而且龙子非人类,不能失礼而“袭我冠裳”,所以他将龙母信仰称为“淫祀”。
考胡寅之所以持这一立场,与他的学术思想主张和对鬼神的一贯看法相关。胡寅是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之侄,历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后迁起居郎、中书舍人,因力主抗金而遭到权臣秦桧的打击,于绍兴二十年(1150)以讥讪朝政被流放至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胡寅对宗教信仰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佛教的批驳。胡寅在理论思维上继承胡安国“心与理一”之说,批驳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3]69,并指斥佛家“了心”说“空虚寂灭,莫适于用”[3]96。其二是认为迷信鬼神“正坏大礼”。他指出:“汉唐而后,道术不明,异端并作,学士大夫昧于鬼神之情状,凡戕败伦理,耗斁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托以窃衣食者,则相与推尊祗奉,徼冀福利。”因此,水旱、虫火之灾是地方长官“政教不善”所造成,盲目祈求、祷祝鬼神是“正礼大坏。”[4]其三是深受理学家群体影响而反对封敕龙(或蛇)。胡安国私淑二程,而程颐就曾对敕封龙神表示反对。程颐(1033—1107)曾说:“既曰龙,则不当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佑,宗庙之灵,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劳也。龙何功之有?”[5]程颐对当时遍布各地的龙神庙不以为然,更不主张施之封号庙额,他赞成的是传统的天地宗庙社稷祭祀体系,裁定信仰合法性的是“义理”,而不是神祗的“灵验”。他的这一立场显然为理学诸人所认同,胡寅拒绝为龙母五子撰拟封号与此不无相关。
宋代对龙母的赐额和敕封主要在宋神宗和宋徽宗时期,靖康元年(1126),吴揆记述说:“唐天佑初载,始封母温‘永安郡夫人’,越明年,改封‘永宁夫人’。国朝元丰戊午,赐其额曰‘永济’,封‘永济夫人’。大观戊子,诏以‘孝通’为额,盖取卜地移坟意也。”[6]“元丰”为宋神宗年号,戊午年为公元1078年,“大观”为宋徽宗年号,戊子年为公元1108年。因此,至少在北宋时期,龙母信仰并未受到任何封禁。只是到了南宋初年,“宣谕官明橐”再请封敕龙母五子时,才发生胡寅拒绝“封爵词命”之事。不过,朝廷虽没有再为龙母五子加封,却也没有明文禁止信仰和祭拜龙母,当然更没有将其定性为“淫祀”。因此,胡寅之言论实属个人行为,并未产生广泛效应。相反,在胡寅去世75年后的绍定四年(1231),南宋政府又再次敕封龙母为“显德夫人”[7]。
胡寅之后,南宋时期也曾发生过对蛇神崇拜进行打击之事,不过对象并非龙母和龙子。胡颖(生卒未详),南宋湘潭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进士,是饱读儒家诗书同时又精通律法的“名臣”。他对神异怪诞之事十分痛恨,历官所至,大力破除迷信,“性不喜邪佞,尤恶言神异,所至毁淫祠数千区,以正风俗。”他在担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期间,曾在潮州斩杀所谓“能惊动人”的大蛇[8]。但是,未见他对龙母信仰有任何举动。清代卢崇兴对此评论说:“且尝考之,胡颖经略广东,凡淫祠之奏毁者不可胜数,而龙母之庙至今独存,岂非以其能为民捍大灾、御大患有功于民哉?是以朝廷而存其祠以永奉之也哉?”[9]
不过,胡寅虽然对敕封龙母五子之事表示反对,但是终南宋一朝却并未对龙母信仰加以禁止。这是因为,龙母传说故事本身所体现的“母仪龙德”的形象与理学家所倡导的“人伦者,天理也”的思想主旨并不发生冲突。同时,龙母种种“灵验”的“圣迹”显然也是其香火长盛不衰的依据所在。由此可见,龙母信仰因其在象征意义和道德权威意义上获得了国家的“征用”,个别官绅虽然对于其龙(蛇)崇拜的起源性质表示质疑,但是也并未因此而遭致官方的全面禁毁。
二
岭南地区历史上十分蛮荒,声名文教远不逮中原,但是明清时期却获得迅速发展,国家的控制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能力显著加强。民间对龙母的信仰和朝廷对其敕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称:“明洪武八年封程溪龙母崇福圣妃,九年封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同时还规定:“每岁五月八日,遣官致祭。”[10]但是,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岭南士绅与庶民、汉文化与百越文化以及各族群之间的交融、互动剧烈,魏校、叶春及等具有理学背景的士绅在两广采取毁淫祀、兴社学、行乡约等以家达乡的儒家伦理仪制普及活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甚至波及到龙母信仰。
魏校是苏州府昆山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兵部郎中,于正德十六年(1521)调任广东按察司副使(通称提学副使)。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仅一年时间,却大力推行毁淫祠、兴社学,并因此产生重要影响。他首先下令捣毁广州城及南海、番禺两县淫祠:“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厂者改建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南社学七区,复旧武社学一区。”[11]后来,又将行动扩大到高明、四会、增城、新会、从化各县以及雷州府、廉州府、南雄府等。由于魏校禁淫祠、兴社学成效显著,故被称赞为“贤督学”[12]。受其影响,少量龙母庙被改建为书院。例如,四会县濂溪祠“在城东二里,嘉靖初知县萧樟以龙母庙改建”[13]。还有一些其他神祠被改建为书院或社学,如肇庆府旧净明寺改建为八贤祠(祀唐代张柬之、李绅,宋代刘挚、邹浩、胡寅、胡铨、留正、张世杰),天妃庙改建濂溪祠;德庆州五显庙与忠勇庙改建社学;阳江县真武庙改建社学;高要县文昌宫改建社学等[13]卷14《祀典志》。
此后,署名“郑一麟修、叶春及纂”的万历《肇庆府志》对龙母信仰采取了较为强烈的否定性态度。叶春及是广东归善人,领嘉靖壬子(1552)乡荐举人,三试春官不第。隆庆初,伏阙上书论时政,“洒洒三万余言,都下翕然,谓刘蕡复出。”隆庆四年(1570),任惠安知县,“毁淫祠五百区”[14],“择其宜为学者葺之”,改建社学凡212处[15]。他主持编纂的万历《肇庆府志》虽然肯定:“圣人以幽明之故,匪特有礼乐以治人,鬼神曶奕亦莫不怀而柔之”,但是认为:“蒲媪祠①在各类文字材料中,龙母姓氏普遍被记作温,如唐代刘恂称:“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刘恂:《岭表录异》,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不过,也有的记载说,龙母姓蒲,如光绪《德庆州志》引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及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曰:“龙母温夫人,晋康程水人也。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夫人故称蒲媪。”(杨文骏修,朱一新纂:《德庆州志》卷5《坛庙》,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显然,万历《肇庆府志》采用的是后一种说法。乃千载事,甚诞。缙绅先生不道如此类,余不敢言之也。”[13]卷14《祀典志》因此,万历《肇庆府志》对于龙母传说与信仰没有作渲染式记载,仅仅以100余字的篇幅转述了龙母传说和德庆龙母之墓[13]卷9《地理志三》。
不过,魏校、叶春及等毁淫祠、昌社学的行动并未对龙母信仰产生太大影响,虽然个别龙母庙被改建为社学,但是德庆悦城的龙母祖庙并未遭到禁毁,万历朝之后的《肇庆府志》也没有再对龙母信仰作过否定性记载②实际情况与此正相反,万历十五年(1587),领衔修撰万历《肇庆府志》的肇庆知府郑一麟还主持修建了一处龙母庙(屠英等修,胡森、江藩等纂:《(道光)肇庆府志》卷2《舆地三·山川》,光绪二年重刊本)。。
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生深刻变化。民国建立后,国家政权试图借助于文化网络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改造和重塑国民社会生活。其中,对基层社会的重要改造方式之一就是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1928年,国民党内政部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将神祠分为四大类,即“先哲类”、“宗教类”、“古神类”和“淫祠类”。其中,“古神类”和“淫祠类”在禁止之列[16]。按照这一“标准”,城隍、文昌、天后、龙王、洪圣等信仰与祭祀活动均应革废[17]。龙母虽然未被明言列入“淫祠”之内,但是其类型大致可以与天后、洪圣等比照而定。
广州市于1928年成立了风俗改革委员会(简称“风改会”),并禁止了部分旧风俗习惯和捣毁了部分神祠庙宇。但是,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龙母信仰所受到的影响甚微。1929年6月,作为国民党党报的《广州民国日报》对当年龙母祖庙的祭祀活动进行了报道。但是,除了对祭祀活动的组织以及相关仪式、龙母诞期之获利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叙外,该报道的否定性用语仅仅表现在副标题之中:“在禁除迷信声中龙母诞之获利”[18]。很显然,龙母信仰在风俗改革过程中虽然属于应在禁除之列的迷信活动,但是实际上禁令却并未得到真正执行。
其间的原因,一方面是民国年间时局动荡不定影响了国家政策的有效贯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破除迷信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恶势力与官府勾结私吞庙产的现象。据解放前曾任德庆县悦城税捐分处主任并住庙监收司祝捐的梁伯超等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后,德庆县内的地方恶势力日渐强大,反动官吏的敛财行为日益恣意,因此龙母庙的巨大收入便成为他们交相争夺的目标[19]13。民国八、九年间,德庆县长在庙里开办“司祝捐”,把全庙的收入置于县署掌握之下,名为协调地方争端,实欲纳入私囊。从民国十三、四年严博球做县长以后,德庆县的贪官、劣绅、恶霸们一直展开着投承司祝捐的斗争,其中以卢超民集团与董谷轩集团的明争暗斗尤其激烈[19]13-19。因此,悦城龙母信仰与祭祀活动成为各种势力利益之渊薮,所谓“移风易俗”的风俗改革运动自然不能得到真正贯彻和执行。
新中国建立以来,总的来说,国家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相关宗教政策较为合理、妥当。但是,“文革”期间,国家宗教政策出现巨大波动,并留下沉痛的教训。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首先指向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宗教界与文化知识界、爱国民主人士等都列入了“走资派”的社会基础“牛鬼蛇神”的行列。8月,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按: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宗教信仰也被包括在内。红卫兵到处散发“彻底消灭一切宗教”、“解散一切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取缔宗教职业者”、“彻底捣毁一切教堂寺庙”等内容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一切被视为“四旧”的东西,统统被勒令封闭或破坏。很多寺庙、教堂被强行关闭或改作他用;大量寺庙、教堂内的文物、图书以及宗教用品、神像佛像被捣毁;宗教界人士被集中学习或离开寺庙教堂从事生产劳动,其中不少人遭到了严重批斗。
在此背景下,龙母信仰一度遭到废止。龙母祖庙内雕像,庙内陶湾公仔(即陶塑)、贡品台、香炉等,都被当“四旧”破除掉了。500多平方米的壁画,被用水泥涂掉,龙母神像也被红卫兵扔进悦城河,龙母庙则被改造成了粮仓。直到1983年6月,龙母祖庙才重新开放,祭祀活动再度兴盛[20]。
四
岭南地区龙母信仰因封建王朝的赐额和敕封而具有正统色彩,但是历代也不乏有主张予以封禁的言论和行为。宋明时期,部分官绅因其理学思维方式或达成朝廷礼制改革和基层社会教化的目的主张禁止祭拜龙母,而民国和“文革”时期则因推行所谓破除迷信和移风易俗的需要而取缔信仰龙母。但是,这些言论和禁毁之策对龙母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不禁使我们深思:这一纯粹民间性信仰为何禁而不止?进一步来看,所谓民间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空间是什么?国家和社会又该如何理性地对待它?
这实际上关系到宗教(包括民间信仰)的功能及其现代转向问题。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代,人类因为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导致了对神灵的崇拜,宗教信仰由此产生,因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就其功能来来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实用功能;(2)人群整合功能;(3)完美目标(或可称“精神偶像”)功能[21]。这三者分别标示了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功能层次。一般来说,在一种宗教产生之初,其主要功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超人间力量”所寄托的福利祈求(诸如风调雨顺、家和人旺、惩恶扬善、祛灾去祸等)。当该信仰获得广泛信众的时候,官方和士绅按照各自的需要对之加以“重塑”,赋予其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内涵(如“仁义”、“忠孝”等),使其具有了人群整合的功能(诸如个体人格的调适、社区力量的组织与彰显、祖先认同、地方社会身份伦理的认同等)。而宗教(或民间信仰)的“精神偶像”功能往往是指其在精神层次上的升华,也就是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将自己的愿望、道德观念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等赋予神灵之上,使之成为自己的情感寄托和完美目标。
龙母信仰与祭祀活动的历史表明,在其产生之初主要是因为岭南民众生产生活中敬畏水中生物(蛇或鳄鱼等)而形成的图腾崇拜和水神崇拜,其后历经各代官绅的“重塑”和年复一年的反复祭拜,又赋予其族群英雄人格以及“母仪龙德”的道德权威形象(如慈龙孝子、执仗护航、降雨救灾、积善行德等),并因此而受到历代王朝的敕封(或“征用”),以至虽有少数理学家或受理学影响的官绅对之表示否定,但是并未产生广泛效应。不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龙母信仰与祭祀行为的实用功能和人群整合功能逐步褪化并被剥离,其“精神偶像”功能则得到了延续和张扬。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历经2000多年的龙母信仰不仅没有衰落下去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仍然有部分人出于实用目的、企图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祈求龙母的赐福与佑护,但是其作为精神偶像的功能显然是其香火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指出:“有人说科学在原则上是否定宗教的。然而,宗教仍然存在着;它还是既定的事实体系;简言之,它仍是一种实在。科学如何能够否定这个实在呢?”[22]。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人世中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的增加人和环境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23]
当然,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总体动员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增强,宗教整合人群、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的确已经成为历史(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华侨本着寻根问祖目的参拜龙母之举仍具有人群整合或凝聚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过度紧张的精神压力以及社会道德失范等都使人们对变幻莫测的未来充满焦虑,并因此而将自己的精神追求寄托于“完美目标”的神祗之上,这其实是当今人们信仰和膜拜龙母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像龙母信仰这样的民间宗教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迷信”而企图禁绝之,只能理性地将其纳入合法与合理的轨道中容留之,直到社会进步到不再需要它的时候为止。
[1]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德庆知州蒋如燕立《秦龙母墓碑》,该碑现立于德庆悦城龙母祖庙内龙母墓前.
[2]胡寅.缴宣谕官明橐乞封龙母五子[J]∥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下册,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93:318.
[3]胡寅.崇正辩:卷2[M]∥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4]胡寅.复州重修伏羲庙记[J]∥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下册,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93:435.
[5]程颢,程颐.伊川先生语七[M]∥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册,卷21.北京:中华书局 1981:295.
[6]吴揆.赐额记[J]∥阮元.广东通志·卷210,金石略.道光二年刻本.
[7]人部七[J]∥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9.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213.
[8]脱脱.宋史·胡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 479.
[9]卢崇兴.悦城龙母庙碑记[J]∥黄培芳.悦城龙母庙志:卷1.转引自叶春生,蒋明智.悦城龙母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9.
[10]坛庙[M]∥杨文骏修,朱一新纂.德庆州志:卷5.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1]岭南学政·为毁淫词以兴社学事[M]∥魏校.庄渠遗书: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
[12]事语·贤督学[J]∥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5:286.
[13]郑一麟修,叶春及纂.肇庆府志:卷14.万历十六年刻本.
[14]叶春及传[J]∥陈志喆等修,吴大猷纂.顺德县志:卷22.民国14年刊本.
[15]社学篇[M]∥叶春及.惠安政书:十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354.
[16]民政厅令颁神祠存废标准[N].申报,1928-11-26:15.
[17]建制略[M]∥开平县志:卷9.民国22年铅印本.
[18]龙母诞期之获利[N].广州国民日报,1929-6-19:19.
[19]梁伯超,廖燎.悦城龙母庙[J]∥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风情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20]蒋明智.悦城龙母信仰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J]∥叶春生,蒋明智.悦城龙母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64.
[21]李亦园.宗教与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
[22]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结论[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65.
[2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