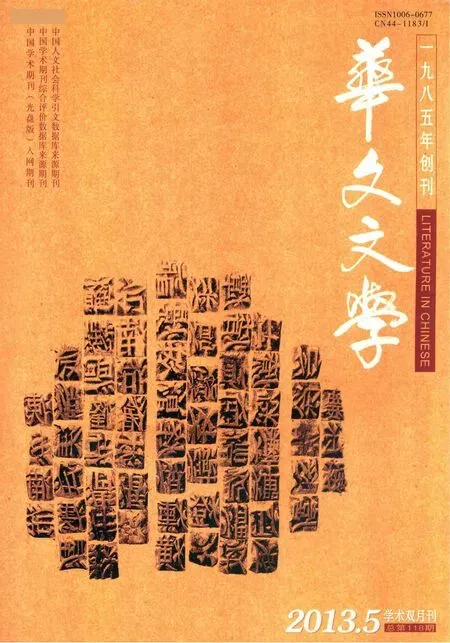再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2013-06-11汤拥华
汤拥华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学者如陈世骧、高友工等一直强调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近年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重申这一提法,极力阐发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联系,并希望以此打造富有中国本土色彩的现代学术话语。这一工作的意义毋庸赘言,但是抒情传统的内涵及应用都还有商榷的空间。笔者曾以《“抒情传统说”应该缓行》(《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一文请益于王德威教授,王教授于答疑解惑之外,惠赠其在台湾出版的《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一书,以之为深入研究之助。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晚辈后学当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专注于问题本身,尽力将所涉理论方案的宗旨与困境辨析分明。
一、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写实与抒情
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一书中,王德威有此提问:“在一片后殖民、反帝国的批判话语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话语资源,引起对话?”正是这一提问引发了笔者的担心,因为过分强烈的中国本位意识有可能形成新的盲视。不过现在想来,这种担心或许多余,王德威本人从来不是文化本位主义者,一直以来他所贡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也不是建构某种中国理论去同西方理论抗衡,而是以他学贯中西的素养发现和研究中国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他总能将光怪陆离的西方理论融会贯通,打造出既能深入文本形式的微妙细节,又能自由关涉社会历史诸般场景的批评方法,从而推进和更新由夏志清、李欧梵等人所代表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或者说传统。
之所以说存在这样的传统,是因为夏志清等人的研究共同建立起一种观念: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仅要重写特定社会/政治史之下的文学史,还可以通过对文学史的研究重写社会/政治史,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等提法之所以在大陆学界风靡一时,正是在于它们能够在重绘文学地图的同时,“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这就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这一研究路线发展到王德威处已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它不再是从某个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另建一套社会/政治史叙述,然后以其重估中国文学,而是致力于营构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的相生互证。此种相生互证的关键词是“想象”而非“影射”,想象是在“再现”之外还有“创生”,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中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一反以往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我因此要说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王德威1990年曾以英文写就一本重要著作《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此书2011年出版了中译本,王德威在此中译本序言中指出,茅盾等三人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抒写的三个面向:茅盾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老舍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和“动人感”因素;沈从文则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即写实叙事是否有安顿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关注,当以他19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为起点)。下列论述尤其值得注意:
写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他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一则又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
王德威谈写实和抒情,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抒情不只是抒发情感,写实也不是依样画葫芦般地模仿现实。现实是被建构的,而建构的规则既不由作家的主观意志决定,也不囿于审美自律性的考量,而是在文学与现实的种种复杂关联中动态地生成。不妨温习一下新历史主义主将葛林伯雷的相关论述:“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通货’是一个比喻,意指使一种交易成为可能的系统调节、象征过程和信贷网络。”葛林伯雷说交易、谈判、网络,王德威则说典律、场域以及编码/解码,他相信抒情(写实当然也是如此)“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这都是要打通文本的内外,使文本历史化,使历史文本化。
王德威最令人佩服的,是他总能从形式的细节中窥知文本内在的冲突,又总能在一个文本中读出其他貌似全无关涉的文本。他所受到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系统训练,使他能从容地将“可读文本”改造为“可写文本”(借用罗兰·巴特的区分),如此方可在文本内外自由出入。不过,我们要注意新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差别,后者基本上持文本一元论,前者则希望以文本和历史的两元展开辩证的探讨。在此问题上,王德威对保罗·德曼的评论值得注意。德曼有一篇文章名为《抒情诗与现代性》(王译为《抒情与现代性》),讨论的正是抒情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王德威归纳德曼的主要观点是:“抒情诗一方面体现亘古常在的内烁精神,一方面又再现当下的现实。抒情文类的不确定性因此让德曼的思考语言和文学徘徊在‘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和‘非再现性’的两端。他的结论是,既然文学已经是种‘寓言’(allegorical)性质的修辞活动,即使‘再现性’的意图和表达也终究不能逃避被误解、延宕的命运。”这一归纳大体准确,但也存在误读。寓言(或译讽喻)这一概念与再现相对立,所强调的是诗歌的自律性和原发性,但德曼的重点不是以寓言否定再现,而恰恰是指出,在探讨抒情诗何以能成为典型的“现代文学”(虽然它也常被当作文学的古典形式看待)时,不能只是将文学的再现逻辑替换为寓言逻辑,语言同时是再现和非再现的。德曼之所以如此辩证,是要强调理解文学的再现与非再现不能丢开“文本互涉”(intertexuality)的前提,没有文本互涉之外的客观描摹,也没有文本互涉之外的原发创生。王德威注意到德曼在《文学历史性与文学现代性》一文中的说法,“任何抒情——求新求真——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总是坠入历史的循环延宕”,不仅如此,“历史知识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被书写的文本,就算是这些文本装扮成战争或革命,也依然须作如是观”。王德威力图扭转德曼所设定的这一文本与历史的不对等状态,他感兴趣的是作为特定编码形式的文学如何源于现实而又重写现实,他相信文学可以凭想象与历史发生真实接触。为了让文本回归历史,他特意介绍了美国学者蓝崔卡的研究,后者不仅揭露德曼与纳粹合作的史实,以说明文本主义者未必能超脱尘世;更以一种现象学色彩浓厚的描述,指明“前于或超越意向或设计”的“抒情时刻”的存在,以重建人与世界的接触,重构历史得以“产生”的契机。不管这一破一立的逻辑是否可靠,我们都能通过它把捉到王德威的理论脉搏。
二、抒情传统如何现代?
王德威在阐述抒情传统说的理论渊源时,特别强调普实克的价值。普实克一方面以中国古典抒情传统来解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另一方面又将此抒情性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定位。举例而言,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不惜牺牲故事情节和叙事的完整,着力创设具有感召力的抒情场景,既是源于清代小说“强烈的主观性、私密性和个人主义色彩”,又与同时代的欧洲文学声气相通,因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生命的悲剧感以及叛逆心理,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倾向”,是世界文学走入现代的重要标志。普实克强调世界文学的大框架自是不差,但是就这样中西合流,未免失之笼统。李欧梵虽对普氏诸多观点都有阐发和推进,在此问题上也要表明态度,断言“自波德莱尔以来充斥于欧洲文艺的先锋气质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艺术条件决定的,因此与五四文学的气质大相径庭,有本质的区别”。王德威的判断与李欧梵基本一致,但他还有进一步的考量。据他观察,西方论者在讲感情与现代的关系时,总是以西方启蒙运动、浪漫主义为基准,“每每在个人、主题、自我等意义上做文章”,而“晚清、‘五四’语境下的‘抒情’含义远过于此”,如前所述,后者不仅是“文类风格”还是“编码形式”,正是此种意义上的抒情“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抒情在西方是否只是文类风格,但是王德威的推演过程的确巧妙,由“文类风格”与“编码形式”的对立衍生出中西对立,然后自然而然地确立起一个“中国问题”——必须有中国这样的抒情传统,“文类风格”与“编码形式”的对立才会如此生动;反过来,考察“文类风格”与“编码形式”的矛盾,便成为今天研究中国抒情传统的重点所在。
需要特别强调,王德威标举抒情传统,并不是要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做文章,他不想让抒情传统成为民族文化的又一标签。请看他对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议论:“就算我们承认陈先生、高先生他们对于中国的抒情传统的认知和珍惜,我们也承认这个传统可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抒情传统放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化语境里,再重新思索,重新陶冶出不同的境界或现象呢?”这番议论表明,王德威心目中的抒情传统不是定位于民族性,而是定位于现代性。他相信20世纪的文学“很难用一个抒情的传统,一个写实的传统,或者任何其他的传统来界定”;而且当他讨论中国的抒情传统时,他承认“西方至大革命以降的浪漫主义美学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主要抒情资源”。就王德威本人的关切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永远是现代何以为现代。陈、高等人虽然是现代学者,但他们只是“将我们似曾相识的传统话语,以精确的当代修辞融会贯通,做出综合性的陈述”;而王德威想做的是把“抒情定义扩大”,使之“成为现代文学处理‘情’与文字、与世界的表征形式”,这样才算是“能够提出一个自己自觉的以及自为的框架”,“以这个框架为我们和西方汉学界理论对话的开端。”所以,抒情传统首先是对立于浪漫主义的,它的宗旨是以中国的方式重构史诗与抒情的统一,也就是说,使史诗与抒情的统一跳出西方浪漫主义的概念框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以此中国问题为指南,王德威在《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中对江文也、台静农、胡兰成三人做了精彩的解读,其统摄性的观念是:“无论作为一种文类特征、一种美学观照、一种生活风格,甚至一种政治立场,抒情都应当被视为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建构另类现代视野的重要资源。”“现代中国文学和艺术最突出之处不是从‘抒情’迈向‘史诗’的进展……而是尽管史诗的呼喊撼天动地,抒情的声音却仍然不绝于耳。”对王德威来说,对抒情传统之现代在场方式的发掘,可以成为他批判形形色色的历史进步论,构建非连续的、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的手段,这是对“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另一种恢复。就江文也而言,核心议题是“他的现代感性如何凸现了殖民性、民族性与国际都会性的混淆特质;他在战争时代对儒家音乐和乐论的钻研如何为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日本大东亚主义间,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对话;以及更重要的,历史的机遇如何激发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视野”,结论是:“由于他的作品和生命种种此消彼长的变奏,江文也谱写出中国现代性最不可测的一个乐章。”对台静农,则必须认识到“书法不仅仅表现他的困境,更进一步,是他的困境证实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暗藏的玄机:书法就是一种有关流离迁徙的艺术,一个图景(topos)与道统(logos)此消彼长的艺术”;也就是说,“书法不唯消遣而已,而能启动表意文字与编码文字,本体的渴望与存在的追寻,历史的回归与历史的离散的对话。国家不幸‘书家’幸,这大约是书法对中国现代性最奇特的见证了。”至于胡兰成,重点是他如何透过生花妙笔的书写,“瓦解了非此即彼的价值与形象,模糊了泾渭分明的理念与情怀。他游走是非内外,敌我不分,如此娴雅机巧,以致形成一种‘艺术’——文字的叛/变术。在背叛的政治学之外,胡兰成发展出背叛的诗学”,“十足是表彰中国的‘现代’精神最不可思议的指标之一”。王德威总是先将文本内在的复杂性揭示出来,最大限度地破坏其表层意旨,然后另建一个潜在的文本,让此文本与被遮蔽的社会/政治史叙述发生微妙的关联。整个分析过程不仅体现出论者还原历史现场的能力和对形式细节的敏感,还充分利用了本雅明、德曼等人所留下的理论资源,将一种“现代生活的精神现象学”演绎得生气淋漓。
然而,得也现代,失也现代。没有现代,抒情传统不过是老调重弹,但这个现代的文章做得太精彩,抒情传统的内涵也会变得模糊起来。缺少了西方文艺传统的比照,有着特定内涵的抒情传统很容易为至大无外的“文化”——作为“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的朴素表述——所代替。音乐家兼诗人江文也,文学家兼书法家台静农,政论家兼散文家胡兰成,仅从这几个人的组合,便可知所谓抒情传统,其实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怎么定义抒情已不太重要,它早已同言志、载道等混在一起,重要的是怎么描述一个现代人的文化境遇。在做这类描述时,王德威常显出著手成春的本领,但也有四面出击、枝蔓游离的弊病,原因正是文化本身面目不明。如果对抒情传统的讨论本来就是要从抒情跃进至文化,那么如何使抒情传统从无所不包的文化,落实到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对象,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这一难题并非不可解决,关键是如何理解抒情传统的历史性。对王德威来说,抒情传统延伸到现代,已化作万千碎片散入文化的空气之中,它不仅自身碎片化,更要破坏新的宏大叙事(以“救亡”、“启蒙”等为名),以彰显历史之非连续性。也就是说,抒情传统之所以能获得真实的历史分量,恰恰因为它解构了现成的历史叙述,从而为人与世界的真实接触提供了契机。我无意否定这一理解,但是我想向普实克的方向退一步,以便强调事情的另一面向,即:作为文艺传统的抒情不是情感无意识的释放,而是一类不断传承的技艺;文艺创作从来都是背负着传统重负的突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传统,而在于什么样的传统,这个传统如何影响到具体的作家创作,作家在具体的写作情境中如何对特定范式进行重审、批判、抵抗、认同等;这意味着要发掘出一个既开放又层层相因、环环相扣的“作为手法的艺术”的整体(此整体会有不同的层次或者说子系统,甚至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强调此一整体的存在不等于构建普实克式的以进化为指南的宏大叙事,也不是说一定要像高友工、吕正惠等人那样,按照年代顺序,梳理出“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谱系,而是说当我们进入文本的细节,深入领会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之时,不仅要看到抒情与写实的冲突如何破坏了文本的整一性,从而与众声喧哗的时代互为表里,还要能够对米兰·昆德拉的告诫有所回应:“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这个“所属艺术的历史”——不妨称为内在历史——无法否认那个外在历史的存在,但它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起源与目标。以此为前提,它才能与外在历史(社会、政治的状况)展开对话。
强调这一点对王德威的工作有何参考价值?我所希望的是对那个“现代生活的精神现象学”有所制约。首先当然是为了限制对细节的过分引申。《现代抒情传统四论》之中,对台静农书法的分析尤见精彩。分析到酣畅处,几乎任何笔法的变化都能成为历史困境的微妙表达,甚至于由一幅横轴的墨迹来回,都能联想到阮籍的穷途而哭、西西弗斯的无功而返以及弗洛伊德所记录的Fort-Da游戏(将球抛出又拉回来)——这就太过了,每每看到这类分析,我就忍不住想贡布里希那样的技术论者会怎么评说。在形式与观念之间,理当有某一艺术的传统作为中介,如此才能确定形式应该如何被符号化。其次,王德威不仅将众声喧哗设定为现代生活的应然状态,还将一种现代甚至是后现代式的符号哲学作为现代文艺的观念基础,现代文艺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它的基本精神与符号形式是分裂的、反讽的、戏仿的、变化不定的。早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一书中,王德威便依据弗莱有关抒情诗的论述,指出“沈从文对小说抒情品格和语言技艺的强调不但引出了散文的诗化效果,也引出了文本的反讽效果”,因为“抒情诗人和反讽作家有共通之处,理由是他们都在修辞姿态上背离读者”,即所谓“修辞”先于“立诚”。他进一步阐发道,“沈从文对文本和世界的反讽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便消解了写实和抒情,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区别,申明了所有语言根本上的构造本质——也就是诗的本质”,惟其如此,沈从文才能够面对乱世仍有“诗意的镇定”。此处从“反讽观点”到“诗意的镇定”的转换显然太快,两者如何在一个中国现代小说家的观念中实现统一,王德威语焉不详。事实上,弗莱言说抒情诗的反讽本性是站在历史和整体的视点上看的,它不需要成为特定作家的观念(甚或潜意识),作家大可以笃信“诚”与“真”,但只要他在写实中激活了抒情(诗)的传统,文学的反讽性就会显示出来。至少对沈从文来说,抒情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抒情的反讽本质并进而对写实乃至写作本身产生怀疑,而是因为他身负抒情文学的传统进入现代(如此才有所谓“镇定”),自然与现代写实的典律形成“复调”。像其他现代作家一样,沈从文自然感受到了不同文学资源的龃龉,体验到写作的危机,但他只需在此危急中有所抉择、有所承担即可,而无须以后现代式的写作观(或者是海德格尔澄明与遮蔽的辩证法)来武装自己。即便沈从文将所操持的文学事业自嘲为“抽象的抒情”,他也并不额外多出一重反讽,因为抒情之为反讽,在传统而不在作者的观念中。离开了传统,既没有反讽,也无所谓严肃。不管文学的想象是否可以经由反讽通达现代,它都必须从传统中获得依托。
三、抒情传统与古今中西问题
强调传统作为整体的在场,其意义当然不只是制衡“过度阐释”。承接上文“反讽的本质”与“诗意的镇定”的问题,我们用另一则材料来推进讨论。王德威有下述观察:
在江文也、宗白华和沈从文之间,我们发现了十分有趣的对应。对他们而言,“现实”无法呈现自身;它是被呈现的。通过抒情的模式描述中国现实,他们不仅质疑了现实主义的优越地位,同时也重划了抒情传统的界限。在融会修辞/声音形式和主题内容的时候,他们试图模塑人类情感无限复杂的向度,以因应任何道德/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抒情话语使他们将语言与声音的创造性与人类知觉的自由性置于优先地位。他们对诗歌与音乐表现的强调,肯定了作家和艺术家“形”诸世界的选择。究其极,他们的文本/世界观消融了散文与诗的区别,以及诗与音乐的区别。他们确认了所有语言在根本上“形声的”——也就是说,音乐的——特征。
但正如以上所提出的,这种抒情性难以在一个要求史诗的时代存活。
既然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讨论出入文学内外,他便有理由将美学家宗白华与江文也、沈从文这些创作家放在一起。但是,要把问题讲清楚,还是有必要将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分开讨论。就后者而言,虽然王德威此处只提宗白华,但事实上,陈世骧,高友工,直至高氏弟子吕正惠、蔡英俊辈,都把抒情传统的逻辑起点定于形式与内容同一的音乐境界,即王尔德、佩特等人所言“一切艺术最终归于音乐”。这一命题一度接替“比例和谐”、“杂多之统一”等,成为美学新的经典命题。但是,“这种抒情性难以在一个要求史诗的时代存活”,所谓史诗的时代,提示着美的破碎,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将这一破碎的现实推向理论的前台。王德威采用的仍是他使文本历史化的典型做法,即将文本解析为显与潜两个层次:显文本是抒情美学的建构,潜文本是混乱现实中重整乾坤的努力。王德威在两者之间设置了这样的冲突:如果抒情美学试图以审美理想重整混乱现实,那么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会被打破,现实本身成为不可抵达之所;而当抒情美学力求以纯学术的方式构建自身时,它又会被带向特定的历史境遇,带向道德/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如前述蓝崔卡对德曼的批判)。在此基础上,王德威就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动机”提出猜想:如此强调中国文学文化的抒情传统,莫不是因为离乡去国之后,“对于中国的审美‘意念’和审美‘决心’与时俱进,最后膨胀扩张到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宣言”?也就是说,海外华人学者出于文化认同的需要,以现代理论修辞制造出一种对传统的想象,却无法将其安放于现代世界的图景中,时空的错位于是成为论者本人身份危机的表征。
然而,以双重文本的逻辑揭示理论家求取身份认同的动机,作为使理论历史化的路径,本身还需经过一番审查。如果说王德威在讨论创作问题时对抒情传统的整体性、连续性重视不足,那么他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则显得对抒情理论所依托的现代学术传统体察不够。首先,之所以出现形形色色的“音乐本体论”,不是因为理论家“试图模塑人类情感无限复杂的向度,以因应任何道德/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而是因为美学经过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和近代艺术理论的冲击,自然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且,由于黑格尔之后美学最核心的命题就是艺术终结,音乐、诗的世界为散文世界所代替,音乐之境也一直处于解体的威胁之中,而非只是针对某一动荡的政治/社会现实。所以我们需要充分激活艺术史、学术史的研究(首先要脱去那层进化论的旧壳),以开放性的谱系与整体,为特定的文学创造和理论创见定位。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任何一种现代文艺理论,都会遭遇那个古今中西的矛盾。究竟何谓普世、地方,何谓今、古,何谓进步、保守,本身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切都依靠对立确认自身,这种不稳定状态必然会影响到理论的内在逻辑。古今中西的矛盾是种种观念传统延伸至现代的必然遭际,而它自身也成为新传统得以生成的框架。从王国维到宗白华,从陈世骧到高友工,甚至到王德威,他们的学术路径虽然不同,却都在此框架之中。不能将他们的理论简单地还原到某个身份认同的“动机”,是因为现代理论的传统本身就包含了身份认同的问题,而不是身份认同的需要决定了理论的面貌。


①㉙㉚㉛㉜㉝㉞㉟㊵㊸ 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1年版,第 132页;第147-148页;第89页;第190页;第200页;第214页;第254页;第194页;第138页。

③王丽丽、程光炜:《从夏氏兄弟到李欧梵、王德威——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④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40页。
⑤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新历史主义观念在理论和创作上的表现有一个头绪清晰而又富于开放性的探讨,可参看。
⑥王德威在一次访谈中特别申明:“我只是希望把‘抒情’这个词当作我们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另外一个界面,透过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作家,他的抒情面向与史诗面向的来回交错。”见王德威、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访谈录之一》,载《书城》2008年第6期。在《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一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序论的开篇,王德威则明确宣称:“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一向是我所专注的治学方向。”总体而言,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说完全符合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对文学理论的期待,即现代文学理论不仅仅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现代主义,更有必要成为“关于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史书写的一门理论”。见[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王德威也乐于承认新历史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参阅李凤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王德威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吕周聚:《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王德威教授访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⑦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⑧㊷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第233页。
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⑫Allegory的一重内涵接近fable,强调的是形象的原发性。维科《新科学》中有云:“神话学家似乎更确切说是诗人,他们根据寓言(英译为fable)发明了如此之多不同的事物,而这些诗人认为他们的寓言是对他们自己时代的事物所做的真实叙述,因此是真正的神话学家。”参见维科:《维科著作选》,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2页。
⑬Paul de Man,“Lyric and Modernity”,Blindness and Insi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66-186。
⑭ 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09。
⑯《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第26页。参见Paul de Man,“Lyric and Modernity”,Blindness and Insi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65。
⑱⑲㉑[捷]普实克著,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页;第3页;第4页。
⑳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情感的历程》等文章中,李欧梵依循普实克的思路,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情感主义潮流的源流及其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精彩的梳理与分析。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㊱王德威在所译《知识的考掘》一书的导读中指出,应当“放弃传统中以时序纵贯为基准的方法,转而关注以空间横断面为基准的探讨”。见[法]米歇尔·福柯著,王德威译:《知识的考掘》,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王德威导读1,第36页。
㊲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㊳[捷]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㊴汤拥华、张亦辉:《通向“文学整体”的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㊶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230页。参见[加]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㊹参见吕正惠《形式与意义》、蔡英俊《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两篇文章,皆收入蔡英俊主编《中国文学的情感世界》,黄山书社2012年版。


[附]王德威教授的回信
拥华:
大作条理分明,议论恳切,所指出的问题也的确使得我思考。个人觉得比前一篇文章更切中我的关怀和不足之处。我觉得可以投送发表,借以引起更多讨论。
文章中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有如下数点:
1.你指出我的方法学新历史主义的倾向;的确,这是我曾致力的方向。
唯近年越发感觉到新历史主义在形式表现/历史经验转圜(或协商?)的局限,觉得西方学者处理得太干净,或解构得太利落(甚至牵涉到中西本体论的差异),因此希望从中国古典史学知人论世和以志逆意的观念靠拢。论台静农的文章应该已经和以往行文风格有所不同。但如文中指出,这不是中学西学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思考过程中不断自我对话的要求。过犹不及之处当然有继续琢磨的空间(至少对自己的抒情冲动应该有所认知)。2.文中对传统的内蕴活力和辩证力量的提醒,深获我心。
事实上,英文书并未采用台大或三联版的导论,而是全部改写,分为两章。一章以稍长篇幅讨论陈世骧、沈从文、普实克和传统诗学的曲折对话关系;另一章谈鲁迅/梁启超到195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抒情文论值得注意的现象。写这一章让我更了解抒情传统的复杂脉络,左右翼文人学者都有因袭发挥。同时也进一步回应了你的观察:抒情传统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不是简单整理国故而已;如果这个传统值得重视,这是因为它所糅合、彰显的中西/古今资源,以及由此出现的新的话题。3.至于“抒情”一词是否用得太广泛,这是多年以前学生已经提出的问题。
这方面我和陈世骧、尤其高友工先生的论点有相似处也有相异处;我同意高先生对抒情美典象意(symboliz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的看法,也认为抒情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甚至意识形态可以显现在不同文类里。但我更关心以抒情为名的表述行为或形式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从国家到主体都包括在内。我的用意是在革命、启蒙论述之外,找出其他考察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批评向度。从这个观点来看,“抒情”的定义或实践不比我们视为当然的“革命”或“启蒙”来得更为复杂或更为简单。
4.你指出我以往的论述擅用解构方法,所言甚是。
我有另解:或者可以说我们现代评论者面对任何名义的传统时,所不自觉透露的焦虑。我同意如果真要正视抒情“传统”的可长可久,就必须放大历史眼光,浸润在传统中,而不必刻意解放“被压抑的现代性”。我希望英文书能够充分体现这样的风格。5.奉上英文书目录,聊供参考。
除了台大版三个案例外,我处理了林风眠、何其芳、冯至、梅兰芳、费穆,还有沈从文。如你建议,其实不论如何讨论这些案例,有一种传统脉络已经贯穿其中。我应该更大方地说明这个传统。再次感谢你阅读和批评,如有任何想法,欢迎随时提出。
Best
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