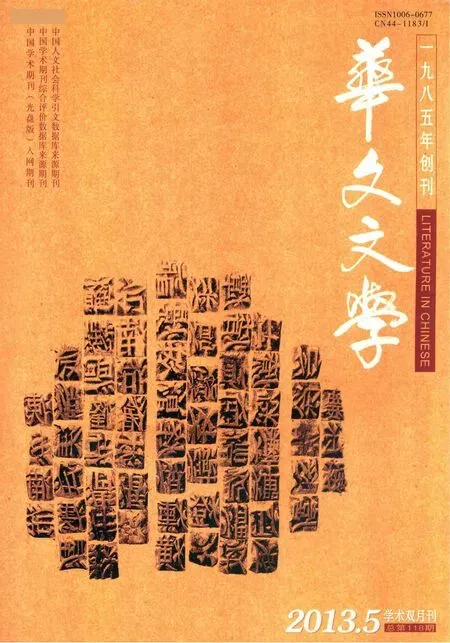中亚华裔东干诗歌的演变:十四儿与十娃子比较论
2013-11-15常文昌
常文昌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东干书面文学从亚斯尔·十娃子的《亮明星》算起,已有近80年的历史,其诗人大体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诗人有十娃子、马凯、马耶夫、杨善新、从娃子、马存诺夫等,其中大多为初期启蒙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他的创作延续了50多年,对东干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代东干诗人有拉阿訇诺夫、伊玛佐夫、曼苏洛娃等,他们的创作延续了十娃子的诗歌,没有大的变化。第三代诗人有十四儿、海彻尔等,其创作也有对十娃子的某些继承,但由于时代与艺术渊源的不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诗人个性的差异,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标志着东干诗歌的一大演变。以下着重以十娃子和十四儿为例,探讨其创作的异同。
一
在比较十四儿与前辈诗人十娃子的不同时,首先要看到其传承之处。十四儿称十娃子为“伟大诗人”,在《世上我也剩不多……》中引了一句“伟大诗人”的诗“光是回族没运气”,这句诗正是十娃子的诗,可见其对本民族前辈诗人的高度评价。两位诗人的相似之处,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强烈的东干民族寻根意识。十娃子的民族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可以《北河沿上》与《我爷的城》为例。《北河沿上》说:“时候到了回中国老家,大舅高兴地迎接我们,团圆之日,我们会欢快地像蝴蝶一样,在黄河边上散步;时候到了还回麦加呢,阿拉伯老爸把我们当儿子一样迎接。”道出了东干人认同的两个根:中国根与阿拉伯根。《我爷的城》写道:“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眨毛上也落哩/一层毒霜。/心总不定,肯念过:/——我的银川。/哈巴还等我的呢,/老娘一般。/百年之前离别哩,/我连银川。/我也没说:——你好在,/没说再见……/把我哈巴忘掉哩,/那个大城。/单怕那塔儿也没剩/认得的人。”将中国情结、民族寻根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儿也始终没有忘记东干民族的根,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世上我也剩不多……》说:“孽障民族,/他为造反/渡了多少宽海,/顶天的山。”在《纳伦·夜晚·滩道》中也回忆:“亲祖辈/卢罕儿把我看见,/待想说一个/啥呢,/不敢言喘。/整一百多年早前/为找安稳/打天山/他翻过来,/到这儿进坟。饿的,冻的/完掉了……/望想没成!”卢罕儿,即灵魂。造反起义,翻越天山,成为东干人永远的民族记忆。两首诗都表明东干族的根在中国。在十四儿诗中,《回族马队》同十娃子诗歌的格调完全一致,对马三成领导的威震中亚的东干骑兵团的歌颂,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白彦虎曾定居的著名东干乡庄叫营盘,十四儿在他的诗中将历史故国称为“老营中国”,也可以看出他的中国情结。十四儿还专门写过一首《回族》关注世界各国回族的命运,诗中说:“回族,回回,/老回回……快两千年/满世上你转的呢,/不知道闲。/那塔儿/没你的脚踪?中国,苏联,/美国,法国,蒙古国,/英国,台湾……”“你的家在哪塔呢?/哪是鸿运?”值得称道的是十四儿还具有民族自省与民族自我批判意识,《单另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将东干族与别的民族进行比较,批判了某些东干人不看长远,只看脚面,重利轻义,不顾全民族大局的短视行为。同哈萨克大诗人阿拜的民族自我批判意识有相通之处。
其次是乡情。乡庄对东干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东干乡庄不仅是东干人赖以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场所,也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生活场所,同时还是东干人宗教及精神家园的处所,因此东干人的乡情具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十娃子诗歌中的乡情极为浓烈,最典型的代表作是《营盘》,其中写道:“在柏林的场子呢我也浪过,/可是它没营盘的草场软作。/我在罗马的花园呢听过响器,/可是赖瓜儿的声气没离耳缝。//说是巴黎香油氽,我也洒过,/可是四季我闻的自己味道,/大世界上的地方多:上海、伦敦……/可是哪塔儿都没有营盘乡庄。”在诗人的感情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东干乡庄营盘好,连罗马最美的音乐也比不上营盘的青蛙叫声亲切动听,可见诗人对乡庄的感情之深。十四儿的诗歌也继承了十娃子抒写乡情的传统,他的乡情诗中的地名多半都是真实的,如稍葫芦、纳伦等。《稍葫芦雨下的呢》是温暖的田园诗,雨中的乡庄更有情趣,小孩子的嬉戏把我们带入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园。这同十四儿的某些悲剧诗的格调截然不同,倒是更接近十娃子播种快乐的抒情诗。《我的亲爱的稍葫芦》把乡庄比作母亲,等待她归来的儿女,诗的开头写道:“我的亲爱稍葫芦,/贵重老家,/我的心呢的杜瓦尔,/一寸王法……”东干人对真主祈福叫接杜瓦尔,同时把避邪的护身符也叫杜瓦尔,上面写有《古兰经》的经文。将乡庄比作杜瓦尔,称为至高的王法,可见乡庄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一回》差不多化用了十娃子《我四季唱呢》和《把亮明星揪下来》等作品的诗意诗境,说诗人死后,不要高抬也不要深埋,把他送到乡庄的滩道——这个顿亚上的天堂里,黑土当褥子,云天当被窝,明月做灯,百灵唱歌,静静地睡去。对东干乡庄的这种感情同十娃子是一脉相承的。
在诗歌意象、诗歌形式方面,也可以看出十四儿对十娃子的某些继承。十四儿诗中不乏东干人物、东干地名、东干民俗。这里以白杨意象为例,看看两位诗人的契合点。如果说白桦是以叶赛宁为代表的俄罗斯诗歌的标志性意象之一,那么白杨,则是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的一个标志性意象。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白杨是不吉祥的,而东干人却恰恰相反,对白杨充满特殊的情感。十娃子多次歌颂白杨,十四儿《在俄罗斯》诗中也写道,在遥远的俄罗斯怀念家乡,首先想到的是白杨。十娃子创造了七·四体诗的形式,即单行七字句,双行四字句。这种形式为许多东干诗人所采用。十四儿诗的形式比较多样,但部分作品也采用了十娃子的七·四体形式。
在文化身份上,两位诗人也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海外华裔作家都有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要寻根认祖,认同本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认同所在国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东干作家也不例外。十娃子一方面写下了一系列公民抒情诗,作为苏联的一个公民赞颂自己的祖国,如《我的列斯普布里卡(祖国)》,称哈萨克斯坦为“亲娘”;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深深的中国情结与阿拉伯情结,在《北河沿上》等作品中又表示,遵从爷爷、太爷的话,时候到了要回中国,回阿拉伯。而在《我去不下》中又明确表示,自己的根已深深扎在了中亚,无法回到中国。第二代东干作家曼苏洛娃曾写过东干文诗歌《喜爱祖国》,表达了对中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她的另一首俄文诗《我有两个祖国》说:“如今我有两个祖国母亲,/可爱的中国和亲爱的吉尔吉斯斯坦。”到十四儿笔下,身份的建构上,同前代诗人既有联系,又不尽相同。他多次追忆民族的根,时而又流露出不能完全融入所在国,《太难活这个世上……》写道:“太难活这个世上/没有祖国,/没人给你给帮助,/你不是谁!”这种身份的书写,同他的现代主义艺术观不无联系。
在指出两代诗人相近之处的同时,本文着重论述十四儿与十娃子创作的不同之处,以勾勒出东干诗歌的演变轨迹。
二
十四儿与十娃子诗歌创作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十娃子处于苏联社会经济与人的精神的上升时期,因此其诗歌洋溢着乐观的进取精神;十四儿的创作则接近苏联解体时期,其部分作品流露出他的悲剧人生观。十娃子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主要是现实主义,也兼具浪漫主义的风格,而十四儿则明显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先看两位诗人对运气的截然相反的看法。十娃子写过几首关于运气的诗,最著名的一首是《运气曲儿》,抒写了几代东干人的命运:“说是世上运气多,就像大河,/在满各处儿淌的呢,谁都能喝。/可是我总没见过,它避躲我,/单怕它不喜爱我,——/我爷肯说。//为找运气我渡了多少大河,/我翻过了多少山,比天都高。/可是运气没找着,命赶纸薄,/你说我的运气呢?——/我大肯说。//我把运气找着哩,就像大河,/就像伏尔加淌的呢,我由心喝。/我在里头浮的呢,就像天鹅。/世上我的运气大——/我也肯说。”十娃子始终认为,在清朝和西迁后的沙皇时代,东干人都没有找到运气,只有苏联时期才找到了好运。相反,十四儿则作翻案文章,多次坚持自己没有找到运气。《我的亲爱稍葫芦……》说:“光是运气没有的,/许是太贵,/每一回他乖张的/光给脊背。”《太难活这个世上……》说:“白白世上活的呢,/缺短运气。”《就是我太没运气……》也写道:“就是!我太没运气/花光阴上。/每一天都找的呢,/它没影像。”反复强调抒情主人公与运气无缘。在十四儿笔下,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找到运气,他还用了复数,《咱们短运气的呢……》说:“咱们短运气的呢/乱光阴上。”甚至认为自己的民族乃至人类都没有找到运气,请看他的以《运气》为题的诗:“找运气呢……给邻居,/给回族人,/我爱思想,在世上,/给世界人。/光是我还没找着/把运气根,/就不说给世界人/给我个人。”对运气的看法,十娃子是肯定的、乐观的,十四儿则是否定的、悲观的。
艾特玛托夫给十娃子的俄文版诗作序,不仅赞扬他对崇高人性的抒写,还肯定他播种快乐的主题。十娃子这类诗中有代表性的如《我种的高兴》:“我种的呢把高兴,/连花儿一样。/把高兴籽儿撒的呢,/往地面上。/叫一切人高兴呢,/都叫欢乐。”
播种快乐,是十娃子诗歌的主调。另一首《我背的春天》说:“我背的呢把春天,/就像天山,/往大滩呢背的呢,/又往花园。/多少鲜花儿我背的,/清泉、月亮…/背的蝴蝶儿、五更翅儿(夜莺),/太阳的光…/往世界上我倒呢/把一切俊。”这是何等美妙乐观的想象。十娃子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老年后写的哲理抒情诗《有心呢》说:“眼睛麻哩,都说的,/有多孽障。/也看不见深蓝天,/金红太阳。/可是没的,有心呢,/也是眼睛。/也看见呢,看得显,/心旦干净。//耳朵背哩,还说的,/有多孽障。/也听不见姑娘笑,/炸雷的响。/可是没的,有心呢,/揣的热心,/也是耳朵,听见呢,/把喜爱音。//谁有真心,也不怕/眼睛的麻。/也不害怕耳朵背,/听不见话。”这首诗为诗人80岁所作,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对一般人来说苦不堪言,可是诗人认为,只要心不老,加之老年人见多识广,就能看清年轻人看不清的事物,分辨年轻人听不明白的话语。这是十娃子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不同于十娃子,十四儿最好的作品所爆发的是其悲剧的美学力量,他将人生的悲剧呈现给读者,令人惊心动魄。如东干文《咱们待概一拿径……》,“待概”,有释为“许是”不妥。有三个证据,甘肃庆阳方言“待概”与“待来”同义,即“已经如此”。而东干语言学家有两个版本的解释,杨善新《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解释“待概”为“生来”。从娃子《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没有“待概”,只有“待来”,释为“原来”。十四儿诗题中的“一拿径”,为“一直”。合起来的意思是,咱们生来就一直像赛马场上的跑马。为了便于读者对诗意的了解,这里采用我们自己的俄文译文,即《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在世上/就像马参加赛跑,/哨声过后,头顶上是/可怕的鞭子抽打与恐吓。”所有的马都拼命地快跑,力图追上并超过前面的。而“驱赶的鞭子/那鞭子将我们/抽打,抽打,又抽打”。结局是:“我们不能从这样的鞭子下逃离,/我们顺从地奔跑……/汗水流成小溪,/热气从鼻孔上升……/刹那间——弦要绷断,/由于劳累而阵亡。/唉,后面的马还在飞驰,/赶上、超过、践踏我们,/而另外一些马又追上它们——/于是隐没在尘土中……”人生就在这样的角逐中,直到倒下为止。这样的悲剧描写怵目惊心。十四儿《啥都没有久长的……》说:“啥都没有久长的,/都有个完,/谁都没有永世的,/这个阿兰。”也是以悲剧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
三
十四儿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还表现在个体生命意识上,不同于十娃子的重集体意识。
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十娃子作为苏联时期有“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称号的作家,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将个体融入集体。“俄苏诗歌传统中,从涅克拉索夫到马雅可夫斯基都创作了颇有影响的公民诗,亚斯尔·十娃子受其影响,也创作了一系列公民诗。”诗人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不仅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且写下了许多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祖国前途的公民抒情诗。他也关注个体生命,从人性的角度,从母亲的视角抨击过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更多的是关注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人类的命运。在十娃子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十四儿诗歌中,缺少公民抒情诗,却突显了他的个体生命意识。这种个体生命意识与时间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他有自觉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感知,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久长的,包括个体生命,都是稍纵即逝的。在《时候儿带人》(时间与人)中写道:“时候儿,时候儿……不住过的呢/打面前呢。往远呢飞的呢。”“人……尽在一坨儿站的呢:/到活上,打活上,再没路!//时候儿飞过就进永总哩,/不剩——也不变卦,也不灭。//人没处去——就在地面上/渐渐老掉哩……叫时候儿收掉哩!//时候儿没无常——有永总呢,/人没永总——有无常呢……”这首诗对时间与生命的感知是独特的,时间在飞驰,生命在死亡;时间是永恒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从俄文将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两行译为:“人的通常的不幸命运——/上班,下班,没有别的路。”人的不幸在于,除了上班下班,别无选择,这就是十四儿对生命的现代主义的诠释。每天撕扯日历,对一般人来讲,已经司空见惯,十四儿的《月份牌》却感觉到扯的是自己的“寿数”(生命)。他的时间意识贯穿于许多诗篇。由于汉字失传,东干人失去了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可能,但是有时却能将古人的意思用最平朴的东干口语表达出来。请看十四儿《不是!咱们没活的……》中的几行诗:“今儿的往明儿推的呢,/明儿的往后儿,/后儿个也有明儿个呢,/‘明儿个’没数儿……/就这么个临尾儿明儿个,/顶头明白,/一回落到面前呢,/叫心后悔。”其诗意与中国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完全一样。
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十四儿这样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的疏离,《汽车走的呢》(俄文版为《电车行驶……》)写道:“下车的人走了,对我来说无异于死亡;我下车了,对别人,也无异于死亡。”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做了这样的比喻,如《在世上》把人比作犍牛,捆绑在光阴(生活)上,把光阴一步一步地往前拉,其命运与臧克家的老马相似。《在睡梦地呢》通过梦境来暗喻现实。梦里燥热难熬,像在蒸笼里,又像扣在锅底下。一个声音从蓝天上传来:“跟上我走!”“我”太想逃出去,心出去了,可是身子出不去。这就是生命的困境。诗人急于摆脱种种束缚,向往广阔自由的天地,《黑马从滩道跑掉哩……》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结尾一节东干文是:“黑马从滩道跑掉哩,/把缰绳忽然顿断。/是谁把它没挡得住,/晚上照住大宽展。”俄文版可以这样翻译:“黑马向田野疾驰而去,/扯断自己的笼头后。/谁正在抓它——/它向自由跑去。”在十四儿看来,人的种种束缚都是生命的枷锁,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黑马向往广阔的田野,向往徐行的晚风和香甜的草木,它挣断笼头和缰绳,奔向自由,融化在霞光里。诗的境界很美,题旨显豁,是诗人现代主义倾向的代表作之一,同第一代、第二代东干诗人的创作风格与思想倾向截然不同,标示东干诗歌的另一走向。
四
十娃子在东干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被公认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十四儿没有这样的地位,但从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十四儿的创作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从题材及内容上看,十娃子的创作相当丰富,他出版过40个集子,其中东干文19个,吉尔吉斯文11个,俄文10个。对东干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有较为全面的反映,具有史诗般的性质。相对而言,十四儿创作的数量没有这么丰富,同时题材相对要狭窄一些,他对现代青年迷惘焦灼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揭示,但对东干民族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反映相对薄弱。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两位诗人的宗教观念也有明显的差异。十娃子的时代,提倡无神论,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与压抑,因此诗人的创作中,对宗教信仰有所回避,几乎没有提及真主胡达。而十四儿作品中,胡达具有主宰一切的地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诗人多次祈祷呼唤胡达,《胡达呀,我祈祷你……》,不仅标题祈祷胡达,全诗三节,每一节都由“胡达呀,我祈祷你”领起。《白生生的雪消罢……》说:“世上啥都不久长,/不长远活,/胡达—讨尔俩的下降,/谁能躲脱……”类似祈祷胡达的还有《啥都没有久长的……》、《人的心到来没底儿……》、《话》、《尽转的呢……》、《就千万年转的呢……》等。这样的诗在十娃子作品中是找不到的。
十四儿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的某些作品与传统的写法截然不同。如《我爱呢》,如此描写忠贞不移的爱情:“把两个活腿剁掉,/有面首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总走呢。//把两个手也揪掉,/有眼睛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看清呢。//把两个眼也挖掉,/有耳朵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听着呢。//把两个耳也割掉,/有思想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总想呢。//把思想也都收掉,/有热心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答应呢。//把热心也掏出来,/泡到碗呢,/光……里头的红爱情,/永世喊呢。”这是一首奇诗,以血淋淋的画面衬托至死不变的爱情,类似于台湾女作家夏宇的爱情诗《甜蜜的复仇》,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典雅情诗。十四儿的部分作品还具有很强的感觉性,有意象派的韵味。
最后,再看看十四儿与十娃子诗歌语言的差异。由于东干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的完全一致,不存在言文分离现象,无论十娃子、十四儿还是别的诗人,都毫无例外地运用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活的东干口语,没有文绉绉的汉语书面语言。但是读两位诗人的作品,明显感到语言上的差别。十娃子的语言,像行云流水,虽然直白,却相当流畅。十四儿的某些作品,中国人读来,感到语言有点磕磕绊绊,个别句子也不很顺当。新近,我们发现十娃子有一首《桂香》,语言干净利落,其文本同黎锦晖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歌词《可怜的秋香》基本相同。肯定地说,是十娃子受黎锦晖影响,而不是黎锦晖受十娃子影响。因为十娃子的创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晚于黎锦晖《可怜的秋香》十年。但是通过什么渠道,十娃子能看到这首歌词,仍然是一个谜。十娃子不懂汉字,也没有资料证实《可怜的秋香》汉文文本传播到中亚。是否有人从内地来到中亚,带来了这首歌,还有待证明。十娃子、阿尔不都及许多东干作家西北方言运用自如,试看十娃子的《营盘》:“在营盘生养哩,营盘呢长,/在营盘呢我跑哩,连风一样。/营盘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呢,我咋不想?”第一代东干作家运用东干语何其熟练。再看十四儿的个别诗句,读起来就有点费劲了,如《咱们就像影影子……》(据林涛译文):“咱们/就像影影子在世上活,/两个心慌影影子,/太短红火。/成一天价奇怪的/都看不见/全凭/一个把一个,/全扰面面。/因为二位有两寸体己光阴:/你背的你的利兹哈(阿拉伯语借词,上天造下的光明),/我讨自命。/运气……/(咱们织下的)一回憋开!/这候儿有你的一块,我的一块……/你有你的望想呢,/我有自甜,你有/你的颇烦呢,我看自难。/就是镜子跌下去,/成两半个,/咋合也罢中间呢/影影两个。”虽然全诗的意思不难明白,但其中诸如“全扰面面”、“我讨自命”、“我有自甜”、“我看自难”等,中国人即使西北人读起来也颇觉别扭。为什么十四儿与十娃子的语言有如此之差别?猜测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十娃子对自己的母语——西北方言十分熟悉,到了十四儿这一代,无论对中国文化或对母语的掌握,都不及他们的前辈。世界各地的华裔,由于各种语言文化的影响,一代人与上几代人所运用的母语,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新加坡记者林义明引述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人在25年前讲的是掺杂方言和马来语的一种特殊南洋普通话。于是政府从台湾请来能讲标准华语的教师,重新训练当地播音员和教师,并从台湾请来电台和电视人员以定下语言标准。因此,现在年轻的一代才能够讲一口较为标准的华语。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主张东干语向汉语过度,以利于东干人与中国人的交流。这种意见尚未得到东干语言学家的认同。如果有一天,果真东干文变成了汉字,东干语成了普通话,那么东干文与东干语的独特性也就消失了。
①本文所引作品出处:1.[吉]亚斯尔·十娃子:《五更翅儿》(东干文诗选),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伊里木出版社2006年版;2.[吉]伊斯哈尔·十四儿:《稍葫芦白雨下的呢》(东干文原文及林涛汉语译文),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3.МакееваФ.Х:Становлениеи развитиедунган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Фрунзе:Кыргызстан,1984年版。[吉]Ф.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 1984年版;4.Музаппархан Курбанов,Тазагуль Закирова,Исхар Шисыр:Шедрая душа.Фрунзе:Изд.Адабият,1990年版。[吉]木扎巴尔汗·库尔巴诺夫、塔扎古丽·扎吉洛娃、伊斯哈尔·十四儿:《丰富的内心世界》,伏龙芝:阿达比亚特出版社1990年版。
②常文昌、高亚斌:《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③常文昌、常立霓:《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④王晋光:《粤闽客吴俚谚方言论》,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