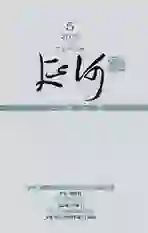故乡两座山
2013-04-29许文舟
许文舟
一
与滇西所有的山一样,故乡的山生得一点也不峻峭,也不挺拔。故乡有许多山,最小的一座只有几十平米,立在阿定河与鲁史河之间,象一个岛屿,但故乡人也称它为“峡山”,名字大山却小。山中生活着两位麻疯病患者,清冷的石头上,连一棵树也懒得生长,倒是炊烟不时从山半腰升起,也只有看到炊烟,人们才想起那茅屋下孤苦伶仃的两位老人。最高的山是格自山,海拔超过3500米,可是从来就没见山头落过雪,倒是雾常纠结在山头,冬天尤厚,夏天简直就象飘过的轻纱。
与我生命有关的山有两座,一座是老家所在地阿定山,属于整个滇西横断山系之中一座,不出名。查遍历史,也没有哪位高人把它写进文字,用文字将它的曾经记录下来。阿定山坡并不陡,也没有三尺平的地方,远远看去,除了七歪八斜挂在山坡的房子,就是房子后面密集的坟墓。祖上到此定居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六代,生命的过程大同小异,活着,借土养命;死掉,就变成一堆生前省吃检用攒钱买下的石头。我记事以来,山后的树长得都很弱小,连鸟都觉得筑巢不安全。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小春种豌豆蚕豆与小麦,间或有人家种些大麦,种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它作酒粮。山下的阿定河流得很急,岸边有些水田,这些年每年都发洪水,水田被阿定河吞噬得差不多了,留一些砂坝,芦苇玩命地长出来,之后翠鸟陆陆续续前来安居。另一座就是与之对应的是格自山。属于西晒太阳的山系,同样长得没有半点可圈可点的地方。格自山比阿定山陡得多,如果不是长着密实的树,上山都有点眩,但当地人仍然在山坡上耕种。山半腰有21户人家,据说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姓氏也有21个,姓富的,始终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姓官的从没有走出过小小的村落。完全没有血缘的邻居,每天按农业的四季完成不同的话计,让豆上架,担心玉米被风蹂躏,会为一只母羊难产伤心不已。
格自山陡,有人用屙屎搬桩来形容是有些俗,但一点也不为过,煮饭的女人不小心拿掉的南瓜,一直会滚到阿定河里,一眨眼功夫便已粉身碎骨。孩子们无聊的时候便会找些石头,从山半腰滚下,石头越滚越快,一直砸到阿定河里,溅起若干水花。滚石头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无聊的举动会带来多少危险。
格自山长满了树,云南松居多,其它杂木上百个品种,树一密实,进入林中,也就不觉得格自山的险与陡了。一到冬天,野风驱赶着野火在山头狂飙,在阿定山这边的家里,会听到烈焰吞噬森林的咆哮。当地老百姓喜欢野火,一场野火之后,春风吹又生的青草能赶上时令,让牛有饱餐的机会。野火让枯枝败叶一扫而光,最重要的是烧死了害虫,尽管有一些小树可能遇难,大树生命力会更加旺盛。阿定山从来就没有一场野火眷顾过,当然因为人稠地密的原因,那家收后的土地上升起浓烟,也会有关注的人前去看个究竟,是谁燃放的火,烧些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人们小心冀冀,与阿定山风大有关,天干物燥的冬季,随便那点失火,都会秧及七个自然村448家农户的安危。
二
阿定山山头的寺院解放后还在,“破四旧”时完全被毁,至今尚有这座寺印制的经卷流落民间。偶然听到某某老人从经卷中悟出什么,说某年某月阿定山要出个什么人物都记得详实,越说越觉得这书有点诡异,这寺有些神秘。于是,逢年过节,顺甸山头原寺院旧址,会有烧香焚纸的香客,发财的想发更大的财,贫穷的想翻身致富。村子里一个叫许正勒的大叔手头就有一本《还源金丹》,那些笔力苍劲的字体完全是手书,比现代电脑里出笼的行楷差不了多少。洇濡着墨迹的道家学说,完全浸淫在阿定人观念里,性格的方方面面,顺其自然,常含在阿定人嘴里,就是连没完成课外作业的孩子,面对第二天可能被老师惩罚,也会说顺其自然吧。山腰的千年老桂花,文革期间被红卫兵们刀砍斧劈,说是影响了地里的农业生产,只有老人们的回忆,不时提到那棵桂花的芳菲。
五个自然村落就在阿定山上,最顶端的陈家村,海拔2400米,算是阿定山的寒带,从家里丢一把苦荞籽出去,只管等着收。但种玉米就差劲了,吐樱后的玉米挂包迟,就是挂出包,秋风一吹天气就寒凉下来,玉米籽粒无法灌满浆,再施肥,都变不成粮食了。山脚是平掌村,海拔只有1100米,土肥地沃,只产粮,栽不活泡核桃等经济作物,大集体年代的小康村,现在落伍了,种粮食的不及栽泡核桃的,生活水平明显落下。我家所在的平路村位于阿定山左半腰,属于温带,典型的山勒巴地段,地瘦不算,还盛产风,每年都刮好几场呢,学校里上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老师就拿我们村冬天的大风举例。的确,一场接一场的大风夜间经过村庄,场场带着尖刀,股股都糙而硬,绝对不会轻易绕过地里的玉米,经风一折腾,长得玉树临风的玉米就要倒伏或折断,那是最让人伤心的灾难。阿定山右半腰虽然也是山勒巴地带,但不知是水左,还是地形怪,这个村出产美女。每到年关,进村的路上都会拥挤着许多豪车,车主一般都是来拜会亲爱的岳父岳母大人的乘龙快婿。
格自山因向阳,土肥地沃,山头的树遮天蔽日,常有熊与豹出入,野兔与麂子不时误入百姓家中,善良的格自村人往往采取放生的做法,顺便还烧柱香焚点纸,担心什么时候得罪了山神自己还蒙在鼓里。在他们意识里,进家的野生动物都是山神派来的兵将,说不准来通知你什么,又会有什么警告,因此,遇上这样的事,全村人也会帮着做些法事,请法师跳神,给迷途的野生动物拴上巴掌大小的红布,做了这些,似乎才心安理得。说到底就是格自山宽人稀,寂寞的野生动物们常以串门子的方式频频造访农户,后来人们也习以为常,不再做这做那。野兔们居然与鸡抢食呢,野雉偷懒,向学布谷鸟的做法,把蛋下到农户的鸡窝里,让老实的母鸡给它孵蛋。格自山方圆五十多公里只有两个小小的村庄,一个是格自,另一个叫茅庐,格自的祖先据说来得很远,一盘白话,捻着胡子说话的老人便会说出“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滑石板”这地方,与阿定山上了年纪的人说的是同出一脉,就是那棵大槐树多高都说得一清二楚,仿佛那树不在遥远的南京,而就在门前,甚至说话时还有意往门外看了看。茅庐人实在,只知道稼种收获过日子,似乎也没有人关心过自己的从前,他们只关心今后,盖几间水泥房,把拖拉开进院场,娶个屁股大的姑娘生娃。
小时候家里穷,放学后就被姐姐带着到对门格自山上挖药草。格自山上的药草很多,记得挖得最多的是一种叫酒药草根的药草,当时也不知道这就是后来炒得异常火热的龙胆草。收购药草的是大队里的购销店,按斤论价,公正公平,每星期可以挖购到一学年的费用,当时算是最有出息的创收手段了。挖酒药草根分季节,一般到了秋后,这时天高云谈,林间的清风居然把色彩斑斓的叶子吹出动听的曲子。格自山上的松子也是我与姐姐采集卖钱的好东西,采松子可不比采药草,采到松包之后,要背回到家里,用簸箕晒,一天的阳光足够让松包爆裂,一阵滴滴哒哒的响声之后,细小的松子带着翅膀弹跳出来。松子价格很高,每市斤收购价是一元,一元钱可以交两学期学费,但一元钱的松子得采半个多月,松包结在高高的松树上,没有两下子攀爬的功夫是不行的。与村里其他男孩子相比,我爬树的能力要弱得多,甚至到了树上,又会因为害怕下不来,常常需要大人们营救,这一点,至今都还落给童年伙伴们一些笑料。
阿定山上没有松子,值钱的药草也不多见,但生长着一些野花,比较出名的要数红花莲瓣。松树与杂木之间的空地,半阴半阳的草丛,时不时掠过一缕缕细若游丝的清香,一定是刚刚睡醒的兰吐出积聚在心里的香味,待你等着想再吸一口,又都寻它不见。有一年兰花热,一苗红花莲瓣卖到一万多元,老百姓谁还静得下心来盘生产,纷纷上山,差不多把阿定山翻了一遍,兰花被人挖光,连长出兰花的泥土也被人一车车运走。迎春花长期被人误解了,给它起名瘌痢头花,让人觉得恐惧。可能因为迎春花粉多花艳的原因,就连我母亲也常对我说,“碰不得啊,会瘌痢头呢”。母亲的警告是每天都要进行的,那时放学后常到地里打猪菜,而迎春花就在田边地角蔓延,风一吹,那些艳丽的花粉纷至沓来,不小心就会粘到脸上手上。小时的我却把那美轮美奂的风景误当危险,刻意躲避着,真的怕自己的头上哪天长出疮痍。许多年后,那些精明的商人将阿定山的迎春花装入营养袋,一车车运到城里,高价销售给市民的消息传到老家,人们这才懊丧不已。倒不是因为没有抓住赚大钱的机会,而是觉得误会了迎春花,让心甘情愿装点故乡穷乡僻壤的花朵蒙蔽不白之冤,承受误解之苦。
三
老家人说这山好不好,一定说这座山上出了什么人物。阿定山人口多,出了一些可以称得上“人物”的人也不足为奇,当然这人物很小。我爷爷许昌庆算是一个,他是阿定山先天教坛主,信众不多,加上他也就几十人,不知是什么教徒传教,问过当过爷爷弟子尚健在的老人,说只知道我爷爷吃素,善行,格守清规。先天教与离卦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是八卦教的一个重要支派。据说,先天教创立的当年,就被清朝廷破获,但先天教徒并未如鸟兽散。先天教的活动方式也是“夜聚晓散”,教徒称入教为“学好”,教徒称教首为“当家”,教首称徒弟为“善人”,并教他们习学拳棒及坐功运气术。每年四季之首日,习教各家都要上供祈福,徒众均要出香资钱文,每人数十文至一二百文不等,穷的人家不出资也行,出个工修桥补路,也记到善行的帐本上。教徒入教时,要向学哲人先望天空,烧香供茶,然后师徒一同跪地磕头、发誓。誓词是:“俺今替祖亲传密密还乡道,俺传正法正道;要传邪法,哄了群黎,自身化为脓血。”然后,徒众要接应说:“情愿向善。若敢不遵,泄露真传,不过百日,化为脓血。”设誓完毕,教首还要命令徒众闭目盘膝而坐,用手抹脸,以鼻吸气,由口中出,名为采清换浊。接着,又授以“耳不听非声,目不观非色,鼻不闻恶味,口不出恶言”等话语。之后,教徒就算正式入教了。爷爷后来的遭遇与这段历史有关,解放后仍然吃素的爷爷,不得不向人民群众低头认错。另一位人物也是我家门中的爷爷,叫许昌华,官至顺宁府鲁史乡长,管辖着现在四个乡镇的地域,只因收到手中的钱一夜之间贬值,不得不回到村子里卖了大部分田地赔款。因祸得福,当他卖完自家田地,勉强凑够该缴的款项,全国解放了,后来划成分,划了个富农,与有头驴子就是地主的标准相比,他是幸运的。搜遍阿定山,当代的人物要数副处级干部学成了,弟兄很多,自然不在殷实人家之列,吃了很多苦。高中毕业带着一床破絮到省城求学,后分配到市工商局,从文字秘书做起,当了官仍然时不时出本诗集,放歌或吟诵故乡阿定山的美。
玉砚塔伫立于阿定山与孔雀山接壤处,据说是另一个村子一个叫杨文鸿的富人看到阿定山出人才,民国20年(1931年),动用人力物力,造了这一尊13层,高约30米,边宽3米的玉砚塔。这塔现在还在,四级条石基座,属于地方风水塔,当年杨文鸿请风水先生写下“永镇山河”四个大字,有点压山脉的意思,文笔塔建成后,不但没有压制住阿定山脉,而且那塔建成后的一百年间,阿定山文化人辈出,据不完全统计,阿定人在正规出版社出过文集20多部,中国作协会员1人,省作协会员数人。十个老头子拉出来,给一支笔九个老头子便能挥写集书法与才情一身的对联。现在想来,玉砚塔反倒象一支巨毫,稳稳地插在阿定山的胸前,让阿定山的儿女才情满溢。
实在地说,格自山就没有写诗的人出现过,就是写对联这样的活,还得到阿定山这边,请人过去帮忙。据不完全统计,有人居住到现在,最高学历也只是中专,而且都还是休学归来的那种,倒是满山的松树让格自人出了几个老板,有的老板已把房子盖到县城,把情人留在小窝,把老婆放在乡下。有的老板出手阔绰,好车一买就是一对。格自山山神庙多,有点年纪的老树,差不多都成了神祗,简陋的石头随手一雕,就是法力无边的山神,管着牛羊成群,管着家运昌盛,甚至管着年轻人的爱情。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就在这些老树下,人们敬神,也敬山川香草,往来明月。
两座山不论出什么人物,也不论离开两座山多久,都会选择回到故乡,生前不能回来的,死后也一定让子孙们将它们骨灰弄回来。如果哪一天有人要为两座山立传,向阳的山坡上,将那些碑文收集整理,就是两座山详实的资料,一理便可以理清两座山上下五百年间的事。
阿定山与格自山遥遥相望,一条阿定河横在中间,许多水磨房就设在河岸。隔不上一公里,就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小房子,那就是水磨房,引水冲动磨轮,再转动石磨,便可以将粮食磨成面粉。除了磨房外还有碾子房,同样是引水冲击磨轮,再转动石碾,将谷脱壳。大集体时代没有电,没有面粉机碾米机,两座山上的村民们吃粮都得靠人背马驮到水磨房,才能将玉米变成白面,稻谷变成大米。水磨房成了阿定与格自两座山上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去处,借故说家里的米面吃完了,随便背上点粮食直奔水磨房,其实一定有一个约会,需要在黄昏时分的磨房里完成,或者是对山歌,或者是密谈,反正黄昏的阿定河,可以看到年轻人影影绰绰的背影,顺着阿定河走着。
四
格自山上的人舒服着呢,柴就在自家房后的山坡,每年几场大风准能将那些苍老的松树拦腰折断,刀斧都不用,便可以搬回烧不完的柴禾。肥沃的土地随便洒些粮种,也能迎来丰收。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格自人慵懒的性格,每天都是鸟将他们唤醒,披衣起床之后,不是忙着去地里干活,而要先将火塘烧着,煨上一阵茶,抽上一阵烟再想着昨天还有什么活没做完。这时太阳已经铺满了院场,这一铺天就开始热起来,他们又会说等到傍晚有凉风呢,于是把桌子搬到村头的老榕树下,甩起扑克牌。阿定山人稠地密,生产承包到户后,许多人家还是因为土地少不够吃,于是就把目光投向格自山脚那些长满密密麻麻茅草的山坡。有的找格自山人家打亲家,给孩子找个老干爹,自然就用礼品换一些山地种植;有的干脆就把女儿许给了格自山的人,也许到头来只是张空头支票。水不缺柴不缺粮也不缺,这样好的条件恐怕难找了。我妻子也是格自山人,那时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每天父亲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赶着家里的5头黄牛40多只羊到对门格自山上放牧,到山上将牛羊往山坡上一放,就自个儿找个荫凉的地方睡觉,那日子闲是闲了,可心憋得慌,许多同学都考取了省内外大中专学校,只有我跟在牛羊后面,每天面对蓝得让人头晕的天空发呆。妻子是一大富人家的小女,富到什么程度呢,格自人说,富到牛有几头都不知道,羊有几只都不清楚。妻子初中毕业就不读了,同样跟在一群牛羊后面,她心灵手巧,缝针线纳鞋垫绣花样样在行,居然还能将随手摘的叶子吹出歌来。我最爱听她吹《军港之夜》,那个年代流行曲代表作,她每次吹的时候,都让我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歌声远了,我们走近,当我离开阿定山来到城里的时候,我始终没敢轻易放下这桩爱情。尽管我们村子里常拿格自人好吃懒做活开涮,我始终喜欢格自山,喜欢偶尔出没花豹的山路,喜欢吹叶子的女孩。
后来,格自山出产铁矿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比山上跑着的山羊都多的投资商。有的画地为牢,试图霸占国家土地为己有,发一笔横财。有的同样采取与格自人打亲家的方式,图联手开发,格自人想一千零一夜也未必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屁股下沧桑的土地,竟然蕴藏着挖卖了就可以变成钱的铁矿。格自人开始财大气粗起来,纷纷将自家山林圈起来,私自与不法商贩签约,将国家财产变成己有。那些已经在他乡生根结果的格自人纷纷回到自己的老家,开始审视那座不奇不峻、不高不低的山冈,正象山歌里所说的那样:“蜜蜂采花去远掉,哪想好花开在家门前”。外省测量队来了一伙又一伙,开发商投资公司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矿洞象毒疮一样疯长,人们眼红了,与矿石价格相比,种粮的收入显然微不足道,当地农民纷纷入伙其中,巴不得挖出个金娃娃来。阿定山的年轻人也加入到探矿大军,胆大的,将自己种烤烟的收入投进他人股份,想以资本入股的方式分到红利;胆小的只能以劳力投入,每天跟在矿老板后面干活,也算是一个工人阶层了。
阿定山没有矿藏资源,但是随着泡核桃产业发展,一些人开始盯梢生长着松树的山地,他们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从外面搬来投机者,砍掉树木,种上泡核桃。仿佛与生俱来与粮食有仇,谁也没打算在土地上多一分钱的投入,都在寻找所谓的致富快车道,结果许多年过去,能带给阿定人的仍然是阿定山上的五谷。泡核桃要十年八年才能挂果,这十年八年间你要吃要喝,拿什么来糊口呢?格自山其实只是一场闹剧罢了,几个投机者乱吹一通,说格自山某处有铁矿,后来神吹到说格自山有金矿,结果国家有关部门一查,子虚乌有。山上的烂尾矿,再也没有人收拾,格自山许多人家背负起沉重的贷款,矿洞就象是一个个伤口,几十年后仍然人有感到痛。
五
人们又开始审视阿定山,想它的从前,那是涧水四流,鸟语花香的山,松鹤山寺钟声悠扬,打麦场牛羊成群。想它的将来,生活的变化有目共睹,虽然变化的速度不是很快,但隔三两年,总也有变的地方让你逮到:小洋房蘑菇一样冒土,小汽车在赶牛大路上进进出出,商店挤占了山神庙地盘……。山坡上有坐南朝北的村落,按时升起的炊烟,鸡鸣是铁的时序,风调雨顺的年景总是很多。现在,树都差不多没有了,连年烤烟种植,树根都被老人们挖去作烤烟燃料,四时皆流的水成了季节水,雨季时出一阵子,旱季来到,山上的人又要回到阿定河边,淘米洗菜,顺便把沉淀淀的水桶背在身上,才能延续生活。有人说,一看到小洋房心就慌,因为那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结果。
做了一个大梦的格自人,同样回归到生活的原始,仍然需要上山挖药草,找菌子,采松籽改善一点生活,那些无望的年轻人又都纷纷离开村庄,到了外面的世界。格自山仍然在春天被满山樱花包抄,天性灵敏的云雀在花香里穿插着飞,玩着老鹰叼小鸡的孩子们,追逐着最简单的快乐,老人们重又回到老榕树下,说着从前。从前不远,是山上森林遭灾的日子,那些拖着滚滚灰尘的大小车辆,让格自山夜不得安宁,仿佛是一场闹剧终是停了,那些粉墨登场的人物们,也都一一离去。当年一买就是两辆好车的老板回到格自山,用吃喝玩乐之后小小的余款买了个小山头,再从集市上买来几只羊。打算这样的方式生活,是因为他每年最大的愿望不再是账单上的日进斗金,而是两只母羊可能产下的羊羔,羊羔长大后,又会生儿育女。与格自山相比,阿定山上的人们算是平稳地生活着,只是同样是光头了的山上,不知哪阵开始,一股股恶风横行,每年都会把挂包的玉米按倒在地上。
进村的公路越来越细,路上面的人家故意将包坎打在路边,挤占一寸算一寸,路下面人家也不甘落后,说是铲草要除根,硬是将有效路路挖到他家地里。“社教”那年,有位工作队长来到阿定山,走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阿定山的小道越走越窄。每年秋收后,阿定山的乡亲们都会进城来找到我,开口就要钱,说是要修路,我理解他们的苦心,为他们能想到若要富先修路感到高兴,但又不明白,好端端的路非要把它弄成小路才想到需要拓宽,就是给钱修好了,又有谁能保证路就能畅通无阻!
虽然离开阿定山多年,但我仍然从不同途径了解到故乡发生在两座山上的一切。我当然也希望格自山的铁矿有天文数字的储藏量,也希望阿定山的泡核桃能见风就大一截,快快挂果,让那些优秀的子女们回到故乡,找到生活的希望。然而我的想法比那些找铁矿的人们天真,当那些初中一毕业就离开两座山的女孩子们再也不回来之后,最为严重的是,大量的光棍找不到媳妇。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找不到媳妇的年轻人,再也没心思从土里刨金,有的成天守在某个小卖铺前,喝着半瓶啤酒,觊觎着留守的妇女;有的学会了偷鸡摸狗,让两座山从此不得安宁。
阿定山上还生活着我八十岁的老母亲,还生活着精神分裂症的弟弟。二十多年来,我都在城市与乡村间穿行,半数的工资收入都花到了回家的路上。但我不后悔,因为那里有我的根。随着年岁的增长,疾病开始缠身,真正推开柴门陪老母亲在阳光的小院聊天的时候少了,更多的是在梦里。一次梦见阿定山上的苦荞都开花了,母亲在苦荞地里唤我回去,我答应着,可母亲老是听不见,母亲哭,我也哭醒起来。又一次是梦见女孩子都被人贩子赶到拉猪拉牛的货车上,那里面有我插着桃花的侄女,侄女想下车,但车绝尘而去。
六
阿定山没有峻峭的峰峦,但人们喜欢上山。山巅是旧时的一座寺院所留下的痕迹,只有四个石头打制的柱脚还牢牢地盘踞在杂草丛生的地上。小时常去攀爬的桃子树已经不知去向,夏天那缕枇杷果的鲜香也被无处不在的尘灰履盖。上山的多是老人,他们一般都不做什么农活了,最多也只是放牛,将牛赶到山上,没事,就去看寺院的痕迹,他们说山巅的风水好,不用请地理先生瞧,随便埋都是好地,都会大发大富。我也喜欢去那个叫松鹤山寺的道教圣地,学着诗人的样子来点沉思,来点抒怀,竟然想到我去逝埋在山半腰的父亲。父亲生前常给我讲松鹤山寺的一些事情,说他小时候常跟爷爷去做会的情况,两个庭院,花开四时,乐师们的生活,产经书的过程。父亲不识多少字,但他惜字如命,遇上地上掉着的字纸,他非要捡起来放到家里恰当的地方。父亲从爷爷手里接过的那些绵纸刻印的四书五经之类,都被我撕毁了,现在想来,如果那些散发着棉花味道的书安放在我书房的一隅,该是件多么添彩的事啊。松鹤山寺现在只是一块被邻村人种苦荞或苞谷的山地,不算瘦也肥不到哪里,倒是在那里看云实在是件很爽心的事情。阿定山的大冬天四处灰头土脸的,只有云异常精彩地表演,让人看到无以伦比的轻歌曼舞,用尽所有色彩的美,似乎也很难道尽云的丽影。鹰常在离山巅不远的空中翔飞,有时好象一动不动,象定格在风中,看到地上的老鼠,刹那间腑冲下来,划破风,发出刺耳的啸叫。
格自山只有松涛,那是大山的潮水,一年四季都在咆哮。松风硬朗,松脂芳香,阳光经过松针筛选,落到地上的是除了燥的暧与温,躺在上面,很多时候就会以梦的方式确定自己为王。而做王者之梦的不是满脑子问题的诗人,而是那些反穿羊皮的放羊老头。嘴里咂着旱烟锅,烟味浓得让蚊蝇不敢拢身,席地一座,羊们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山坡,草色青青,羊却吃得十分潦草。放羊的人少了,养羊的人少了,只有很少人家,仍然舍不得将羊斩尽杀绝,留着羊,不是为了发财,而为了那些羊屎。羊屎是好东西,用它施地,没有肥不起来的庄稼,再瘦再寡,施一季羊屎,这土便松软泡酥,再瘪脚的粮种入土,也会茁壮成长。格自山上的矿洞象一处处好了的伤疤,不时被放学后的孩子们揭开,那是青年人约会的最佳地点,可能留下什么,让孩子们费尽心机不得要领。公路通了,“若要富先修路”的标语还在,但格自山的人似乎不懂,这路给他们带去了什么。
阿定河性格再怪,仍然摆脱不了夹在两山之间的命运,这些年水磨房少了,又有人想利用阿定河的水磨房进行旅游开发,于是又有人建盖一些水磨房,只是空落的水磨房再也没有人唱情歌了,月色很贫血,山歌魂已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浸润,水磨房只有机械的翻转与苍白的利诱。
每次回老家,一定要过阿定河去,去看格自山间那些我采过松籽的大树,我挖过药草的山坡,我逮过野兔的小路,偶尔会遇见从深圳或上海打工回来的女孩,在神性的老榕树下顶膜拜,也许她们只是回来喘一口气,还要重新回到工业的机声中。我也不希望她们留下来,嫁个男人,把羊粪背到山头,把收获背回老屋,再让花朵一样的孩子,沿着她们成长的小路出发,从小学到初中,从初恋到结婚。而我每次离开阿定山,又都希望自己留下来,年轻人的闯荡已经足够我回味与嘴嚼,但又怎么能说留就留呢?于是还得顺着母亲的目光出发,在能看到故乡最后一眼的山梁,转过身,站成一棵树的样子,向软弱的眼泪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