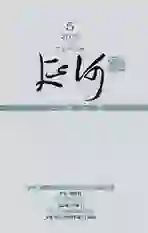追忆路遥二十年(外一篇)
2013-04-29朱文杰

2012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的祭日。转瞬间已是路遥逝世二十周年了,但在我心中,总觉得路遥还活着,有时闭眼冥想,那总爱侧身面对镜头,迷着眼,凝望中显得有点空朦的,却让人感觉异常沉重的影像,会闪现在你的幻觉中。让你眼发潮,心泛酸。我知道我是想路遥了,我的朋友,我的在“平凡的世界”里,创造了不平凡“人生”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兄弟。
怀念路遥,让我想起我曾在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英年早逝的记录”一章中,随电视专题片《老三届故事》拍摄路遥,并回忆我与路遥十年交往的那一段文字。
进入1998年,老三届人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是走进了丰饶金黄的秋天里的人了。长期的追求,竭力的拼搏,不懈地追赶着年轻时丢失的时间,使这一代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而这种长期超负荷的生命消耗,没有休止的疲劳奋斗,使一批本该放射出更加璀璨之光的老三届明星过早的殒落。是的,这一代人活得太累太艰难,于生死已是无所顾忌了。一批英年早逝的老三届人,路遥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你可从中探讨琢磨人生苦短与生命的非凡。
1997年10月21日,剧组到延安去拍摄路遥墓。当年与路遥、闻频并称的“延川山花”之一的谷溪领路。谷溪现在是《延安文学》的主编。到了延大后山的路遥墓前,谷溪点燃几支红塔山香烟,献在墓前,用发颤的陕北口音说:“路遥,这是你最爱抽的烟,我给你点着了……”一时间声音哽噎,老泪纵横。
路遥是延川永坪中学初66届的老三届。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很活跃,当过县上红卫兵的头头,很是狂热了一阵子。返乡后他逐渐清醒,结识了来延川插队的陶正等一批北京知青,影响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并和闻频、谷溪一起创办《山花》小报。恢复高考,路遥经过刻苦学习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奋斗,考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分配西安,到他逝世那么短短的十多年间,他创造了多么辉煌灿烂的生命奇迹。先是反映“文革”武斗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反映青年生活的《人生》,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轰动一时。《人生》拍成电影更是风靡影坛,获电影“百花奖”,成为中国西部电影的发轫之作。接着历时三年多就创作完成了100多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于文学创作是不惜血本的拼命劳作,通宵熬夜,体力严重超支,引发潜伏的病患。他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为此作了注脚。他没有早晨,经常是一根黄瓜一个馍就顶一顿午饭,嗜烟如命。有人说路遥是自虐,是苦行主义的信奉者,多年的积劳使他身体衰竭,看似健壮如牛的他突然就被肝病轻易地击倒了。
路遥的身体底子其实很差,多年农村贫困生活的折磨以及生长发育时遭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都在他的中篇小说《困难的日子里》反映出来。那种挨饿的经历,严酷的饥饿感是太逼真太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了。路遥在和我议论这篇小说时说:“那个年月可伤人哩。整个就是在饥饿中度过的,饿害怕了。”
我认为这部中篇实际上是路遥最好最出色的,路遥同意。我们都是从三年自然灾害挨饿过来的,当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每到上午第三节课学生就跑光了,饿得上不成课了。我的胃溃疡、胃出血就是60年代种下的病根,连我这个生活在省城里的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更何况路遥生长在更为穷困的偏僻的延川农村呢?那恶劣的环境和我可能是天上地下之分。
认识路遥是在1983年西安西大街上的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召开的陕西作协的三次会员代表会上,当年路遥是《延河》文学月刊的小说组组长。我们一下成了好朋友。他的弟弟王天乐当年才二十岁,在铜川山区里一个叫鸭口的煤矿下井当矿工,路遥把天乐托付于我,我看天乐在文学上很有天赋,就让他写些文学作品,不久天乐就把他写的散文拿给我,并按我提的修改意见改了一遍,于是,天乐的处女作发在我主编的《铜川文艺》上。天乐给我说矿井下矿工的苦累和艰辛,那么些天,他是天天盼望着我给他写的让到市上修改稿子的信,或到市上来开文学座谈会的通知,……因此矿上就会同意他请假,还不扣工资,他就能美美地歇上几天。还说他的散文在《铜川文艺》发了,矿上那些坏家伙就不会欺辱他了。我忙问为啥欺辱你?天乐说:我给他们说,写《人生》的路遥是我哥,他们说我瞎吹牛骗人呢?就把我揍了一顿。我说:鸭口的矿长我认识,我到矿上给你们矿长说去。天乐说:不用了,稿子上了《铜川文艺》,矿上都轰动了,还要把我调上井呢!
当年文学有点热得疯狂,一首诗一篇散文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事并不稀罕。……后来,天乐上了西北大学作家班,调进《陕西日报》,成了驻铜川记者站的站长,在铜川风光一时。
1984年路遥应我的邀请到铜川讲课。在铜川,几天的接触、彻夜的长谈,我们彼此间更加深了了解,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而我主持的《铜川文艺》编辑部的编辑、北京知青齐亚萍,就是《人生》中黄亚萍的模特,同名换姓,北京知青换成南京知青。齐亚萍先被招入延川县剧团,又成了延安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八十年代初调入铜川。在铜川,路遥和我们几个人一起相聚,听路遥回忆陕北,唱当年北京知青爱唱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我陪着路遥参观了耀州窑遗址、药王山、耀县水泥厂,记得路遥还给耀州窑遗址挥毫书写了“耀瓷之光”四个大字。路遥走到哪里都引得哪里的群众欢呼围观,特别的红火。我说:路遥,你看大家都带着羡慕的饱含着泪水的眼光在仰望你呢?!路遥马上机敏地回答我,我咋就羡慕你的个子高呢?并随口调侃一句顺口流:“雄伟的朱文杰,把事弄大咧,铜川跺一脚,震动满世界。”引得一车人高兴地大呼小叫,我也胡编了几句回敬:“路遥是国宝,像个大熊猫。谁个来亲近,咋都惹不恼。”又是一阵轰笑。一路上平日严肃的路遥兴高彩烈的像个顽童……。
晚上,路遥和我谈起他要写《人生》的续集,探讨高加林被退回农村取消了当教师的资格,续集中高加林的出路在何方?我说:“铜川煤窑多,旧社会为躲官司、避仇怨就是钻煤窑,而且现在铜川各个煤矿从陕北来的农民协议工很多,都是为了挣下钱回去娶个婆姨。而且你弟弟天乐就在鸭口矿下井,生活是现成的。”路遥一听高兴极了,说:“让高加林下煤窑,我也下煤窑。”于是通过铜川矿务局宣传部的黄卫平联系,一起去见了矿务局局长单甫义,路遥下到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省委组织部和省作协并安排他挂职铜川矿务局,任局宣传部副部长。
经过一段体验生活,路遥放弃了写《人生》续集。他要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城乡结合部的,一百万字以上的大部头、重量级的作品。第一卷出来时,还没个名字,当时1986年吧,《长安》文学杂志要选载,路遥就在我们的办公室想名字。他原先想叫《苍茫》,让和谷一句话,毛主席的“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路遥听了马上摇手,我写的是平凡人,不敢主沉浮。我说不如叫《普通人的世界》,大家沉思中,《长安》主编子页在纸上写了《平凡的世界》,路遥马上认可,就是它了。而同时我也要出一本诗集,名字没确定,暂定为《历史行吟图》,路遥一听,就说了两字:“不好!”我让路遥参谋,他就拿过诗稿翻起来,先说:“你发在《诗刊》上的《陕北唢呐》,我记得呢?可写得好呢,我当时一看,就给你打电话,对不对?”我用醋溜陕北话回答:“一满莫忘”。他忽然一拍桌子说:“《哭泉》这首诗名字好,就叫《哭泉》吧!……
其实,被路遥认可的两首诗,命运虽截然不同,但都遭遇坎坷。先是《陕北唢呐》被评上了陕西省首届新诗奖,但后来有人告状,对极个别获奖作品有意见。整个评奖结果就被搁置起来,没向社会宣布。我因评职称去作协找老诗人田奇,想要个奖状。田奇先生是省作协诗歌领导小组副组长,老田说我已在报上发了获奖消息,但奖状发不成,正好路遥过来了,他一听就说:“老田你填个奖状,我给你找主持工作的让盖章。”沒过两天,我就拿到了盖上“中国作协陕西分会”章子的获奖证书。一封匿名告状信,竟像一颗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真是让人感慨。而我却因了路遥,成了这届评奖唯一有证书的人。
而《哭泉》这首诗曾因争议,涉嫌影射,被从已印制好的《星星》诗刊1987年第2期撤下。据时任《星星》诗刊副主编的叶延滨说:光重新印目录和两页内文,再装订,使刊物损失近三万元,这在当年可不算小钱。最后这期《星星》诗刊上只发了我的一首诗《无题》。一首23行小诗,横跨两个页码,相当开了天窗,呜呼!一年后,此诗被上海《文学报》老诗人黎煥颐先生看中(当时他到西安来组稿),又因同样问题,《文学报》沒发成,最后黎先生推荐到上海《建设者》杂志发表。
当路遥生命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我是有预感的。当时我给省出版局图书处处长李天增建议,让哪个社给路遥出个文选,李天增一听说是个好主意,马上打电话叫来陕西人民社的一位副总编,他们一拍即合,并立即让报选题。上个月和李天增老兄回忆此事,他说:当年,路遥带病骑自行车给他送来签名的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让他非常感动。
为筹划此事,我先到路遥家中商谈,想探一下路遥的口风。记得路遥强调了两点,一是书名要叫《路遥文集》,不叫《路遥文选》;二是要陈泽顺当责任编辑,陈泽顺是路遥在延安大学的同学,北京知青,当时在陕人社当编辑,后调到北京华夏出版社当副社长。说起出成文集,我说不好,你创作正旺盛急个啥?路遥说:“40岁该有个总结了。”我一听“总结”,感到不吉利,从他家出来,心里一直犯嘀咕。怪啦,我这个人平时并不太迷信的。记得《人生》写出时,路遥专门到佳县白云山抽签,抽出一上上签,“鹤鸣九霄”,果然《人生》一发表就使路遥一夜成名……
路遥为人厚道,大方仗义,属性情中人,而这个世界上唯性情中人可交。一次我在建国路和几个朋友会餐,餐后到作协院子时已快晚九点了,谁知因食物中毒而昏倒,正好让一个人在院子转的路遥碰到了,他就着急的跑前跑后,一会让人叫狗娃,又让找根社。这俩都是作协司机,于是就近把我送到了附近大差市口的四院,诊断为胃出血,打了一夜吊针。当时昏迷之中的我,已记不得送我到医院的是随后赶来的闻频老兄,还是路遥?开车的司机,也不知是小名叫狗娃的余国柱,还是张根社?
路遥比我整整小一岁,从一认识,我就感到我们特别投缘,他对我特别的好,他的中篇小说《人生》一出版就签上名,让他弟弟天乐专门给我送到铜川。正好路遥亦师亦友的诗人闻频到铜川组稿,我说给闻频听,闻频第一反映是不信,“这家伙连我都沒给呢?能给你?……”我请路遥到铜川来讲过课,开过会,引得我西安朋友惊异地说:“能请动路遥,你面子真大。”路遥几次和我说话,都客气地称文杰兄,更惹得周围的人惊奇,他们说:路遥在作协连比他大上七、八岁的人也从不称兄。这话当然不准,我就听过他当面称闻频、子页为兄呢?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一写完就打电话让我过去,拿出已排好版的一叠稿子说:“你拿回去给看一下,看咋个相?”我以为路遥要修改征求意见呢?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专门鸡蛋里挑骨头,一口气写了六条意见。当拿到作协给路遥看时,我发现路遥看完后,脸立刻阴沉下来,手还有些抖,我一看,坏了!惹下事了,忙告辞回避。我走时,路遥沒说活,屁股也沒抬一下。很快《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杂志发表,还在北京开了研讨会。《花城》主编李士非是子页的诗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就是子页推荐《花城》发表的,记得李士非派人到西安来取稿,路遥和子页一起去人民大厦交的稿。好长一段时间,我和路遥都没联系。到1987年6月的一天,路遥给我打来电话,说:“《平凡的世界》出来了,你过来取,顺便帮我给晚报的副总编高平和商子雍也带一套。”见到了路遥,他就说,“书一来,我就跟你联系,你比作协院子里人都拿得早,西安市我就送这几套。”路遥马上为我签字,嘴里还念叨着:“文杰兄惠存。”我和路遥提起当年的六条意见,带点歉意地说:“我有点莽撞了。”路遥说:“好着呢,你等于给我打了预防针,《花城》在北京开研讨会,会上提了一大堆意见,尖刻着呢,但基本都在你六条意见之中,要不,我可能吃不消。”我和路遥结识十年,他从来都很高看我这样一个基层业余作者出身的没啥成就的人,感到我们俩一见面,就有一种亲近感,可以说是能交心的挚友。我一直都非常珍视这种友谊。
路遥爱文艺,爱唱歌,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爱和朋友们一起海阔天空的胡说乱谝,他还痴迷的爱足球,最欣赏德国队,他到德国访问,竟然想办法亲临赛场近距离去享受足球,在西安他得意的给我说,他爱足球是陕西作家头一份。路遥最爱唱的歌除了陕北民歌,就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草原》,还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纺织姑娘》,路遥那时爱和几个年龄相仿的作家聚在王观胜的房子唱,我曾赶上过好几次。有时大家合唱,有时听路遥独唱,他唱得很投入,很动情,声音低沉,音质中有一种金属味,具备美声男中音的范儿。但他跳舞不行,首先不敢下场子。下面看我的一篇散文《遭遇舞会》中写的一段。
记得还是1985年,一次西北作家在西安开会,会间自然安排了舞会,当然也就出现上边所说的奇特现象。舞场里依然空空落落,于是主办者从大学及宾馆请来的一些佳丽们纷纷上前拉作家下场,那时文学神圣,作家社会地位如同今日之歌星影星,请来的佳丽中不乏对作家之追星族。佳丽们热情大方,展开温柔攻势,作家们畏畏缩缩,百般后退推托,那场面美丽的叫人难忘。这时有旁观的作家在调侃,为自己的胆怯找理由。A作家膀大腰圆,戏谑地说:你看我肚子这么大,一顶就把人家女的顶跑了,下舞场有碍观瞻;B作家个头矮,短小精悍,诡谲地说:你看,现在女的个子都高,我上去搂人家的腰,不是成了“双手搂定宝塔山”了。A作家马上驳斥:啥些,你还“仰望北京天安门”呢?你那个子还能搂在人家腰上,一搂就搂在人家尻蛋子上去了。说完俩人相对哈哈大笑。
相信看完这段,明眼人已知这俩幽默的A作家和B作家是谁了。
路遥识人才,还特别关心基层的业余作家,例如当年对叶广芩、王观胜、郑文华等。还有笔名叫黄河浪的张仲午,仲午在西安市文联的《长安》文学月刊社当临时编辑,路遥就曾对我说过:“你要多关心一下张仲午呢!那是个下苦人。能关心一定多关心。”我一直记着路遥的这些话,我虽然人微言轻,给仲午解决不了大事,但瞅准机会让我的一位派出所工作的朋友给他在西安上了户口,因为仲午在西安结婚生子。虽然黄河浪工作关系在榆林,但我聘他为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的驻会工作人员,为他出差,为他夫人单位分房出证明等。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怀念着路遥,愤恨着老天不公,天嫉英才。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始终怀念着路遥,记得几次去延安,都专程到路遥墓上去祭拜,我曾先后和商子雍、赵熙、莫伸、丁晨、商子秦、渭水等一起去爬延安大学后边的山,采上几束野花,点上几支香烟,敬在路遥墓前,每个人都和路遥说上几句话,每当这时我都热泪盈眶,下坡时腿有点发颤,回到歇息处,本来习惯熬夜的我更是整夜难眠,脑子里全想的是路遥了。
我在《老三届采访手记》“英年早逝的记录”一文结尾的话,至今读起来仍然让我心疼。就用这些话再一次说给路遥听吧,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应到。
而今路遥已经驾鹤西行了,他的平凡的人生似一颗耀眼的明星永远在闪烁。在他的墓前,剧组的同志把一束野菊花献上,那黄灿灿的野菊花在萧瑟的秋风里摇曳着凄迷,在有着凉意的秋阳中闪射出光怪陆离的亮斑,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之中。返回西安时经宜君的哭泉镇,就想起路遥为我的第一本诗集选的名字了。我哭路遥的英年早逝,文星殒落;我哭老三届人的坎坷一生,命途多舛。
林则徐与王鼎
林则徐是人所共知的民族英雄、禁烟名臣,天下谁人不晓,他领导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华民族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四周的八块汉白玉浮雕,一幅就是“虎门销烟”。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林则徐的恩师,一位义薄云天,肯为林则徐以生命去“尸谏”的,永垂青史的伟人。他就是陕西蒲城人的王鼎。而林则徐曾到王鼎老家的蒲城,为他的恩师,与他肝胆相照,志同道合的王鼎守“心孝”三个月。则更是少有人知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一曲悲壮的历史颂歌,中国人向来推崇“士为知己者死”,可纵观历史,真正有勇气为知己者而死的人,又有几个呢?
就是这个王鼎,从蒲城走出去陕西少有的几个状元之一,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关中汉子,在1842年4月30日这一天,以死劝谏道光皇帝收回贬谪令,不要签订不平等条约,应委林则徐以重任。留下了“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摇撼人心,悲情呐喊式的遗书。
那天在朝堂之上,王鼎奏请皇上重新启用林则徐。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说得痛哭流涕,但都无济于事。愤怒到极点的王鼎,又当着道光帝的面痛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明之严嵩,宋之秦桧”。王鼎明白此时的道光帝正暗中命穆彰阿和英国侵略者草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哪肯重用力主禁烟的林则徐。道光帝听到王鼎这些激愤之语,很窝火亦很无奈,以“卿醉矣”为由,命太监“扶”王鼎下朝。道光帝急忙退朝之际,发现他所穿的龙袍一角,被王鼎用牙齿紧紧咬住,猛力一挣,龙袍撕破一块,便悻悻退去。而王鼎被道光帝这一挣,牙齿碰着丹墀,折了两颗,血流满口。
当晚,对道光十分失望的王鼎,悲愤难抑,他决心,“欲效史鱼尸谏之议,不惜以头颅护良才”。写了遗嘱,再次力荐林则徐是个难得的人才,请皇上开复使用。写完,自缢而死。
王鼎以死抗争,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新疆,戍守伊犁的林则徐得悉后,悲痛欲绝。写下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诗悼念王鼎,诗云:“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林则徐还在自己不少诗文中,寄托其对王鼎的无限怀思,例如《次韵寄酬高穉庵(步月)》的诗中就有:“痛哭王尊今宿草,久悬揆席未宣麻”之句,可见林则徐对恩师之死的千分悲切,万分怀念。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生死之交、真情厚谊的感天动地。每当笔者读王鼎和林则徐留下的这么多的诗文,无不热泪盈眶、心潮难抑。
王鼎,字定九,号省厓,陕西蒲城人。生于1767年,长林则徐17岁。嘉庆元年(1796年)中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师,是道光时军机重臣,清代著名抗英名相,也是嘉庆和道光皇帝的老师。他一生端方正直,政绩卓著,在朝野享有盛誉。
关于王鼎与林则徐由相识而结师生之谊,有几种说法。最早的一种是1811年春天。那一年,27岁的林则徐会试中二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被派去学习满语。于是,他和早在翰林院任职的王鼎相识,成了王鼎的学生。第二种说法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林则徐在江西南昌时与王鼎相识,成为至交。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禁止鸦片,成绩卓著。王鼎则向道光帝极力推荐林则徐可以担当领导禁烟任务,说他:“多谋善断,有守有为,堪当重任。”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时,深知此行禁烟并非易事,行前只向王鼎一人辞行,见于记录的是林则徐1839年l月4日的日记:“晚在王省涯(鼎)相国处饭”。而王鼎在日记中所记有:“1且4日晚,设家宴为林则徐饯行”。这是林则徐离京前参加的唯一一次饯行宴,由此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林则徐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后,懦弱的道光皇帝怕得罪洋人,于是,降罪林则徐,竟要把他流放伊犁戍边。王鼎闻听后,震惊异常,他想尽办法去周旋营救。而正当这个时候,刚好河南祥符(即河南开封)黄河决口,王鼎急忙上书道光帝允许准备赴伊犁戍边的林则徐和他一道去救灾,他不顾自己74岁的高龄,目的无非是请求道光帝给林则徐一次“戴罪立功”机会。来挽留这位令人敬佩的爱国功臣林则徐。灾情如火,道光很快批准了王鼎的请求。两位同命相惜的挚友,终于同赴治黄工地,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呕心沥血、劳心费力。尤其是王鼎带病苦作,不顾背部疮痛地顽强坚持,直到大坝合龙之日。谁知昏庸无道的道光,在治黄工程胜利竣工时,又降旨让林则徐“着仍往伊犁”。心中十分不满的王鼎,在含悲咽愤中为林则徐送行,老人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林则徐则坦诚劝慰。并写诗相赠。诗前写道:“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诗云:“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诗中对自己遭遇无怨恻之言,对老师王鼎则满怀敬重之情,寄望綦切。
林则徐三次来陕、两次在陕为官的经历。先后任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陕甘总督,陕西巡抚。时间虽不到二年,但他抗灾救民,关注民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和陕西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林则徐不但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陕西写有《过紫栢山留侯庙》、《定军山谒武侯墓》、《武侯庙观琴》、《寒溪》、《女郎庙》、《题杨太真墓》等诗。其中《秋怀》一诗,是一首扬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忧患之诗、不朽之诗。诗云:“一卷《离骚》对短檠,凉生昨夜旅魂惊。隔窗梧竹萧萧响,知是风声是雨声? 遥怜绝塞阵云寒,万户宵砧泪暗弹。秋到天山早飞雪,征人何处望长安? 天涯芳草旧萋萋,流水无声夕鴂蹄。何事戍楼鸣画角,双尖耳耸马悲嘶。官如酒户力难任,身比秋林瘦不禁。漫拟沙扬拼热血,忽窥明镜减雄心。”此诗于道光七年(1827年)秋,林则徐在陕西任职时所写。诗意阐述了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攻陷喀什噶尔的事件,清政府调兵3万余人进剿。林则徐由秋分时节的凉意,想到新疆八月已飞雪纷纷及前方将士征战的艰苦,他心怀天下,渴望着上前线杀敌报国,但又窥到镜中年迈苍老的自己,身比秋林瘦不禁,深感力不从心。写出了身在长安的他,面对征人所望,既愧歉怅然,却又急迫关切的心情!
在这些诗中,还有他的代表诗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二首。就是在陕西养病时创作的,其中第二首:“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他一生人格节操的佐证,闪射着伟大精神的光芒,遂成为流传千古之名句。
中国人民邮政于1985年发行的《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二枚。第一枚的“林则徐像”,背景上就是费孝通手书的这二句诗。而第二枚是“虎门销烟”。就是 “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虎门销烟”汉白玉浮雕。
台湾邮政部门,于1973年6月发行了《名人肖像邮票---林则徐》。看来,海峡两岸人民都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怀有深厚的崇敬、怀念之情。
再有,林则徐是清代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蒲城的林则徐纪念馆就收藏有他不少书法作品。林则徐纪念馆就建在王鼎族弟王益谦的家宅原址上。1847年初,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时,请假三个月专程来蒲城为恩师王鼎守心孝(不穿孝服)时,就住在这个宅院里,故也称“林则徐寓所”。林则徐纪念馆收藏有林则徐在蒲城时为这座宅院题写的七块匾额,特别是林则徐所书的《味兰书屋》匾,更被确定为二十四大历史名匾之一。
林则徐题写给王益谦的扇面。扇面上的字体为行书,笔法苍劲有力,为林则徐书法中的珍品。正文共有19行,内容是林则徐借陆游诗文抒发自己的心迹,也借陆游与朱熹的真挚友情,来比喻自己和王益谦的亲密关系。王益谦为陕西蒲城人,他曾在福建为官6年,当过知县,两人为挚友,在纪念馆中还存在新发现的林则徐校阅过的王益谦编的《太华山人诗集》,林则徐为王益谦之父七十寿庆而撰写的《王实田封翁寿序》,为王益谦之母撰写墓志,还有为王益谦之兄王之谦撰写的“三爻饮易韦编古,百岁娱亲彩服荣”的对联,该对联上款题“地山大兄大人同年有道之教”,下款署“少穆第林则徐撰句书”。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林则徐《游华山诗》刻石。另外,“碑林”二字也传说为林则徐所书,而笔者的朋友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室主任王其祎研究员已从他收藏的《林则徐临皇甫诞碑》拓片上找到了证据。2006年2月王其祎在接受报社记者一次采访中说,这张拓片上的“碑”“林”字样和悬挂在《石台孝经》碑亭上的“碑林”二字书体风格一致,如出一辙。林则徐是清朝临写欧阳询的大家,而《石台孝经》碑亭匾额上的“碑林”二字也恰恰是欧体。
林则徐和陕西的缘分很深,他走过的三秦大地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精神的光辉。而尤为令人感动至深的,就是他与他的恩师王鼎的那种超越了师生之情、朋友之情,以忧国忧民为基础,用三十年时间镕铸的一种升华了的,以忧国忧民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的伟大高尚之情。而这种友情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九州共仰,光照千秋,青史流芳,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