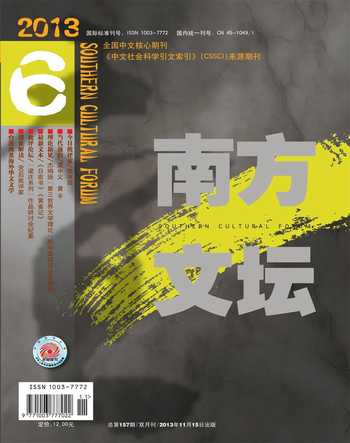消失空间的文学记忆
2013-04-29张柱林
生活的变化常常表现为空间的变化。从1992年邓小平启动政府主导的全面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生活已经面目全非,其最大的变化也就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改变上。那么,哪些空间消失不见或被大面积压缩了,哪些空间又生产出来或得到扩充膨胀呢?前者包括工业空间(如工厂、仓库等)、公共政治活动的空间(如广场、会场、礼堂等等)、普通民众的休闲与聊天空间(如弄堂口、公共的小院门口等等)的收缩以至消失,后者则包括城市道路(想一想拓宽的车道、高架立交桥、地铁等等吧)、商业空间(现在有些地方将购物中心叫做“广场”!)、政府和带着官办垄断色彩的各种办公空间,当然还有作为地方主要经济支柱的房地产所带来的住宅空间的扩张①。这些空间结构的改变不仅改变了居民的社会和群体生活,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形塑了个人的新的感知和行为模式。到今天,人们已经不会在街头巷尾驻足谈天,也很少在自家门前与邻居闲聊,人们知道明星的绯闻轶事,关注茱丽的乳房、莫斯科的天气、遥远的无人小岛,而对邻居的搬迁、身边道路上出了事故的人的生死漠然置之。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读柯天国写于二十年前的一系列以城市小巷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物为主要题材的所谓市井小说,就产生了一种追忆往事可堪回首的意绪。这些小说,产生于1992年开始的全面市场经济改革与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前夜,但毫无疑问那时已经出现了后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征兆,敏感而诚实的作家当然会把其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用感性的笔墨描绘出来。作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作为作品人物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的那些小巷院楼,最终将会从城市的版图中消失。比如烟花楼(《烟花楼》),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因为新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初下令取缔妓院及一切色情场所,而在多番的城市改造之后,只剩下一栋处于当时的花街柳巷最末尾的三层小楼,简陋残破,周围全是高楼大厦。而风流巷(《风流巷》)也是一条“死巷”,窄小灰暗,小车进去了只能倒着出来。作家解释这样的地方之所以没被拆迁,“也许是城市设计师手下留情”,当然也可能恰好由于位置偏僻,当时的商业价值不高,所以侥幸保留下来。作者要描写这样的地方,自然不会是由于它是一个可欲的客体,如田园小说家描写乡土是将其当作乡愁的对象,而童话描绘辉煌宫殿其理由可想而知,柯天国既没有将这些小巷院楼当作理想对象,那么仅仅是为了给这些市井小民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吗?
在《烟花楼》的结尾,一生坎坷的许春兰从医院出来,想起自己和女儿的命运,感慨万千,这时作者写道,“路上虽然碰碰磕磕,可是那个相依为命的家——烟花楼已在眼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把家当成最终的目的地。虽然烟花楼的历史不光彩,现在又破破烂烂,可住在楼里的住户并不嫌弃它,甚至觉得这里算得是出入方便,加上住久了自然产生依恋之情。所以这并不仅是由火砖、木板、油毛毡等材料建成的房子,如英文之所谓house,而是充满情感记忆的地方,英文谓之home。邻居之间自不免冲突不断,有时矛盾甚至势如水火,但他们的命运总是休戚相关。《少妇梦》里的陆家小院,与烟花楼、风流巷一样,曾经也有过自己的辉煌,现今确是败落了,年久失修,早已不是理想的居住空间,但作者仍带着明显的赞赏口吻描绘道:“几十年的世道沧桑,风云变化,都没有打破小院宁静安谧的格局,这里就像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一个幽幽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住家,也都是与世无争的平民百姓。尽管这院子的房舍已是陈年旧屋,甚至是残破的……但是,他们都十分留恋这小院。哪怕是已搬迁多年的老住户,回过头来,还是说陆家院子好,那里太祥和安静了。”作品也描绘了这样的情景,邻里之间毫无秘密和隐私可言,同住在陆家小院里的土狗,为了二百元钱,就替刘金龙监视其情妇白雪的活动,还美其名曰“私家侦探”。但在小说最后,当白雪出于羞愤,吞服安眠药自杀时,还是土狗妈发现了白雪屋中狼狗不停叫唤的异常情况,与土狗破门而入,才及时挽救了一条生命。试想,现在住在小区高楼里的居民,常常互不相识,彼此不相来往,出于尊重隐私等习惯也不再关心邻居的事情,要发现邻居屋里出现的异常几无可能,而且一般家庭厚重的铁门紧锁,想在短时间内破门救人,也不现实。《少妇梦》的重心并不在此,但却为读者思考今天的住宅空间安排与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柯天国的小说创作中,值得反思的地方并不只是其所描绘的注定要消失的那些传统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作家为那些人物所提供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舞台,即发展的空间。表面上看去,柯天国为其人物安排的结尾,很多时候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的设计,即让其回归家庭,如许春兰和许娟母女,离婚后曾经成为别人情妇的白雪也要回到前夫医生的家,其他人,如黄七的忏悔,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柯天国对1980年代城市平民的描绘中,他关注的主要是他们的出路,想象他们如何安排和拓展生存空间。从这方面看,就像作家将女性的归宿安排回家庭一样,他对那些“待业青年”的前途的设计似乎显得有些保守,如《狗肉香喷喷》里的何梅和二狗,他们经营的狗肉店生意红火,但他们却并不满意,总想着有一天国家招工,自己能有个“正式职业”和“正式的单位”,《在绿色的圩亭里》,艳姐和阿猫开的粉摊也很红火,给他们以希望,但同样怀着进国营工厂才是正道的想法。谁能料到后来国有企业会大规模转制,大批工人会“下岗”失业呢?但只要认真推敲其中的缘由,就知道在当时,这些考不上大学又没有关系进入正式单位的年轻人,其最好的出路仍然是进机关、工厂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做工人,就像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无论如何也要拼命考公务员一样,是由中国的体制现实决定的。柯天国的作品恰恰是在这种地方,体现了一种“写实”的精神。
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社会管理的松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实给当时的待业青年提供了一些新的谋生空间,这些空间正是柯天国笔下的人物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的舞台,当然说穿了就是做点小本生意,或单独经营,或与人合伙,或者帮人打工。我们看到,有开旅店的,有开舞厅的,有开狗肉店的,有摆粉摊的,有卖酸嘢的,形形色色。作品所写作的物理空间虽然破败,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空间却呈开放状态,具有当时的活力和生机。原先溜门撬锁偷窃钱财的王锁,在服刑回来后决心痛改前非,利用自己的特长做修锁的特种行业;而插队回城的知青何梅,一直没有工作,就女承父业,开起了狗肉店;艳姐(刘艳)的遭遇与何梅相似,她开起了粉摊;风流巷里的张芸开起了家庭小旅店……不过在情节安排上,作者似乎过于依赖偶然性:如王锁是刑满释放回来的人,他能从事修锁这样的特种行业是因为他碰上了两个好心的官员;小偷二狗能到狗肉店帮助何梅,是因为何梅不歧视他,心地善良宽容。也许有心人会读出其中的弦外之音:这些下层人物、平头小百姓要想谋生并不容易,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操控在那些手握权力和资源的人手上。居委会主任、物权所有者、市场管理人员等等,无时无刻不想从他们的劳动中掠取一杯羹,处处刁难这些弱势群体中的小人物;而他们周围也不乏用心险恶之辈,或嫉恨他们的顺利,或想占他们的便宜。所以这些人物的未来也就具有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张芸的小旅店被迫停业,她自己也只好到农村的砖厂做工;阿三的狗肉店虽然生意兴隆,但常常会有职能部门的人前来明查暗访;王锁被人陷害,前景难料。当时就有很多评论认为作者这样的安排过于残酷,过于悲观,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主流,没有完全展现小人物奋发的英姿。也许,现实中确有个别人从修下水道开始起家,最后成了大老板,但置于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固化的时代,这样的事岂非天方夜谭?就是那些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发财而做的小本生意,也在城市管理日益规范(至少是在这种名义下)、只有垄断和规模化才能生存的时代趋于消失。
正是在作者没有将张芸、何梅、刘艳们塑造为成功的女强人,没有将阿三、王锁们设计为最终变身大老板的情节安排中,我们感受到作家对人事和世事变迁的准确预见。柯天国的作品同样写到了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是谁呢?风流巷里的陈家常、《锁王》里的宋大炮。陈家常油滑狡诈、心狠手辣,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所以能屡屡化险为夷,竟然“空手套白狼”,钱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大。总体来说,柯天国的作品“实写”有余,而“虚写”不足,但《风流巷》的最后一章却是例外。小说写风流巷里的每个人都在做梦,六婶梦回她的光荣时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时她担任战斗队队长,胸前戴着大红花,载歌载舞;五叔公梦见自己发大财;而真正发了横财的陈家常,却是梦见自己做了大官,当了市长;最不祥的梦是张芸的,她做的砖砌成的金碧辉煌的宫殿最后却倒塌了。经过一番风雨,六婶觉得风流巷不对劲,无端生了许多晦气事,张芸的旅店关门了,“舞王”王大哥丢掉了自己的位子,而五叔公跌断了右腿……小说到了这里轻轻一转,语含讽刺地说这是妇人之见,她只看到风流巷的背时倒运,却没有看到也有人“发”,她做噩梦的那天,风流巷里鞭炮长鸣,贺客络绎不绝,陈家常的生意换了更高更大的招牌,“南方横向发展贸易中心”,为风流巷添辉加彩。倒是五叔公看透世事,知道命也重要钱也重要,而“鞭炮一响,不知又是哪家倒霉,哪个发财了”!在那个鼓吹“把蛋糕做大”的时代,能够认识到那一切背后其实是“零和博弈”,五叔公真可谓空谷足音、醍醐灌顶。
柯天国所要处理的题材很容易走向其他方向,如果要讨好那些喜欢“生活的主流”和“事物的发展方向”的评论,他可以将其处理为英雄的、浪漫的或传奇的题材与故事;如果要讨好猎奇的读者,他可以将其处理为当时已开始流行的奇闻轶事、曲折离奇的凶杀或香艳的色情读物。他坚持将自己的作品对准平凡的、当代的、日常的现实,并且按生活的实际状况来进行书写,既不美化现实,也不将其扭曲。这是非常困难的书写,读者总是很难满足,悲观者觉得他描绘得不够深刻,乐观者又觉得他暴露太多,过于黑暗。其实柯天国的不足并非在这些地方,他对现实的描写和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如前所言,他的作品常常显得“写实”多,“写虚”少,也就是对环境和人物行动描绘多,情节也充实,但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作品的内在观念缺乏经营,主题与题材不相配。有些作品,如果他再加剪裁提炼,将会大大提升其文学品质。如《少妇梦》,这是当代中国较早涉及所谓“二奶”题材的作品,现在已经铺天盖地了。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刘金龙为了继续承包酒楼,想用钱收买主事者不成,提出让白雪牺牲色相拉其下水,白雪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不但严词拒绝,还在派出所检举了刘金龙。对照今天“反腐不能光靠二奶”的现实,不能不说这是不可多得的先见之明。但作品在这里再一次将事情的转化奠基在机缘巧合上,损害了小说的逻辑结构和人物的性格丰富性。而作品对白雪之所以愿做刘金龙的情妇的缘由的解释,同样处理得有些简单仓促。白雪的困境和挣扎,作品都有涉及,但始终给人浅尝辄止的感觉。这确实是让人遗憾的事。
几十年的时间,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但也有许多事情仍在延续。柯天国笔下的“待业青年”,现在的年轻人已不知其为何物,他们面对的是“下岗”“待岗”,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自由职业者。”名字变了,境况没变。不过,其所处的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当时存在的空间已经消失了,或者被大规模大面积地挤占压缩了。今天,我们只能在文学作品中重逢那些消失的空间,唤起我们沉睡的记忆,这也就是“写实”的小说的价值所在吧。
【注释】
①王晓明:《从建筑到广告》,载王晓明、陈清侨编:《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86—1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