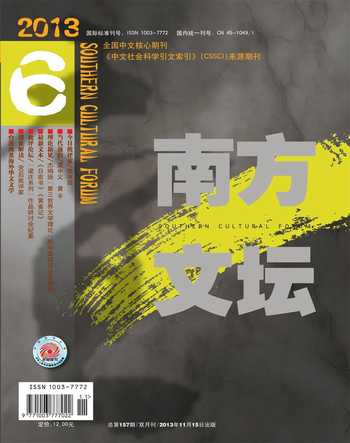童年时光的魅影
2013-04-29方卫平
一、童年、回忆与往昔时光
《格子的时光书》是一本触及童年时间感的小说,也是一本从作家自己的童年记忆里生长起来的小说。
20世纪70年代末,女孩格子在她十二岁的燠热夏天里游荡,时间的影子被年少的感官拉得如此之长,望不到尽头。这静静的时间里留纳了名为芦荻镇的水乡小镇里不为人知的风情与轶事,也见证了少年格子和老梅、瘦猴、荷花、小胖们的友情。小说主要透过格子十二岁的视角来打量这个夏天里小镇上发生的一切:大表哥参加对越作战的“阵亡”消息所引发的骚动,梅家二姐梅香的忽然“疯癫”所带来的谜团,以及在解开上述谜团的过程中,从少年神秘的揣想里逐渐显影的古老庵堂,经由人的认可、采撷而变得鲜活起来的山间药草等。格子努力想把这些繁杂的印象安放入她自己的生活图式里,她在整理,在理解,更在吸收,十二岁的身体和心灵就这样默默地成长着。
但小说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十二岁的格子的生活视角和经验;在叙述者关于格子十二岁的生活的讲述中,时时叠加着成年后的格子回望童年的感觉、情绪与领悟。作品中遍布各处的“多年后”“许多年后”,提醒着我们这个十二岁的夏天属于发生在过往时间里的童年往事,或者说,它是一件与回忆有关的事物。
这一点很重要。小说中间有一章特殊的“插叙”,讲述长大后远离故乡并且“已是大记者”的格子应姐姐的急约回到芦荻镇,“给家乡的孩子讲一堂课”。孩子们的课堂和对话勾起了格子对童年的回忆,她“沉浸在往昔的世界里,这么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以这样一种方式,深情回望她的童年,童年里漫长的等待、希冀……种种不自知的懵懂与迷惑,寂寞与忧伤”①。然而,从小说的情节来看,格子十二岁的经验似乎难以与“寂寞与忧伤”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就格子在这个夏天里的所作所为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些“野”的女孩如何在生活现实和自己的想象编织而成的罗网中不知疲倦地游走,波澜不惊的小镇生活因为她的充满热情的好奇和冲撞,居然变得有些丰富和鲜艳起来。尽管盛夏的溽热烘托了生活的无聊,但这份无聊感恰恰反衬出格子的行动力。面对这样一种童年生活的姿态,说格子的十二岁是“寂寞和忧伤”的,显然并不合宜。
然而,在小说的叙事间,的确常常流动着一种特殊的伤感,它有时是少年格子的当下生活体验,但更多的时候属于一种回忆的气味,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回望自己童年时光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氛围。小说中,这份感伤的情绪最为浓郁的时刻,是成年后的格子在返回家乡的寻索中、在为孩子们讲课的大教室里、在异乡的宾馆忆起自己的童年,“以一颗成熟的心重归自己童年时代的视角看世界时”②。不妨说,这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感伤——当我们隔着岁月的距离遥想童年时,那段充满新鲜感却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影像,总是伴随着格子体验过的那种“美好而又失落的心情”。
正是在这里,小说触及了童年时间美感的某种本质。毫无疑问,童年的时间有它自己独立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当下的,而不是由成年生活的目的来决定的。但童年最重要的时间意义,却需要经过成年时间的发酵,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成年格子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十二岁的格子提供了另一面镜子,透过这两种视角的交织,我们既看到了童年时代的许多“大事”在事实上的微不足道,也看到了这种微不足道投映在童年视线中的巨大魅影。正如同一条故乡的小街,在童年和成年的格子眼中,有着全然不同的模样:“多年后,当她终于以长大了的姿态回看童年的小镇时,她不无惊异: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吗?如此破败和陈旧。尤其那条长长的、市声杂沓的小街,怎么就突然变短了。”在这里,“长”与“短”本身都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是,当成年后的格子站在“短”的视点上,回过头去重温那段“漫长”的少年时光时,她看到了这段时光的局限,也看到了这种局限的意义。由此,格子与她十二岁的那个夏天的道别,既带着告别一个世界的忧郁(“山冈上草木葱茏依旧,可再来一次这样的玩乐却是不可能了”③),又蕴含了打开一个世界的欣悦(“她似乎比任何时刻都站得高、看得远”④)。这两种感觉的交叠赋予了作家笔下的童年时间以一种清澈而又真实的生活质地,更传递出一种因其自然而复杂、也因其复杂而自然的少年成长体味。它使得小说的叙事尽管不以情节上的引人入胜见长,却因其把握住了这一微妙的时间体验,哪怕是写童年生活中的各种细小事件,令我们读来也时有甘美的回味。
这也是《格子的时光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儿童小说的写作中,要准确地把握住这一微妙的童年时间感觉,殊不容易。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理由相信,这种感觉的抵达,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作家调动了她自己最切身的童年回忆和内心经验——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印证着我的这一揣测。或许,唯有深入我们自己灵魂的童年往昔,才有可能滋养这种生动的写作感觉。也只有这样的切身经验,才能从这一普遍的童年乡愁里,发现独一无二的诗的境界。
二、从怀旧的乡愁到“非日常”的诗学
童年与成年视角的交叠,在小说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乡愁,进而赋予了小说的叙事以一种怀旧的美感。这种美感在很大程度上点亮了小说的有些散文化的情节。同时,成年视角烘托下的童年视角,也为小说的故事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毫无疑问,《格子的时光书》是一部叙写特定年代里童年日常生活的作品。作者并没有刻意夸大或修饰这种日常性。小说里,格子在十二岁的这个夏天所经历的一切,如果平铺直叙的话,即便以孩子的眼光来看,或许也过于平淡了些。小说中最具悬念感的梅家二姐梅香的疯癫事件,揭晓后也不过是一桩普通的乡间家庭龃龉,而缺乏我们期待中的那种传奇性。然而,童年视角本身却令这些最平常的生活事件焕发出某种“非日常”的诗意。小说开篇前,作者援引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彭塔力斯的话:
对童年的依恋,与其说它是对一段已经过去时间的乡愁,不如说是被这个非日常所吸引。它把我们维系在虚构的领域,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
这里的“非日常”,并非是指对日常生活的离弃或否定,而是指对日常生活的某种“陌生化”观看。它也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在童年时代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盛,雨更滂霈,天更苍蔚,而且每个人都有趣得要命。”⑤童年的“非日常”的目光,总是善于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之下发现各种新鲜、奇妙的内容。
这也正是十二岁的格子眼中的世界。在有些百无聊赖的夏天里,她的眼睛搜寻着任何令人兴奋的对象,同时也为自己“发明”着这样的对象。河面上偶尔划过的普通的小船儿,也能引发少年格子的无限遐想:“她看着小船儿缓缓驶去,脑袋里浮想联翩,她想象自己随着小船一路漂……有一回她看到一个半大婴孩趴在船舱里,半个身子伏在甲板上,天气很热,小孩儿只罩着件水红肚兜,她假想这个小婴孩就是她自己,出生在船上,船就是她的世界……”⑥这个年龄的格子,自然不会放过生活中任何一个可供想象力生发的支点。发生在好朋友老梅家的变故,正是这样进入了格子的视线。她想要探知梅香“发疯”的真相,这一探知的愿望甚至进入到了她的梦中。对大人们而言,老梅家的变故不过是寻常的家庭事务,对十二岁的格子来说,梅香的遭遇则意味着一个亟待解开的秘密。这又把格子带向了名为恩养堂的尼姑庵的秘密。后一个秘密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精神引导角色,因为正是在进入恩养堂之后,“小猢狲”般的格子体会到了她所从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平和、宁静、优雅的世界。透过少年格子的眼睛,庵堂的日常性退到了生活的背后,它的不同寻常的静穆和庄严,则在少年的敏感和想象里被放大了。
确切地说,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主要不是通过它的题材或结构体现出来的,而是由这种“非日常”的感觉支撑而成。透过童年的感官,普通的生活被点染上了故事的质地。类似的生活惊奇感,是童年时代的精神标志之一。它也暗示着童年天然的发明故事的能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惊奇的能力会从我们的感官中逐渐退位。譬如小说里,仅仅是多过了一个夏天,格子就感叹地发现:“那些曾经占据了格子整个的身心的人和事,曾经鼓动得她睡不着觉、连梦里也怀着探看的兴致的秘密往事,如今竟遥远得仿佛不曾存在过!”⑦与此相应地,小说的故事到此也走向了尾声。随着格子的成长,童年的某种“非日常”的内在感官,似乎永远地闭合了。这一处理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童年叙事的乡愁感。
然而,作者对此并非简单地叹惋。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的成长是由非日常的惊奇日渐走向日常生活的理性的过程,但我们终会发现,那看似消逝了的童年“非日常”的诗意,始终营养着我们接下去的日常生活。正如对于成年后的格子而言,童年的时光虽已逝去,却以另外的方式永远地活在自己体内,“原来,她曾经以为的、不会再来的童年始终是存在着的。”⑧这使得小说对于童年乡愁感的表现,没有仅仅停留在一种“非日常”的怀旧上,而是写出了这种怀旧的诗意与日常生活的诗意之间的积极关联。这一关联尤其体现在小说的下卷,在这里,前来镇长家做客的大女孩荷花,最后促成了格子的成长。作为成人世界的准代表,漂亮、活泼、知性的荷花是格子的偶像,她教格子学着以理性的成熟理解她自己的梦境,理解梅香的疯癫,理解自然和生活的另一种更内在、更丰厚的美。在荷花的引领下,格子逐渐走出了童年眼中的魔魅世界,走向了更为宽广的日常生活。很多年后,长大后的格子慢慢领会到了“日常生活才是美的中心”⑨的道理,但这一领悟的伏笔,实际上在格子十二岁的那个夏天就已经埋下了。
这样,小说对于童年的“非日常”视角和生活的书写,就成为了一种具有精神生长性的书写。这体现了小说作者对于童年日常生活的尊重。我们对此理应给予充分的认可。然而,如何将这种指向日常化的书写与儿童小说的故事艺术恰当地结合,无疑还是一个充满困难的任务。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在少年格子的故事里,正是上述日常化的笔墨,将小说的情节过早地带离了故事的索道,而走向了一种过于诗化的境地。
对于长篇儿童小说的写作来说,这样的诗化处理,也可能会导致小说艺术层面的另一些问题。
三、诗与小说的距离
《格子的时光书》起始于一个暖水瓶倒地炸开时的“忧伤碎裂声”,按照作者的自述,这个声音似乎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而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碎裂的状态和声音,似乎也预言了小说的某种基本情节形态。整部小说几乎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而是由各种零碎的日常事件串联在一起,其中最具故事的悬念性和持续性的,大概是梅香发疯的秘密。除此之外的许多分情节,更像是从格子童年的树干上随意伸展出来的旁枝,它们以一种比较散漫的方式出现在格子十二岁的夏天里,有些叙述只是一晃而过,并未真正参与到小说叙事的有机体中。
比如有关格子父亲身世的小插曲。格子是在初入恩养堂时,由庵堂的来历联想到了父亲从这里被领养的可能,这个猜测后来也在饭桌上得到了父亲的默认。这样一个富于叙事潜力的细节,在小说中却被处理得云淡风轻,它的出现既没有对格子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也没有参与到此后的情节建构中。再如老梅跟着父亲去县城悄悄卖掉祖传的座钟和石鸟一节,小说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石鸟的“神奇”:“里头一只石雕的画眉鸟能迎风啾啾鸣唱”,“别的鸟儿是在空间飞翔,而这只石鸟永远在时间中翱翔。时间拍打着它的双翼,拍打了双翼之后,向后方流逝了”。然而,在老梅短暂的感叹之后,这只神奇的石鸟也再无踪迹。有关大表哥的叙述,算是小说中相对周全的一个分支线索,但它与主线索之间仍然缺乏必要的关联。小说起首部分,大表哥阵亡的流言引发了小镇上的骚动,也搅动着格子十二岁的夏天。之后,我们从格子的断续回忆中得知了这位这位从未现身的大表哥的若干往事。故事最后,格子家人收到了大表哥从医院写来的平安信,阵亡的流言也不告自破。显然,这个分支情节为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时代背景,它也是格子这个夏天里的一大系念。然而,从小说的整体来看,这个线索本身始终像飘荡在格子天空上方的一小片阴云一样,没有落实成为小说叙事必要的构成部分,或者说,除了作为背景之外,它并没有为小说叙事的推进提供特殊的动力。它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的许多事情那样,自然地发生,又自然地结束了。小说后卷中,格子与荷花、小胖和恩养堂小尼姑的结识和交往也是如此。
我在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想到了我们生活着的现实。谁能说我们经历过的一切时间和事件,必然有着前后的因果与耦合?相反,很多时候,它们不过像随水漂浮的枝叶那样,偶然经过我们的生活,没有来历,也没有既定的目的。除了匆匆的一面,它不与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发生交集。或者说,现实生活本身是不严密的。《格子的时光书》写出了生活的这种不严密感,从格子大表哥的“阵亡”、老梅二姐的发疯到瘦猴母亲的失踪等事件,都留下了生活本身的散漫痕迹。尤其是到了小说下卷,其叙事几乎完全循着生活的自发状态向前推进,对于事物的叹喟和感悟也愈来愈越过对于事件的叙述,成为了小说叙事的主要推动力。
在这一风格的影响下,小说的情节和语言均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倾向。有关童年阅读的感慨、思考与探讨,正是以这样一种诗化的方式出现在了小说的叙述流中。格子对于阅读的特殊感觉,最初是被大表哥屋里的一架子书给唤醒的。在小说一整章的“插叙”中,童年时代的阅读成为了成年后的格子与家乡的孩子们探讨的核心话题,尽管这个话题与小说的情节之间,的确不存在太多逻辑上的勾连——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插叙”多少显得累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又与小说所努力传递的那种童年诗意有关:“有些东西不必说出,它自身就有一种力量,或者说品质,无论在多么喑哑的环境下,它都能令你的身体一下子绽开放出那种光明嘹亮的气质!——比如书。”⑩在这里,书成为了点亮童年诗意的一个符号,实际上,后来逐渐启蒙了少年格子的精神世界的恩养堂、佛经、药草等意象,都可以视作是那最初击中了格子心灵的一架子书的符号衍生,它们共属于同一个诗的脉络。
然而,由于过多地被这样的诗意书写所拖滞,小说愈写到后面,其故事性的气氛愈显稀薄。如果说作品的上篇对于故事本身还保持着某种自觉的关注,那么其下篇则越来越像一汪散淡的清水,虽然也具观赏性,却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和统摄力的核心,将小说放开去的各个叙述支脉紧紧收纳在一处。
这当然也是儿童小说的一种写法,但这却不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种写法。关于小说的艺术,我一直信奉契诃夫的名言:如果你在作品开头时描写到客厅墙上挂着一把猎枪,那么在故事结束之前,这把猎枪就一定要用上。美国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和经验时,同样引述并强调了相近的舞台剧规则:“如果第一幕中壁炉上摆着一支枪,第三幕里枪就得开火。”11就此而言,在《格子的时光书》中,有太多“不开火的枪”摊开在小说的文本之间,其中有不少是小说的闲笔、余笔,它们可以为小说的故事助兴,却永远不可能替代故事本身。而小说的魅力,归根结底在于它的故事。
面对一部书写童年时光的儿童小说,我期待着从作品中读到对于这一时间话题的更为小说化的处理。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期待,是因为《格子的时光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儿童小说,而不是像许多冠名长篇的作品那样,实际上是一批短篇故事的组合。这样的作品,是我们可以真正拿来探讨儿童文学的长篇艺术的作品。因此,我所表达的这些感想,其实也是对当代儿童小说写作的一种期待。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⑩陆梅:《格子的时光书》,93、8、192、193、14、192—193、15、113、28页,接力出版社2013年版。
⑤K.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李时、薛非译,26页,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11斯蒂芬·金:《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张坤译,2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YJA7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