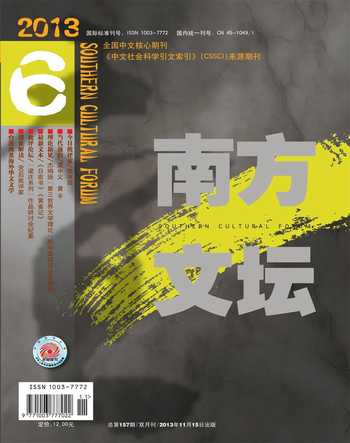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德”“才”之间:才女主体性的建构
2013-04-29陈树萍
在三十余年的写作中,王安忆始终保持着变动的力量,在思想与日常之间寻求着突破的可能,一次次地超越自己,以致成为现时代上海文学的代言人。从“三恋”的锐意性爱到《叔叔的故事》营造精神之塔,再到《长恨歌》反观急遽变换的上海史,从《上种红菱下种藕》描摹小女儿的天真到《启蒙时代》精雕一代青年思想漫游者的精神刻痕,再到《天香》对于史前上海的逼真描绘,王安忆的文学世界蓬勃而大气,一个现代都市上海或是一个偏远乡村远远不能承载她的想象。在其上海叙事中,王安忆一步步地以断代书写方式,建构了这座城市的文明史。就此而言,王安忆表现出了与1930年代茅盾同样的企图,同时也有别于1940年代的张爱玲。而与此前文本不同的是,《天香》直接楔入明末清初,成为上海叙事中远远荡开去的一笔:在一片繁花似锦的江南温柔地中呈现上海,从而彻底抹去了百年来上海叙事中挥之不去的殖民阴影。现代视野中的上海总是与因殖民而摩登的景象无法分开,《天香》则在一个完全没有殖民的时空里重新勾勒上海日常印象,还原了长期被忽略的原本富庶而健康的前世上海。更为难得的是,《天香》用反传奇的方式为晚明上海,为昔日闺秀做了一次话本传奇,从而为中国的才女文化传统做了一次了不起的确认,以对“才女”主体性的建构为已然远去的中国传统女性注入生命的灵光。王安忆则借此向一代才女遥遥致意。
一、园:男性的撤退/女性的滋养
国色本天香,天香亦倾国。王安忆笔下的“天香”既非名花亦非佳人,却是晚明上海的一座名园。“要写明末文人故事,几乎不能不写其时的名园,因为许多故事本以大小园林为敷演之所,也赖有这一种特殊的背景而展开。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就写到了陆氏南园、杞园、三老园、不系园等。”①与曹雪芹的大观园一样,申氏天香园内不仅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更兼有诸多裙钗粉黛。但与曹雪芹不同的是,王安忆既无意去书写家族盛衰史,亦无意去描摹园内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却心心念念于私家园林文化意味的探索。
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晚明社会风气一变早期的简单质朴而走向奢华之途,拥有一座园林成为彼时诸多上流人物的共同向往。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私家园林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人生志趣、情味的传递。就士大夫阶层的志业而言,“园林”恰好与“朝堂”构成人生天平的两极。朝堂是男性建功立业的公共场域,风险与机遇并存,自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私家园林则是男性从朝堂撤退下来的修养栖息之地。由于儒家文化强调男/女家庭事务分工的内外之别,男性往往在外忙于建功立业,而无暇也无意处理家庭杂务或从事家庭生产。在此意义上,造园既是男性立业成功的标志之一,也是他们对家庭事务的最大贡献之一。关于私家园林的繁华盛景与奢豪气派,清人叶梦珠的一段描述可作参照:
汇海豪奢成习,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选胜,务在轶群,不同侪偶。园有佳桃,不减王戎之李;糟蔬佐酒,有逾末下盐豉。家姬刺绣,巧夺天工;座客弹筝,歌令云遏。②
叶氏笔下之园乃指蜚声海内外的上海顾氏露香园,正是《天香》原型之园。据史料记载,露香园主人顾名世,字应夫,上海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尚宝司丞。名世曾筑园于今九亩地露香园路,穿池得一石,有赵文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园③。上述引文中所提汇海便是顾绣家族的第二代顾箕英。王安忆原本就是因对顾绣的好奇而激发出写作欲望,所以《天香》以上海顾氏家族为蓝本实在合适不过。凭着对顾绣家族及晚明时代风气的稔熟,那个一度兴盛过的“露香园”逐渐在小说中获得核心地位。惯于在纪实与虚构中穿针引线游龙戏凤的王安忆既按耐不住小说家虚构的天性,又“生怕落入纪实的窠臼”④,忍不住“错接”起来。“错接”恰是阿暆的见识之一:“稻粱秫麦,瓜果蔬菜,非要错接才能生良种,然而,一次错接,必要再再错接,一旦停住,即刻返回,比原初还不如,好比那一句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302页)王安忆也借势一路错接下去,通过对顾绣历史与人物的重新设置与叙述,排演出天香园的虚虚实实。于是,叶梦珠的描述不经意间就成了天香园无尽奢华的底本。
与顾绣一样,小说中的天香园绣实乃大家闺秀之绣。大家闺秀缘何刺绣?又如何成就了一种艺术?故事虽然重要,但为天香园绣寻觅、建造一个好处所则至为关键。王安忆拔地而起造出了一座漂亮、雅致而又具有休闲气质的园林,刺绣则附着于此,园、绣因此相得益彰。
王安忆的匠心独具在于以“申”姓代替“顾”姓。本是申家(顾家)在园子中挖出“露香池”石并以之命名园子,王安忆将之错接给彭家,说是彭家在园子挖出了一块刻有“愉”字的石头,因而有“愉园”之称谓。而申家“天香园”却从一片芳香四溢的桃园得来,远远地招引着天香园绣的核心锻造者——杭城希昭抹着龙涎香于归天香园。“天香”之妙便在于“天然”。在隐蔽的层面上,人与物相辅相成,等待着相互贯通的良机。如此偷梁换柱李代桃僵显然意在扩大私家园林的文化品格,也显示出了写作者本人的大境界与大格局,即名为写园,意在写城。小说也因而有了城市寓言之意⑤。
原本造园是为颐养性情,换在申家则是对喜庆排场的热衷,这其中既有着不计利害的一派天真,又有着真正愉悦身心之功用。无论是“一夜莲花”还是“三月雪”;制桃酱抑或制墨等等,不过是一家老小的热闹豪奢性情而已。只有在无数的奢华之后,天香园绣这一最为奢侈的艺术才能得以诞生。园子与绣艺之间方才能默契相关,充分演绎进/退、显/隐、速朽/流传的变换。
申明世从仕途隐退居于天香园的举措,成了申家从此无意科举仕途的标志。儿孙虽然聪慧过人,却无一人用心于仕途,完全是一副任性而活的人生态度。一个从官场隐退的家长带着一群完全与仕途无关的青年男性继承人就像钢架结构一般,构建了天香园内的申氏家族谱系。但问题随之而来:在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如果放弃了在外博取仕途,又将何为?以何为生?一直仰仗祖产与申明世为官时的积累吗?显然,这终究会有坐吃山空之时。就小说而言,无意仕途的申家人还很缺乏商业实绩。柯海经常出门远游,与朋友交往甚多,但最值得提起的收获就是纳妾以及为阿潜看好希昭之事。这样说来,柯海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天香园引进奇女子。
男人从朝堂退隐到天香园中,又娶进各式各样的女子,来自不同人家的妻妾们则借着刺绣述说无限心事。钟灵毓秀的刺绣就不再仅仅是器物,而是跃升为传递心声的艺术样式。它将与诗文、绘画一样具有穿透历史的力量。如果说“天香园”是男人所创的家庭实业,那么,刺绣就是女性提升天香园文化资本的重要方式。天香园的女子奇就奇在:在男人无法再作为依靠之时,女人不是情天恨海枉自嗟叹,而是撑起一片天空,既为整个家族遮挡风雨,也织就了女性的独立人生。
在传统诗文中,“芜城”与“废园”是两个常常并置的意象,但园之废显然更为寻常:“城之芜通常在大破坏中,而园的废,则升平世界也时有发生——因了财产易主,因了人事代谢,因了不那么戏剧性的个人事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如中世纪欧洲的坚固的城堡,而是古代中国不设防的园林。”⑥一不留神,申家的天香园就显出了破败的神色。而锦心一片的绣品穿越速朽的厅堂、易凋的花草,抵达无尽的后世。
彻底从政治权力结构中撤退的男人栖息于天香园,看似不求上进的举措却滋养了女性的才能。为女性营造艺术世界并催促其孽变是申家男人的最大贡献。高彦颐发现,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的发展,是与这一地区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相辅相成的,它发达的先决条件是有相当数量的受教育女性和支持她们创作的男性⑦。闲居在天香园的申家男子将自觉地担当起将内闱绣品推广到艺术市场的媒介责任,在不违背传统儒家文化教义的情势下,完成由“内”到“外”的双向交流。如果说,柯海先将各式奇女子引进天香园,以至于她们用家庭结社的方式组成绣艺班底,后又在银两短缺之际以希昭的人物画绣换得老父珍异寿材,无奈中催促了绣品的商业化;那么,阿潜则是难得的专业伴侣。碍于儒家男女之别,阿潜去向董其昌学习书画,回家后再转授希昭,希昭由此悟得真谛,将绣品与松江画派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松江文人画派宗旨在针黹领域内的延伸⑧。
《天香》的潜在意义就此呈现:正因为男性对宏图大业的忽视,女性的闺阁事业才格外令人赞叹。但似乎也在证实:只有在男性休闲文化(园林)衰落的同时,女性文化(刺绣)才有了进一步崛起并为外界承认的空间。不过饶有兴味的是,男性在家族中形象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消失,因女性正是经由男性引入园林,从而得以构建自身。
二、自持与妥协:才女的基本立场
沐浴着现代光辉的人们在回望前面无数世代的女性时,常常因为历史后来者的优势地位而情不自禁地产生笼统的悲悯之情,悲叹传统女性不能自主的命运。对于传统闺秀,张爱玲一言刻骨:“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⑨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封建制自然会产生极为凌厉的批判冲动,更会启发后来者对女性权利的坚定主张,但亦会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在用“悒郁”概括了传统女性之后,我们也许会忘记那些生命本身的能动与变通。
在论及明清之际的才女时,高彦颐发现简单化地将妇女都置于儒家文化的受害者的位置是危险的,高氏认为她们创造了“才女文化”:“这一才女文化的产生,固然受阶级及社会性别所局限,无法在大众社会中广泛流传,但它肯定不是隔绝的、单色的或是贫乏的。”才女皆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上流阶层,因此才女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文化的存在,正彰显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优势。“她们是在体制之间,灵活运用既有的资源、趣味自己争取更大生存空间。她们不是儒家文化权力运作的受害者,而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⑩
大量史料证明,明清是女诗人辈出的时代:“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专擅诗词的扫眉才子,仅以明清两朝而论,刊刻所著者即达三千五百人之多。”11才女从事诗词创作并有意识地结集出版这一行为在明清两代惹来很多议论,毁誉交加。但女性将刺绣变成展示才华的艺术品这一举措却令天下才子折服。天香园众女性并不沉迷于诗词创作,而是巧妙地将纯粹女性化的日常技术升格为艺术,在回避了儒家规范中的对女性“内言不出阃外”的道德要求之时又将刺绣作为自我书写的纯粹的女性方式。这“对构建女子特性有着深远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诗歌才华的提高相似,作为艺术的刺绣的发展,成了上层女子特性中的一个属性,它表现的是一块于儒家妇工原始含义之外的处女地”12。
天香园绣之所以能升华为艺术的关键点是完美技术与卓绝才情在刚刚好的时间与地点相遇相融,“情殇”则是女红从技术向艺术飞升的催化剂。天香园中的第一个值得书写的相遇发生在小绸、闵女儿与镇海媳妇之间。正如柯海暗自惊异的那样,妻妾原本应该是冤家,却在镇海媳妇的穿梭之中渐渐有了交谊,而小绸与镇海媳妇更是有着刎颈之交。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寻常世道中不可思议的妻妾情、妯娌谊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出身世家的小绸对柯海一往情深,岂能容得丈夫纳妾?于是愤然与丈夫决裂。由璇玑图便可知,小绸的热烈相思与刻骨怨恨原本就是一面镜子的两面。她用自我禁锢的方式批判着柯海的负心,闵女儿自然就是罪证。镇海媳妇既无小绸的诗画才情,也无闵女儿精美的绣艺,却以锦心绣口穿梭出这对妻妾的默默之情,而生育之危更将她与小绸之间的妯娌情谊上升至以命相共的义胆衷肠:“她们想起那临危时的一幕,两人互诉自己的乳名,好比是换帖子的结拜兄弟。自后,再没有重提过,是害羞,也是心酸。”(第73页)
如果说,小绸与丈夫绝交是在声张爱情平等忠贞的诉求(这在视纳妾为当然的社会中自然显得出格),那么,与镇海媳妇间的互告乳名就有着临危诉说女性隐秘历史的意思。在儒家礼制中,女性出嫁之后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身份地位因丈夫而决定。所以,女性的乳名就与其女儿时光一样都属于女性的私密历史。小绸曾告知丈夫乳名,便是含有将全部秘密托付之意。从对丈夫的高期待与大伤心转到与镇海媳妇的割头刎颈之情,小绸的自主意识得到了充分锻造,在硬生生地拔除夫妻相守的爱情理想之后,她开始接纳外部的女性世界,包括闵女儿。闵女儿则从对天命的信仰中感觉到女性共通的困苦,直觉到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在由男人做决定的婚姻中,妻、妾都是受伤者。
她是在乎姐姐的,大约因为姐姐和她是一样的人。不是说她能和姐姐比,无论家世、身份、人品、才智,她自知都及不上,但隐约中有一桩相仿佛,那就是命。男人纳妾,总归有薄幸的意思,闵女儿虽然是那个被纳的人,但从来没有得到柯海半颗真心。所以,她们其实是一样的。……假如姐姐要来和自己好,她就和姐姐好!(第88页)
一夫多妻制虽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常见模式,但并非所有的女性都能安之若素。小绸与闵女儿构成了两个典型态度:小绸绝不宽恕丈夫,闵女儿则消极应对丈夫,转而向大妻小绸寻求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情谊。就此而言,柯海所遭遇的妻妾一心的尴尬是一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女性意识。经过种种交锋与解铃之后,小绸把诗书融入闵女儿的绣艺中。正如蚌病成珠一样,三位女性的才与情凝结出艺术品的天香园绣。
天香园绣的另一个值得纪念的节点是沈希昭从杭州嫁入上海申家,将闵和小绸的长处融于一身,以绣作诗书,集天香园绣之大成,让天香园绣更上层楼,成为难得的高档艺术品。有着男子般心气的希昭并不以天香园绣为尊,甚至要求向香光居士学画。希昭对书画的重视以及对刺绣的排斥都在说明一点:她很自觉地接受了儒家对男女事业分工以及高低之别的判断。她已经将这套规则自觉地内化在个人的观念中。这时早已将生命的情感体悟化在了一针一线中的小绸的点拨就尤为重要。
小绸不免得意,说:……天香园绣可是以针线比笔墨,其实,与书画同为一理,一是笔锋,一是针尖。说到究竟,就是一个“描”字,笔以墨描,针以线描,有过之而无不及。小绸这话既是说给众人听,更是说给希昭听,知道她一心只在书画上,又将书画看得比绣高,骨子里是男儿的心气。(第224页)
小绸在经历情殇之后曾经创作璇玑图,但并未到达她设想的读者手中,而她渐渐涉入原本并不擅长的刺绣。这意味着小绸从对“男性凝视”的期待中转身并找到了一个女性独立自主的领域,一个自我诉说的最佳方式。这时的小绸并不需要用刺绣去换取金钱,因此其独立意识更为鲜明。冰雪聪明的希昭豁然顿悟。阿潜的离家出走让希昭对于女性历史地位有了清醒的认知,她踏进绣阁,寻求其他女性的慰藉,尤其是蕙兰的真心相伴。而蕙兰对其才情的肯定直指内心隐衷。
希昭的女性个体认知与顾绣代表人物韩希孟有着相似之处。“由于身处上层阶级妇女较具游走空间的晚明,文学、绘画各方面都有众多才女突破既有限制、大放异彩,韩希孟方能以艺术来成就其女性自我意识之追求与肯定。而这也可以说是女性在文学与绘画之外的另类发声途径。”韩希孟曾经绣过一幅《补衮图》,画面中女子端坐绣衣,但并非绣制普通衣裳,而是在补衮。这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谁说刺绣就是卑微之事?女性一样从事着极具分量的大事业。董其昌显然领会了她的苦心,因此在对页题赞:“龙衮煌煌,不缺何补。我后之章,天孙是组。璀璨五丝,照耀千古。娈兮彼姝,实姿藻黼。”这幅刺绣更被认为是韩希孟的自画像。13
天香园众女性的个体意识多有变化,天香园绣的落款便是一突出表征。落款既是女红独立价值的宣言,亦是女性徘徊在“独立”与“从众”之间的结果。在小绸等人的绣艺轰动上海引起民间模仿之后,生意人阮郎教柯海在绣品上留下落款以免事端。柯海拟名为“天香园绣”,因不敢与小绸明言,便曲折过话,小绸明知是柯海的意思,将错就错,于是所有的绣品上皆落下“天香园绣”的署名。小绸对丈夫所拟名字的默认正是她与外界妥协的步骤之一。希昭则更为强调“武陵绣史”的个人身份,初初绣出倪元林的山水小品,落款便是自己拟的名——武陵绣史。但最终出于对众人情意的尊重,在绣品上加署“天香园”。 相较于早期小绸的骄傲任性,希昭要含蓄内敛许多,同时也更有韧劲,其个体认知的意义也更为明确。阿潜离家出走,希昭绣人物四开寄寓心中隐痛,第一幅就是《昭君出塞》,负气与心志兼而有之。申家小姐蕙兰则与希昭相反,出嫁之后在绣品上落款“天香园绣”引来丈夫张陛不满,丈夫为她另取一名“沧州仙史”,这名字并非要赋予蕙兰独立的意志,而是意在强调她已经不是申家天香园中人了。于是,蕙兰的落款就变成七个字“沧州仙史 天香园”。落款的改变传递出个体身份/家族归属之间的较量与妥协。三个女子是三代人,都有着不凡的资质,但都采取了一样的妥协策略,因为适度的妥协远比完全抗拒要明智得多。
对于申家女性而言,刺绣是其生命体验方式。通过刺绣,女性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展开并得到尊重与承认。毋庸否认,无论是小绸还是希昭都是难得的才女,她们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准都相当令人惊奇与满意。明代晚期的上流社会虽已重视女子的教育,将女子的文化素养与娘家的声誉连接起来,但显然没有培养反抗传统妇女规范革命者的意图。因此,一个有才华的女子若要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就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她必须能够在“才”与“德”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这样才不至于冒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让自己身心愉悦。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意识转化过程。毕竟,对于“妇德”的强调一直是社会舆论的重点。同样生活在晚明的女诗人沈宜修显然没有天香园女眷的福气:婆婆担心她写诗会妨碍家务,于是对她管教极严,并让婢女监视她是否会偷偷写诗14。而希昭呢?“希昭虽是做母亲的人,却还如同在闺中,概不过问家务。人都说这媳妇被宠坏了。”(第185页)相对而言,天香园中的女性却可以尽心尽力于刺绣,因为这既是女人分内之事,又具有娴雅、贞静的道德象征意义,实在是讨巧至极。
不过,这种在“才”与“德”之间两全或者说是两难的才女主体性,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正因为要两全,女性首先要能接受、认同男性的文化与道德价值判断。如通过对韩希孟绣品《花溪渔隐》的分析,研究者发问:“以韩希孟的女性身份,有何大谈隐居的必要?显然,谈男性文人心目中的隐居,所欲引发的是男性文人的共鸣。这也正是当时女性藉由拟同男性价值观以博取认同赞赏的手段。”15这样一来,妥协的策略是否还能清晰地传递女性的个体诉求就成了疑问。在一份关于女画家陈书的研究中,作者对比了陈书与韩希孟不同的艺术命运,并指出韩希孟的女性意识被忽略了。16
三、纯净典雅的诗学
王安忆的小说中常常有类似国画的“留白”之处。在傅抱石看来,这是中国画家以主观的空间意识表现空间感的创造性手法。这种手法利用虚实对比,通过实景与虚景的联想,通过画面和画幅外的联想,创造出主观意识上的空间感觉,从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7。王安忆小说中的留白不是为了表现空间感,而是以对某一部分的回避得到虚实相生的效果,留白所造成的不是空白,而是在虚与实、显与隐之间营造文本内部的对照18。《天香》纯净、典雅的诗学也由此得到充分的展示。
有必要指出的是,留白式的写作并非《天香》所独有,但在《天香》中最为显著。且以《长恨歌》为例,王安忆极为用心地回避了王琦瑶在“文革”中的遭遇。忠诚守护者程先生在1966年的夏天化作了上海街头的一朵血花,那么,王琦瑶呢?一段空白并不意味着全无事故,只是,“不提也罢!”唯有经历过,才敢省略去这一段不能言的时光。似乎减轻了疼痛感,其实却是催促着王琦瑶赶快抓住最后的艳丽,因为这是再世为人的意思了。否则,她又怎会急忙忙去做一场老少恋的幻梦?那么,当王安忆在进行天香园中的才女叙事时,到底又隐藏了什么?如果真切回到晚明,我们首先会发现王安忆着实回避了女性最为切己的身体经验——缠足。
《天香》中特别强调了两位女性是天足:一是蕙兰的婆婆张夫人,一是张家的女仆李大。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其他闺秀应是裹脚的。张夫人“是巾帼英雄,家中大小事由她做主”。(第255页)张夫人治家直接威慑老少三代男人。李大“不裹脚,衣袖窄窄地系起,腰带扎紧了,做事走路都很利落”。(第280页)主仆二人都很有点强悍之气。李大未裹脚是因劳作需要,自是另当别论。更重要的是这女仆直接秉承女主人的精神气质,成天捉弄比自己年少很多的男仆范小,将夫人威严风范延伸至仆人关系中甚至是将来与范小的夫妻关系中。而在明代,对于一个体面的家庭而言,女性缠足关系到个人与家族名声,更关系到女孩子的婚姻。因为缠足是对女孩子进行身体训导的重要部分,为女性制定的各种闺范通过对脚的束缚落实到身体实处。用现代眼光去看缠足,自然是极为苦痛惨烈之事,亦是很不符合现代人道之事。但是在所谓现代人道主义远未进入中国之时,在男性赏玩女性小脚的时代,女性对自己的小脚大概未必尽如今人所想之可怜可叹。也许在将男性的眼光转化为女性自身的审美观之后,女性也会对小脚产生爱恋之心,而疼痛则被认为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天香》在回避闺秀们的“脚”之时,则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典雅空间,在不纠缠的状态下将大家闺秀的美丽镜像借助读者的想象建立起来。因此,这一留白恰与书写女性的柔美、婉约气质相连。
《天香》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留白就是故意隐蔽申家如何将绣品彻底商品化。在申家必须依赖绣品生活之后,商品化便是水到渠成之事,那么,申家与顾客如何议价?男性无疑是在外部世界中的议价者,但是他们的商业运作被隐而不言。除去阮郎这样既渴慕绣品而又豪奢、讲义气的朋友之外,申家如何对付其他买家?原本尊贵、矜持的闺秀艺术一旦成为走向商品化,其间的生意手段就极为重要。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记载了顾绣价格由高到低的走势,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水准下降的问题19。此外,申家的男性一旦坠入需要依靠刺绣生活的境地,又将有何反应?据载,在顾绣成为顾家的经济来源之后,“顾太学醉后尝拍案,曰:‘吾奈何一旦寄名汝辈十指间,作冷淡生活。”20可以想见,这一留白更与《天香》中的男性叙事相关。在这样一部以三代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男性更多以衬托的方式出现,尽管他们是家族之中的权威人士。因为他们到底不能在绣阁上创造出天香园绣!
在谈及《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的成就时,胡晓真认为“作者不但在史料上采用女性自己的作品,让女性不再只由男性凝视(gaze)来呈现,她更有意识地将妇女置于十八世纪历史的中心地位,揭露男性中心史观的不足之处,由女性角度出发,探索新的历史议题”21。《天香园》所做的亦是相似的工作,将女性置于核心位置,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历史,自然就会呈现出不同向度的叙事。《天香》放弃所谓妻妾之间的妒恨,转而去赞美女性间的深情厚谊并非全是理想化在作怪。
因为要以女性凝视的目光来看天香园以及天香园的落脚地上海,王安忆自觉摒弃了传统家族史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方式。她在呈现天香园外的上海史时采用了简略提示的方法,就好像在水面上留下一些标尺那样,提示着外部的大变动。王安忆自承“落笔前,我先列一张年表,一边是人物的年龄推进和情节发展,另一边是同时间里,发生的国家大事,上海城里以及周遭地区发生的事情。看上去似乎只是背景和气氛, 但实际上却是和故事有潜在的关系”22。可以说,《天香》的轴心是绣阁与女性,但这一轴心并非封闭,而是像天香园中的竹子那样向外延伸、拓展,整个上海的历史也由这个轴心开始由近到远的叙述。离她们越远的事件、人物也就越简略,但并非就完全无关,这就像是安居园子的女性听讲外边的神奇传说一样。将严肃的正史事件融化在以女性生活为中心的日常记忆中,同时被融化的还有男性/女性、阳刚/阴柔、兴/亡等等相对应的序列,于是构成太极般的生生不息。这也是王安忆屡次提及的“生机”,而对于天香园的败落并不十分伤心的理由:在不停的盛/衰、贵族/平民的历史转化中,天香园绣起自民间而又散落民间,终于是处处生机。正是所谓“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23。对文明生命力的信仰让王安忆成了一个不歇不竭的歌者。
【注释】
①⑥赵园:《想象与叙述》,54—56、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居第二》,来新夏点校,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徐蔚南:《顾绣考》,1页,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版。
④22王安忆、钟红明:《访谈〈天香〉》,载《上海文学》2011年第3期。
⑤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⑦⑩1218[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21—23、17—19、185、182—1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⑧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顾绣》,7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⑨张爱玲:《茉莉香片》,见《张爱玲文集》第一卷,54页,安微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美]孙康宜:《明清诗媛与女子才德观》,李奭学译,见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七集》,131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版。
13黄逸芬:《女性、艺术、市场——韩希孟与顾绣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107、68—69页。
14周叙琪:《明清家政观的发展与性别实践》,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9),211页。
15黄逸芬:《女性、艺术、市场——韩希孟与顾绣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48页。
16赖毓芝:《前进与保守的两极——陈书绘画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108—109页。
17傅抱石:《中国画的特点》,见《傅抱石谈国画》,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9[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来新夏点校,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0[清]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一),5页,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
21胡晓真:《导论》,见《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7页,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版。
23[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71页,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
其他未注明者,皆出自王安忆著《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
(陈树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台湾大学访问学者。本文获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基金资助、江苏省首届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