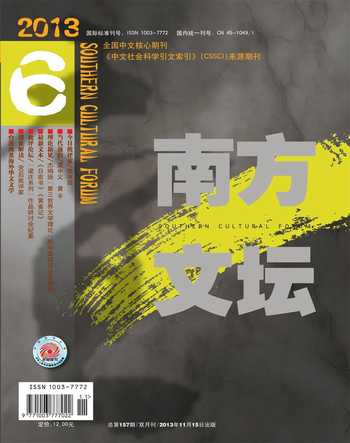80后批评家的历史际遇与机遇
2013-04-29周明全
自去年以来,关于80后批评家难“冒头”的话题,经媒体放大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深究根源时,有论者直指教育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也有慧眼者看出了当下浮躁的社会,对学术研究的回报大不如从前,年轻人在生活重压下,对文学批评了无兴趣。这些诊断无疑是从根本上切入了当下80后批评家难“冒头”的根本病灶。然而,80后批评家难“冒头”,非一因一果那么简单,它由多方面的因素所致,这包括外界环境和自身问题。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当80后作家被媒体、书商炮制、包装,闪亮登场已多年后,作为同龄的80后批评家,至今却依旧寥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社会影响力上衡量,都无法和同辈作家相比。然而,80后批评家也并不像悲观者所言,完全了无声息,绝迹于当下火热的文坛。相反,他们正积极发声,顽强而生。他们中的金理、杨庆祥、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徐刚、李德南等等,正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改写着当下文学批评的版图。
因本人所供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日前正在策划组织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作为策划和统筹者,且同为从事文学批评的80后,这让我对80后评论家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的体悟。
本文试图从80后批评家的整体处境、知识结构,以及对较活跃的几位80后批评家目前所研究的方向和成就作简要介绍,并对这批卓有才识的批评家的未来作一些预测,以便文坛、社会能更全面地了解80后批评家,并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扶植。
一、批评的流变与80后批评家的处境
单纯地讨论80后批评家为何难“冒头”,有点重标轻本,要认清80后批评家当下的处境,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经历的几次较大的流变,甚是必要,这样,能从根本上理解80后批评家们在当下的处境。
(一)当代文学评论的流变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漫长的时间内,文艺批评充当了“思想斗争”、甚至阶级斗争的工具。“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批评的那种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和鉴赏活动,不是最主要的职能;它主要成为体现政党意志的,对作家作品、文学主张和活动进行政治‘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规范确立、实施的保证。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不同程度地对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加以警示。”①这个时期内,主管宣传的官员、作协里的官员、刊物主编等等“文化官员”都成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批评家。比如,周扬、冯雪峰、茅盾等,一直到后来的李希凡、姚文元等人。他们按照最高当局对文学创作的指示精神,以及按意识形态去管理、指导文学创作,享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着创作、甚而是作家的命运。“一旦优越性转化为政治权威,批评对文学更觉高人一等,最后出现拉大旗做虎皮包了自己攻击别人甚至动辄置人死地的棍子批评。”②比如,当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等,都是按照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粗暴批判的实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批评仍然在当代文学制度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由‘文革到‘新时期过渡中,文学批评一方面参与‘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引领新的文艺思潮、推动创作主潮的形成。虽然文学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在近三十年来也有所使用(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历史也因此具有某些复杂性),但由于重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批评更主要的是回到了文学本位。”③粉碎了“四人帮”,改革开放已开启,文学亦迎来了高潮期,虽然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仍然保持着特定的要求,但文学批评选择的自由性和多样性也随之增强。④此一时期,批评家大都是从高校里受过系统学术训练出来的,像吴亮那样,出身工人阶层但才情颇高的批评家并不多见。他们中的很多人随后留在学校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作为批评家,他们指导文学创作的功能逐渐减弱。金理与陈思和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陈思和说:“我觉得一九八〇年代后期批评家开始分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看上去批评家的功能是减弱了,但是其实是走对的,因为减弱了以后,批评家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就凸出来了,他有创作作为依据,本来模糊的、理念化的东西就变得实践化了。”⑤
上世纪90年代,文学界的分化或者说多元化趋势更趋明显,文学制度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摆脱了“思想斗争”陈旧观念的束缚,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批评缺席”“批评失语”的论调也不断浮现,但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认为:“我一直认为1990年代文学取得的成就高于1980年代。所谓‘批评缺席其实是伪问题,大统一的批评家没有了,批评的权力中心没有了。但是从多元性、自由性、个性来说,使1990年代以后的批评更有力量。”此一时期,文学批评早先附加的政治权威功能已基本丧失,但文学批评在引领创作风潮、对作品进行解读鉴赏等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批评家备受指责,但其地位依旧很高。
文学批评经历的第四次流变是在新世纪,这个时期,网络开始盛行,发表没有门槛设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评不批评,该写的依旧在热火朝天地写,批评家指导创作,已然成了明日黄花。而评论家也更加分化,一个是传媒批评圈,一个是学院批评圈。传媒批评被冠以“酷评”,大有跟风之嫌,但其威力不容小瞧。而学院批评,深奥难懂,批评家常年避居学院的深墙大院,与当下社会和文学创作隔膜越来越深,批评也变成了自说自话,无人理睬。
80后批评家就是成长在这样的批评环境中,其境况自然好不到哪去。批评不被关注,批评家指导创作更是变得滑稽而可笑。这不是80后批评家自身不作为,而是大的时代环境所致。
虽然80后批评家身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批评的处境也相对困难,但是不是当下就不需要文学批评了呢?显然不是。虽然文学批评在指导和规范创作上的意义在当前已经显得可有可无,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毫无意义。对于批评家而言,一方面,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剖析、解读、阐释,在发掘文本背后更为广泛深刻的人性、人生,乃至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在表现和传达着批评家本身对这一切的态度和立场。同时,文学批评也并非是对作品简单的描摹,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可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既是相互的,也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本身就具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由此可以引申出作家与批评家对社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当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介入方式。除此,从文学批评的流变来看,文学批评本身也形成了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而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方便容易地把握文学发展史的脉络以及各个时期文学与时代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其次,每一个批评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批评理念和批评观本身就是一种独到的思想体系,批评家的这些思想体系和各自的思想架构,对于文学批评这一学术思想的建设以及丰富和壮大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80后批评家“浮出”的阻力重重 从目前评论界的整体情况看,当下的评论界,老而弥坚的50后、60后批评家依旧是中坚力量(批评家的成长和作家有些区别,作家可能凭才情能较早成名,但也容易早衰,批评家不一样,批评家成长需要时间的淬炼,一旦成名,状态基本能保持,而且会越来越好,生命力总体比作家旺盛)。而80后评论家,不仅从数量上难以和老一辈评论家相抗衡,而且,在社会关注度上、甚至是圈子内,也时常被遮蔽,显得黯然落寂寞。当80后作家被媒体炮制、包装闪亮登场时,同样贴着80后标签的评论家,却被晾在了边上坐冷板凳——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群孤独的坚守者。
在全民阅读那一个让人温暖的时代,写作成了不少作家的专利,一举成名后,作家们不仅能享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甚至官方的肯定,因写作而加官晋爵的作家,不在少数。而彼时,作为文学创作最有力的指导、最有价值的创作分析和对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的评论家,自然能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同时,批评家还能享受到来自作家的膜拜和追捧。而在当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人皆作家,发表权也不再掌握在极少的纸媒编辑手里,不仅仅人人皆作家,而且人人都是编辑家,可随时随地能发表自己的“作品”。
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出生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成长时期又是物质相对丰富的时期,是享受了改革之利的一代人。然而,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其价值衡量体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钱、权、利、名成了当下量化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最近,连《人民日报》都刊文,感慨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然而更可怕的是,80后精神的早衰——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那么精神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了。“早衰”的年轻人,有时会显得和“成熟”很像,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⑥。而在教育上,“80后基本上是在一个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接受文学教育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文学‘失去轰动效应、遭炮轰……”⑦,都使得他们无心恋战在文学或者文学批评这一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而这一切,都造就了他们存在于自身或者主观上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80后评论家难于像鸡 一般拱破厚且坚的土冒出来,也跟老一辈评论家目前仍然是各主要评论刊物的重要作者有关,另外,目前批评刊物的主编,也不太愿意刊发尚未成熟的80后批评家的文章。当然,像《南方文坛》《创作与评论》《西湖》这样,力推80后批评家的刊物也有,但毕竟还是少数。刊物是新人获得社会认识、认可的一个主要平台,但这一平台,目前自身存在了不少问题。在生存的压力下,目前不少理论刊物走上“以刊养刊”的路子,大多增设增刊,主要以收费刊登文章为主。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亦是80后批评家“浮出”的一个重要渠道。但目前,国内出版社除保留四家事业编制有部分经费支持外,其余五百八十多家出版社,均被革了命,处于自找活路的艰难境地,将眼光放在80后批评家身上的气魄,早被“五斗米”折了高贵的腰。
金理与陈思和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金理说:“我觉得‘先锋的出现,是要‘人力和‘天时相配合的。它是在常态的文学上加上一鞭,这首先来自主观的能动,同时也要获得客观社会形势的支持。我记得章太炎、胡适都表达过这种意思,近代中国之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原因之一是‘中间主干之位(‘社会重心) 的不稳固、一直处于寻求过程中。胡适多次提及‘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相反,等到国家安定了,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就不明显了。也就是说,当变态的社会,学生运动、青年力量在社会生活,以及少年情怀、青春意象在文学中,均能大显身手、鼓动人心。像您提到的‘中年作家,他们的出道,正逢一个大转折过后百废待兴、重心重建的过程,这是历史提供的客观际遇,他们是这个过程的推动者、参与者,今天看来也是受益者。五四与八十年代都恰逢这种客观际遇。但是如您所说,从‘文革后到今天,中国社会结束持续动荡、骚动的‘青春期,逐步进入了告别理想、崇尚实际的‘中年期。这样的局面中是不利于青年人脱颖而出的。”⑧
在相对固态的“中间主干之位”之下,加之社会的世俗化,年轻人依靠自身奋斗上升的路径并不通畅的主体现实下,再加上目前文学批评界的自甘堕落、自我轻视、自我放逐,80后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的已经不多,而自甘“将冷板凳坐到底”的80后评论家就更是寥若晨星。
当然,如今是一个多元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靠一两篇文学批评一夜成名的时代已成了历史,而文学批评,又是需要靠知识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为支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80后难以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支劲旅,自身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外患内忧中,仍有那么一些有志的青年热爱着文学批评,艰难地在这个行当中勇敢地突围。正如金理所言:“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对于真正热爱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⑨
二、80后批评家的知识结构及成果
80后批评家的成长路径和同龄作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80后作家除张悦然、张怡微等少数几位是在传统教育下,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外,几乎是清一色辍学的“问题少年”,比如,以反叛著称的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更有如恭小兵、春树等完全来自底层的“草根作家”。80后批评家却截然不同,他们基本都是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毕业的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有着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完好的学术训练。当《萌芽》在1998年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重点关注80后作家,以及2004年,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出版社集中宣传80后作家时,80后评论家还正在学校接受教育。
从毕业学校来看,目前较活跃的80后批评家,几乎清一色地毕业于名校,且导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批评家。金理、刘涛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教授。杨庆祥、黄平乃同门师兄弟,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文学批评家程光炜教授。何同彬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导师是丁帆教授。傅逸尘硕士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导师是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教授。徐刚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张颐武教授。李德南目前正跟随著名70后批评家谢有顺就读于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上述几位80批评家都在很有影响的评论刊物发表较有深度和影响的文章,且多人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从出版专著上看,目前,金理出版了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刘涛出版评论集《当下消息》,杨庆祥出版有学术专著《“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多人合著);主编有《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傅逸尘著有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徐刚出版了《想象城市的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包括:金理的《一眼集》,杨庆祥的《现场的角力》………
三、展望80后批评家
从80后批评家目前成长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情况分析,其实不难看出这批人今后的成长方向,甚至是在批评上的造诣。我理解的外部环境,包括期刊出版以及各级主管机构,如宣传部、作协的扶持;而内部环境,可以理解为80后批评家的批评志向、关注趣味,以及自身在提高修养上的努力。
(一)苦练内功方有出路 必须经历漫长的学术训练,才能成长为一个批评家。写作是要靠天赋的,而批评除了天赋,更需要勤奋。
作为一个批评家,首先要有大量的阅读,对当下文学创作、走向有清晰的把握,同时,必须接轨传统,打通经典。“丰富的理论修养,起码的思辨能力,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文学史的完整概念,这些作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的必备素质对于批评家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具备。”⑩这样,在做批评时,才不至于大惊小怪,见什么都是“最”“首创”等。除了阅读,批评家“不参与到当下生活的激流中去,对当下复杂的生活现象没有大是大非的观念,没有大爱大憎的感情,那这个批评家也做不好,不管从哪里搬来多少理论,都是没有用的,如果批评家对生活采取冷漠的态度,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生活的话,那么,这个批评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11。
80后批评家中,黄平、杨庆祥已经是副教授,金理、何同彬亦在高校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阅读既是他们的工作,亦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刘涛、徐刚在科研单位,虽不像以上四位,能常年泡在书中,但阅读量同样大得惊人,尤其是刘涛,不仅有在美国访学的经历,而且近年开始关注晚清以来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态,对拓展其视野意义巨大。傅逸尘、周明全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接触面相对广一些,这也有利于他们在从事批评时,视野的拓展。
在目前80后批评家中,刘涛对提升自身修养有深刻认识,我们聊天中,刘涛常规劝我,要少写多读,最好是做一个专业读书人,而不是批评者。刘涛在最近刚写的一篇文章《现在的工作》中说,我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初衷是希望看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理解时代和理解自己,写文学批评大致也奔此志向,所以我没有学科意识,亦不希望作一个文学史专家或评论家。文学可谓国风,文学批评相当于观风的工作,观风或能了解时代、知得失,那么自己或也能知道进退出处,应隐或应显,知道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看懂一个作家,或看懂一种文学现象,比较简单,看懂一个时代则较难。如何看懂?或有两路:读书与历练。由于每个人机缘不同,会各有不同的经历,不可强求。读书则应求精求深,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业者易浅,原因即或读书不精不深,因为工夫在诗外。所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者成名可较早,但难免后劲不足,每况愈下,应深戒之。
金理也多次提到,80后批评家一定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要不,80后批评家最后只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在5月13日中国作协举办的“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说,他发现80后批评家对理论的热情远远高于阅读的兴趣,他认为,要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定要做好文本细读工作,“两条腿走路”。
(二)期刊、出版要关照年轻人成长 期刊出版和文学的发展之间的关联,被不少论者关注和论述过。“一个作品从作家构思、创作到摆在读者面前,要经过很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作品创作、传播及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生产机制、传播机制……文学期刊处于在作品走向公众的传输带的中间环节,它通过对一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塑造在无形中参与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12批评的发展和期刊、出版的关联,甚至高于其他文学题材。
60后那代批评家的横空出世,离不开1990年代两套批评丛书“火凤凰批评文丛”和“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的出版。很多年轻的批评家,都是凭借着这两套丛书走上文学批评之路,为外界所认识的,有的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本书。以集子出版时间来计算,当时张新颖二十七岁、郜元宝二十八岁、罗岗三十一岁、薛毅三十一岁、张业松三十一岁、严锋三十三岁、王彬彬三十四岁……
自2009年,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内五百八十多家出版社,除四家仍然保留为事业单位外,其他全部转企改制。可以说,生存的压力是压在出版社头上的一座大山,出版社无法像之前一般,花费巨资去打造、培养文学新人。陈晓明早就感慨道:“文学批评在出版社那里遭到的冷遇跟沿街乞讨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没听说哪个出版社愿意赔着本出批评文集,除非作者有权有势。……如果哪位搞批评的要出本书,如果还提到稿费的事,那出版社肯定会认为这人是个‘疯子。”13陈晓明这话虽有点偏执,但不无根据。只是亦有例外,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就愿意花费巨资,主动出击,打造“‘80后批评家文丛”。
云南人民出版社虽为地方出版社,但其胸怀和视野却是站在全球视野谋划出版。早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文体学丛书”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这两年,陆续出版了《爱尔兰文学丛书》、《莫言文集》(精装全本),正着力打造《印度文学丛书》,可以说,对当代文学和译介外国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是作出了自己突出贡献的。正在实施的“‘80后批评家文丛”,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扶植、培养文学新人的一个重大举措。
目前,网络以其特有的便捷和优势,对传统出版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传统读者群已经分化。在此大背景下,期刊普遍采取“以刊养刊”的路,依靠收取版面费维系生存。不少批评刊物一个刊名两张皮,一本刊物依旧艰难地保持原先定位,另一本收费发稿,或改头换面另做它用,目的是赚钱养主刊。据说,目前大学学报都是以收费发文为主。哪怕刊登本校副教授以下职称的文章,也要收费,而且收费颇高,一般的学生是难以承受的。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广西的《南方文坛》,自1998年始,开设“今日批评家”,被赞誉“催生了90年代青年批评家的成熟”。“集结起中国一支有生气的批评力量”(《人民日报》2000.6.17),该栏目旨在推介新锐的青年批评家,一年六期,一期一名,十五年来已有近九十名青年批评家在此亮相,其中不乏80后,比如金理、杨庆祥、何同彬,据《南方文坛》主编、著名批评家张燕玲介绍,年底至明年,已确定将继续推出80后批评家傅逸尘、刘涛等。另外,前年开始,《南方文坛》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协每年做一次今日批评家论坛,邀请的是70以后的批评家,囊括了不少80后。这个群体无一例外地都已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中流砥柱。
近年,在培养80后批评家上,做得最好的除了《南方文坛》,其他如《批评与创作》《当代作家评论》《西湖》《名作欣赏》《滇池》也在极力推荐80后批评家。
(三)80后需抱团取暖也需得到社会帮持 从目前80后评论家的成长路径来看,他们几乎清一色地跟随导师和追踪当下文学热点而逐渐成名。比如,杨庆祥、黄平,他们的成名是加入到“重写文学史”中,傅逸尘是研究军旅作家起家的,很少有一上路就关注同辈作家的。这当然有外部环境制约,比如,评论同辈作家,发稿困难,或者容易下错判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关注同辈作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的有效回应,也是80后批评自身成长的需要。著名批评家张柠说:“‘80后应该有自己的批评家,不要等到30岁才搞批评,更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经典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要直接对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应该自己对自己进行阐释和总结。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艺批评必须和写作同步。”14
金理一再呼吁:“批评家一定要和同龄人中的作家群体多通声息、多合作。”15他举例,文学史上批评家与作家互相砥砺、互为激发、甚至长时间共同成长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近的说,比如胡风和路翎、杜衡和戴望舒、王佐良和穆旦、吴亮和马原、陈思和和王安忆……
来自同龄人的评论,无疑会更容易获得80后作家们的信任。作家郑小驴说,80后批评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文学经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一致,这让他们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写作,对作品进行较为准确的解读。而且很多80后批评家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比如杨庆祥从初中以来就持续在写诗,李德南写有长篇小说《遍地伤花》,这使得批评家对作家们的写作更容易心领神会。16
自去年以来,80后批评家更多地涌入文学现场,并努力跟进同辈人的创作节奏。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80后批评家2012年在《南方文坛》开设了“80后学者三人谈”的专栏,从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杨庆祥和金理今年起在《名作欣赏》主持“80后评80后”栏目,每一期重点推出一位80后作家,同时邀请一位80后批评家写该作家的专论,力图在年轻作家和年轻批评家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湖南的《创作与评论》今年起开办“80后文学大展”栏目,每期推出一位80后作家小辑,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及弟子李德南主持,目前,金理、刘涛、杨荣昌、周明全等80后批评家都积极撰文支持。《西湖》杂志今年开设了“80后观察”,徐刚、徐勇两师兄弟主持,每期集中讨论一个80后作家。《滇池》杂志自去年开始,不定期推介青年评论家,80后批评家杨庆祥、傅逸尘等人已被专题推介过,影响不错。在新锐杂志的全力支持下,80后评论家通过对80后作家的评述,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更有利于彼此的成长。
“‘80后批评家要引起人们关注,甚至说以他们的力量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那么靠散兵游勇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要集体亮相。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要说到引起社会关注、介入公共世界,确实得集体亮相。所以,如果说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关注和帮助,我想首先是希望那些手握资源的前辈们多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各级宣传和文化部门多对年轻人落实制度上的扶持、资金上的投入,同时尽量保护年轻人的个性和锋芒,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个整体。”17
5月13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相信有了这个开始,今后80后批评家今后将得到更高层面的关注。另外,自前年开始现代文学研究馆举办的客座研究员,对80后批评家也多有扶持,目前,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同彬、傅逸尘都是其麾下研究员。
四、结语
在“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上,《文艺报》主编、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说,文学批评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是一项需要坚守的事业。今天的时代和文学众声喧哗,批评不再像上世纪中后期那样受到重视,但这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有时候土壤太过滋润可能不利于批评家成长,比如西瓜,土壤太肥沃,可能长得大,水多,但不甜。一直处于呵护下的批评无法获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批评家除了关注作家作品外,还应当多做‘脑体操,关注个人批评观的建构。”
80后批评家毕竟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自去年以来,已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对80后批评家来说,亦是一次机遇。俗话说,暴得大名不祥。80后批评家也就三十多岁,不要为名而太焦躁,沉下心来,安静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多读书,多关注当下社会,一定能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2013年5月9日初稿于云南人民出版社办公室
2013年6月2日修订于昆明丰宁小区家中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郜元宝:《论“中国批评”》,见《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2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③王尧、林建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发展与转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导言〉》,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④⑤⑧金理,陈思和:《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⑥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
⑦1517金莹:《“80后”青年评论家为何难“冒头”?》,载《文学报》2012年4月6日。
⑨朱自奋:《“80后批评家”正在发言——访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金理》,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7月6日。
⑩李星:《关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载《文艺报》2012年7月30日。
11陈思和:《批评与创作的同构关系——兼谈新世纪文学的危机与挑战》,《思和文存》(第三卷),208页,黄山出版社2013年版。
12周立民:《文学期刊:在困境和困循中挣扎》,见《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陈晓明:《后现代的间隙》,58—5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张柠:《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载《南风窗》2004年6月(上)。
16黄尚恩:《“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作家》,载《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
(周明全,供职于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