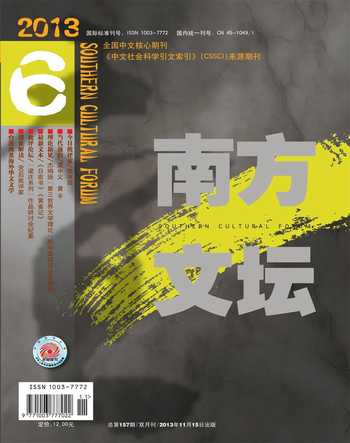关于《通三统》
2013-04-29张新颖
我初次读刘涛的文章,还是他念硕士生的时候,他学的是西方美学专业,却写了篇关于《随想录》的论文,参加了2005年巴金逝世几日后在嘉兴召开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的论文题为《巴金先生的真话、身体和疾病》,展开的是真话、身体和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略有些生涩,却尝试着去突破一般研究中一再重复的论述,给我印象很深。我就此认识了这个人,并且得知我们还是胶东同乡。
不知道为什么这本论文集没有收这篇文章,也许是成熟了,“悔其少作”?因为这篇文章的印象,所以刘涛读博士的时候转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陈思和老师,在我想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也很快就熟悉起来,有一些日子一起打打乒乓,他和我的一个学生张昭兵算是陪我活动一下;我刚起了兴头,却因为有人抗议影响了他们而撤掉了球桌。这活动未能持续是个遗憾,给我的回忆却是美好而生动的。
刘涛寡言少语,我也是,所以我很长时间也并不太清楚他读书用功的方向,从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访谈等等,总觉得是蓄积着的想法、愿望和活力在寻找各种形式的表达。直到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才多少有些明白他都干了些啥。我确实有点吃惊,没有想到他讨论的是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个人—家—国—天下体系的变迁。我读过一点章太炎、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但对这样的思想史问题,实在是没有发言权,对刘涛论述的那个东西说不上什么来;然而却因此对刘涛本人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大致上可知他的学术视野、思想重心、个人关切。我看他的论述,尤其是那些吃力、吃重的地方,反倒生出敬重的感受来。他未必能够做到处处圆通,却并不因此而回避困难,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刘涛毕业后去了北京,我还是时不时会看到他的文章,但与过去有点不同的是,我多少能够感受到这些散乱的文章背后他的用心。日前他编成这本论文集让我写几句话,我以为他这个看起来有些“大”的书名,也正是那些看起来散乱的文章用心用力之所在,因而想起了前面所述的事。我自己虽然不用刘涛“通三统”的说法,但那个意思倒是一直在说的,即中国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我们最切近的传统,而且至今仍身在其中,观察、思考、论述今天的问题,脱离了这个,恐怕很多地方还是说不清楚。
2013年5月12日,复旦光华楼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