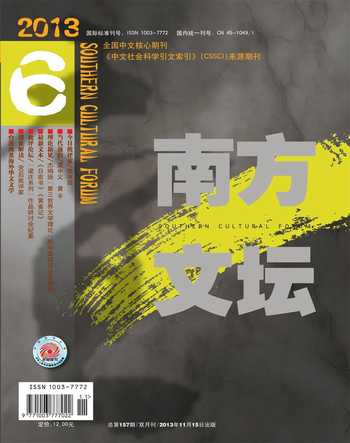关于“‘80后’批评家文丛”
2013-04-29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五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来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二来,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是常见于报纸杂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作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上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但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自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是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