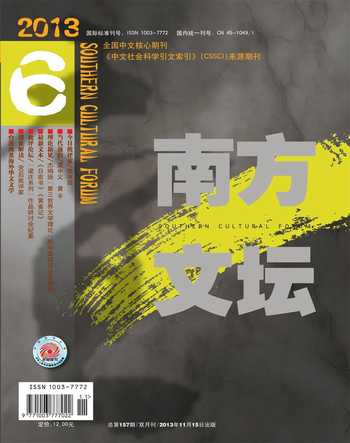为历史而烦
2013-04-29段建军
人是一种事业性的存在。人为什么样的事业操劳繁忙,在什么领域里创造自己平凡或神奇的业绩,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所有生存者,虽然有所谓圣贤、凡愚之分,劳心劳力之别,但他们都为“历史”而繁忙,为“历史”而烦神。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先祖过去未竟的事业,圣贤总结的社会人生经验。乡土社会从上到下,从贤到愚,所有的人都是眼睛朝后看着“历史”的过程,心思朝后总结着“历史”的经验,行动朝后完成着“历史”的使命。由于他们都为“历史”而繁忙烦神,所以他们的人生,几乎可以说都是“历史化”的人生。乡土史诗的《白鹿原》,正是通过对乡土生活的叙事,给我们诠释着中国乡土社会“为历史而烦”的生命哲学。
一、乡土人生是与“历史”相关联的人生
在中国乡土社会,上层统治阶级都有自己的“家法”。即祖宗立下的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程。这“家法”以“历史”上的圣哲贤良为楷模,以过去的昏庸无能之辈为借鉴。它是创业祖宗尊重“历史”的铁证,又是后来守业者或引以为戒,或奉以为师的经典教材。这一传统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的轴心时期便已产生。先秦诸子之中,孔子慕周,墨子推夏,孟子崇尧舜,他们都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以古代圣贤之言加重自己理论的分量。到了宋明儒学时期,各个思想家都坚持自己的思想是直接取自于六经孔孟。王阳明在龙场顿悟之后,作五经臆说,重定大学古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格物新解是儒学的真血脉。当时学者们都反对为学的人不取证于经书,而执持于师心自用造成的错误。在他们眼中,圣人之道只存在于经书里,经外绝无圣人之道。谁若无视经书,也就等于无视圣人之道。谁若舍弃经书,也就等于舍弃圣人之道。儒者做人之乐趣,就在于学习圣人之言。反复玩味圣言中的哲理,体会圣人的深邃用心,并在自己的做人过程中践行圣人之道。于是,孔圣之言就成了他们必须遵守的家法。罗汝芳说:“孔门立教,其初便当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当敏求言行。诵其诗读其书,又尚论其世。是则于文而学之。”他们诵读圣贤书,听信圣贤言,其态度之认真,信仰之坚定,比法家遵守法律条文,士大夫执行皇上圣旨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鹿原》中的圣人朱先生也是这样。朱先生有天清晨正在书房晨读圣贤书,适逢省府两位差人要见。他头也不抬地说:“我正在晨读。”示意别来打扰自己向圣贤学习。对方强调:“我这里有十万火急的命令,是张总督的军谕。”朱先生说:“我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等就请自便。”对方怕他不知张总督是何许人,专门提示了一番。门房张秀才答道,就是皇帝来了也不顶啥。因为对朱先生来说:“诵读已不是习惯,而是他生命的需要。世界上一切佳果珍馐,都经不起牙齿的反复咀嚼。咀嚼到后来,就连什么味儿也没有了。只有圣贤的书是最耐得咀嚼的。同样一句话,咀嚼一次就有一次新的体味和新的领悟。不仅不觉得味道已尽,反而觉得味道深远。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经得住一辈子诵读。朱先生诵读圣贤书时,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如同进入仙界。”除了读圣贤书,朱先生下最大力气做的工作就是编县志。考证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特产。叙说历朝百代达官名流文才武将忠臣义士的生平简历。核查数以百计贞洁烈女的生卒年月和扼要事迹。“历史”之外的东西都在他的意向中被悬置,他的生存意向主要聚焦于“历史”上。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后人的生存成长领域,往往都经祖先作了“历史”圈限;后人的生存成长志向,往往都出于祖先的“历史”筹划;后人的生存成长理想,往往都出自祖先的“历史”昭示。因而,这里的朋友往往都是世交,仇家往往都是世仇。每个人无论是做好人办好事以利人,还是做恶人办坏事以害人,都有其“历史”的原因。在这里,信任往往是“历史”的信任,鄙视也常常是“历史”的鄙视。鹿三之所以要做白家的义仆,甚至为了白家的荣誉,不惜杀害自己那不名誉的儿媳,是因为白家“历史”上就以仁义闻名,从白秉德起就对他有恩。他之所以瞧不起鹿子霖,是因为在他眼中,鹿家祖先“历史”上就根子不正,靠卖沟子起家的没什么德性喀!鹿子霖之所以对当乡约兴趣大,是他想实现创造鹿家“历史”勺勺爷的遗愿,改变鹿家世代只能给白家当帮手的劣势地位。盘龙镇吴老板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爱女,嫁给家境已经衰落、生活已经潦倒、人们都认为有克妻之命的白嘉轩,是因为其祖先在“历史”上曾经提携过他姓吴的,他要以嫁女来报答那段“历史”的恩情。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与古人古事相拉扯的社会,中国乡土人生是与“历史”相关联的人生。在中国乡土社会曾经有过,荣耀都佩戴着光荣的“历史”勋章;曾经受过,耻辱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十字架。
乡土社会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历史情结,是因为在乡土生存者的眼中,世上的人、人的“历史”,以及人所栖居的世界,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互轮回。“历史”的过去,犹如白鹿村老爷庙那棵七搂八乍另三指头的老槐树,即使被岁月掏空了心,却依然能够郁郁葱葱地生长,并形成一种凝聚不散的仙气神韵,保佑着现在,祝福着未来。故而,“历史”上曾有的人生事业,曾经历过的生命体验,曾筹划过的光辉前景,在新的现实中绝不会化作毫无生气的化石,它往往会以新的形式继续生存。这种新的存在方式,又都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不断重演着“历史”,另一方面又在挖掘着过去的生存潜能,完善着过去的存在缺陷,实现着过去的生存遗愿,开拓着过去所发端的生存前景。因此,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关注“历史”时,从来不把“历史”当作一种单纯的景观。他们谈论“历史”时,也没有把“历史”当作一种打发空闲的无聊话题,而是将其作为自身的现在以至未来,必须消化和占有的有机养分。在这种“历史”视点下,“历史”成为有机的生命体,它也生生不息地轮转运动着。
二、乡土生存是为历史而烦的生命过程
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者之所以大都为“历史”而烦,其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性生存的历史传统所致。由于几乎乡土生存者世世代代都定居一地,生存空间很少有变化。大多数乡民都是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又老于此。这首先造成了枝叶扶疏、延续千年的大家族如孔家,从孔子上溯,一直可推到夏代,约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从孔子下延到现代,又大约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为了生存的关系,大家族又常分蘖出许多小家族,同样又绵延上千年的历史。生存在这种有“历史”传统的家族中,人们自然会养成对家族“历史”的关怀,自然会关注自己在家族“历史”中的地位,会关心自己对家族“历史”应尽的义务,对家族“历史”应作的贡献。这就形成了乡土社会所特有的人道——以家为中心的人道。在这样一种以家为人道的文化心理制约下,乡土生存者为历史而烦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是以个体肉体生命持存来延续家族历史。
家族文化中为“历史”而生存决定了生存者向父母所尽的最大责任就是“孝道”。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所以创生新的肉身,使父母的遗体继续生存,让祖先传下的万世之嗣,绵延不绝,以至永远,便成为乡土生存者生存筹划的历史性事件。在有子之外,他们还重视子肖其父,以为只有这才是父母之生命获得再生的铁证。这也是每一个做父亲的人最为高兴的事情。白嘉轩就是这种典型:
这两个儿子长得十分相像,像是一个木模里倒出一个窑里烧制的两块砖头了;虽然年龄相差一岁,弟弟骡驹比哥哥马驹不仅显不出低矮,而且比哥哥还要粗壮浑实。他们都像父亲嘉轩,也像死去的爷爷秉德。整个面部器官都努力鼓出来,鼓出的鼻梁,鼓出的嘴巴,鼓出的眼球,以及鼓出的眉骨。尽管年纪小小却已显出那种以鼓出为表征的雏形底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鼓出的脸部特征将愈来愈加突出。
白嘉轩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他往往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专注地瞅着他们那器官鼓出的脸……
这是一种独具中国乡土特色的生命情怀。他对“历史”的重演,人生的重演,格外在意,格外喜欢。并且在乡土哲学中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儒家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相互交感,阳施阴受,创生亿万的男人女人;创生亿万的牡牝之物。创生之物只有像创生者,才有价值,才得人们的喜欢。再对男女分别观察,则男人主阳,女人主阴。男女各具特性,不容混淆。倘若男不主阳,女不主阴,男不男,女不女,性别混淆,就没有价值,受人诅咒。对男女作总体观察,则男人身上有阴性,女人身上有阳性,男女各一太极。同理,就牡牝之物分别观之,则牡物主阳;牝物主阴,牡牝各具特征。将牡牝之物统而观之,则牡物中含有阴性成分,牝物中含有阳性因素,故牡牝各一太极。既然男女牡牝,创生于太极又各为一太极,那么,儿女诞生于父母,自然又是新生的父母了。新父母只有像旧父母才受人尊敬,否则会受人轻贱。这种尊敬是对肉身“历史”延续的尊敬,这种轻贱,是对肉身“历史”改变的轻贱。所以,在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不只白嘉轩喜欢子肖父,鹿子霖也有此心态。当他做了田福贤的钦差大臣之后,在国民党强抓壮丁的灾难日月,他过去的一个女相好,要求他把他俩所生的娃子认成“干娃”,以逃避壮丁。鹿子霖所欢喜的,是自己的干娃一个个都浓眉深眼,五官端正,的确是他肉身的再生,感到惋惜并为之慨叹的,是这几十个以深眼窝长眉毛为标记的鹿家种系,只能做他的“干娃”。他所希望的,就是干娃们常常来他屋里走动,让他看着他们,就知道鹿家种系自他而后枝儿越分越多,叶子越发越茂,他鹿子霖分身有术,遗体有方,无愧于祖先了。
其二是报本返始,通过对祖先精神的传承来复活历史。
乡土生存者从家族情感出发,以“孝”为中心,探讨肉身生存者如何通过自我的报本返始之心去思慕祖先,让已故的祖先在后代的思慕中得以永生,让“历史”在生存者的思慕中得以复活。这种思慕的外化和对象化,就是乡土社会中最为神圣的祭祖活动:修建祠堂,续写家谱,定时定节给祖先灵位烧阴纸供鲜果。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常在自己祖先灵堂前写上“音容宛在”的奠文。此宛在的音容已经不在天地之间实存,却通过“孝子”的思慕之心,充塞于天地之间,与“孝子”的生命融为一体。在此,“孝子”的思慕记忆起了沟通阴阳,连接死生的作用。正因为有“孝子”的思慕记忆,“历史”就不会死去,过去又整合到现在之中。
作为华夏一角的白鹿原,也把祭祖当作回返生命之根的神圣活动。在那场灾难性的瘟疫过后,白鹿原显出一片空寂与颓败的气氛。九月里收完秋再种麦时,一反往年那种丰收与播种的紧迫,平添了人们的悲戚之情。大家觉得那么多人死了,要这么多的粮食做什么!正当这种情绪蔓延的时候,白孝武在其父白嘉轩的支持之下,及时地主持了敬填族谱的神圣活动。他从三官庙请来和尚,为每一个有资格上族谱的亡灵诵经超度,让后辈儿孙为其先祖燃香叩首,最后将死者的名字填入族谱。这件牵扯到家家户户的“神圣活动”,扫除了一个个男女后生脸上的阴影,给他们的眉眼中灌注了轻松的神气。一下子提高了孝武在族人中的威望。它充分表现了乡土社会中的所有肉身生存者,不愿让死生路断阴阳道隔的心理。
乡土社会的后生们,觉得祖先在世时,不但用辛勤的劳作生养后代,而且用深厚的情思顾念后代。祖先的心中只有家庭和子孙,他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临终前又将这一切移交于身后的子孙,希望后辈子孙能够把这一切照看得更好。这表明祖先虽然离开了阳世进入阴间,然而,他对阳世生存着的后生,仍留存下最后的热情,此情就是对家庭和子孙的难抛难舍之情,是祈盼家庭在离开自己后,能够人财两旺万事顺心如意之情。祖先对家庭和后代的这一番深情,是超出个人生命限度的情意。它发生于祖先临终之前,洋溢于祖先已逝之后。感动孝子贤孙们自然地以其诚敬去祭奠先祖。召唤孝子贤孙们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态度,去承载先祖的情志,接通死生的裂隙,打通阴阳之间的阻隔。并且,在自身的人生过程中,努力成就死者之志,甘愿遂顺死者之情。切实地用行动让祖先的精神昭垂于后世,使祖先的英灵永垂于千古,这就是精神之“孝”的核心内容。古人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里,“孝子”通过尽自身的“孝”心,同时也就尽了先祖的遗愿。二心合一,促成了古今的浑融。它的极致就是孝子贤孙自觉地或本能地用自己的肉身,重演祖先的人生经验,发扬光大祖先的生命精神。白嘉轩在生父白秉德死后,每天早上都要“坐在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靠背椅子上,喝着酽茶,用父亲死后留下的那把白铜水烟袋过着早瘾”。吃罢晚饭,他又悠然地坐在那把楠木太师椅上,像父亲一样把绵软的黄色的火纸搓成纸捻儿,端起白铜水烟壶,提一撮黄亮黄亮的兰州烟丝装进烟袋。噗地一声吹着火纸,一口气吸进去,烟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又徐徐地喷出蓝色烟雾。他拔下烟筒,哧地一声吹进去,燃过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粉碎了。母亲白赵氏看着儿子临睡前过着烟瘾,她时不时地把儿子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那挺直腰板端端正正的坐姿,那左手端着烟壶,右手指头夹着火纸捻儿的姿势,那吸烟以及吹掉烟灰的动作,简直跟他老子的声容神态一模一样。
鹿子霖再度春风得意之后,有天晚上从南原喝了一场酒。带着几分醉意回家,在坟园遇到了为逃壮丁专意来投靠他的“三娃”。他一定要三娃骂自己一句最粗俗的脏话,抽自己两个耳光子,或者给自己脸上尿一泡。三娃听罢,撒腿就跑。却被鹿子霖扯住了后领,怎么也脱不了身。三娃既然无法脱身,只好仗胆抽了鹿子霖一个耳光,骂了一句难听的话,之后站在原地等待受罚。没想到子霖却夸奖他,“打得好也骂得好呀三娃!好舒服呀!再来一下让我那边脸也舒服一下。”三娃照办之后,鹿子霖将他拦腰抱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哈哈笑着又扔到地上,并称赞他“有种!”而且爽快地收他做了长工。看了这一幕戏剧,好心人会觉得这位向来不吃眼前亏,善于以毒攻毒以怨报怨的鹿子霖,突然变得不像他自己。甚或错误地认为,鹿子霖若非酒后发狂,就是突然之间良心发现,于是,借机自惩以减轻内心之不安。然而,事实却是鹿子霖通过这一番作为,用自己的肉身对勺勺爷的勾践精神进行了具体化的“重演”,他想通过这番“重演”,获得对家族中最有影响的祖宗的人生,进行一次深切体验。与这位模范祖宗,进行一次深入的心灵感应。他在这种感应中,找到了祖先创家立业的那种生命精神,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和生存向度。他为自己能与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一位祖先进行身心感应而欢畅,更为自己肖于家族中最有影响的祖先而自豪。
其三是通过向历史学习来认识自身、刷新历史。
中国乡土社会中各阶层生存者,向已往先辈学习做人的“历史”意向,其摹仿先辈过往行为的“历史”方式,都是在为“历史”而烦。这在某些现代人看来,是对生存者自身的能在向度进行遮蔽,对人的潜能进行窒息的一种生存方式。现代人认为,人的生存是面向未来的能在式的生存。每个现世生存者,总是向着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不断生成和发展。“此在本质上是现身的此在,它向来已陷入某些可能性。此在作为它所是的能在让这些可能性从它这里滑过去,它不断舍弃它的存在可能性。但这就是说:此在是委托给它自身的可能之在,是彻头彻尾被抛的可能性。此在是自由地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在种种不同的可能的方式和程度上,可能之在对此在本身是透彻明晰的。”①生存者之所以能由现实向可能境界生成和发展,是因为他的肉身中有灵性,他对自己和世界有所领悟,有所谋划,他把世界看作有种种可能意蕴的世界,把人生看作有种种可能性的人生。然而针对上述认识,乡土社会的生存者却会反驳道:每一个生存者最初对自身可能性的领会,几乎都是本能地从传统方面继承下来的。他最初的人生谋划,基本上是对其祖先人生谋划的一种承袭;他要实现的理想,往往是祖先早就立下的宏愿。只有了解古始,才能把握现在。所以,在中国形成了信好先古的悠久传统。
尽管,还有些现代人认为,我们人类既不是生存于过去之中,也不是生活于未来之中,而主要是生存在现在之中。每个在世者都是在当代世界的繁忙和烦神活动中,展开其生存成长历程的。在这一过程中,人认识了自我,实现了自我。而不是通过各种“历史”活动来认识和实现自我。然而,在中国乡土生存者的眼中,上述生存者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事实,即人们现世所要繁忙的事情,往往是“历史”交付的事业;人们现世为之烦神的人际关系,常常是“历史”造成的人际格局。这就是说,“历史”比现实更为威猛。后来者只是普及祖先在“历史”上的创造成果,只是应用“历史”积淀的人生技能。因此,现世的生存成长者仅仅沉入到当代世界之中,并通过其反光来认识自身是不够的,更需要不断沉入到自身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之中,并通过“历史”传统来认识自身。白嘉轩如此,鹿子霖如此,朱先生亦如此,乡土社会的生存成长者们无一例外。正因为无一例外,过去的生存传统就对当代生存成长者,具有一种优先的统治权,要求他们为“历史”而烦。倘若现世的生存者把“历史性”连根拔除,让自身盲目漂游于五花八门的当代文化观念中,就会变成真正的文化浪子。这种文化浪子由于整天活动在与自身极为疏远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无法创造性的占有自身过去的那些宏伟志向,只好与自身的宿愿决裂。这一决裂,既中断了自身与既往“历史”正常而有意义的对话关系,又失掉了摆正自身位置及正确把握自身生存成长方向的机会,使生存者备受无家可归之苦。因此,每个时代的生存者都有返回“历史”,追寻文化之根,正本清源,倾听历史呼声之必要。唯有这样,人类才不会在生存成长的途程中迷失方向。
三、乡土史诗叙事是为现实生存成长者开启生命活力渊源的探索
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在为“历史”而烦。他要敞亮我们民族一直被遮蔽的秘史。“为了知道历史是什么,必须知道实现历史的人是什么。”②人既是建造历史的砖瓦,又是设计历史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乡土社会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明白。他们仅仅生活在第一个层面上,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建造“历史”的一块无关紧要的砖瓦,是“历史”循环过程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被动的存在。他们忘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建筑师和建筑工人的主动角色。放弃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和决定,否定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这种人只会“回想”,不会“预想”,只知道“历史”在循环运动,却没有思考这一运动的出入口就在当下。只知道过去的“历史”对当下的现实作用,却不知道当下的决断对将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对“历史”的回顾意识,却没有直接参与“历史”的意识。他们忘了“我”作为时间性存在的唯一性,忘了“我”对自我的承当以及对“历史”的建构作用。在乡土社会,有两种人具有对“历史”的设计和建筑意识。一种是圣贤,一种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明白自身生存于当下,自己的行动却深入到将来,因此,“当下”决定着“将来”,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人自身成长变化的模样。所以,人自己“当下”所做的选择和决断,既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进入“历史”的出入口,又是为重建“历史”找到一个基础和开端,让自己置身其中,进行“历史”设计与建造。《白鹿原》复活“历史”,让那些被当代遗忘和遮蔽了却仍然可以对当代人生存成长起开导作用的往事开口说话。让它告诉现世的生存成长者:虽然每个生存者都是在流传下来的生存成长观念中领会自身的能在式样,虽然每个生存者都在既往的“历史”中为自身选择值得模仿的英雄榜样,并在其人生历程中重演榜样的品行,然而,“历史”中既有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白鹿”,也有浑身患病衰朽害人的“白狼”。膜拜前者能给生存者开启生命的价值之源,把世界变得“己安人安”,万民康乐,让“历史”进入和谐健康的轨道。模仿后者则只会毁灭人生的一切价值,让世界变成你踢我咬人人自危的战场,让“历史”滑入瞎折腾的泥淖。那些根据现实生命体验开启“历史”渊源,并以面向未来的心态,与既往健康向上的英雄榜样对话的生存者,才是真正有益于当代的生存者。《白鹿原》对“历史”进行揭秘,就是为现世的生存成长者开启充满生命活力的历史渊源,让现世的生存成长者从中发掘有益的能在式样,为生存者的肉身中灌注灵性。让生存成长者们倾听原始意象——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声音,从而继往开来,创造光辉灿烂的能在天地。
《白鹿原》为历史而烦,就是要沉入历史之中,揭示“历史”本身发展变化的“常道”。沉入“历史”的设计者和建筑者之中,揭示人本身生存成长的“常性”。他既为我们展示“历史”与人性的本色,又激发我们对“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的追问。司马迁《报任安书》讲自己著史的目的,“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道出了古今所有史家的心声。所有正史、野史、秘史的作者,都想把“历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必然与偶然,划分一个大的界限,从而突破“历史”的乱象,把握“历史”的大方向。都想通达“历史”的变化,把握“历史”的实体。陈忠实也不例外。他的《白鹿原》让我们看到了那貌似循环的“历史”,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那貌似“重演”的人性,其实一直在进行着更新。首先白家父子两代的“历史”和人性的就在变化。白嘉轩是通过对对家族“历史”以及祖先人生的“重演”中创造自己的新生,他坐在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坐过的那把生漆木椅上,握着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握过的白铜水烟壶吸烟的时候,总是进行这样的人生思考:每一代人都是家庭这架大车的一根车轴,当他断了的时候,新的一代应当尽快替换上去,让家庭之车尽快上路,奔向祖宗指定的目标。但是儿子孝文却认为,家庭只能引发他怀旧的兴致,他根本不想再去领受那老一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禾垛顶引颈鸣唱。”他对重演祖先的“历史”已毫无兴趣,只想在未知的新天地里,创新的事业,写新的“历史”。其次,沉入“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历史”的“常道”。“历史之所以可贵,正因为他是显现变与常的不二关系。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地向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常到实践前进。”③只有在变中发现常,才能把“历史”贯通起来,才能找出人类行为的大准则,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鹿原上的每个乡土生存者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白嘉轩本人由最初的信奉皇帝到后来自行剪掉辫子;从把宗族祠堂里的事看作终生最神圣的事业到自愿卸任族长职责;从起初不理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到主动帮助共产党的游击队员。这一切都说明,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在者”本身,也在“历史”的运动中逐渐变化着。他们不可能只重演过去的一切,而且也在追求和创造着未来。“能在者”本身的这一特色,使“历史”在过去与未来的两力作用之下,呈现出一种曲折地递进发展态势。然而,有一点在他身上始终都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对白鹿精灵的追逐与向往。他早年为了得到白鹿精灵的庇护,不惜割舍自家的几亩水田,他晚年看到白家后代干成大事时依然想的是白鹿精灵。白鹿精灵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之德”,他经过哪里,就给那里带来生机,他激发人们相互感通,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我”和“他人”因白鹿精灵而相互感通,“历史”和“现在”因白鹿精灵而相互融合。就连那个极端自我的白孝文,在他创造新“历史”的开端,也要回乡祭祖归宗,也不敢站在家族“历史”之外,纯靠自力创造自身全新的“历史”。这就是《白鹿原》所唱明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色,也是它着意为中国“历史”而烦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76页,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②科耶夫:《黑格尔导读》,19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③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23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段建军,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新时期新时期主义文学》(编号11BZW02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编号10YJA751017)的中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