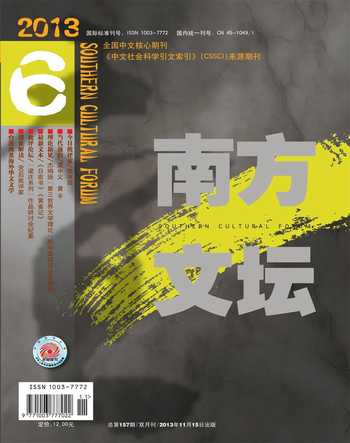从象义关系谈小说之“小”
2013-04-29孙方友孙青瑜
孙方友 孙青瑜
编者按:2013年7月9日,著名作家孙方友与他的女儿、青年评论家孙青瑜做了一次关于小说创作的思考与对话,这距7月26日12时20分他突发心脏病逝世,只有短短的十七天,这也是他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次关于小说创作的谈话。我们刊发于此,以 哀悼、纪念和致敬!
被誉为“小小说之王”的孙方友生前一再与本刊主编张燕玲说:喜爱《南方文坛》,也一直自费订阅《南方文坛》。我们感念孙先生的文学追求和成就,也感念他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孙方友先生安息吧!
孙青瑜(河南省签约作家):前一段《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版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短篇小说创作论坛”——《像蒲松龄那样讲精彩的故事》,细看之后发现论坛并没有涉及故事在小说中到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没有细说如何通过故事把小说“短”下来的方法问题?所以我很想听听您作为一位笔记体小说家,是如何认识故事之大用的?
孙方友(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这个问题好像把我推到了浪尖上(笑)。可能是会议上时间有限,他们没法细谈,而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怀揣着一肚子让人醍醐灌顶的真经。因为每一个作家对故事都有独特的认识,也都暗怀一身独特的小说观和方法论。但我个人觉得,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故事和现代派小说中的语言功能一样,它的第一作用就是充当联系文本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现代派小说家一直想解构故事,其实就是想置换掉文本与世界的那根联系纽带。比如在《芬尼根守灵夜》中,乔伊斯在用语言互文世界时,巧借了一个语义学和语言逻辑之间的一个偶然性和巧合性在结构文本,通过句子的互文、文学样式的互文、语种的互文等等,不但曲线妙说他的纸上世界,并让他笔下的语言世界一直处在“正在构成着”的状态,进入了有“根“的互文状,将艺术联系世界的纽带直接从故事置换成了语言。当然,从乔伊斯、卡弗、卡夫卡等作家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在现象学的影响下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趋向于中国古人。而中国文化大体概括下来,就是一种正在生成着的动态文化,看重的不是物质自然,也不是主体的人,而是人在物质自然中摩荡生发的时境,所以极为讲究“变”、“几”和“域”,而故事在小说中恰恰能够承担起生成它们的重任。这种艺术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庄子以寓言为主的方法论,本来是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没法直接言说的“道”,不想他借在用“事象”这个中转站曲线论道时,却给中国美学、中国文艺留下了很多具有实战经验的方法论,可以说,庄子直接为小说定下了一个“以事载道”的基调。而故事在小说中的第二个大作用,正是你常说的曲线“载道表情”功能,当然也可以传趣,比如传统笔记体小说就是以趣味为主,义味为辅。
孙青瑜:我之所以提出以事载道的概念,因为我在研究八卦和中国语源学时,发现言和义之间没有直接的互生关系,从言到义必须要有一个中转站——象。无论是事象,还是镜像、物象、气象、还是形象……这些具有“中转站”性质的概念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无处不在,可以说离开了它们,中国古典文论几乎要有瘫痪之险。正是这些“中转站”的存在,让语言在能指无力的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丰盈、动态的象外之义,正是你刚才所说的“正在生成着的”。而在营造这些能生出动态意义流的“中转站”时,是不是有很多技术手段?
孙方友:是的,因为再高水平的语言学大师也不可能单单通过压缩文字本身,去直抵笔简义丰。文章贵活,这个“活”,不是现成的展示,而是生成着的。如何营造这股子活性意义流,主力军不是语言自身,而是你所说的这些言义“中转站”。但是光有概念意识还不行,还得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比如庄子通过寓言故事曲线论道为什么要比老子鲜活生动,就是因为庄子利用了一个言道中转站:事象。比如卡弗的简笔主义小说里几乎没有一句心里直陈,为什么我们却能从中看到那么多动态、多维的心理展示?原因就是卡弗的言和他所要表达的人物情感之间也有一个中转站:时境;再比如中国传统诗学,四言五字,便能巧通世界。其内在手段,却是通过物象的比兴关系为语言结构出了一个互体空间,来以小指大,以微探宏的。
孙青瑜:您说的这些都是极简主义文学的代表,那小说如何才能小不遗大呢?
孙方友:这又是一个难回答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方法论是理论倡导得以实行的“根”,也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方法论的推行,又必须要由作家也就是艺术操作者来完成,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家。比如“气韵”外延和内涵的急剧萎缩,就是古人没有积极地将自己的方法论贡献出来,才让“气韵”这个鲜活的中转站萎缩到不能再担当言义“中转站”的地界。这就是说,每一个作家积极地将自己的创作经验贡献出来,才能全面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
孙青瑜:是的,不少作家都有这种使命感,我记得方方老师曾在微博上说:“中国的小说只剩说,没有小了”,眼光就很敏锐,在中国文学的叙事普遍过满过密的当下,如何回归艺术的空灵,如何形小义丰,真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孙方友:要说形小而指大,我觉得必须得从“最简”的中国诗学说起。中国诗学四言五字,便能巧通世界,其内在手段,就是诗人在营造艺术时,找了一个具有类推功能的“巧事”或“巧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这个寻物表义的过程,正是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来寻“兴”,从而结构出一个文本与世界联系纽带,以达《周礼·春官宗伯》中说“兴是见今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的美刺效应。而在传达过程中,这个具有类推功能的“彼物”和“巧事”,恰恰是读者进行“艺术还原”的机关所在。比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从镶道的角度来说,作者将清白之心镶在玉壶上,为啥不镶于铜壶和砂壶上呢?因为玉在中国文化里有清白、君子和高洁之喻义功能,而铜壶、铁壶和砂壶们都不具有这种类推式的隐喻功能。所以作者在营造艺术时,必然存在一个目扫众“物”涉猎所需的过程,一打量不当紧,就看到了玉壶与中国文化间这层特殊的隐喻关系,玉壶便成了诗人以“比”及兴的媒介工具,成了载道载情的艺术之物。进入艺术传达后,我们要想进行意向还原,必须将“玉”这个具有类推功能的特殊之物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场域里,如此一来,玉就成了文本与世界联系的一个眼或纽带,成了牵出本象与外象(世界)的互体联系的一个重要机关,从而才能让读者进行活泼的意向构成。
孙青瑜:小说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种比兴关系来以小胜多嘞?
孙方友:是的,中国诗人在营造“中转站”时,可以说将八卦触类旁通的解卦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以此达到了字少义丰的艺术效果。诗学的比兴手法说白了就是八卦中的类比、演绎推理法的一个术语异变。而这种变异,好像与小说创作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却有着极强的内在互通性,这种互通性之所以没有被打通,原因就是中国文论里没有小说,当西方理论框架像潮水一般涌来时,中国小说的理论建构,因目光的过分向外,而缺失了很多精华的传统因子,比如作家们自觉的“比兴”意识,因为得不到理论上的阐释和推广,让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陷入了低迷状态。
孙青瑜: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影响下,很多人都误以为言可以直接达意,这是一个误区!因为从《易经》一直到王夫之和来知德,差不多整个中国哲学史都涉及了言义问题,都强调中转站“象”的重要性,而企图直接用言表义的结果,只能像来知德所说的“止于一死理”。
孙方友:对,卡弗就非常聪明,他在环境主义思潮影响下,从来不直接说小说人物的心理,而是将读者掉进他的小说时境之中,让读者在小说境域中摩荡生发出一种动态、多维的心理,活性意义流像滔滔黄河水,汹涌而来,从而达到一种以少胜多的效果。通过时境表义,也是比兴手法之外中国诗学能以少胜多的一个重要写作技巧。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等著名的诗句,多是通过时境的虚像铺述,让读者引入入其中,与诗句之时境相摩相荡,生出的活性意义流。
孙青瑜:您说的真对,卡弗的创作等于说抛弃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拒绝了定义性的文字和观点性的阐述,抛弃了“想”“觉得”“以为”等词语,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努力模糊着语言被对象化的尴尬,力图回到语源学的层面,还原出那个由象生言——由言生象的“原初”空间,从而将叙事语言从作家全知全能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让读者直接入到“镜像”中去体义。从结构语义学来讲,卡弗的白描语言,既是语境又是元语言,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双重身份,等于说把具有开放性的元语言放置在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在其中的世界)里,让读者直接站在第N层复义上去考察它们的妙处了。这是不是卡弗笔简义丰的内在玄机?
孙方友:是的,卡弗习惯让他笔下的人物“陷”进具体的“象中”,在不知然而然中进行着言着、行着。他的大笔呢,就像在拍摄电影,摄像机和录像机并用,拍录下一个个镜头,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推进“艺术虚象”中,自由地直观小说人物的复杂心理。比如《取镜框》中,无手先生无儿无女的生存状态,卡弗没有作直接的交代,但我们却能随着场景的线性发展,一一可“见”。比如《凉亭》一开场,“我受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带着浓烈的情绪指向,向我们直扑而来,但是卡弗却没立即交代为什么?而是让我们突兀地陷入了一个生存场景。如果我们认真地把小说看完,就会发现,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写实,真正的写实,没有旁白解说,没有插叙插议,没有倒叙,也没有看似“真实”其实仍属作家全知全能的意识流,因为它就是我们线性进展着的存在场景。
孙青瑜: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卡弗为什么在他生平最后一篇小说《差事》中,借助契诃夫之口中说出他“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因为是卡弗面对缺失外部环境的书面语言,认知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一直在巧用语境的活性空间,将人物的复杂心理都镶于场景、活动和对话中,从而把他的叙事推进他所说的“五官所感受”的“体觉”层面上,由此所达到的空灵性和延展性,都是直述人物心理的传统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而传统心理小说那些“直接给予”的心理直述,属于“系辞”式的意向直陈,其实就是企图想从言直接及意。这种写作方法到王安忆先生和毕飞宇先生这里,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位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写作现状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中国女性作家影响很大,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灾害,我不知道这种词用的是不是有点过?但我觉得中国只能有一个王安忆和一个毕飞宇,当大家都去学这种由言直接及义的创作形式时,无形中将中国的心理小说推向了一个死胡同。因为这种试图由言及意的直接后果 就是来知德所说的“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已”。
孙方友:王安忆和毕飞宇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小说观和小说方法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力超级之大,正是这种影响力的无形存在,让他们的写作方式得广泛普及。一种文学形式普及得过广,就会面临着改革的问题。比如魏晋玄言诗、骈文都是很好的说明。再加上模仿者模仿的都是“表”,而内在的“魂”,由于内功不到,所以摹仿不来,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尤其是女性写作“过繁”“过密”,没有阅读空间,遗失空灵感的现状。这种直接把握的心理指向和“直陈式”的做法,无疑是想走一条从言及道、从言及意的捷径,而实际它有点“看山近,离山远”的意思,不但抹杀了“象”这个言意中转站,还扼杀了艺术传达过程中读者进行“艺术还原”——自主解义的过程。所以我们只得在那个作者直接给予的心理直陈中,被动地收获着单向度的“意义解说” 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来知德所说的“无象,所言者止一理而已”。
孙青瑜:刚才我们说的卡弗之“小”,只是众多方法论中的一个,而您作为一个以小取胜的作家,肯定有一肚子如何让小说小下去的真经。
孙方友:真经不敢说,小经验还是有一些的。如何用故事让小说小不失大,还得回头看诗学之物和比兴的关系。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中,通过“玉”与中国文化场域的呼应;“李广难封”中,李广与广大老来嗟叹者的遥相呼应;“春风又绿江南岸”,“又绿”二字与“四象”的动变间的呼应;再比如《庖丁解牛》中,庖丁“技进乎于道”之后的解牛过程,与人类所有技艺工作的呼应。更有趣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单抽一篇来看,多是以趣味为主,甚至可以说只有趣味,义味寥无,可是当你将一个又一个的鬼故事联系起来,就于形而上的角度与现实世界构成了强烈的比兴联系,阴阳两界靡荡而存,人鬼结婚,阴阳合一,于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大世界就产生了……正是因为“比”的存在,艺术才有了一个“显器”的“活结”机关,让解构成为可能,让“象中”“象外”回应激荡成为必然,让意义场域和生存场域浑而同一成为必需,让喷发出的活性意义流在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激荡徘徊,甚至生生不息,都不再是传说。
孙青瑜:如果说卡弗通过“象中”取义,来直抵笔简义丰的,那您的笔记体小说,是不是就是通过“象外”观义,通过比兴手法完成了传统诗学意义上的笔简义丰?
孙方友:比兴手法经常用,但是笔简了神丰有没有达到,这还得让读者说(笑)。我在创作上的确吸纳了很多诗学技巧,包括“镜像”手法我也是常用的,比如《程老师》《王洪文》《张氏修车铺》《雷老昆》《大洋马》等,都借用了“时镜”空间这个表义中转站。只是这种手法,不像故事那么张扬,很多读者看了,还以为我是在利用故事走向在推动“道”的暴发,其实从方法论上来说,它们已经是多元因子杂糅后的产物了。也就是说,方法论是活的,一篇小说写下来,可能要牵筋动骨用到很多方法。比如我写《蚊刑》就借用了中国诗学里的比兴手法,将读者从象中取义推到象外去观道,目的自然是想完成“艺术虚象”的象外建构。就像我前面列举的“一片冰心在玉壶”,在阅读时,读者通过“艺术还原”,玉成了读者联系世界的一个“眼”或者纽带,换句话说,玉这具有隐喻功能的“物”,成了读者扩卦取义的“本卦”,我们要想进行意向还原,必须将“玉”这个具有类推功能的特殊之物,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场域里,如此一来,玉就成了我们与“外卦”互体联系的一个“纽带”,一个“观道”的谜口,它已经不是本象,也不再是卡弗的“象中”,而是在本象与外象(世界)的互体联系中,进行着意向构成。比如我那篇只有一千四百字的小说《蚊刑》,正是巧借了这一传统思维。让读者通过阅读文字还原出一个“蚊子吸人血”的事象。“蚊子吸人血”就像“一片冰心在玉壶”中“玉”一样,具有比兴艺术功能,从而让我们深入到社会化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类推出“官吸民血”的残酷现实,构成了文本与世界的联系,让这篇看似简单的寓言小说,内藏了一定的所指意蕴,原因就是我借用了一个具有比兴功能的特殊事象,建立了象中与象外的互体空间,从而完成了文本与世界,个体与历史、人性与政治,特殊与普遍间的深层联系。人民反贪官,贪官层出不穷,官员的频繁调动让底层人民饱受了吸血之痛。当您审美不强时,或许看到只是一个趣事,当审美提高时,您会恍然大悟,这个寓言故事内藏着我近二十年的思考。因为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手法运用上,与传统诗学都有着极强的互通性。比如《阿Q正传》中,鲁迅物色出的阿Q,与整个国民性之间的呼应,汪曾祺《陈小手》中,陈小手这个男医生因给人家老婆接生,被害死的事件,与中国文化影响下人的世界观间的遥望;毕飞宇《睡觉》中,被人包养的二奶对“纯洁”的渴望和追求,与“铜臭”污秽着的世界间的遥望对比;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白天当白领,晚上当“鸡”的双重性生活,与人的多重性、多面性导致的多重人格间的遥望;鲁敏《思无邪》中,祥和无邪的村子与道家文化的遥望,以及刘庆邦的《鞋》等等。当然这样的小说,我也有不少,比如我的系列小说《雷老昆》中,雷老昆的反常举动与整个大时代背景下国民的恐惧心灵间的呼应;《狱卒》中,白娃人头落地后,那双依然滚来滚去、滚去滚来的眼珠子和求生欲望的对视;《宋散》中,假宋散“革命”的目的性,与历代农民起义目的性之间的遥望……
孙青瑜:我觉得您的另一篇小说《雅盗》,比兴手法也很明显。
孙方友:是的,《雅盗》属于一个知域背景较强的小说,读懂它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首先,您得看懂《灞桥风雪图》这幅画。其次,您得知道中国古典文论提倡的“入”是何意。我为啥让赵仲一次次从入神的欣赏中走出来。原因很简单,雅盗在面对《灞桥风雪图》进行审美活动时,想直入到艺术虚象里,实际上却入不了,一次、两次、三次……中国文论家大倡“入”,而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赵仲(当然也包括我们)面对审美对象“入”不了的状态,刚好和在儒道两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的中国文人“入中有出,出中有入”的集体性格形成一个很强的比兴关系。此等大文人的代表有李白、苏轼,小文人的代表,有《范进中举》中的范进、有《灞桥风雪图》中赶考归来凄孤而行的老者——正是因为这等比兴关系的存在,我借用雅盗赵仲几“入”和几“出”的审美过程,隐喻了中国文人的悲凉命运的病灶。而实际上“比兴”到中国文人这里,审美活动还没有比兴完。读过我创作谈的读者都知道,我在创作谈中提到了艺术原形张父,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军人的艺术原型,联想到一个沦为贼寇的文人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文化联系,因为在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的影响下,中国人还有武而优则仕的心理,求学为了当官,从军也是为了当官。出而为仕,出不了的情况下,内心的不甘和失意,让很多人在哀怨、自怜、悲愤、看似死心,其实是不死心不甘心,这依然属于入不能全入,仍想出的心理,好像有个词叫东山再起,起来了皆大欢喜,否则就是雅盗赵仲和作者创作谈中提到的艺术原形张父。
孙青瑜: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比兴功能的事象媒介,文本才得以神通内外。而“比”得好不好,直接关乎着“兴”的艺术效果,是不是这样?
孙方友:是的,可惜中国文化里有太多精华的思维传统,皆因西方理论框架的全盘侵占而失去了。或者说,我们的小说理论从诞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头的殖民式理论体系。在没有中国的中国小说理论中,中国的小说创作严重缺失了“以小及大”“以微探宏”的内在性技术支撑,只能落下方方所说“中国的小说,没有了小,只剩下说”的严重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