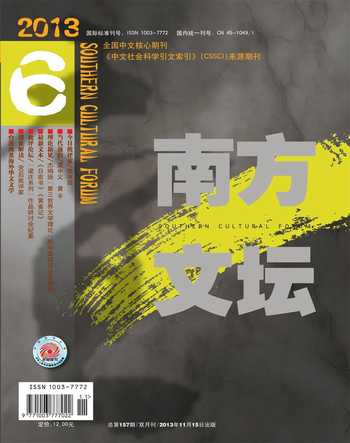既远且近的距离
2013-04-29岳雯
近些年来,短篇小说爱好者苏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以三四年一部的速度稳步推进着:2009年,《河岸》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收获》第3期上刊载了最新的长篇小说《黄雀记》①,据说很快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只有一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才能最终确立一个作家的地位,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作家摩拳擦掌,野心勃勃地要在最好的时候留下一部用以标识“苏童”的作品。结果如何,自有时间去分晓。在读完了《黄雀记》之后,我想起了苏童发表于《人民文学》2003年第5期的短篇小说《五月回家》,讲的是永珊带儿子回梨城探亲,经历了人去楼空之后,突然萌生了去白菜市看老屋的念头。整个过程,都纽合着儿子的不感兴趣、不配合、不情愿,可是对于一心想探访旧居的永珊而言又如何呢?小说写到,“白菜市一带的废墟迎来了离别多年的永珊和她的儿子。晚清的、民国的、社会主义的砖瓦木料混在一起,在五月的阳光中哀悼着过去的日常生活,现在这种宁静的哀悼被最后的来访者打破了。”②之所以想起这篇小说,倒不是因为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而是觉得,它更像一个隐喻,象征了苏童的长篇小说在今天的遭遇:回到家乡,可是家乡已然成为一片废墟,在废墟中的凭吊某种程度上也变得荒谬了,还有与下一代之间深深的不可跨越的鸿沟,尽在其中了。
一、为时间绘形
苏童在《黄雀记》里再一次回到了香椿树街,这一个“不思量,自难忘”的地方,似乎隐藏了苏童所有的写作秘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有了最充分的认识,以至于作家不得不得一次次站出来,为自己的“沉溺”作出辩护。在一个访谈里,他说,“这是我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需要捋清的一个事情。我在台湾出了一个短篇集,后来看到一个书评在批评我,我不是不能容别人的批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这样批评我。她批评的论点在我这里引起了戏剧化的反应。说一个作家怎么可能一辈子陷在‘香椿树街里头呢?你老陷在这里走不出一条街,算怎么回事?而我所担心的问题不是陷在这里面的问题,而是陷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否守住一条街,是陷在这里究竟能写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要写好这条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几乎是我的哲学问题。”③这话有些义正词严的意思,我明白,作家这么说的意思是为了强调“香椿树街”之于他本人的意义。
那么,“香椿树街”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在《黄雀记》中,我们读到了一如既往的“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④论者大多将“香椿树街”落实到其地理特质上去阐释,比如“南方”⑤,大概只有南方才充斥了如此潮湿阴郁的意象,比如城镇生活与市民社会⑥,不过在我看来,“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空间的,不如说是时间的,它完成了对沉寂于历史深处的“七八十年代”的绘形。
对于集体记忆而言,“七八十年代”显然并不荒凉,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大事件,是从过去投过来的一束光,时至今日仍然在影响今天的文学生活。但是在一个少年眼中,“七八十年代”是贫困,暗淡的。显然这是后设视角,是站在物质极大繁盛的今天向过去回望。倘若记忆是一帧帧照片,那么,这照片不是加了昏黄的“怀旧”的光晕,而是《五月回家》里偶尔掉落出来的全家福照片,“背景一看就是块画出来的布景,但画的是北京天安门。”⑦《黄雀记》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当祖父被送到井亭医院之后,他的房间租给了邻居马师傅,开起了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苏童是这样描写的,“时装店的面积虽然不大,却尽最大可能浓缩了时代的奢华,堪称时尚典范。墙纸是金色的,地砖是银色的,屏风是彩色玻璃的,柜子是不锈钢的,吊灯是人造水晶的,它们罗列在一起,发出炫目的竞争性的光芒”。金色、银色、彩色,不锈钢,人造水晶,今天看来,可能更多的是一股暴发户的气息,但那确确实实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尚。苏童通过“是……的”句式的反复运用,透露出些微的反讽的意味。文学史上有一个词叫“以乐景写哀景”,这个细节可看作以奢华写破败的实例,预示了商品经济将要对香椿树街的彻底改造,传递了处于夹缝时期的躁动不安的氛围。
倘若是仅仅是破败,或许是不值得追述的。苏童为这一时间点染的另一层色彩是属于少年人的活力与青春。整部小说弥漫着浓浓的荷尔蒙气息,电影院、工人文化宫的旱冰场是荷尔蒙聚集之地,或者这么说,这部小说的关节点就是属于青春的莽撞与冲动。如果没有保润和仙女的约会,就不会有八十块钱旱冰鞋押金的争端,没有八十块钱的争端,也就没有对兔子的处置,没有对兔子的处置,就不会有小拉之约,没有小拉之约,就不会发生水塔里的暴力事件,也就没有三个人的命运大挪移。在苏童笔下,年轻人因为无所事事,常常混迹于街头,街头就成了年轻人获得社会启蒙的最佳场所。在绵延不绝的暴力事件中,在对异性的小心揣测和打量中,一代代少年终于走向成熟。这是独属于一个时代的景观。
显然,对于一个时期的描述,每个人都可能据于个人经验而不同。对于青春期的回望则容易陷入浪漫或者悲情。苏童的意义在于摆脱了单一的语调,将一段时光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来,赋予其价值。这个“七八十年代”是属于苏童个人的,大时代是隐匿在身后看不见的背景,小青春是活跃在香椿树街上的嘈杂声形。它们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耦合在一起,散发着无尽的诱惑,也让苏童一次次回到过去,去追忆曾经的好时光。建立价值——时间范畴,是作家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文学,也似乎天然是为此而存在的。顺便说一句,苏童所建立的这一价值——时间范畴影响了其后的一些被命名为70后的写作者。比如徐则臣的“花街”系列,截取了“香椿树街”的“水”的元素,在弥漫着潮湿混浊的水汽的氛围中,去寻找少年木鱼的命运。在徐则臣的这些小说里,显而易见苏童的影响,悠远、暗淡、迷离……他和苏童一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精致、颓靡的旧日世界的远去,心存悲伤,却无能为力。路内则将“香椿树街”上少年的无聊与暴力挪到戴城,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努力向苏童学习,如何将一段青春讲述得既诗意充盈,又每每用狂欢、调侃、戏谑、反讽等多种方式将叙述带离感伤的边缘。可以说,这种引而不发的饱满状态,构成了苏童式的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指出苏童的两位学习者并不是为了证明作为作家的苏童多么伟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苏童为一个年代所赋予的价值很可能将成为一种文学传统,通过写作者的笔墨逐渐传递下去,直至最终形成另一种集体记忆。
二、回到“苏童”自身
“回到家乡”并不仅仅意味着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少年记忆,还意味着回到熟稔的写作天地。假设苏童作品的粉丝阅读《黄雀记》,是会感到分外亲切的。曾经熟悉的各个符号和意象纷至沓来,汇集到这部长篇小说里。
比如仙女这个人物。研究者热衷于谈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但这些女性更多的是指向《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这样的女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女性与女性对峙时候的各种小心思、小手段、小把戏,也惊骇于女人非要置女人于死地的那份狠毒。这是苏童的一类作品。事实上,苏童写的更多的还是仙女这样的女子。怎么形容她呢?还是用苏童自己的话吧,“她像一丛荆棘在寂静与幽暗里成长,浑身长满了尖利的刺。”这简直要从小说走向诗歌了。这一类女子必然是美的,这美丽能令这女孩子从嘈杂的香椿树街的背景上凸显出来。当然,因为跟香椿树街有着脱不了的干系,所以,这美,大多也有几分泼辣、市井的气息。你也能猜出来,像这样的女子,一定会是香椿树上的少年心目中的女神。讲述蒙昧时期暗恋的、单恋的故事从来都是苏童的拿手好戏。他能在细腻的描写中让人真切触摸到少年矛盾而纠结的心理。当然,如你所想,所有的暗恋大多都无法结成正果。少年们眼睁睁地看着心目中的女神长成了别人树上的果子。他们仅仅只是旁观者,波澜壮阔的人生大戏是只有这样美丽又妖娆的女子才有资格出演的,虽然,结局都不是那么好。荆棘一样的仙女就是这样。她在保润的单恋中旁若无人地盛开,或许因为对自己的美太自信,也或许是对单恋者的感情太笃定。但是这样的美势必是要被毁灭的,仙女也会在青春躁动的力量冲击下凋零。很多年过去了,仙女成了白小姐。这不能不说是悲哀的事情。在《黄雀记》中,苏童续写香椿树街少年的故事,看着他们如何在人世里沉浮,如何身不由己,被错愕的命运一步步推至原来不可想象的境地。怒婴的出现将结尾有了几分寓言的色彩。顺便说一句,苏童也擅长以婴儿为题作文。就我视力所及,就有《拾婴记》《巨婴》,似乎在他看来,婴儿就是人间的奇迹。还回到《黄雀记》。事实上,这样的题材在苏童具有创作道路上具有典范意义。不信,请看使苏童成为苏童的第一篇作品《桑园留念》,已经天然地包含了《黄雀记》中所有元素。像丹玉,就以“一双乌黑深陷的眼睛”深深留在了少年的记忆,包括突然的死去,使生命豁然敞开一个黑洞,呈现在未经世事的少年面前。谁又能说,仙女的身上,就没有丹玉的影子呢?
还有马。马在《黄雀记》里的出现简直有如神助。白小姐需要柳生去为她追债,追债的对象是马戏团的驯马师瞿鹰,也是白小姐曾经的恋爱对象。于是,就有了马在香椿树街上的出现。马的出现,使香椿树街多了些许“玄妙的诗意”,特别是白马在清晨的香椿树街上奔跑的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苏童的一部短篇《祭奠红马》。似乎“马”这一物象是苏童必须借助的“道具”,有了这样的道具,苏童就可以实现对现实的变形,带我们到一个既实又虚的世界里去。
细究起来,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小说的结构。《黄雀记》分为三章,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个人物,分别对应了三个季节。如果从季节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苏童非常注重引入季节元素。这一点,已然为研究者所发现。有论者说,“苏童小说中,季节变化是最为重要的标志,它远远地超过了外部历史事件的变化对人事的影响。”他举出的例子有,《肉联厂的春天》顾名思义写的是春天,《我的棉花,我的家园》写的是夏天,《樱桃》写的是秋天,《三盏灯》写的是冬天。对此,研究者的解释是,“季节的更替在苏童那里具有某种神秘的与生命状态相对应的意味。季节变迁,大自然胎息转寰,对应着人事的变迁折转。这不仅因为季节的气候性力量,也因为人事轮回与季节轮回的天然对应。”⑧简单点说,季节就是一个隐喻,象征了人事的繁荣枯衰。所以,单单从章节题目上,就可以理解小说人物的境遇。“保润的春天”是说保润为青春蓬勃力量的掌控而不能自持,“柳生的秋天”解释了柳生在躲过牢狱之灾之后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的景况,“白小姐的夏天”是在暗示仙女也就是白小姐的人生繁芜,看似有无尽的可能最后却走到了未知的境地。用季节来对应人生,似乎也不是那么新鲜。不过,这也暗示我们,苏童可能不是一个线性史观的拥趸者而更可能是循环史观的信奉者,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一再回到自身的原因。
三、“短篇小说化”了的长篇小说
说苏童一再回到他自身,不是指责他在重复自己,事实上,作家总有自己特别关注的母题、意象与情节,他一辈子所关心的,可能就是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一遍又一遍的返回的过程中,他在不断整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但是,在阅读《黄雀记》的时候,另一个感觉攫住了我,那就是,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化”了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诸多短篇小说的集结,如果把许多小节拆开来读,会饶有趣味,但是,放在一起,似乎一加一的效果反而小于一了。这么说比较冒险,很可能会被质疑,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真的有质的差异吗?难道不能说,这样的长篇小说代表了未来长篇小说发展的趋势吗?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就我目力所及,国内关于文学体裁的理论实在乏善可陈。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分辨这其中细微的差异。
除了历史小说以外,长篇小说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就是如何处理当下现实。关于这一点,巴赫金的说法值得参考。在《史诗和长篇小说》一文中,他说,“长篇小说——是唯一在形成中的体裁,因此,它更为深刻、本质、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的形成。只有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能理解形成。长篇小说之所以成了近代文学发展戏剧性变化的主要角色,就因为它能最好地表现新世界形成的倾向,其实,它——是由这个新世界产生并在一切方面和这个世界具有同样本性的体裁: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并正在预示整个文学未来的发展。”⑨“经验、认识和实践(未来)决定着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把探讨性,意义上特有的未完成性及与未定型的形成中的现代生活(未完成的当前)的生动接触带到它们里头。”⑩巴赫金是将史诗作为比较对象,因为史诗所讲述的是“绝对的过去”,必然与作者和听众隔着一段史诗距离。倘若把比较的对象换作短篇小说,也是不难理解的。短篇小说大多写的是一个场景,一个画面,是静止的,而长篇小说则不同,它须得写出人物的时间变化,所以长篇小说的时间是绵延的,势必会跟当下有所接触。关于如何写当下生活的问题,俨然成为中国作家的死结。与《黄雀记》差不多同时推出的余华的小说《第七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一个明证。评论家陈晓明分析说,中国作家处理现实问题一直相当困难,这是1949年以后落下的病根。他认为中国作家一直是在规定的观念情境中处理现实问题。苏童本人对此也很是踌躇。他屡屡谈到,“写当下其实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当下的问题提炼成永恒的问题,可以囊括过去和未来,这倒是个问题”。“急于拥抱现实而去发言的时候,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会白费。”事实上,像余华和苏童这样经过先锋洗礼的作家,已然不可能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像时下许多作家那样,老老实实贴着现实写。就是写现实,他们必然会有自己的姿态和角度。苏童自己的说法很形象,他说,“我投向现实的目光不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我转了身,但转了90度,虚着眼睛描写那个现实”11,在《黄雀记》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他处理过去的时光的时候,他立刻陷入一种真诚的怀念中,就连青春的暴力都那么迷人,举个例子,小说是这样写保润将仙女捆起来的情景,“一,二,三,数十二下。一个少女神秘的肉体世界被镇压了,那个世界天崩地裂,发出喧嚣的碎裂之声,碎裂声穿透她的皮肤,穿透她的身体,回荡在水塔里。四,五,六,数十二下,莲花在她的身上开放了。他的手上留下铁链子冰冷的触觉,还有她皮肤上的体温。七,八,九,十二下,数十二下,数十二下,莲花结上的莲花渐次开放了。”那么美的文字,倘若不仔细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是在描述一个少女被捆绑起来。如果说,作家在描绘过去的时候主要运用了写意的笔法,那么,当笔墨一旦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就漫画化了。白小姐带着小姐们为郑老板庆生就是一例。这就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效果:现在与过去的区别,是通过漫画与感伤的对比体现出来的。这大概也正是作家所传递出来的情绪:当下于我们是荒诞的。青春消逝在过去的时光里。至于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无处可追寻了。这样的美学效果究竟如何还可以在讨论,但至少,巴赫金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苏童这里止步了。
苏童在长篇小说里亟待解决的另外一点是深度模式的问题。陈福民在《长篇小说和它的历史观》中指出,长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蔚为大观的辉煌奠基于18世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了它的巅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哲学基础。这种历史哲学相信:世界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完整的过程,通过对诸种事情、流程的清理分析,就可以透过纷乱事态抵达世界的“绝对精神”。史诗性、厚重、历史进步、大容量的社会生活等等,这些因素正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哲学观念之下才成为长篇小说的刚性规定。这个欧洲传统,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一般来说,短篇来源于对日常生活偶然性和叛逆性的发现,长篇则来源于某种伟大的理念和关于世界整体性的思考12。由此可见,长篇小说有其质的规定性,读者需要作家通过长篇小说提供一个新的关于对世界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黄雀记》在整体性上贡献不大。它有没有对社会的思考呢?显然有。比如祖父的丢魂可隐喻为灵魂的迷失,再比如保润为祖父打的民主结、法制结,读者读到此大概会会心一笑,认为该隐喻暗示了中国社会的状况。问题在于,这些隐喻巧则巧矣,但大多单兵作战,无法构成集团力量,彼此声援彼此补充,也无法将现实的历史进程包容于自身。这就是为什么《黄雀记》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化”了的长篇小说。
从这个角度上讲,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以挑剔。比如从目前小说的材料上看,可能撑不起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保润、柳生和仙女的少年往事,线索显得单一,即使作家又旁逸斜出,写出了柳生、白小姐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人生遭遇,写出了保润出狱之后三人的关系,但依然稍显单薄。再比如结构。中国作家在处理长篇小说结构的时候总显得力不从心。除了依据时间线索推进以外,我所能看到的在结构创新上做得最好的当属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苏童以“季节”安排小说的结构,已是别具匠心,但也算不得多么新鲜。远的不说,在同为南京籍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中,就实践了从六个经验主体出发依次讲述故事的结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趣。
在阅读《黄雀记》的时候,我时时驻足,感叹苏童有着远胜于常人的记忆力和感受力。在这个时光飞逝,“崇新”成为时代最高准则的今天,他固执地怀念着少年时期,怀念着记忆深处的昨天。这似乎与一路高歌凯进的社会格格不入。但奇怪的是,作家苏童依然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被一部分读者心醉神迷地阅读着。是文学史惯性使然吗?我不知道。也许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所需要的正是一个看似古旧的故事。也许所谓的过去里正埋藏着我们的未来。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黄雀记》文本,均出自《收获》2013年第3期。
②⑦苏童:《五月回家》,载《人民文学》2003年第5期。
③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见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21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苏童文集·少年血·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⑤王德威说:“检视苏童这些年来的作品,南方作为一种想象的疆界日益丰饶。南方是他纸上故乡所在,也是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走笔向南,苏童罗列了村墟城镇,豪门世家;末代仕子与混世佳人你来我往,亡命之徒与亡国之君络绎于途。南方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而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参见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载《读书》1998年第4期。
⑥张清华说:“……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城市边缘地带的特有景观。所以说,在当代的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个能够像苏童这样如此丰富地书写出一个城镇生活的风俗图画,当代的图画。”参见张清华:《天堂的哀歌——苏童论》,载《钟山》2001年第1期。
⑧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⑨⑩巴赫金:《史诗和长篇小说》,见《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靳戈译,300、308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11苏童、张学昕:《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 见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2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陈福民:《长篇小说和它的历史观问题》,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长篇小说艺术论》,164—166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岳雯,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