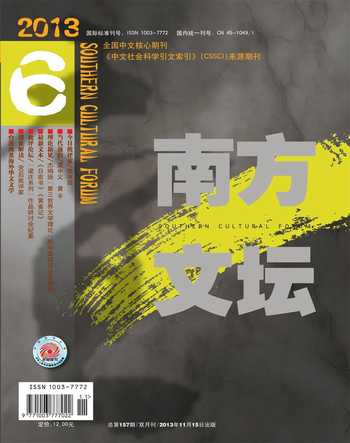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第三世界文学”:“寓言”抑或“讽喻”
2013-04-29姚新勇
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但也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的引进关系甚密,而张京媛翻译的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以下简称《第三世界文学》),就是一篇影响重大的西方汉译文献。它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领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直接作用于了中国本位价值、中华性知识范型的建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说”的误译,有着复杂而悖论的联系。
一、误译的“民族寓言”观
(一)因误译而致的喧宾夺主 “寓言”,《辞海》的解释为:“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散文或韵诗的形式,讲述带有劝喻或讽喻意味的故事。结构大多短小,主人公多为动物,也可以是人或非生物。主体用意在惩恶扬善,多充满智慧哲理。”①不过《第三世界文学》一文所谓的“民族寓言”说之寓言,并非体裁,而是指第三世界文学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内在品质,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学作品对某一民族的观念、品性、精神、命运的表达,对于民族使命的承担。因此所谓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集体性、政治性,也更具有观念性、抽象性、象征性与神圣的使命性。但杰姆逊真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认识第三世界文学的吗?
汉语“寓言”一词的英文对应词一般有三个,分别为fable、allegory、parable,出现在杰姆逊原文中的只是前两个,除了当allegory与fable同时出现于一段落的情况,张京媛将它们都译成了“寓言”。allegory及其变形(allegories、allegorical、allegorically、allegorization)②在杰姆逊原文中一共出现了三十三次,所有与所谓“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相关的表述在原文中用的都是allegory,而fable只出现了四次。很显然,仅仅是根据它们所占份额的巨大差异,这样的处理就是不恰当的,更何况fable在原文中的含义基本就限于体裁的意义。
杰姆逊原文第一次出现fable是在第二十五自然段。此段提到了鲁迅的《呐喊·自序》,杰姆逊用the little fable(那则短小的寓言)来指称《呐喊·自序》中“铁屋子”的喻说③。fable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三十八段,虽然这次它不像头一次那样被明显地用于“体裁”的意义,但根据前后文,也基本可以推断此处所指仍然接近具体的作品④。而且很可能是怕读者混淆fable和allegory,杰姆逊紧接着写道:With the fable,however,we are clearly back into the whole question of allegory.⑤
很明显,杰姆逊在提醒读者,要想更好地了解讽刺性的fable,必须返还到与allegory相关的整体性的问题中去。也就是说,fable归属于allegory的范畴。但是这句话的张译却是这样的:“谈到寓言,我们明显地又回到了关于讽喻(allegory)的问题上来。”孤立地看,这次将fable译为“寓言”而将allegory译为“讽喻”是正确的,但这偶然的正确,却造成了更大的偏差。因为在整篇文章中,张京媛基本将allegory都译成了“寓言”,而现在突然又译为“讽喻”,结果是把从属性的fable替换成了被误译为“民族寓言”表意系统的主词,而将此处的allegory从此系统中排斥了出去,造成了喧宾夺主的结果。
更明显的一处错译是对原文第四十二段中一句话的翻译,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perfectly suitable to the allegorical fable as a form”⑥,张译为“在寓言形式中仍然很合体”。如果依照张京媛将allegory和fable都理解为“寓言”,那么这里不就应该译为“寓言性的寓言”了吗?为了避免因误译而带来的床上架床的问题,张译只好去掉了一个“寓言”。其实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对于讽喻性虚构这种形式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二)被系统误译了的核心词 “民族寓言”的表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族的品性、精神、命运、使命等本质化、抽象性、象征性的意涵,而且国人对此概念的使用也基本如此。但在杰姆逊原文中,勉强可以从抽象的观念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的allegory只有两个,分别是第一和第三十二个;另外根据行文的需要而作为一般性指代的allegory有六个,分别是第五、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个;其他二十五个均在以下意义上使用:“跨文化比较”、“矛盾的悖论性文化生存语境”、“悖论性文化生存语境的具体文本呈现”、“悖论的、断裂性的表现形式和结构”等。它们构成了allegory在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以下简称:Third-World Literature)文本中基本的表意结构系统。即作为“矛盾、悖论、反讽、结构、形式化、语境性”等的表意结构系统,且此系统还将前两类用法纳入其间。杰姆逊自己也明确指出,他用national allegory来把握第三世界文学,具有特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用意⑦。所以显然应该将allegory译为“讽喻”更为恰当,因为“讽喻”要比“寓言”更能表现悖论的反讽性张力。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做进一步地论述。
其一,杰姆逊不是在普遍、泛指的意义上来谈论第三世界文学的,而针对的是第一世界的问题或文化语境。作为认识论术语的national allegory的提出,首先针对的就是第一世界的读者,所涉及的直接问题是他们应该怎样去阅读第三世界文本。杰姆逊指出,西方读者要想正确解读第三世界文学,既要破除习惯的西方文学标准的神话,同时更要认识到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文化语境的巨大差异。此差异不仅意味着要求第一世界的读者设身处地地从第三世界文化语境出发去理解第三世界文本,更是要通过跨语境的阅读(对话),激活第三世界文本之于第一世界的批判性与革命性。这种比较阅读的视野,被杰姆逊贯彻始终。因此杰姆逊才把第三世界文本的“民族讽喻”之特殊性与按照讽喻性的方式去阅读相提并论:“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地是讽喻性的,并有其特殊的方式;应该把它们作为民族讽喻来读。”⑧也就是说,第三世界文本并不必然是民族讽喻的,它们在相当意义上是按照讽喻性的方式被读成民族讽喻的。进一步说就是,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并不一定会按民族讽喻性来写,但他所处的语境,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他和他所在的语境共同生产出来的文本(是文本,不是作品)必然是讽喻性的。
其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或心理机制所形成的跨文化的对照(对话)性讽喻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识论要求贯穿Third- World Literature始终,成为其核心链,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语境既表现为意识或无意识层面的差异,也表现于两个世界的文学文本的表述方式的差异。
具体而言就是,在第一世界中,“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⑨;而在第三世界那里却恰恰相反,文本中的个人和利比多趋力, 总是以民族讽喻的形式,投射出政治的维度,有关个人命运私人性的故事,“也总是公共性的第三世界文化和社会的困扰之状的讽喻”⑩。不过杰姆逊告诉我们,不应该将这两种文化心理机制的差异本质化理解。实际上,与其说这类第三世界的“讽喻性结构不存在于第一世界的文化文本中,不如说它们是无意识性的,必须通过一种能够对我们目前第一世界的情况进行整体性的社会及历史批判的诠释性机制来解码”11。而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讽喻”性的解读,恰恰就是要为已经失去了公共批判性的第一世界文化引进或激活这样的诠释性机制或批判的纬度12。也正因为此,杰姆逊才说,“我本质上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来使用‘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我不认为反对这种用法的意见同我正在进行的辩论有特别的关联。”13
其三,第三世界作家本身所处的悖论的讽喻性文化语境以及第三世界文本表述与此语境的同构(或互文性)关系。对此杰姆逊分别列举了三位作家对比分析,他们分别是中国的鲁迅、西班牙的小说家班尼托·皮拉斯·卡多斯以及塞内加尔小说家兼电影制片人奥斯曼尼·塞姆班内。就杰姆逊文章所讨论的主题看,他们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即悖论的讽喻性结构关系的一致。
在鲁迅那里,一方面是外来西方文化对传统中国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恐惧性的吃人文化的梦魇仍然普遍地存在,甚至欲推翻这种吃人社会的先觉者本身也成为被吃的对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当钱玄同向鲁迅约稿、希望他能够出来助新文化运动一臂之力时,鲁迅才构想出那个著名的讽喻性的铁屋子的意象:一个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坚固难以摧毁,里面的人都昏睡于此而“不久都要闷死”;先觉者的呐喊,并无从毁坏这铁屋子,反倒使“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而鲁迅的作品,就是这种矛盾的讽喻性语境的表述。或换言之,正是通过《狂人日记》《药》等一系列的悖论性作品的书写,作为一个清醒的先觉者与其无助的生存语境的讽喻性关系,才得以戏剧化地呈现。这些都是中国读者再熟悉不过的了。
杰姆逊引入卡多斯的小说,具有在西方世界文本和第三世界文本间搭起既区别又沟通的桥梁的作用。就沟通性来说,虽然卡多斯生活的19世纪的西班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缘性国家,但却具有介于殖民主义的英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其他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半边缘性,这恰恰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间性的存在状态14具有结构性的类似。因此,当在卡多斯的小说《佛吐娜塔和贾辛塔》中,男主人公处于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遇:“他一方面周旋于两个妇女之间(妻子和情人、中上层阶级妇女和‘人民妇女间),另一方面又在1868年的共和革命和1873年的波旁复辟之间狐疑不决,从而使其个性上打上了民族—国家的印迹。这里,我们在阿Q那里所发现过的‘漂浮不定或可转换性的讽喻式结构又再次出现:佛吐娜塔已经结了婚,而她又离开自己的合法家庭去寻找爱,可是最后她又返回到曾经放弃的家庭中,所以(阿Q的)在‘革命和‘复辟间的轮流选择,也适合于描述佛吐娜塔的处境。”15不过杰姆逊指出,与鲁迅等第三世界作家的作品不同,在卡多斯的文本中,讽喻性的结构远远没有使政治和个人或心理的特征得以戏剧化地突出,相反而是“趋向于用绝对的方式从根本上分裂这些层次”16。而这正表明了西方世界的心理无意识机制,如何驱动着作家与读者本能地分割公共政治与个人的关系。这一点通过卡多斯与奥斯曼尼·塞姆班内的比较就更为明显了。
在塞姆班内的作品《夏拉》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讽喻式或反讽性生存境况:男主人公哈吉拥有三个妻子,第三个还年轻漂亮,但他却是阳痿症患者,不得不到处去寻医求药。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哈吉以前是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者,因此蹲过监狱,但现在他却是一个帮助西方人剥削自己国家人民的掮客,这“明显地表明了独立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失败”17。在《夏拉》中,个人的心理、生理问题,再次与国家、民族等公共政治性的事务讽喻性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与卡多斯的作品不同,这种个人力比多与公共事物之间的讽喻性的联系,在塞姆班内的作品中得到了强烈、突出的戏剧性的表现。到处求医却得不到治疗的哈吉,最后被指引向一个“生活建立在团体相互依赖的原则之上”的村庄这一乌托邦性的隐喻,就充分显示了第三世界文本个人与公共事务之间存在着一种与第一世界的“观念十分不相同和客观的联系”18。杰姆逊不仅向第一世界的读者揭示这种联系,而且还从中看到了奴隶、被奴役者能够真正“勾画(mapping)或把握社会整体”的能力19。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这种集体性的乌托邦指向简化为抽象的“民族寓言”。请注意,《夏拉》中“过去的空间和未来的乌托邦——集体合作的社会”是“被嵌入独立后的民族或买办资产阶级的腐败和西方金钱经济之中”20,正是这种被嵌入的语境,决定了那还未完全消失的第三世界集体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但也同时决定了其意义的有限性与非本质性。而这就涉及了下一个方面。
其四,讽喻形式的不断变化性,讽喻性文本的能指与所指的不对应性。
杰姆逊将第三世界文本的讽喻性与西方浪漫主义讽喻(寓言)传统进行比较时指出:“讽喻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 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 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它的形式超过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过了现实主义本身。”21熟悉后学理论的读者会很容易看出此与西方后学理论的联系。然而很可惜,在我们这里,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否熟悉解构主义,他们在接受或质疑杰姆逊的这一文本或其他后殖民理论文本时,则往往对于这一点视而不见,从而使得本来应该是充满反讽张力与具体复杂语境性的“民族讽喻”的认识视角,在相当的程度上倒回到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寓言”时代,甚至倒回为“十七年”或“文革”时期的政治寓言性的写作。
二、误译的扩散与当代思维
话语范式的转型
(一)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观”张扬到“中华性”的诞生 中国主流文化界22对“民族寓言说”的接受与扩散,就思维话语范式的转换来说,集中发生于1990到1994年之间。这几年中,被误译为了“民族寓言”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逻辑纲领,被中国知识界进行了中国本位性的系统化理论改造。这又集中地表现于两个互为一体的方面:一是以主流/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改造或定位西来的后殖民、后现代等理论;二是使用被改造了的西方理论对中国现象进行再解释、再定位。
1990年张颐武接连在《文艺争鸣》《读书》《上海文学》等六家刊报上发表文章,热情推荐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主张“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深刻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寻找人类文化成长与发展的新的契机”23。
1993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设了“拓展理论思维,促进理论繁荣”专栏,邀请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以后殖民、后现代话语为主导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化现状24;《读书》杂志第9期也集中发表了四篇与后殖民批评有关的文章”;同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25。这些似乎是不约而同的行动,促成了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后现代话语及后殖民主义三者的并接。不过当时具体的文化指向还是比较复杂的。例如王岳川对利奥塔德的引介,重点不是突出后现代话语与现代主义的对立,而是让我们看到在貌似严重的对立中,后现代思想与现代主义或高级现代主义的相通性,从而突出后现代思维中的不懈的怀疑、批判精神26。李杨则试图通过后学思维方式的引进,既从民族国家叙事的角度,来更为弹性地理解自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传统,同时又将后学解构主义与传统的现代启蒙批判精神相整合27。
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但就基本的文化走向看,以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逻辑来改造后现代解构主义、固化后殖民批评、伸张中国价值,则成了主导的文化趋势。而在此进程中,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启蒙性解读被系统性地加以改造。
在此新的解读框架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文化传统,不再被视为由启蒙知识分子所开拓的伟大而艰难的启蒙传统,而成了全球化时代下的以西方文化霸权为主导、为中心的中/西二元对立话语逻辑的中国展开。这样,五四新文学就成了自绝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急躁”的不成熟的产物,白话替代文言则是对西方逻格斯中心论的臣服28;而鲁迅以降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成了西方学术话语的代言人,以傲慢的态度去对”人民行使“牧师的权力”,屏蔽、推延、扭曲、抹擦了“人民记忆”。只是进入到90年代以后,当商品化大潮涌来之时,新的历史才开始了,“人民的记忆”才得以在《渴望》等通俗文学的叙事中苏醒、恢复。虽然它们显得“世俗”“琐碎”,但却“朴素”“温和”,不再是“‘单一性的、直白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一种新型的人民“神话”。它既“与商品化的语言/生存状态相联系”,同时又可以将中国人引领向物质丰裕、“人伦关系”和谐的现代社会。从而既解决了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也最终想象性地解决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29。
当然并非所有的“后学”言说都如此乐观,但在重归传统、走向世俗、拥抱市场经济大潮的语境下,就连高调宣扬“先锋写作”“无边挑战”性的学者,此刻也暧昧地徘徊于“先锋”与“世俗”的模棱两可间,对“纯文学”坠于“自言自语”的命运发出嘲讽与哀叹30。而当1994年《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一文发表后,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历史,更被以“中华性”的名义所打量,不仅“中国话语”已经呼之欲出,而且中国价值为本位的超越臣服于西方“现代性”的“后新时期模式”也已然降临。
(二)学界的批评及其局限 被误译了的“民族寓言说”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相互嫁接而促成中国话语或中华性话语范式转型的过程,并非始终一帆风顺、毫无批评与质疑。首先所谓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就遭遇到了批评。学者们指出,他将第三世界文学进行了简单化、整体性、本质主义的抽象;想象性地取消了第三世界文学的复杂性与个性,用第一世界的白人声音替代了第三世界中国的声音,将中国及第三世界矮化成了西方世界的被动他者。很显然,杰姆逊的中国批评者并未发现“民族寓言说”的误译,而且不少也是站在第三世界中国/殖民主义西方之二元对立的逻辑上来发言31。
相较于对杰姆逊的批评,批评中国式“后学”言说的文章更多,它们大都较为准确地指出了批评对象所存在的问题。诸如,二元对立本质化地曲解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以中/西对立、对抗模式整体性地解读中国现象,实则回避中国现实问题,陷于“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的陷阱中还不自知32。不过这些批评也没有发现“民族寓言说”的误译,而且在批评中国学者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时,却往往在自己的文章中犯着类似的错误33。不少文章大都纠缠于西方理论的辨析和对中国同仁相关文字的批评,却很少能从中国文学现象,尤其是当代文学现象中,发掘出与“第三世界文学”及后殖民理论切实关联的现象。不过还是有少量文章显示出了批评的直面与深度。
早在1993年陶东风就以朴素的语言坚持80年代反专制的启蒙批判立场,他尖锐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潜藏着与现实的荒诞、虚无达成默契的危险性,‘它以一种宽容的姿态肯定了生活中的黑暗以致罪恶,这是一种极可怕的‘宽容。”34这比海外学人类似的批评至少早了两年35。而十四年之后,更多地汲取了后现代理论营养的陶东风,不再简单地将中国传统作为中国问题的替罪羊,而是在娴熟地对照、梳理西方理论与中国言说的同时,更为尖锐地揭示了紧接“八九风波”之后迅速走红的中国后学的犬儒主义与文化投机性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36。
另外,杨念群也以其历史学素养的严谨性和多学科视野的引入,作出了比文学圈中的“自我批评”更为到位的分析。例如针对所谓“人民记忆”被启蒙文学叙述遮蔽的看法,他指出,这并不是在释放“民众记忆”,而是将“西方理论作为背景资源”,“转化成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制度宰制方式,从而成功抑制了民众记忆的表达渠道”。所以,“目前迫切需要揭示和反思的是,来自民族—国家内部集团和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的关系如何影响到了民间基层社会的成长,而当权的利益集团又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掩饰新形式的压迫关系”37。
三、“误读”还是“新词”的游戏
上述考察表明,对Third-World Literature错译相当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但能否说这一现象恰好证明了跨文化交流中“误读”总是无法回避的,而且这里所进行的重读也不可能“真正”返回杰姆逊的原文,只能是新一轮“误读”的开始?加达默尔的名言不是说“并非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38吗?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误读呢?有人认为:“误读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39或者“误读”意味着,“在实践意义上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是以‘他者的‘存有来补充自己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中影像来肯定和确定自身。”40
两种解释一个“朴素”一个“哲理”,但都自觉不自觉地假设了一种主体性的“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关系。姑且不问作为“文化的主体”何以可能,其实这种主体性的设定,暗含着阐释者“主体”主观性与被动性的内在矛盾。作为主观性的主体,他或她似乎在跨文化翻译中有着纯然的主动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他者来肯定自我、确定自身。这样,被阅读的他者也就被视为了纯然的被动的客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超越于阅读主体的文化先在性的设定,又悖论地将此主体变为了文化、文化模式的被规定者。
其实在加达默尔看来,“误读”“偏见”或“前理解”之所以不可避免,并不是因为先于阅读而在的主客观文化条件对于主体的制约,而在于跨文化视域相互汇合时的“主体”的生成性,解释学就是“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41;跨文化交流或更广泛的文化接受中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带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主体对文化他者的阅读、打量、观看,而是主体通过不同视域间的对话方得以生成,而且生成的是时间或历史之流中的主体。因此“加达默尔突出的重点并不是放在某个主体对某种方法的使用,而是把历史根本的持续性作为既包括所有主体的活动,也包括主体所理解的对象的中介。理解是一种事件,是历史自身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无论解释者抑或文本都不能被视作自主的部分”42。虽然加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视界融合的目的指向,与后殖民理论所强调的“文化断裂性”相当不同,但在主体间性的指认上,两者是相同的。不管是对于跨文化交流或碰撞的看法相对更为积极、乐观的解释,还是更为悲观的后现代学理,对偏见或不可解释性的指认,既不是给所谓的主体留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对方、确定自我的任意性,也不是给不负责任的文化阐释行为,预留逃避他人或自我批评的通道。
但问题是,既然纯然正确的阐释并不存在,既然文化翻译、阅读、阐释者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工作的,我们又何以判定具体的文化阐释活动的性质呢?或说我们又何以区别哪些“误读”是包含着文化阐释者充分反思性的“误读”,那些是缺乏反思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错译、错读呢?或者干脆放弃判断,以所谓“后现代”的名义宣布,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误”之分,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谈。
对此福柯给出了有助于质询我们实践的三个反思性路径,其中之一就是“系统性”,它涉及三大领域和三条轴线之间的对应关系图式:
对物的控制关系领域:知识轴线
对他人的行为关系领域:权力轴线
对自身关系的领域:伦理轴线43
将此模式用于“质询”我们的认识实践活动就涉及如下序列的问题:“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操作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主体?”44或可以将此质询模式称之为“三领域轴线反思模式”。以此来检视《第三世界文学》的错译及其随后的扩散性传播,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至少许多人在知识轴线上,未能做到尽可能准确、全面、清晰、客观地理解认识对象;在权力轴线上,未能自觉全面、多角度地反思相关的阐释活动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努力厘清其所赖以展开的与权力相关的语境或结构性关系;而在伦理轴线上,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自我反思性。因此,或许在总体上可以将由《第三世界文学》的错译所引导的二元对抗逻辑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话语播散,定性为缺乏足够责任心及自我反思的犬儒性的人文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不能否定相关西方理论的引进,的确丰富了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理论“装备”,但其本质上,不过是一场玩弄“新语”的游戏:
“当我们复述着越来越长的翻译名词,从当年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历史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到眼下的‘后冷战、‘后殖民、‘后革命——‘后一切主义,仅仅因为它们正时髦,却根本不在乎那到底有什么含义。那么,谁能推脱作为‘新语缔造者的责任?我们能说一切,可什么也不意味!唯一的后果,只能是词、义彻底分裂。最终,唯一胜利的,是‘语言玩世不恭主义。它瓦解了思想。用词语的空洞,放纵了赤裸裸的权——利游戏。今天,泛滥空洞的政治说词,已经成了商业全球化的有机部分。”45■
【注释】
①《辞海》(普及本),450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②为简便,下面统一用allegory来指称该文中allegory及其变形。
③鲁迅《呐喊·自序》“铁屋子”的喻说,不过一百一十个汉字,称之为little fable是相当恰当的。fable的基本词义之一就是“虚构的寓言故事”。
④相关原句为:One is led to conclude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raditional realism is less effective than the satiric fable: whence to my mind the greater power of certain of Ousmane's narratives (besides Xala, we should mention The Money-Order) as over against Ngugi's impressive but problematical Petals of Blood.(Fredric82)根据前后文可以看出,这句话的大意思指,在杰姆逊所讨论的那种反讽、悖论、“讽喻性的(allegoricl)”语境中,讽刺性的寓言作品对于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效果,要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此处杰姆逊在fable前加上了satiric这个形容词,使得satiric fable一起有了接近allegory的含义,并且将奥斯曼尼的小说与努基的小说进行了比较。
⑤⑥Fredric ,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Autumn,1986).82、83
⑦19请参阅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一文注释26。
⑧1113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48、53、47页。笔者对这几处译文做了修订。
⑨⑩1617182021张京媛译:《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48、48、54、54、53、54、50页。
12在“单向度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中难以发现批判的社会力量,早在杰姆逊之前就困扰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4根据杰姆逊的论述,可以推论出三重第三世界的中间性:一是介于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第二世界的中间性;二是既取得了表面的独立但却以变相的新形式仍然处于过去宗主国的剥夺中。这两重中间性可以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基本的讽喻性语境。不过对于革命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还面临着另一重矛盾的境况:他们既要对外继续批判新帝国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必然与民族主义发生关系;但同时对内,他们又面临着反抗篡夺了独立果实的本国反动统治者的任务,他们的革命目标指向,又不能不是超民族主义的,所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学文本,就不能不是“民族讽喻”性的。
15这段引文笔者做了重译。原文中这段共出现了三次与“讽喻”相关的表述,一次是“民族讽喻(national allegory)”,另两次是“讽喻性的(allegorical)”,都是在悖论的语境或结构性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张京媛却不仅依然将它们译为了“寓言”,而且又延续了前面第二十五段对allegory和fable对译的误译,凭空加了一个“寓言(fable)”,又多了一次与其“民族寓言”的译法不相干的“讽喻”。所以,在其错误多出的译句中,仍然或多或少地消解着“讽喻”的语境或结构的悖论性特质。
22所谓“寓言性”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误译,在中国的影响还波及了少数族裔文学创作上,但因为问题比较复杂,将另文专论。
23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载《读书》1990年第3期。
24该专栏推出的七位作者分别是:王一川、张颐武、王岳川、王宁、王德胜、陶东风、陈晓明。此阵式已经囊括了以后中国后学弄潮儿的基本主力。
25该丛书由谢冕和李杨主编,除了张颐武的《在边缘处求索》,其中还有好几本也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说或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相关,如李杨、陈晓明、程文超的著作。
26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现象研究——后现代知识与美学话语转型问题”》,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27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8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29参见张颐武:《在边缘处求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3、81、96、12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晓明:《中国文化的双重语境》,载《文艺研究》1993年1期。
31例如郑敏:《从对抗到多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4期;韩毓海:《詹姆逊的企图——评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载《上海文学》1993年11期等。
32萨伊德语,转引自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33例如一篇题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第三世界文学》(收于2008年,“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的长达二十二页的文章,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还不到两页。
34陶东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35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
36参见陶东风:《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
37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二十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3 期。
384142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编者导言”,夏镇平、宋建平译,7、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
39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2期。
40陈跃红:《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见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3彭发胜:《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2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4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45杨炼:《诗歌跨越冲突》,根据朋友赠读的电子文稿。“新语(New Speak):乔治 奥维尔《1984》中的术语,指通过再造语言,完成思想专制的目的”(杨文原注)。
(姚新勇,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