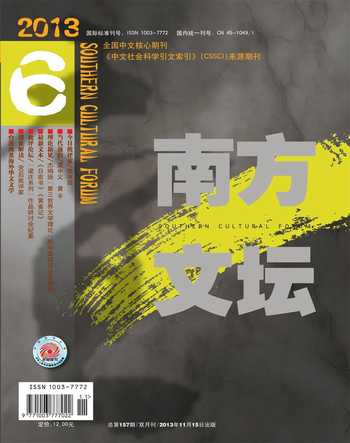走笔至此
2013-04-29郭冰茹
郭冰茹
“在古典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回的蜻蜓”,这是余光中的诗句,专治古典文学的同事将它做了自己的个性签名借以抒怀。我虽不治古典,但迷恋书卷,所以,若将此句中的“古典”二字改为“书卷”,也颇能表达我若干年来埋首案头的感受。
自我以文学为专业、继而为职业以来,我的不少同学、同事和朋友被我戏称为文学行动者。他们写诗、写小说、写剧本、筹建文学社、出版自己编辑的文学刊物;他们热烈地讨论心仪的作家,充满激情地参加诗歌朗诵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改编或创作的剧本搬上大大小小的舞台……。然而,我不属此列。我虽兴趣盎然,却喜欢安静地驻足观看,如同翻阅一本书,看一出戏。
我的兴趣在阅读。举凡“杂事”“异闻”“琐语”或是文学专业所要求的理论和文本,我都愿意去涉足,或者手不释卷,或者浅尝辄止。前些日子读林岗老师《口述与案头》,书中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对于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最现实的追求‘不朽的方式,其实就是埋首案头,摇笔不辍。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对于受过良好文化教养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不仅容易做到,而且日益亲切而有味。现实的人生路,越走越拥挤逼仄,越走越艰难险阻,而文字里的人生世界则反其道,越来越宽阔和丰富。虽然这个可以无限驰骋和展开的世界是虚拟的,是不真实的,但正因为这样而越来越对文人士大夫有吸引力。”我虽无意于在书卷中逃避现实人生的琐碎和沉重,也没有追求“立言”以“不朽”的伟大理想,却享受文字世界带给我的那份自足与充实。
我喜欢宁静、心无旁骛的读书的状态,品味文字、玩味史料、沉醉其中。也正因如此,我将自己归入那类很少介入文学批评前沿、深入文学生产第一线的研究者。若果参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批评家”不仅仅是及时跟踪当下文学创作并能迅速作出反应的书评人,还接纳更广泛的文学研究者,那么我非常荣幸能被囊括其中。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尝试辨析“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三个概念,同时也指出这三者之间的互相支撑和密不可分。如果具体到文学批评,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总会或多或少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他所信服的文学理论,开展创造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换言之,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既能体现出作者的史家眼光,显示出作者的理论素养,同时又不失锐气、才情和锋芒。
在文学批评日益“学院化”的今天,我钦佩那些能对当下文学创作发言的学人,他们不遗余力地做着披沙拣金、海中采珠的工作。这些及时的批评文字或许不能完全禁得起时间的推敲,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艰辛的工作积累,当下的新人新作才得以浮现。但我想,一个好的批评家当不仅仅满足于此。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谈作品并非批评的全部,批评家的工作应当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发现、揭示并阐释文本与现实、文本与文学史、文本与读者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同时作出判断和引导。
我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