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桥,珍贵的幻觉
2013-04-29史航
史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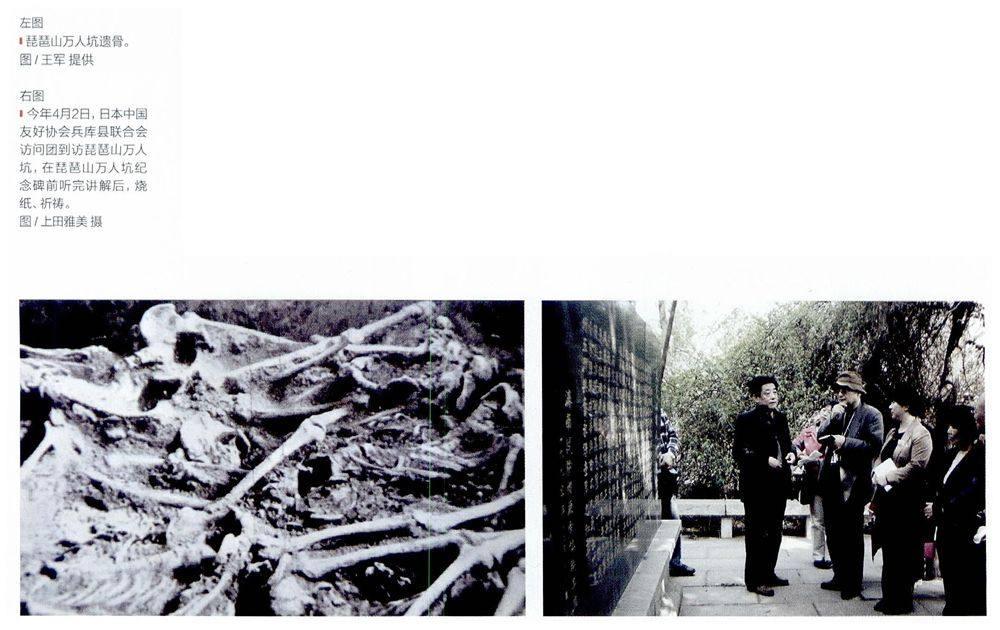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侵略者闯进我家乡;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抄下这歌词,似已听到口哨声,好像黎明破晓,正该上路登程。当年这歌都进了杨振华金炳昶的相声《下棋》,此刻回想,却未沾染一点油滑,只觉得它来自最高贵的战争电影,最动人的敌后穿梭。
首先难忘的是守桥德军的两位长官的舌战,霍夫曼博士:“请允许我问您,战争开始您是什么军衔?”冯菲尔森上校:“上校。”“战争开始我只是一个党卫军上尉,战争是发挥一个人才能的好机会。”“如果他能活得长的话。”“您不是还活着吗?”“我受过四次伤。”“三次,是三次,第四次您不过被炮弹震了一下。”
这边的轻蔑你若学不到,可以学学游击队那边如何挑选战士。主人公老虎本来在休假(那时的游击队还能休假!)现在要挑选部下去敌后炸桥。三个战士习惯的武器分别是刀子,绳子,枪。你只要记住那个喜欢刀子的就行了,他叫迪希,可我们同学间都喊他刀子。
老虎只挑了迪希,然后去找炸桥专家、意大利人朱塞佩·扎瓦多尼。他和小徒弟班比诺在一起,每次爆破前他们都要叨咕:“好运气,班比诺。”“好运气,扎瓦多尼。”扎瓦多尼对迪希有点不以为然,见面午餐,他问人家:“朋友,你吃吗?”回答是慢吞吞的,我特喜欢模仿的:“有就吃。”扎瓦多尼问老虎:“他会干什么?”“什么都能干。”“可是他会笑吗?哎,朋友,给我刀子。”迪希不动声色,刀子就飞过来了,扎在饼上,扎在意大利佬的手指间。哼哼。
现在要找建筑这座桥的工程师。可他“跟自己都不合作。他连茶杯都不会打碎,还会炸毁他的桥?”老虎赶到工程师家,盖世太保正要带走他。工程师看着这一番恶斗,然后郁郁寡欢地问:“我该荣幸的跟谁走呢?”虽然一起上路,但工程师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被挟持的人质。当他知道此行是为了炸他的桥,就溜了,而班比诺为了找他,陷入德军包围圈。扎瓦多尼别无选择,他刚才还说:“圣母啊,好艰难的一天啊。”现在他长嚎一声:“好运气,班比诺!”然后扔出了炸药。
这一刻太难忘了,玉石俱焚。几年后,导演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也出现了抗日土匪瘦烟鬼,被迫开枪打死要落在日军手中的女卫生员的情节。
游击队落到了德军手中,审他们的军官叫猫头鹰。他带来全片最精彩的台词:“先生们,你们这趟旅行得不错啊……我给你们看看手相……这是一个杀过人的手,一个老兵和多年流浪汉的手……这条纹能干大事,但是寿命短,我预言你的桥要比你寿命长……请你把手放下吧,女人的心思我总是捉摸不透……从餐厅给他们拿饭吧,我付钱。”
游击队还是逃出来了,他们来到桥的面前。工程师眼睛亮了:“变漂亮了,跟峡谷融为一体了。”竣工后,他就没来过这里。因为班比诺的死,歉疚的工程师决定跟大家到桥上,但不参加炸桥。
可是扎瓦多尼被击中,最后能按下把柄炸桥的,只有工程师,而且,引线卡在石缝里他甚至只能站在桥上炸桥,与自己的桥同归于尽。
再见了,美丽的桥,你被霍夫曼的勤务兵形容为“像个屁股,像臀部”,但你依然是一座美丽的桥,一座美丽而不复存在的桥。
《桥》的姊妹篇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演员班底相同,那也是个好电影。若你都还没看,建议先看《桥》。然后你会发现,桥上桥下牺牲的人,在萨拉热窝复活了。
这是一个令人无限感激的珍贵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