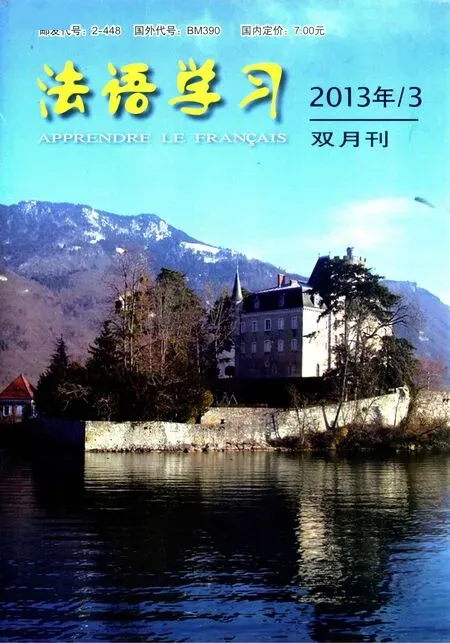梁宗岱论象征主义、自由诗和纯诗
2013-04-18福建师范大学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 彭建华
梁宗岱论象征主义、自由诗和纯诗
●福建师范大学 彭建华
法国象征主义是一场发生于18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革新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法语自由诗发生在浪漫主义时期,1880年代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促进了法语自由诗的迅速发展。1890年代马拉美则鲜明提出了纯诗理论。此后,迪博、瓦莱里促进了纯诗理论的发展,诗歌音乐性则成为其核心观念。基于白话新诗建设的目标性批评,梁宗岱在论述象征主义的同时,也论述了自由诗和纯诗。
象征主义,纯诗,自由诗,音乐性,梁宗岱
一、引语
虽然魏尔伦、莫里斯、瓦莱里先后否认象征主义是一个独立的文艺运动,19世纪象征主义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莫雷亚斯《象征主义宣言》写道:“作为教训、诵读法、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描述的敌人,象征主义诗歌追求的是:给观念提供一个敏锐的表现形态,这个形态却不是探索的目的,然而它有助于表达观念,且从属于主观。”(Moréas,1886)居斯塔夫·康《自由诗·序言》认为,象征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年轻的象征派诗人高举纯诗的理念,发起了对自然主义的反动。(Kahn,1897)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人们(最初是穆木天、王独清等人)把自由诗和纯诗看作象征主义的重要方面,这无疑包含了某些对法国文学的误解。
二、梁宗岱论象征主义
梁宗岱多次论述过法国的象征主义,1928年《保罗梵乐希先生》写道:在自然主义和帕尔纳斯派衰落的时候,象征主义的新奇的诗歌,“有如一座神秘的幽林底飒飒微语,它底呻吟,它底回声,甚至它底讥诮,都充满了预言与恐吓,使当时文坛底权威悒悒然预感他们底末运。表面上看来,那一般青年诗人底言行,至少在当代人底眼光里,不免调侃与嘲讽底嫌疑。其实他们态度之严肃,求真求美的热诚与恳挚,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没有与之比肩的。”(梁宗岱,2003:7)这些含混的抒情文字,大抵比较近似1880年代象征主义发生的情景。梁宗岱还指出,“当象征主义——瑰艳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在法兰西诗园里仿佛继了浮夸的浪漫主义、客观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后,忽然在保罗·梵乐希底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2003:11)显然,梁宗岱认识到法国象征主义运动是在1895年前后衰落的事实。
梁宗岱在《象征主义》中写道:象征主义“在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乏的普遍和重要的原素罢了。这原素是那么重要和普遍,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一切最上乘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一首小诗或高耸入云的殿宇,都是象征到一个极高的程度的。”(2003:68)梁宗岱较大程度上移用了瓦莱里的观念,“所以我们无论读他底诗甚或散文,总不能不感到那云石一般的温柔,花梦一般的香暖,月露一般的清凉的肉感——我并不说欲感,希腊底雕刻,达文希底《曼娜李莎图》,济慈底歌曲,都告诉我们世间有比妇人底躯体更肉感的东西,而深沉的意义,便随这声,色,歌,舞而俱来。这意义是不能离掉那芳馥的外形的。因为它并不是牵强附在外形底上面,像寓言式的文学一样;它是完全濡浸和溶解在形体里面,如太阳底光和热之不能分离的。它并不是间接叩我们底理解之门,而是直接地,虽然不一定清晰地,诉诸我们底感觉和想象之堂奥。在这一点上,梵乐希底诗,我们可以说,已达到音乐,那最纯粹,也许是最高的艺术底境界了。”(2003:18)梁宗岱显然超出了瓦莱里,把象征追溯到波德莱尔的“应和”论(correspondances),“像一切普遍而且基本的真理一样,象征之道也可以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2003:68)梁宗岱认为波德莱尔揭示了一个玄学上的深刻基本真理,即“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其实只是无限之生底链上的每个圈儿,同一的脉搏和血液在里面绵延不绝地跳动和流通着”。(2003:13)梁宗岱进而引入流传于古典中国的佛教的象征论,“因为这大千世界不过是宇宙底打灵底化身:生机到处,它便幻化和表现为万千的气象与华严的色相——表现,我们知道,原是生底一种重要的原动力的”(2003:13)梁宗岱进而把“象征”运用到歌德《神秘的和歌》(Chorus Mysticus,Faust II)和《流浪者之夜歌》、《诗经·小雅·采薇》、陶渊明《饮酒》、杜甫《登高》、林和靖《山园小梅》等古典诗歌。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评论瓦莱里《水仙辞》时,指出,“在一首诗中吟咏数事,或一句诗而暗示数意,正是象征派底特别色彩”。(2003:13)
基于多层面折中的象征观念,梁宗岱把西洋“象征”和《诗经》与《文心雕龙》中的“兴”比附/归属为同义,这似乎是更为合理的中西打通。梁宗岱反复申述宗教式的神秘性,甚至于《象征主义》有一个宗教祈祷般的结尾:但丁《神曲》最终融成了一片颂歌底歌声或缕缕礼拜底炉香;波德莱尔的每首诗最后却是整个破裂的受苦的灵魂带着它底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并凭借着这呼唤底结晶,而飞升到那万籁皆天乐,呼吸皆清和的创造底宇宙:神奇的、崇高的、完美的、一致而调协的、不可言喻的世界。(梁宗岱,2003:78-79)
三、梁宗岱对白话自由诗的矛盾态度
在法语诗歌的进程中,自由诗(vers libre)发生在浪漫主义时期,1880年代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促进了法语自由诗的迅速发展。大抵接受了英语素体诗(blank verse)和自由诗(free poetry)的影响,年轻一代的象征主义诗人是自由诗的积极而富有成就的创作者,例如兰波、居斯塔夫·康、拉弗格(Jules Laforgue)、维勒-格里芬(Francis Vielé-Griffin)、科里森斯卡(Marie Krysinska)、萨尔曼(AndréSalmon)、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瓦莱里等。在象征主义群体之外,杜雅丹(Édouard Dujardin)、布洛瓦(Léon Bloy)、波希(Saint-John Perse)、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米肖(Henri Michaux)等也创作了自由诗。梁宗岱在《保罗哇莱荔评传》中称克洛岱尔是提倡和创作自由诗最力的作家。
1931年梁宗岱在《论诗》中,在与梁实秋的争辩之外,基本肯定了古典自由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歌德《流浪者之夜歌》等)和初期的白话自由诗。而后,1935年《新诗底十字路口》却表示反对白话自由诗,如果白话新诗选择自由诗的道路,便只是“和欧美近代的自由诗运动平行,或者干脆就是这运动一个支流,就是说,西洋底悠长浩大的诗史中一个支流底支流。这是一条捷径,但也是一条无展望的绝径。”(梁宗岱,2003:156-160)梁宗岱进而提出为白话新诗发现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理由是“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梁宗岱写道:“这并非我们无条件地轻蔑或反对自由诗。欧美底自由诗(我们新诗运动底最初典型),经过了几十年的挣扎与奋斗,已经肯定它是西洋诗底演进史上一个波浪——但仅是一个极渺小的波浪;占稳了它在西洋诗体中所要求的位置——但仅是一个极微末的位置。这就是说,在西洋诗无数的诗体中,自由诗只是聊备一体而已。说也奇怪,过去最有意识,声势最浩大的自由诗运动象征主义,曾经在前世纪末给我们一个诗史上空前绝后的绚烂的幻景的,现在事过境迁,相隔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回头作一个客观的总核算的时候,其中站得住的诗人最多不过四五位。这四五位中,又只剩下那有规律的一部分作品。而英国现代最成功的自由诗人埃利奥特(T.S.E1iot),在他自选的一薄本诗集和最近出版的两三首诗中,句法和章法犯了文学批评之所谓成套或滥调(mannerism)的,比他所攻击的有规律的诗人史文朋(Swinburne)不知多了几多倍。”(2003:158-59)
四、关于纯诗的批评
迪博《关于诗歌与绘画的批评思考》(Jean-Baptiste Dubos,Réflexionscritiquessurla poésieetsurlapeinture,1719)、柯勒律治《文学传记》(Samuel Taylor Coleridge,Biographia Literaria,1817)、爱伦·坡《诗的原理》(Edgar Allan Poe,ThePoeticPrinciple,1850)分别指责了教训诗等“不纯”的诗,1870年代,魏尔伦、兰波分别有“纯诗”的创作,1890年代马拉美则鲜明提出了纯诗(Poésie pure)理论。1924年莫尔编辑出版了《纯诗选集》(George Moore(ed.)An AnthologyofPurePoetry,1924),1925年卜瑞曼在法兰西学士院举行了“纯诗”的系列讲座(AbbéHenri Brémond,Prièreetpoésie,1926;LaPoésiepure,1926),由此发生了(主要是针对超现实主义的)“纯诗”的争辩,同时,师从马拉美的诗人苏扎(AbbéHenri Brémond et Robert de Souza,LaPoésiepure;Undébatsurlapoésie.Lapoésieetlespoètes,1926)加入到卜瑞曼的论争阵营,坡歇(François Porché,PaulValéryetlapoésiepure,M.Lesage,1926)更是追溯了瓦莱里的纯诗论。而后,瓦莱里发表了评论《纯诗》(PoésiePure,1928),1930年代瓦莱里在其文艺批评中一直坚持了纯诗论,并认为这是必要的诗歌理念。英国的里德(Herbert Read,Phases ofEnglishPoetry,1928)、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PurePoetry,1928)在其法国文学评论中分别有纯诗批评。更后,沃伦(Robert Penn Warren,PureandImpurePoetry,1943)也加入了这场持续的诗学争辩,表示不赞同纯诗论。在纯诗理论中,诗歌的音乐性占有核心的地位。梁宗岱重述了瓦莱里的观点,“把文字来创造音乐,就是说,把诗提到音乐底纯粹的境界,正是一般象征诗人在殊途中共同的倾向。”(2003:20)
1920年瓦莱里为法勃《认识女神》(Lucien Fabre,ConnaissancedelaDéesse,1920)作序,使用了纯诗观念(poésieàl’état pur)。而后瓦莱里在《论纯诗》中写道:“几年前我在给朋友的诗集写序时信笔提出了这两个字(纯诗),但当时并没有给予它过重的分量”,“纯诗这个词之所以说不太合适,是因为它使人想到与之风牛马不相及的纯道德,在我看来,纯诗的观念是与基本分析观念背道而驰的。总之,纯诗是浓缩于观察中的幻想,应该有利于确定整体诗的观念,而将我们引向语言与其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的效果的千姿百态及形形色色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如果不用纯诗更恰如其分,但其意思必须理解为是对词语关系的效果的研究,总之,它意味着感觉性领域的一种探索。”(瓦莱里,1996:303-304)“纯诗的概念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概念,是一种欲望的理想范围,又是诗人的努力和强力所在……”(瓦莱里,1996:311)然而,梁宗岱认为,纯诗是诗的绝对独立的世界,纯诗的观念构成了梁宗岱重要的诗学基础。梁宗岱把纯诗运动,正如把象征主义,都追溯到波德莱尔,”“这纯诗运动,其实就是象征主义底后身,滥觞于法国底波特莱尔,奠基于马拉美,到梵乐希而造极。”(2003:88)《谈诗》写道: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像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且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它得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换言之,只有散文不能表达的成分才可以入诗——才有化为诗体之必要。即使这些情绪或观念偶然在散文中出现,也仿佛是还未完成的诗,在期待着诗底音乐与图画的衣裳。”(梁宗岱,2003:87)
梁宗岱移植的纯诗论,包含了波德莱尔式的应和论、魏尔伦或者马拉美的诗的音乐论、兰波的神秘预言说、马拉美和瓦莱里的纯诗语言论,(瓦莱里模糊的倾向于诗歌与散文的对立划分),以及中国古典的诗文分野,梁宗岱还声称汉语文言诗词中纯诗并不少,最突出的是姜白石的词。
五、结语
如果仅仅把象征主义看作19世纪晚期(1874—1895)法国的一场诗歌运动,它继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更深入地推动了法语诗歌的自由探索和心灵上的解放,以及格律形式的革新。兰波的“神秘预言者”说、自由诗甚至走向对传统文学的反动,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指出,魏尔伦、兰波、瓦莱里和许多自由诗的作者被批评家称为“机械主义的破坏者”(2003:23)。魏尔伦、马拉美、瓦莱里等诗歌音乐性的批评和尝试,以及纯诗理论,加强了诗歌心灵主义的倾向,卜瑞曼进而把诗歌指向宗教和神秘主义。尤其是极力推崇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一系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马拉美、瓦莱里一派的象征主义理论确乎较好接纳了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梁宗岱对魏尔伦、马拉美、兰波及别的象征主义诗人的翻译和批评展示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中西比较的角度。值得指出的是,梁宗岱的象征主义批评是基于白话新诗建设的目标性评论,白话新诗的建设是梁宗岱(象征主义)诗歌批评的出发点和土壤。中国古典诗歌和汉传佛教的象征论,为梁宗岱接受法国象征主义提供了异质的构成要素。
☉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II(马海甸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瓦莱里,瓦莱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Moréas,Jean,Un Manifeste littéraire:Le Symbolisme,Le Figaro,18/09/1886,Supplément littéraire,150.5.
Kahn,Gustave,Premiers poèmes,avec une préface sur le vers libre,Paris,Société du Mercure de France,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