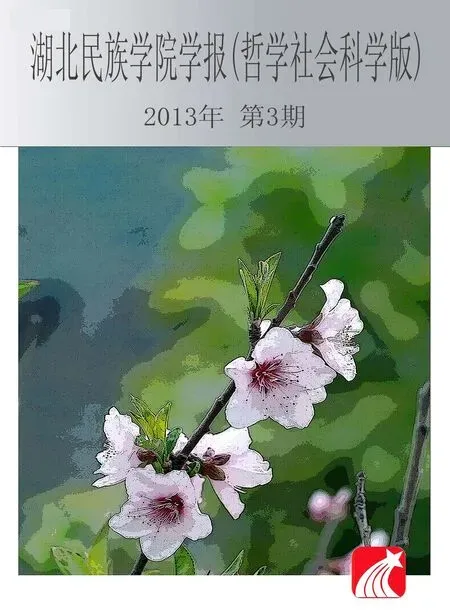艺术与人的归属感的建构
2013-04-12朱思虎
朱思虎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艺术与人的归属感的建构
朱思虎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归属感是本源性的人性需求,文化创造了人的归属感,同时又导致了归属感的丧失。归属感不能建构在以主客二元模式为基础的科学之上,也不能建构在以消解自我意识为目的的宗教之上,艺术以其强烈的生命意识、鲜明的主体性品格和超越主客体的关系模式使个体生命的归属感成为可能。
归属感;自我意识;孤独;生命意识;主客体关系
一、归属感是人类的天性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的理论。他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重要的心理需要,“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1]只有满足了这一需要,人才有可能“自我实现”。在弗洛姆看来,归属感的产生根源于两方面,一是“人需求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将导致人的精神崩溃”。二是“主观自觉意识,即人借以认识到自己是个异于自然及他人的个体的思维能力。”[2]12-13前一种归属需求与共同的行为方式、价值和观念对人的长期濡化有关①濡化也叫文化熏染,又称文化熏染,指个人在社会环境熏陶下获得人生知识、技能的不自觉的学习过程。凭借濡化,社会文化借以从一代传给下一代并且个人成其为社会成员。参见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531.,也就是说归属感的获得意味着个体生命能够与他涵泳其间的文化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后一种归属需求是终极意义的,即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微不足道和无意义性,很显然这种归属感是建立在个体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的。
在我看来,归属感的需求是与人独特的在世方式有关。哲学人类学阿尔诺德·格伦指出人和动物的最大差别就是人的未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动物因为器官的特定化可以凭借本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而人由于其非特定化特点,决定了人依靠本能将无法生存,莱辛由此将人称为“生命的死胡同”[3]。在此情况下,人类的生存必须求助于超越本能的文化活动。兰德曼说:“人是一种必须以其生活环境来决定自己的生物,人类自我决定的这个方面即是我们所说的文化。”[4]由于文化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这决定了人对文化的强烈的依赖性和归属感,因此人的归属感从本质上讲就是栖居于文化世界中的人所获得的安全感和落实感,它反映了个体与文化世界不可分割的关系。相反,归属感的丧失必然导致人强烈的焦虑意识。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焦虑意识都表征着个体与文化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
个体生命这种独特的“未特定化”的在世结构意味着人一出生必须就置身于文化世界中,否则个体生命会因为自身的“匮乏性”而走向终结,因此个体生命从一开始总是处于濡化之中,对于社会大多数人而言,由于濡化具有强大的文化编码能力,导致个体的文化行为与外在的社会要求和规范高度耦合,因此归属感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那些经过后天的巨大努力并具有高度的文化创造力的人也必须和必然归属于某一文化共同体之中。归属感的需要是终极性的,弗洛姆说:
由于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及他人的不同,意识到——哪怕是非常朦胧地,死亡、衰老。与宇宙及其他所有非“他”的人相比,他必然备感自己的微不足道(insignificance)与渺小。除非他有所归依,除非他的生命有某种意义和方向,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像一粒尘埃,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感所压垮。他将无法同任何能赋予其生命以意义的,并指导其方向的制度相联系,他将疑虑重重,并最终使他行动的能力——生命,丧失殆尽。[2]14
也就是说,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不仅仅是一种欲望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而归属感则是个体生命一切精神性需求的基础,也是一切意义的终极意义。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就意味着当代人的归属感的置换和丧失。
二、文化与归属感的丧失
人虽然具有先天的归属感的人性诉求,但是文化本身却又导致了归属感的丧失。原因有二:一是文化自我更新和创造需要对濡化的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超越;二是自我意识的产生使人意识到归属感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性诉求的同时,也意味着孤独本身的不可化约。
人的匮乏性导致了人对文化的归属感,但是文化本身却需要保持足够的张力以维持自身的活力。汤因比指出,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都与它所面临的挑战和由此激发的应战相关。文明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文化本身。就纵向的角度看,个体与社会也必然存在一个结合与分离的问题,文化世界中总有创造性个体会从社会结构的缝隙之处游离出来,柯奈姆·布里奇(Kenelm Burridge)在《某人、非人:关于个体性的论文》中指出这些人“总是在寻求那些无序和新的东西,拒绝服从事物本来的面目或者传统的理智和当局者所期望的那样。”在此情况下,“总有个体命定是‘独自地’去与他者互动,以非预先设定的方式与既存的理智互动,逃脱既定文化规则和批评的压力,从而成为尚未结构化的未知领域的先驱。”布里奇由此得出结论,“从‘某人’到‘非人’再到‘某人’的循环是必然的,个体性是文化的一项基本事实”[5]。所谓“某人”指的是一个独特的生物学意义的个体,“非人”则是将生物学的个体纳入到濡化进程中并被文化高度编码的个体,而最后的那个否定之否定的“某人”则是不能被现有文化有效整合的、具有文化创造力的个体。文化导致了人的归属感的需要,而文化本身的张力结构又需要突破归属感为文化创造提供必要的前提,因为“无论对谁而言,包括采集狩猎者、畜牧者、自给自足的农民、村民、集镇居民还是市民,道德变更、裂变、更新和变革的普遍性机制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5]
如果说上述归属感丧失是文化创造性对个体提出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孤独的产生却深深地根源于自我意识之中,正是自我意识导致了个体生命对归属感的本源性的欠缺。这是所有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化个体的宿命。
三木清说:“孤独之所以令人恐惧并不是因为孤独的本身,而是由于孤独的条件。”[6]这个孤独的条件就是“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表明人的主体性品格的确立。主体跟主体性有区别。我们把具有自我意识即理性思维能力的人都称之为主体,甚至将具有潜在的自我意识或理性思维能力的婴儿和已经丧失自我意识的精神病患者甚至智障人士都当作主体看待,就在于婴儿、精神病患者甚至包括智障人士在理论上都具有获得自我意识的可能性或者曾经具有过自我意识。然而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主体,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具有主体性品格。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我们都曾经缺乏主体性。而我们能否具有主体性在于我们是否具有自我意识,即对自我和社会进行反思的能力。自我意识越强,则主体的尊严感越强,主体性也就越强。
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格的形成。人格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ersona,原指在舞台上的演员戴的面具。按其本意人格意味着人通过各种人格面具与社会进行交往。因此只有一种面具和有过多的人格面具与社会交往的人很难说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也就是萨特所说的‘自欺’(mauvaisefoi)。真诚(即‘是其所是’)只不过是自欺的一种现象,其欺骗的我(是其所不是)和被欺骗的我(不是其所是)之间的一个临界点会暂时的平衡点。”[7]37也就是说,不能自欺的人(只有一种人格面具)和不能真诚的人(人格面具过多)都无法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
孤独正产生于自欺与真诚的张力之中。小孩不会自欺,普通人又不够真诚,因此都远离孤独意识。因此人的主体性正在于真正人格的确立。邓晓芒说:
人格的第一个前提是孤独意识,没有意识到人有孤独的权利的人,也就是没有意识到人格。所谓孤独的权利,是指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肯定自己的孤独性、唯一性。对孤独的需要,即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划分开来的需要。用日常的话来说就是“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
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的。但只有把孤独视为“我之为我”的根本,而肯定并且需要这种孤独,这才是一个人初步意识到自己人格的标志。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感到过这种需要,他就在人格上不成熟、未长大的,在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中所体现的移情、拟人或交感的心理活动本身还只达到对人的孤独的否定性意识,人还忍受不了一个人独处,他从情感上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一切对象都看作自己的同类、同伴,他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团体,乃至宇宙的一分子,乃至全宇宙与他齐一,与他“共在世”。[7]82
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性”、“唯一性”,意味着孤独是作为主体性的人必须承受这一不可化约的事实。不仅如此,一个孤独者针对任何人,甚至与自己心灵最近的人,“都必须坚决维护自己的孤独。”[7]96
三、日常世界归属感建构的失败
前面已经谈到,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意识都导致了人的归属感的再度丧失,然而归属感却是终极性的人性冲动,尽管面临归属感的缺失,人类总是努力通过各种努力希望重新获得归属感。
在现实的文化世界中,归属感的建构必然是一种西西弗斯的努力。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的创造性与归属感之间的张力必然导致了“某人”到“非人”再到“某人”的无限循环;另一方面自我意识不可化约性也必然导致人与世界的疏离感。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所谓的“幸福指数”。在我看来,个体生命的幸福指数与财富和社会的和谐有关,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原因在于真正的幸福感是与人的归属感相关的,而现实社会与政治建构模式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这一愿景的。也就是说,除非面临巨大的人类灾难(战争或自然灾害),在常态的文化世界中,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之间的个体总是处于一种现实或潜在的紧张关系之中,而这种紧张关系恰恰也源于人性本身。斯皮罗指出:
相信竞争、竞赛、敌对等等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非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这是一种被误导的、谬误的观念,这种观念由卢梭发明,并被后来的信仰者——真正的信仰者——在高贵的野蛮人中继续扩散。我开始相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竞争和敌对动机的强度从文化上(和个人)来讲是可变的,尽管文化能够驯服这些动机,但产生这些动机的却正是文化本身。[8]
这些动机就是人的欲望。文化的创造性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人类的各种欲望来展现出来的。比如,马克斯·舍勒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就特别指出了作为欲望的“怨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同时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无助于人的归属感的获得。
由此可见,归属感的建构需要通过对现实的文化和社会的超越性方式来达成。也就是说,归属感必须以消解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为前提。因此以主客体关系为前提的科学不可能具有超越性品格,自然也无法让个体生命获得归属感。怀特海说:
作为精确科学基础的经验完全是表面化的,瞎子和聋子能够获得完满的人生,尽管他们丧失了生活的拐杖。高速公路的交通信号灯有助于现代目标的实现。然而没有汽车和信号灯,也有过伟大的文明。[9]30
怀特海指出科学基础的经验是完全表面化的,亦即,科学的基础仅仅与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相联系。这些感觉世界的能力是高等动物都具有的,只不过科学将这些感觉世界的能力深化和扩大化了(比如人对宇宙的认识)。但无论如何,科学永远只能徘徊在现象世界中,而无法进入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领域之中。这意味着科学与以精神安顿为诉求的归属感相去甚远。
那么宗教能够成为人类归属感的诺亚方舟吗?
宗教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宗教的产生显然与弗洛姆所指出的人的基本在世状况有关系,即人的生命与宇宙相比显得极为有限和渺小,因此宗教对人类归属感的建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宗教特有的神圣意识表现出的对生命的敬畏使得人获得了对自然和宇宙的强烈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就是“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10]。对于生命的神圣性的感受正是宗教归属感获得的起点之一,怀特海用了一段非常形象化的描述表达了这种感受:
举原始森林中孤零零的林间空地上的一朵鲜花为例,没有一个动物有如此敏锐的经验去欣赏它的美,但这种美却是宇宙中的一个庄严的事实。当我们考察自然时,想到动物对自然奇观的享用是如此的肤浅易逝,当我们认识到单个的细胞和每一朵颤动的鲜花是多么不可能享用到自然整体的面貌,那么,我们对整体的细节的价值感就会被我们我们的意识所领悟到。这就是对虔诚的直观,对神圣的直观,这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9]108
然而作为信仰的宗教,在让人心怀敬畏、感恩和崇拜而归属它的同时,却从根本上隐含着一种反生命的倾向。我们已经在前面通过分析表明,归属感的获得是以自我意识和人的创造性为前提的。没有人与文化的分离,就没有创造性,同样也没有人的自我意识。没有人与自然的分离,也不真正存在所谓人与生命的一体感。也就是说,归属感的前提恰恰是一个悖论。亦即,真正意义的归属感不能以丧失自我意识为前提,自我意识的丧失也意味着深度归属感的丧失。然而在宗教信仰中,最终都以对个体生命独特的自我意识的消解为目标。“没有一种主流宗教形态,会仅仅满足于精神世界的营造,而不再由此而进,通过对‘心’的降伏而实现对‘身’的控制。其结果当然并非是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们的得救,而是让那些以上帝或真主的名义轮流坐庄者,以此为诱饵享尽荣华富贵。”[11]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要求导致了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彻底接管,不仅没有造就真正的归属感,反而造成了无数的偏执狂和愚氓。正是这些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在宗教救赎和皈依的名义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造成绝大多数战争与屠杀的重要因素。
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宗教虽然以超越性为鹄的,但是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它又不能不返回现实世界,而一旦返回现实世界,就无法避免被二元对立的现实社会所异化和改造,并成为二元对立的文化世界的极端体现者和执行者。
四、艺术对归属感的建构
上述分析表明,归属感的建构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归属感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归属感不能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二是归属感应该建构在一种超越主客体关系的文化世界中。也就是说,归属感的建构只能存在于一种非日常化的世界之中。
前面已经指出,自我意识就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换句话说,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那种既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或者说是既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的人。因此与自我意识相关的主体性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必然的认识,二是对或然的把握和认同。如果只有对必然的认识,那么人的一切行动将变得合符逻辑和秩序,不过人类本身的变化性、可能性却丧失了。而这恰恰是与人的自由本性想违背的,因此最能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恰恰是与人的未特定化相联系的人的或然性。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了人的主体性品格:
如果有可能根据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的表现而如此深入地洞察到一个人的精神特性以至于能知道他一切的(甚至最小的)动机以及影响这些动机的一切外部机缘,那么我们就可能以推测一次月食或日食那样准确的精确性来推测一个人未来的行动;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说,这个人是自由的。[12]
在人类的文化实践中,对或然性的认同和把握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就深度和可能性而言,或然性在艺术领域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海德格尔说:
艺术是技艺,但不是技术。艺术家是艺人,但既不是技术员也不是工匠。
因为作为技艺的艺术基于一种知道,因为这种知道应当被带入那个指引形态、给予尺度、但依然不可见的东西之中,首先被带入作品的可见性和可听闻性之中,所以,这样一种对迄今尚未被视见的东西的预先洞见,就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需要视见和光亮。[13]
正是艺术活动特有的神秘性特点蕴涵了人无与伦比的主体性品格,所以人类只把艺术生产称之为创造性活动,其他活动称之为“制作”。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创造”或“创世”的能力。由此可见,艺术活动鲜明地体现了人类主体性和自我意识。
宗教建构人类归属感的起点是对生命的敬畏,同样真正的艺术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对生命的神圣感受。艺术价值当然也包括各种娱乐宣泄价值、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等世俗取向。但艺术价值最重要的向度却是以个体生命归属感为核心的精神价值。“艺术眼光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14]余秋雨说:
艺术眼光,是一种在关注人类生态的大前提下不在乎各种权利结构,不在乎各种行业规程,不在乎各种流行是非,也不在乎各种学术逻辑,只敏感于具体生命状态,并为这种生命状态寻找直觉形式的视角。[14]
因为只有关注生命,才能摆脱“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等黑格尔所说的“速朽性”的因素,而长时间地留存于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变幻不居的现象世界中为个体生命寻找到精神栖息的家园。
艺术对生命的关注,并非是个体生命简单的浅唱低吟。尽管它表达的是个别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忧伤、欢乐和挣扎等各种情感状态,但是它仍然在顽强地呼唤和表达个体生命与世界的休戚与共的本源性关系。霍华德·奈洛夫说:“如果写诗的诗人不曾觉察到寂寞的反面,那么一首寂寞的诗便不可能产生。”[15]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神会不会沦落到宗教那样从守护生命开始却最终走向了反生命的结局呢?回答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建构世界的方式完全超越了主客体关系模式。张世英说:
诗意或审美意识从何而来?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超越主客关系式,达到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境界。谁多一分这样的境界,谁也就多一分审美意识。中国传统哲学之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重天人合一,而后者重主客关系。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诗的国度。《老子》教人复归于婴儿,教人做愚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婴儿和愚人,而是超越了知识领域的高一级的婴儿或愚人,也就是超越了主客关系模式的天人合一境界。诗人可以说是高级的“婴儿”或“愚人”。[16]
哪么艺术是如何做到这种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呢?盖格尔说:
如果我们想得到审美享受,那么,我们就必须不再使自己纠缠到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事物中去;我们必须把这个领域抛在脑后,对于“高尚”的艺术来说,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音乐厅、博物馆、戏剧院的气氛,切断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正是这些准备条件的庄重严肃使这样的一种分离成为可能。
为什么艺术是时间的和空间的,而不是味觉和触觉的,就在于,在味觉和味道方面,生命的侧面占据了支配地位,所以它们很难达到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层次。[17]
盖格尔的论述深刻而又简明。他不仅告诉我们艺术在现实世界是如何进行超越的,而且指出了这种超越的目的指向了与现象世界相反的“生命的另一个侧面”,最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生命的另一个侧面”(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同时,个体的归属感并没有以丧失自我意识为代价。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艺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在这一精神家园中,人类的归属感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其他文化领域无法比拟的。杜夫海纳说:
使人们分裂的是生存方面的冲突。所以黑格尔认为,意识斗争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审美对象在更高的层次把人们集拢到一起。在这一层次,尽管个人仍是个人,却有休戚与共之感。我们简直可以说审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如同舍勒所说的,爱、服从和尊敬都是社会行为一样。这一行为至少暗示着有与我平等的他人,因为我觉得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在一定意义上要为他负责。即使暗含中的他人的出现不是我负责的这个人的出现,那也是我与之休戚相关的那个人的出现。[18]
[1]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1.
[2] 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3]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0.
[4]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36.
[5]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6.
[6] 三木清.人生探幽[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50.
[7]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8] 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19.
[9] 阿尔弗莱德·怀特海.思想方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0]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1] 徐岱.基础诗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26.
[12]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45.
[13] 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J].世界哲学,2006(1):5.
[14] 余秋雨.艺术创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9,24.
[15] 霍华德·奈洛夫.诗人谈诗[M].北京:三联书店,1989:202.
[16]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4.
[17] 盖格尔.艺术的意味[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59.
[18] 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96.
责任编辑:毕 曼
I206
A
1004-941(2013)03-0115-05
2013-05-10
朱思虎(1970-),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