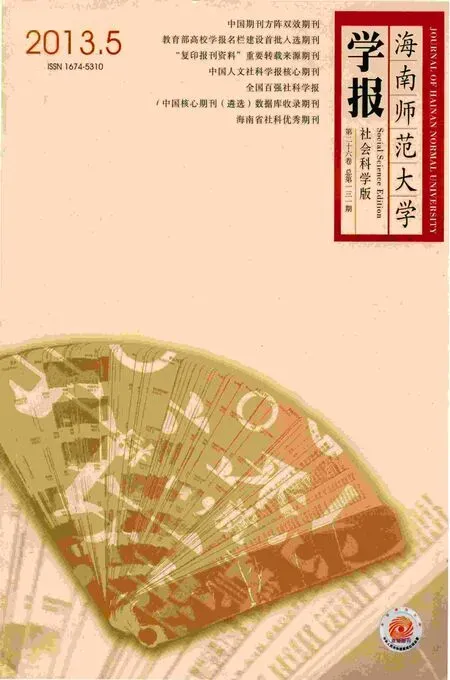重大自然灾害后我国参与国际救援协调机制问题研究
2013-04-12曹彩雲
曹彩雲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8)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后果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出频率高、种类杂、范围广的特点,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就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如何有效地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国际救援被学界认为是我国大规模参与国际救援和一线救灾行动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我国之前缺乏大规模的实践,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全面地展开,因此缺乏专门协调国际救援的机制,导致很多优秀的国际救援资源没有充分地利用,降低了国际救援的效率,成为我国在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协调能力方面的“短板”。
因此,在国家和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一国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救援力量,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源等各种资源来最大程度减少重灾之后造成的损失,建立一套高效运作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不仅成为我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重要议题,也是摆在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际救援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协调,保证国际救援力量能在一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后的综合协调机制内正常、有序、依法地开展。
一 基本问题概述
(一)国际救援
国际救援即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是某一地区发生严重灾害后,由国际组织和援助国提供技术、物资、资金或其他方面救援的活动;[1]抑或是某一国家或地区遭受自然或人为灾害侵袭,造成重大人员和经济损失时,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给予人道的、义务的、无条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的行为。[2]据此,国际救援基本上包含了救援方、援助的对象、救援的内容三个要素。其中,援助的对象一般就是领土内的人或者财产由于重大自然灾害而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国家,国际救援并不是在一国或者某个地区遭遇任何类型的灾害后都会发生,除了在遭受重大的人为灾害侵袭外,更多的情况是在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后产生的,例如海地地震、印度洋海啸或者我国的汶川大地震。其他两个要素笔者下文将详细阐述:
1.救援方
在《Introduction t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domestic facilita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lief and initial recovery assistance》(即《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重建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①2007年11月,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第三十届国际大会通过。中,救援方是指任何提供慈善救灾的人道主义救助组织、援助国、外国人、外国私营公司或对受灾国领土内的灾难作出回应,给予实物或者现金捐赠的其他外国实体。在2011年《Model act for the facilita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lief and initial recovery assistance》(《关于国际救灾和灾后初期恢复重建援助便利化和规范化的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②2011年IFRC世界大会讨论并通过、得到联合国国际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和国际会议联盟认可。中,救援方被界定为在某国救灾的所有国际援助方和国内援助方,国内援助方是指根据某国法律依法成立的参与该国救灾的非营利性实体。国际援助方是指在某国领土上从事救灾或者通过某国领土过境参与另一国救灾的外国国家、组织、实体或者个人。虽然《准则》和《示范法》都是非政府组织通过的一些示范性和指导性文本,但是这两个文本对于厘清和明确援助方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结合上述概念,笔者认为,在国际救援中,援助方的概念界定宜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即排除国内援助方,因为,当一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一般国内的援助方都会参与救灾过程中,而国外援助方则不一定会参与进来。因此,重灾后国际救援的主体从狭义的角度解释,更能够契合国际救援的本质。按照援助活动参与者的性质,可以分为:
(1)援助国,即参与另一个国家救灾的外国国家实体,一般是通过民事或者军事方式,提供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重建援助的国家,其中民事援助是主要方式。
(2)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即几个国家实体通过事先达成的条约而形成的区域救灾组织,例如欧盟为了向其成员提供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专门成立了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the European Community Humanitarian Aid department,简称 ECHO),专门为在自然灾害中的受害者提供援助,1998年7月成立的亚洲减灾中心(ADRC),专门用以加强亚洲各国在减灾方面的合作,推进各国在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联合减灾的机制。[3]158
(3)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性救援组织,联合国作为一种国际组织,具有独特的地位,为了使其成员国在重灾后能够迅速恢复,已经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应急组织体制,形成了包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应急组织体制,成为在国际救援中非常重要的国际实体。
2.救援的内容
关于救援的内容,《示范法》中规定“进入受灾某国的用于救灾或灾后初期恢复重建的援助”,基本上包括人员、资金、物资、技术与服务四个方面,其中物资即向灾区提供的食品、药品及其它各种重要物质,技术和服务即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的医疗援助,资金主要是指援助方向受灾国提供的资金,人员主要是国际救援队伍及提供救灾或者灾后初期重建的国际工作人员。例如,汶川地震后,新加坡派出的救援队,俄罗斯国际救援队。
(二)国际协调的界定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协调是指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从法学的角度讲,协调主要就是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构建相关主体能够从程序上和实体上保持相对基本一致秩序的行为。国际协调,也不外乎是各国能够采取谈判和协商的方式,来达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基本一致的行为。
(三)国际机制的概念
国际机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与国家对国际关系认识的深入程度是一致的。只有当国家意识到了某种共同需要,并愿意为此而合作时,国际机制才能产生发展。[4]4关于国际机制的概念,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斯迪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所下的定义:“国际机制可定义为一组隐性或显性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这些基础上,某一特定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为者能有类似的期望。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和正义的信仰,规范是行为的标准,由权利和义务界定,规则是对应当或违规行为的详细规定,决策程序是在制订和执行集体决定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基欧汉对国际机制所下的定义则略有区别,“一种政府的安排—政府通过制订或采用某些活动的程序、规则或组织制度来调节和控制跨国的和国家间的关系”。[4]2
尽管两位学者对于国际机制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都被认为是国际机制的四大重要要素,一方面这四个要素的是否完善有助于国际机制的形成,从而使国际社会在某一领域内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另一方面,越是明确的原则或者规则越可以营造互信的氛围,扩展国家在该领域的决策空间,有助于国家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减少顾虑和不确定性,促进正常的国际交往的顺利展开。
综上,根据前述对于国际救援和国际救援协调机制的理解,可以得出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在本质上是指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调整由于国际救援中涉及的人员、资金、物资、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国际关系。
二 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模式
随着国际救援活动的频繁,国际救援协调机制也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推动下得到形成和发展,根据国际救援中不同的援助方,现行的国际救援协调工作机制也基本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一)受灾国与援助国双边协助协议下的救援协调机制
为了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国家和国家之间加强了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互助条约,例如1985年丹麦和德国之间签订的《丹麦和德国关于灾害或严重事故时互助协定》;中国和俄罗斯于2006年3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预防和消除紧急情况合作协定》,该协定阐明了中俄双方在灾害发生时相互援助的形式,实施紧急救援的途径、保障手段、权利、义务以及救灾信息沟通、技术和人员培训交流与合作等内容。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所形成的双边救援协调机制往往是两个国家之间具体协调的结果,不具有明显的代表性,本文暂不作为重点探讨的模式。
(二)区域内多边合作组织内的协作救援协调机制
欧盟地区通过成立欧盟人道主义办公室来协调和组织援助事务,向自然灾害中的受害者提供有力的人道主义援助,2001年,欧盟还形成了“欧洲共同体民防机制”(Mechanism For Civil Protection)来解决欧盟地区应对重大灾害后的协调问题。类似的区域性协调行动,比如中美洲国家于1988年成立的“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CEPRECENAC)等等。同双边协调机制一样,区域协调机制的协调模式的构建同样根据区域内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虽然区域性协调机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究其广泛性上还是不够。
(三)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救援协调机制
联合国在长期的国际救援活动中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协调体系,建立起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为中心的协调机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主要是负责协调人道主义救援、制定政策和宣传,它的产生提升了联合国在应对复杂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提高了联合国在该领域内采取人道主义行为的有效性。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通过设在日内瓦的应急响应处,设立了一套应急响应系统,以协调国际组织面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急救援行动。该应急响应处下设有五个快速反应单元:现场协调中心、灾害评估与协调系统、国际搜救咨询小组、应急储备登记处、军民协调部。
当一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OSOCC首先协助LEMA(当地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评估是否需要联合国或者其他国家派遣国际救援队伍,而这个行动的完成则主要是依靠UNDAC,UNDAC应受灾国的请求,开赴灾害现场展开需求评估,协助受灾政府和联合国常驻协调人协调灾害现场的国际救助。当通过评估需要国际救援队伍时,OSOCC便向LEMA介绍这些国际救灾队伍的行动能力,并对前来的队伍提供后勤支持,其后勤责任主要是建立和管理接待中心,以协调到达的救援队伍。OSOCC也将根据自己的已知情况向LEMA推荐国际救援队伍以执行行动任务。在国际救援过程中,一般都会有INSARAG作为智囊,制定搜索救援标准,促进救援国际合作,创建救援理论和方法。
为了保证国际救援能够顺利展开,在外围还会有全球灾害警报与协调系统(GDACS)和地理信息支援队(CIST)为先导,主要是发布各种自然灾害预警,应急响应与救援资源及信息,公布灾区救援资源以及灾区救援的进展情况,通过反应灾区救援的实时情况,促进国际救援资源的高效利用。
重大自然灾害后,联合国在国际救援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海地地震中的国际救援为例,在灾后几近无序的状态下,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成为协调各个国际救援力量的协调中心,各国的救援队伍在联合国的协调机制下有序进行,国际救援物资也迅速发放到灾民手中,国际人道救援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
通过联合国应急协调机制,不仅能够最大程度集合国际社会的力量减少灾难造成的损失,而且在联合国高效的协调救援机制下,也使灾后的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对于以后我国以后参与构建国际救援的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 我国参与国际救援协调机制的现状
(一)我国参与国际救援的工作机制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从拒绝国际救援的态度转变为开始接受国际援助:从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谢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到1980年“南旱北涝”谨慎接受外来援助;从1991年华东水灾呼吁大规模的国际救援,到2008年汶川地震,首次接受外国专业救援人员入境参加救援。几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后,我国深刻到认识到国际救援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注重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协调国际救援力量,而且积极参与到国际救援协调机制的构建中,目前,我国参与国际救援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灾后的救灾援助。《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向国际社会发出救灾援助呼吁”,每次大灾之后,民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争取外援,接受救灾援助,开展灾民紧急救助联合行动。5月12日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积极对待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地震不久,我国政府就做出了接受国际援助的决定,迅速对国际援助物资和人员实行快速通关及运送机制。同时,相关部门还就援助抗震救灾开设了专门渠道,同有关国家和组织就此保持沟通。外交部向国际社会和我国驻外使馆通报灾情,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获取一切有利的国际援助。[5]例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州检验检疫局就本着“优先检、快速检、免费检”原则,特事特办,迅速行动,制定国际救灾援赠物资快速通关便利措施,设立“国际救灾援赠物资报检专窗”,实行24小时受理报检服务,确保国际救灾援赠物资快速验放和安全卫生。[6]
二是开展灾害领域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目前,民政部代表中国政府在灾害管理领域正在与俄罗斯联邦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起草签署国家级应对突发灾害的双边和多边救灾互助协定,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
三是与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灾害管理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目前,民政部已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备灾中心、亚洲减灾中心、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7]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之前我国在接受和参与国际救援方面的实践比较少,因此,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稳定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更多的情况是依靠特事特办的原则,建立一些临时性的机构来解决问题,缺乏协调国际救援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导致很多优良的国际救援资源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严重降低了国际救援的效率。例如,在汶川地震中就表现为对有关国际救援力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由临时组织的指挥部或者委员会来负责,但是这种临时性的机构却有很多的弊端。
2.没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方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在事前对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处理做到未雨绸缪,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灾难造成的损失。例如对于外国救援队的统筹调度通过重灾后设立的临时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来负责,还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不能让我们真正梳理出一套在遇到重灾后接受国际救援应急方案,而如果我国在国际救援方面已经建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不论从救援的效率还是实践的效果上,都会有很大的好处——通过专门的协调机构,每一次操作的方案都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不断地更新,从而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做到有备无患。
四 完善我国参与国际救援的综合协调机制
(一)健全和拓展目前应急机构接受国际救援的职能
从汶川地震接受国际救援的实践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接受国际救援协调机制,针对上述笔者所分析的问题,建议今后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要明确我国接受国际救援的启动标准。对于如何界定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灾害级别,除了按照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来确定灾害的级别外,还可以采取快速评估的方式判断是否需要启动国际救援。快速评估一般是由应急人员或者红事会的工作人员展开迅速评估,评估的目的主要是对危机的伤亡人数、人员伤亡情况,建筑物倒塌数、影响范围和应急需求有一个最初的了解。虽然最初的评估由于在速度上比较快,可能最终的结果会和最初的评估结果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在重大自然灾害后的第一时间获得援助却大有帮助。
2.完善启动国际救援的外部协调,主要是指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及时报道灾情,我国之所以在汶川地震中获得了来自世界很多个国家的关注和援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到了及时准确地报道灾情,这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利于在重灾发生后及时获得国际援助。
3.要注重我国目前协调机制中对如何接受国际救援的工作机制,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对于接受国外援助的运作机制可以以应急办(应急救援指挥机构)为协调机构的基础,在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拓展协调机构的职能,主要是将这些协调机构的职能同我国民政部有关接受国际救援的职能相整合,制定专项的接受国际救援预案和操作流程,同时还要注重建立和中国国际搜集队的配合机制。
4.拓展我国目前协调机构的职能中,要特别注意界定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小组(UNDAC Team)、人道主义事务处(OCHA)及当地应急指挥机构和报告(接待)中心的角色和功能,以便中国在与国际间的互助合作上能更加协调。同时,界定国务院应急办及各级应急办或应急指挥机构、当地政府和国际救援队(或机构)在整个救灾作业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地位,以便整合防灾体系业务,发挥其罄合功效。[3]237
五 积极参与海外国际救援协调的机制建设
(一)确立参与国际救援活动的总体战略
在国家和国家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一旦一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其他国家往往会通过派出国际救援队或者进行国际捐助的方式进行国际救援,这已经成为当前重大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纵观我国在参加国际救援方面的实践,虽然我国也在印度洋海啸、海地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派出国际救援队伍参加当地的灾后救援,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最明显的一点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战略。因此,今后,我国需要明晰这方面的整体战略,既要对救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研究,又要注重提高救灾队的效率,充分参与国际救援协调,展示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这方面,日本已经有很多比较成功的经验,例如前述所讲的日本为了在一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做到快速反应,积极在海外设置相应的应急储备仓库,我国也应当逐步加强政府机构的派遣系统的建设。可以根据外交工作的总体需要,怎么派遣,什么地方要派遣,形成很有效的快捷的派遣机制,以便决策之后就能很顺畅的开展起来。[8]
(二)积极参与区域间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救援机制
建立与完善应急国际协调机制,首先应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国际救援协议,建立灾害互救的联动机制。这样,一旦发生灾害,协议国的救援力量可以快速抵达,从而大大提高灾害救援的效率,使灾害损失降到最低。[9]
其次,应当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救援协调,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拥有人道救援专门机构和完善的救灾架构,”[10]不仅“在制定政策、设计和实施方案方面经验丰富、机制完善,完全可以作为协调国际救援的中心,而且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集中各项国际救援资源并且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国际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救援效用”[11]积极参与联合国为中心的救援协调,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而且能够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例如,美国在协调国际社会对海地的救援行动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力地配合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协调工作。
(三)完善参加海外国际救援的法律法规
目前,虽然我国经常会派出国际救援队参加海外的国际救援,但是长期以来,都把类似的行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友好方式的参与,而不是作为法定的职能。笔者认为,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我们应当把这种参加海外国际救援的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规范,一方面可以为我国的国际救援队伍参加类似的行为提供国内法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此类行为提供法律的保障。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例如日本就专门制定了关于如何派遣国际救援队、如何提供救灾物资和资金的《国际紧急救援队派遣相关法律》,不仅使每一次行为有法可依,而且规范了派遣的条件、程序、任务范围和指挥协调,在国际救援协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影响和强烈冲击下,重大灾害发生后的救助已经超越了国界,虽然国际救援的力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我们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即使有很多的国际救援力量参与到灾后的救助,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于是我们不仅要从理论的角度去探析国际救援协调机制在当前的运作模式,尤其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救援协调机制,而且应当对照透视出我国在参与国际救援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汶川地震后积极接受和参与国际救援,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救援,我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协调机制准备和法律准备,幸运的是国际社会正在健全的国际救援方面的工作机制以及法律规范为我们完善有关国际救援方面的工作机制和法律规范提供了一个范式。“一个民族的进步,总会由他的进步来补偿”,我们需要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如何完善我国接受国际救援的协调机制,更需要高瞻远瞩从国际的视野去思考如何在海外国际救援协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白潇卓.国家主权在国际自然灾害救援中的合理制约[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0):41-44.
[2]韩亭.我国重大灾害应急管理接受国际救援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8.
[3]游志斌.当代国际救灾体系比较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6.
[4]张向晨.发展中国与WTO的政治经济关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魏飘飘,郭慧峰.中美两国政府对待国际援助的行为比较—以“汶川地震”和“卡特里娜飓风”为例[J].中国商界,2010(9):310.
[6]中国质量新闻网.广州局快速验放国际救灾物资[EB/OL].2008年6月24日发表,2012年12月3日访问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210854.html
[7]柯菡.我国自然灾害管理与救助体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0.
[8]总结篇: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赴泰国救援服务总结座谈会上讲话[EB/OL].(2005-06-17)[2012-12-03].http://www.moc.gov.cn/zizhan/zhishujigou/jiulaoju/zhuantizhuanlan/futaijiuyuan/200710/t20071023_439898.html
[9]马佩英.对当前社会应急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1):148-151.
[10]杨学娟,杨子岩.国际救援进行时[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5-24(08).
[11]焦佩.从印度洋海啸分析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模式[J].南亚研究季刊,2005(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