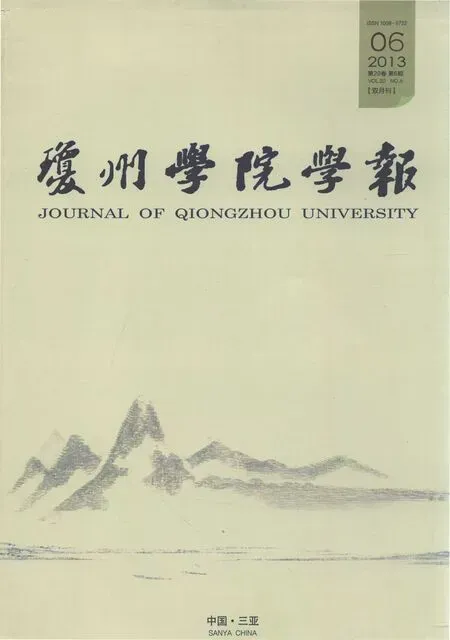“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2013-04-12孙浩宇
孙浩宇
(长春师范大学昭明文选与中国诗歌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32)
注意到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是在五年前,读完他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最大的启发是木斋身为文史学者思想的大胆和思维的新奇。中国文化讲贵和尚中,文史学者更是追求温柔敦厚,按部就班,平和中正。观点、方法、证据甚至表述都无不以此为准则。木斋是个例外,他将曹植甄后恋情与古诗创作这两个似乎并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且能圆通①笔者不同意所谓的“循环论证”说。以科学思维看,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事物或事件并非必须要分出个前因后果、前提与结论,比如自然科学就有很多一空依傍、非逻辑判定的假说。其实,传统文史研究也有类似意识,如章学诚强调识见,梁启超讲到直觉!,这更像是科学家做的事——冥王星与太阳,苹果与地球等等。翻开这部天外来客般的大作,你会发现此中并无臆想之笔,而若再知道这是近十年之功的累积创作时,有一点怕是你否认不得的,木斋的确是当今于古诗研究最用力、创获最大的人!
木斋的成果不妨称为“木斋曹植说”(下省称“曹植说”),其观点大致为:《古诗十九首》乃至其他佚名古诗的主要作者是曹植,曹植作这部分诗以及其佚名的原因与甄植恋有关。这是个颇具想象力的六位一体的理论。木斋将《古诗十九首》(下省为“《十九首》”)的写作时间、作者、本事、主旨乃至曹植五言诗创作、文人五言诗成熟等融汇一体来研究,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味道,而其所以受学界争议也正因于此。须知,千百年来这六个问题一直是汉魏五言诗研究的焦点,哪怕拈出任何一个都够得上大课题,木斋竟能拿出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解决方案,难道是入宝山得了秘笈?其令人不解自所难免。
对“曹植说”的置疑有二:一是观点及论据,二是方法论。首先是观点不能接受,却也无法推倒,因为木斋的理论建构已足够宏大、论证已足够精详。那么只有来否定论据了。资料摆在那里,千古不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为真孰为伪,不是以征用多寡,个人接受与否为转移的。换言之,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因为别人用了就以一句“靠不住”抹煞!如对甄植恋典故的使用;对虞世南《北堂书钞》认为“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是曹植诗句的使用[1]156等等。其实这只是木斋论据的一部分,他还运用了对语汇语句进行科学考量的方法,对史料也有剔抉入微的梳理,所以若先入为主,一票否决未免会有点匆促。当然也并非说“曹植说”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
再说所谓的方法论问题。其实,木斋最可贵的贡献不在观点,不在方法,而在精神。木斋在古诗研究中大胆贯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在价值观上实现了扭转和突破。木斋打开了一扇门:文史研究也应求准确而非求模糊,也应求是,而非求正图稳,这注定是孤独的。我私下曾说,木斋的研究走了险途。在理论建构上,文史学者敢走险途的太少,而木斋宁可置一己于万劫不复,也要勇往直前。想居里夫人之研究镭,诺贝尔之发明炸药,不都如此么!此点本人将有另文,在此不赘。
以下讨论的思路是,不再谈“曹植说”本身,因其内部的推定、资料、观点,看家自有法眼,而是将其放在《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上来观照其产生之可能与必然。不能否认的是,任何理论、学说的诞生都有漫长的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奋其私志、兀兀穷年的过程,要知道,木斋不是孤立的,“曹植说”的产生也不是孤立的。首先从《十九首》的研究史来看,此说的产生正是一次学术发展的必然。
一
“曹植说”的核心在于解决《十九首》的创作时间、作者及主旨问题,此处笔者以时间研究为例谈。这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疑案。要研究这一问题,除文本推断外的主要依据有:萧统《文选》的编排、刘勰《文心雕龙》的论述、钟嵘《诗品》的论述、徐陵《玉台新咏》的编排、李善《文选》注的论述等,还有皎然《诗式》、李防《文苑英华》的论述也属较早的文献。综合起来,就有了大致三种说法①此不同于木斋表述的西汉、东汉、建安三说。:一是梁启超的“东汉末年说”。此说集明清相关研究之大成,但不论及著者,后经游国恩、马茂元、袁行霈推布,影响最大。二是刘勰提出的“两汉说”。三是钟嵘提出的“建安说”。对比三说,“两汉说”文献证据较多,“东汉末年说”、“建安说”推定成分较多,因各有道理,又都无法一锤定音,于是留给后之学者的便是个站队问题了。不过迄至今日,人们从未放弃过对《十九首》作年的探索。仅1949年后就有叶嘉莹、林端常、郑文、李炳海、张茹倩、张启成、冈村繁等学者先后论及,这或许也给木斋的研究赋予了动力和使命,使“曹植说”的产生成为一种可能。需补充一句,因陆机拟作与萧统《文选》编序的影响,人们虽不认为《十九首》是一时一人所作,但虑及风格等因素,都更愿意接受创作年代较为集中的说法,这便使得后两说更易于让人接受。而“东汉末年说”跨及汉代,又不论作者,即模糊又稳妥,故最易为人钟情。
以下则重点谈“建安说”的发展,这与“曹植说”关系最密切。
钟嵘之后认同“建安说”的还有明人钟惺,在《词府灵蛇二集》中,他几乎是全盘引用了《诗品》中的相关表述来评价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其外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然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2]3977二钟氏都倾向于曹植,实千载知音,有趣!
此外,历代诗评家论及以曹植为主的建安诗与汉代古诗及乐府关系的也颇不少,这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辨彼此,统而论之的,可说是为后人选择“建安说”或“曹植说”提供了支持。如:
1.宋吕本中《吕氏童蒙训》: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诗皆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13]
2.明谭浚:故曰取式乎上,仅得乎中。为上而未极,犹胜其下者。若失始于下而图上,难矣。朱子曰,取汉魏古词如苏、李、《十九首》及曹、刘七才子选以附《楚骚》,又次等近古者如阮、陶、李、杜选各为一编……意则不期高远而自高远矣。(《说诗》)[2]1811
3.明王世贞: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艺苑卮言》卷三)[2]1907
4.明许学夷:汉、魏人诗,但引事而不用事,如《十九首》“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子建“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王仲宣“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等句,皆引事也。至颜、谢诸子,则语既雕刻,而用事实繁,故多有难明耳。(《诗源辩体》)[2]3245
5.清施补华: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质浑厚为正宗。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后,为陈思诸作及……等篇,不踰分寸。(《岘傭说诗》)[3]976
以上五条,前二者是说曹植诗与《十九首》一样风格高远而有兴味;后二条统言汉魏,讲如论其质朴自然,二者难别彼此;第三条王世贞则直言曹植、曹丕的某些作品与《十九首》可以混同莫辨,即使不举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述①如《隐居诗话》:《古乐府》中《木兰诗》、《焦仲卿诗》,皆有高致。盖世传《木兰诗》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又如明杨慎:挚虞,晋初人也。其《文章流别志》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殆是假托,非尽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来古矣。即使假托,亦是东汉及魏人张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升庵诗话》卷十四),以上也足证二者之高度相似了。
第二种是注意建安尤其是曹植对古诗的继承和学习,强调其承接相似处。如:
1.明胡应麟: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送应氏》、《赠王粲》等篇,全法苏、李,词藻气骨有余,而清和婉顺不足。然东西京后,惟斯人得其具体。……子建诗学《十九首》,此类不一。而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俱现。(《诗薮》内编卷二)
《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诗薮》外编卷四)[2]2505
2.明冯复京:《十九首》一派,子建源流相接。(《说诗补遗》卷二)[2]3856
3.清沈德潜:苏、李以后,陈思继起,父兄多才,渠尤独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邺下诸子,文翰鳞集,未许执金鼓而抗颜行也。故应为一大宗。(《说诗晬语》卷上)[3]534
4.清潘德舆:茗香又谓“汉诗之于《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干等,皆不足于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于魏,岂通论乎?(《养一斋诗话》卷十)[4]2001
5.清近王寿昌:何谓自然?曰:古诗如“今日良宴会”、“庭中有奇树”是也。其次则子建之《公宴》、《美女》二篇……何谓高?曰:《古诗十九首》尚矣,其次则陈思之《白马》七篇……(《小清华园诗谈》卷上)[4]1867
上述之中,后二条可见曹植诗与《十九首》及汉诗风格的相近;前三条,可证曹植对《十九首》与汉诗的学习,虽不能至,庶几近之。
第三种同样是关注建安尤其是曹植诗与古诗之关系,但侧重谈其不同。如:
1.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进而追两汉也。嗟夫![2]1338
2.明许学夷:子建乐府五言《种葛》、《浮萍》二篇,或谓于汉人五言为近,非也。汉人委婉悠圆,有才不露。子建二篇则才思逸发,情态不穷……学者于此能别,方可与论《十九首》矣。(《诗源辩体》卷四)[2]3226
3.清叶燮: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诗盛于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原诗》卷一)[3]566
以上虽是强调曹植诗与《十九首》及汉诗之别,但显然也是承认其源流相接相近的。
综上,诸资料论证了曹植诗与《十九首》等汉诗的关系:或言“源流相接”,或言“得其调者”,或言“规模酷肖”,或言“不能辨也”,可见二者高度的相似性。若推其理,以上诸论很难说不是受钟嵘《诗品》影响,因其品评以《古诗》第一,曹植则紧承其后。这大概是启迪后人将曹植、建安与《十九首》建立联系的根源所在,于此罗根泽、徐中舒、胡怀琛、郑宾于、陆侃如等考证了“建安说”,今之学者赵昌平、张亚新、范能船等也从不同角度关注到建安诗与《十九首》的联系。如张亚新认为,时代的接近,作者、文学观及文学趣味的共同性决定了二者在思想内容、抒情性、语言、风格必然的相似。[5]赵昌平认为二者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主情任气,重感兴,都继承了国风至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14]二是始见作用之功,婉丽而不失自然之致,二者在表现手法上共同构成一个特殊阶段。以上研究之种种,想与木斋的研究应不乏承启之处。
二
“曹植说”能产生在于打破了两个成见:一是指出《十九首》不是民间作品;二是对其主旨做了新诠释。那么检视研究史,以往之研究是否也同样存在某些端倪呢?必须再次承认,任何学术创新都是漫长积累加上质变创新的结合,当然这其中还有个关键的背景就是发展变化的时代因素。如木斋所言:“个人在学术史的发展方向上总是渺小的,学者们总是不自觉地、潜移默化地受到时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遵从着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以致出现某种卡里斯马现象的精神文化产品。”[1]3时代因素的变化是“曹植说”可能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首先说作者的判定,《十九首》是民间无名氏还是文人的创作呢,这个问题受时代观念影响较大,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结论的差别。文学作品是创自民间还是文人写作,这个话题几乎与现代《十九首》研究的历史一样长,一样纠缠。这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1917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政治色彩,由此开始的文学史书写也不同程度留下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进一步明确了这个逻辑:“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从民间发端,经文人之手而繁盛,再因过分脱离民间而由盛及衰,这种模式化的文学发展观几乎成了20世纪前期文学史书写的基调,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被郑振铎、徐嘉瑞、谭正璧、胡云翼等人反复阐释,俨然成为文学演进的一个不移命题。
在此背景下的《十九首》作者研究深深地被民间创作意识所主导。但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是不容抹杀的,马克思曾说过,“由于分工的结果,艺术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别人身上,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却无从发挥。”[6]纵观现代文学研究史,关于文学起源的作家创作论不绝如缕,即使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也不乏坚持己见者。如朱自清在《古诗十九首释》中讲:“《十九首》没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间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7]翻检最近十年的研究,对《十九首》创作中所呈现的文人特点,人们基本表示认同。如宁宇认为《十九首》在内容、形式和语言方面带有明显的文人特征;[8]陈斯怀指出其具备由民间性向文人性过渡的明显特征;[15]黄敏、肖伟认为其体现了诗歌从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的过渡。[16]木斋提出“曹植说”实际上是对《十九首》民间创作观的彻底颠覆,这显然于时代的发展,与人们的文学观更加科学,更加独立有关系。
其次谈《十九首》的主旨研究,木斋将甄植恋与《十九首》创作结合起来,有点人证、事证俱全的味道,颇能自成体系。需知,对《十九首》主旨的探究也是个受思想文化等时代因素影响很大的话题,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会在其所处的时代“以意逆志”、“揆情度理”,其中诸般欧明俊在《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中多有论及。此处我们的关注还是与“建安说”或“曹植说”所论相关的脉络。
木斋“甄植恋”的联想很大胆,让《十九首》的阐释颇多艳丽色彩,这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根本在于诗歌创作的情真说,古人的《十九首》评价不乏此论。如:
1.元陈绎曾: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诗谱》)[9]
2.明许学夷:汉、魏古诗,虽本乎情之真,未必本乎情之正,故性情不复论耳。或欲以《国风》之情论汉、魏之诗,犹欲以《六经》之理论秦、汉之文,弗多得矣。(《诗源辩体》卷三)[2]3206
3.清王夫之: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婉娈中自矜风轨。(《姜斋诗话》)[3]21
4.清近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何谓缠绵?曰:如古之“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4]1863
时代发展,一气下来,关于《十九首》的解读不免有愈艳愈甚之势,“比兴寄托说”显得牵强,“友朋说”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人们越发承认《十九首》心迹流露的旷诞和大胆,并逐渐敢于解读为“夫妇说”,如清人方东树、张玉谷、今人马茂元等,这其中钱基博在《古诗十九首讲话》中的主旨区分已相当进步:“一曰怀春,凡五首,又细分为处女、荡妇、静女、寡妇不同类型;二曰伤离,七首;三曰悲穷,二首;四曰哀逝,六首”。[10]对照近世思想史的变迁,自王阳明心学经过李贽等王学左派发挥后,从汤显祖到公安、竟陵,人们在思想解放的同时,文学观念也更加强调真情至性,独抒性灵。明清以降,不乏有人像王夫之一样视《十九首》为“艳诗”。时至今日,这一方向的阐释更是丰富多彩。如丁峰山有这样一段文字:
“诗歌作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自然大都通过诗来释放,那么占有人生很大比重的男女之情不仅成为诗人咏叹的核心内容之一……性的欢乐与痛苦相伴着文人诗歌的始终,虽有起浮盛衰的波动,但在诗中一直是不绝如缕,有时甚至成为诗中最活跃、最受重视的中心。……‘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性压抑的无奈和苦闷,一句‘空床难独守’真实地道破了所有思妇性压抑、性寂寞的内心酸楚。《十九首》中的大部分相思之作写得没有此诗直接,但却很明白地表达了同样的情怀。”[11]
他还例举如《客从远方来》《冉冉孤生竹》《行行重行行》等,阐明《十九首》都是颇带性爱色彩的情诗。其后蔡靖芳、陈红梅等从女性研究者的视角对《十九首》的主旨做了类似阐释。
以上,可说是“曹植说”主旨发明的前提背景,木斋“甄植恋”本事的引入与相关主旨的发明于此看也并非过分突兀。
三
“曹植说”的产生与个人研究理路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后记》中木斋对该课题的缘起与个人的研究历程多有叙述,读后让人有“原来如此”之晤。观照木斋的个人学术史,“曹植说”能产生关节在于三点:
一是文学史研究中明确的诗人史观。木斋讲“我所研究的两大诗歌起源发生史,即五言诗起源发生史和词体起源发生史,都证明了这一规律。它们都不是在民间,或者由无名氏作者在漫长岁月中集体创造出来的……一部诗歌史,并非白话文学史,更非民间创造史,而是以精英诗人作为里程碑的诗人史。”[1]302民间史观与诗人史观哪个更全面,更接近历史本真,或许还不能因为“曹植说”的出现而一锤定音,星火燎原,但客观审慎地对待其中纠结对以后的文史研究定会有新启发。
二是学者诗人的气质。学术观点是公器,但文章却自弥漫着学者个人的气质,尤其是对诗人木斋,阅读其文,不免对其诗性化、个性化的学术论文写作心生向往。行云流水的文笔,诗性的妙喻,师者的哲思,那将是若干年后学术研究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此不赘。“诗史本由诗人写”,[12]诗人写诗史自然会有更深的诗性相通,于此看木斋的研究是科学的,也是浪漫的,是严谨的,也是大胆的,在史料与史观之间,木斋呈现了一个顺理成章又充满魅力的“曹植说”。
三是宏观微观结合的学术思维。宏观→微观→宏观是木斋的研究路径。木斋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所谓整体的,是指需要具备将中国诗歌史整体打通,至少是将相关的历史阶段进行通究,在这种大文学史观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对诗歌史的某个局部阶段深入理解和诠释。”[1]302对照其研究,自1986年4月发表第一篇论文起,从《略论中国文学的分期》、《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到坚持开展的诗词缘起流变课题到“曹植说”,无不是整体流变思维与深耕细作、抉疑发微相结合的成果。
行文至此,“曹植说”缘何得以产生?便不妨用一段夫子自道来回答了:“就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同样不能超越这两大基本属性的制约:首先,受现当代学术的思辨精神之被,得以在前辈学者建树的楼台之上,看到更高更远的风景;其次,我也同样受到当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只不过,这种思潮开始从百年之前的思潮走向反拨而已。”[12]这是学者的自谦,更是学术的自觉,道出了研究史发展的规律和必然。“如果并非为颠覆而颠覆,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探寻和研究的自然结果,则这种颠覆和创新尤其值得鼓励。”[12]放下“曹植说”,至少木斋带给我们的求真务实、果决无畏的研究精神将是很宝贵的财富。现在,他的孜孜以求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如胡旭说:“木斋先生在古诗研究上的开创性,最根本之处在于其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对陈陈相因的研究坚决抵制,大胆假设,骋力追新,表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木斋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学者,他的研究目的很明确,不计功利,追求真理。”[17]林登顺说:“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的创见,带来古诗研究的新视野。”“无论如何,木斋先生以自身深厚的学识,在无疑处作出莫大学问,开拓了我们对古诗的理解和境界。”[18]当然,也有学者对木斋的结论持商榷意见,如柯继红已撰文以大量材料,“就木斋先生2005年9月《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2013年1月《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文讨论的基本观点‘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提出不同的意见。”[19]但不管怎样,木斋,已经是学界一个蓬勃而令人振奋的存在。
就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又闻木斋的古诗研究有了新推进,在其《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一文中,笔者惊奇地发现,无论在资料、观念还是视阈上,木斋都有了新的深化与扩展,他刚刚张本的《古诗论》写作,他对《七家后汉书》、《新校本后汉书并附编十三种》的新阅读,他对秦嘉诗、苏李诗的新观照,他的“六十首古诗曹植甄后论”都已超出了上文所述,笔者期待窥其全豹。无论如何,那都将是古诗研究界的一股劲流,会触动人们的固有观念,推动新的古诗研究高潮的到来,如此,将不仅是古诗研究者的幸事,更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自觉、自信的幸事。
[1]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周维德.全明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5.
[3]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张亚新.试论《古诗十九首》对建安诗歌的影响[J].延安大学学报,1981(2):3-9.
[6]刘建军.民间文学不是“源”而是“流”[J].人文杂志,1959(3):85-87.
[7]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J].国文月刊,1941(6):8 -10.
[8]宁宇.古诗十九首形成臆测[J].广西大学学报,2003(4):70-73.
[9]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623.
[10]钱基博.古诗十九首讲话[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4):74-75.
[11]丁峰山.明清性爱小说的文学观照及文化阐释[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42.
[12]王一娟.诗史本由诗人写,何由散落到民间:木斋先生访谈录[J].天中学刊,2012(2):1-8.
[13]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94.
[14]赵昌平.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J].江淮论坛,1984(3):77-85.
[15]陈斯怀.由民间性到文人性: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貌[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6):91-94.
[16]黄敏,肖伟.论《古诗十九首》之过渡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7(3):134-136.
[17]胡旭.开创与回归:木斋古诗研究的思考[J].琼州学院学报,2013(3):20.
[18]林登顺.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带来新视野[J].琼州学院学报,2013(4):18-20.
[19]柯继红.“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J].琼州学院学报,2013(4):3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