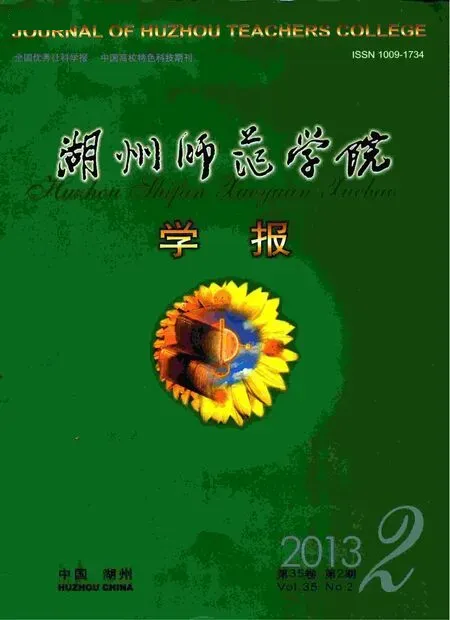民生幸福:社会救助伦理价值向度*
2013-04-12陈文庆王国银苏平富
陈文庆,王国银,苏平富
(1.湖州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2.浙江省教育厅 高教处,浙江 杭州310000;3.浙江外国语学院 社会科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310000)
民生幸福,从字义上是民众生存的持续的心理满足状态,一种让人感觉愉悦,生而有价,生而有所值的情感体验。这一满足的情感建立于物质的适当满足基础上,体现为精神的自得。由于人类,特别是强调群体,注重集体的人们,幸福作为生存状态的样式,离不开社会的安全与保障,离不开群体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爱。如被视为追求大众幸福主义的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若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1](P14),此即为笔者所理解的民生之幸福。社会救助本是基于同情心、恻隐心对遇到天灾人祸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陷于生活困顿的同类施予临时性物质援助的行为。此后,在以救济为主的临时性、自发性慈善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内容的社会福利性事业。社会救助以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机构为施助主体,集体与个人为辅。受助对象则是由于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而处于生活、生存困难的人们。救助方式有应急式的也有长期性的,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资源的再次分配与调节,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平。因而,鉴于民生幸福及社会救助的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从生命本体意义或从大众幸福主义的角度上,社会救助伦理价值追求的是民生幸福。
一、民生幸福作为社会救助伦理价值向度是政府及社会的本份
民生幸福首先要建立在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保障与人人之间互助友爱二者统一的基础之上。社会救助从物质层面上是解决民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需要问题,从精神层面上是满足社会中人人之间互助友爱的情感需要,从行动层面上是道德良知及人人关系的互惠互利原则的实际践履。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公平与社会关怀的完美结合,其作为民生幸福的重要内容,其作用小到关系个人安身立命,大到关系社稷安危。在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宣公十二年》里就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P49)鲁宣公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少衣食。《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P49)《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2]《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2](P49)《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P49)这些论述既强调民之幸福安康在于勤劳致富,亦强调国应以民为本,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国家安康,社稷太平。正是有这些认识和思想,社会救助,互济互助自有人始即已存在。社会作为人们生活与发展的共同体,政府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与发展的公共代言人,追求民生幸福必然会把社会救助纳为自身的应然或本份职责。
在古代中国,救助是处庙堂之高的君王和达济天下的政府的应当责任。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古时候水灾、旱灾、霜冻、虫灾发生频率较高,农耕生产主要是靠天吃饭。一遇灾荒,民生幸福就遭遇挑战。为解决灾荒时期的民生问题,那时虽然没有使用社会救助一词,但已有社会救助之实。如《春秋穀梁传》、《左传》、《公羊传》、《管子》、《晏子》、《礼记》等篇章中都有赈灾、济荒、救民的描写与思想。在《春秋穀梁传》中记载当诸侯国中有遇天灾者,其它诸侯国在粮食物品上要给予受灾国接济。为备荒年,提出储粮备荒应急的思想。诸侯国至少得有三年的储备,备下六年,九年更好,“丰年补败,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3](P2388)可见,救灾备荒关系民众的生存安康,是执政为王者应然的责任。到宋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灾情上报到灾民登记、救灾物资发放,形成了完整并非常成熟的体系。宋徽宗时更是专门成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在全国范围内救助鳏寡孤独疾废者。近代,国弱民贫,北洋政府也对贫民等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孙中山则把民生作为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民生幸福是各种历史活动的中心问题,强调对流浪者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宋庆龄则在慈善救助事业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成为社会稳定的第一项工作,生产互助,以工代赈,以至发展到今天的健全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在民间,守望相助,互助共济是宗族邻里的习俗。直至今日,在乡村,若某户人家遭遇灾害,遇到困难,乡村邻里都会尽量到场,或是送来钱物,表示慰问,或是由宗亲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主持族人、亲邻共商救助救济的方式,帮助困顿者脱离苦境。
在西方,从总体上说,社会救助的主线由早期城邦互助,到以宗教为主体的非政府组织为救助主体,以宗教的慈善活动为主要方式,慢慢发展为政府、国家、社会责任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及慈善人士为辅的社会保障的民生福利层次。以城邦政治作为社会生活重心的古希腊古罗马,救济与救助包含在个人与城邦,道德与政治,美德与人生的关系中。在《伊利亚特》中就有记载,女神救起了遇到风暴船只沉没的阿喀琉斯,这就说明神本就有救助遇难者的本份。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虽然阶级等级森严,但强调城邦的共同体,在《奥德修记》中有城邦中对罹难的他人的援助的描述,这被认为是公民的美德。伯利克里则把生命置于第一位,他说:“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4](P233)对于为保护城邦人民生命英勇作战的英雄,对于给予接济处于生命危难的人们,要给予优待。安提丰则在《真理》中强调人与人天生平等,没有差异,对于处于困难的人当施以援手。中世纪的基督教从上帝普遍的爱出发,卢梭从社会契约出发,休谟从人的天然同情心出发,强调对弱势群体,灾荒饥民的救助。到了近现代,罗尔斯、麦金太尔等则从社会公平和正义,从美德伦理中表达了对弱势群体予以救助的思想。到16世纪,功利主义强调大多数人的幸福,认为弱势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主张应从国家的层面给予弱势群体救助,以此作为市场优胜劣汰法则的补偿,由此,1601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救助的法典《济贫法》,标志着社会救助正式纳入国家法制层面。此后,西方许多国家,如德国、瑞典、芬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效仿英国,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接受并获得救助是社会福利的部分,是公民的权利。从而,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及公民的权利,作为民生幸福,社会安康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意识层面以法制的形式得以确立。可见,无论东方或西方,社会救助作为社会安定,幸福民生的保底线是历史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是政府与社会应尽的本份职责。
二、民生幸福作为社会救助伦理价值向度是人类理性的必然
使人成其为人,而与一般动物分野的特殊性是人的理性。在西方的创世说中,世界本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神先用五天的时间区分天地并使世界拥有了阳光、空气、水份、飞鸟、走兽与虫鱼。第六天则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圣经中第26条是“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人是世界的统治者,而人成为统治者是因为他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自我化身,它与其它自然物不同,他被赋予理性,并由理性而拥有自由、人性、人权,或曰区别于其它自然物而存在的独立价值。人的独立价值的实现并不只是个体的自我认可,个体价值需要在群体中得到确认与确证,而这一价值的确认与确证来源于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他们的帮助。东西方都认为恻隐之心与生俱来,即对苦难困难遭遇的感同身受。这种感觉虽然首先表现为被情景的触动和震憾,由心而行给予困顿者救助,但实际上是人的理性使然。动物由于先天和后天等多种因素而因高低强弱而产生秩序性,在动物的世界中表现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源于动物,自然也存在先天的智商、体能、后天的情商,技能等的个体差异,或由于资源占有不均,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等,在人类社会的群体中也一样存在动物界的优胜劣汰。但是因为人的理性,人高于动物,人类在进化中摒弃了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而是给予同类人道主义的援助。事实表明,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对遭受天灾人祸的同类给予及时的救济,对因技能或身体等原因而处于生活困顿和窘迫的群体或阶层施予援手是人类理性自觉的实践印证。
从个体施救者的角度,其对遭遇困难者的援助是其自我价值的理性确证,是强者能力和德性的证明。因为人的能力和德性是以价值和尊严来体现的,而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确证是以他对社会、他人所做的贡献做为评判的依据和条件的。对社会进步及他人帮助和贡献越大,其价值越大,受尊重程度越高。造福于民,改善人民生活,扶危助困成为人在理性认识中追寻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放弃部分权利,结为整体,这个整体称为国家,而参与者称为人民。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由原来的自然生存状态进入了社会的状态,国家的权力是一种公意,作为公意就得把民生幸福放在第一位,甚至于关注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正是如此,所以在东西方都有民贵君轻的思想。文明越发展,做为人类生存低线的社会救助就越完善,虽然救助的是弱者,但从公意理性的角度,则是为每个公民拉起了一道最低生存保障线。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享有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每一个人在受益的机会上是均等的,个体的人的生存发展纳入了社会、国家的共同体中。
从受助者而言,接受救助也是理性的自然。如康德所说“人性尊严属于每个个人以及自己所欲之价值,建构成为个人本质上不可放弃之要素。基于该尊严,人类方有自我发展之能力。人性尊严存在于每个人,寓于人之本质内涵中,是无法派生之核心要素。那个核心内涵突显在外的即是自治、自决的真正意义,以及人性尊严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抛弃”。[5](P8)受助者作为弱者自己所欲、自己能欲的能力不足,往往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地位,从个体的外在表现上自我意识缺失或被弱化。可是再穷再弱再困难,作为人这一独立个体,其自我意识不可能完全甄灭。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低保户、困难户,他们一方面在人群中总感觉到低人一等,身份卑微,这是因为接受救助,受惠于人,人的个体价值及尊严受损害。但是我们同时也能感觉到,当这些低保户、困难户接受救助的那一刻,他们又有一种欣慰,一种隐隐的快乐。因为他们作为类的一分子,作为类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穷困潦倒被抛弃,而是以救助的方式得到社会、他人的认可。对弱势群体及因天灾人祸处于困顿者的救助,往往可使人们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集体、同类的共同体有种归属感。受助者在物质上渡过困境的同时,精神上更有一种生存于类群体中的幸福感。
可见,无论是从施助者,或是受助者而言,追求民生幸福是人类理性对生命及类存在认可的必然,民生幸福作为社会救助伦理价值向度是自然的了。
三、民生幸福作为社会救助伦理价值向度是人类感性的需要
“幸福”二字既可联之又可分之,可是幸而福之,亦可幸福同而有之。民生幸福主要表现为人们感性的满足,一段持续的对生活与生命状态的满足感,一种由心而生的持续的愉悦心理体验。这一愉悦的心理体验不仅是对当下的乐,而且是对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的理想状态的期待或期许。它是人们对生存状态感觉愉悦、舒适、如意的积极情感体验,是人们对发展前景乐观向上,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情绪表达。幸福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情绪体验,其具体的内容因时因地不同。幸福虽然是一种人生的目标,但在本质上幸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幸福的状态、幸福的内容往往因主体的不同,理解和规定各异。基本层次的民生幸福是指衣食不愁,家庭安康的生存状态。提升层次的民生幸福则是在基本层次之上,精神情感有归属,民主政治权利能落实,个人尊严及人生价值可实现。民生幸福作为人们的感性需要,其体现为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健康、生活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感,健全的公共服务和民主权利得以实现的满足感。而这些感觉并不简单的是某些个人自己得到了就叫幸福,这种幸福的体验还依赖于其作为人类群体共同的权益的保障。社会救助,特别是作为社会福利和保障被固定成型的社会救助事业恰恰就是这一幸福的感性需要得以产生的基础。
社会救助能满足人们对人际关系和谐的感情需要。人际关系的和谐贵在“和”,然而“和”的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则是“美德”,如宽厚仁爱之心,见义勇为之举,诚实守信、礼让三分之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仁爱”。仁爱在儒家思想里涵义广泛,它包括亲亲,爱民,爱物,即包涵了人人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而把这种关系联系起来的是宽仁、慈悲、同情之心。道家强调上善若水,强调柔顺,但上善之中包涵了同情和怜悯之心。古希腊柏拉图则把幸福等于善,亚里士多德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认为人生所追求的幸福就是最高也是最后的善即“至善”。梭伦认为幸福在于善始善终。在梭伦看来身心健康,生活安宁,善始善终,才是幸福的人。[6](P37)对弱者施以援手是宽仁、慈悲、同情之心,是善良与美德之举,是人们追求情感的高尚性,求得心灵安宁的需要。近代虽然受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作为个人更爱自己,作为非神的普通人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利益,如霍尔巴赫认为:“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7](P616)虽然幸福由至高的德性降到了人的现实的生活,但是正如爱尔维修所说,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如果每个人只是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及公共利益,就不会有个人利益。个人幸福离不开社会幸福,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不是行为者自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社会救助是善、美德、宽厚仁爱之心的实践证明,是公众幸福得以保证的底线,是人际关系“和”的基础。“我今日帮助了某人”,“我得到了某人的帮助”是人们表达自己人际关系和谐的幸福体验时说的众多话语之一,可见人人关系往往是在这些类似社会救助中感受到的互助友爱的情谊而得到满足的。
社会救助能满足人们对生存安全感的感情需要。如果说古代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对自然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分化进行应对,那么现代的社会救助除了古代的意义及功能之外,还作为社会分配机制,对市场经济竞争等一次分配机制的不公进行补偿。以优胜劣汰的竞争为特征的市场机制,在强化竞争,把人对个人利益追逐及满足最大化的同时,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与不足等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社会两极分化明显。而两极分化不只反映在物质层面上的差别,还由于阶层的差别,导致群体社会地位及阶级或阶层情感的分野。当这种物质差别和社会地位、阶级阶层情感分野达到一定程度,发展为对抗时,一是导致社会的纷争和动荡,因为活不下去了,没了前途和希望,只能舍命抗争了。二是人们丧失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甚而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和惶恐中,因为他不知道这种艰难的困境什么时候就落到自己身上。1601年,英国以立法的形式把救助及接受救助作为政府责任,公民权利确定下来,其背景就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失业、贫困、流浪人口急剧增加,只依靠教会等慈善机构进行救助已无法解决问题了,直接表现为社会动荡,人们生活幸福指数急剧下降,安全感缺失,人们迫切需要政府介入,以政府的力量和权威建立所有人共享的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社会救助事业。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实际地享有社会救助提供的具体钱物,但每个社会公民在遇到困境,处于个人力量无法摆脱的境况时,都可享有获得并接受社会救助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人们就可以摆脱遭遇赤贫的后顾之忧,获得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对社会生活少顾虑而有信心,自然其幸福的情感体验增强了。
以上的论述,主要想表达的是社会救助问题不仅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实践伦理问题。社会救助问题的基本内容虽然基于民众最基本的生存诉求,但其本质是国家社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每个人提供或创造符合民众诉求的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和条件,让生命的价值得到确证和体现的公意使然。人们处理社会救助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情感态度及行动方向建立于社会公平、互助友爱的情感及理性的需要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文明秩序建设的需要,社会救助涉及到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公共教育与服务等多方面,其伦理价值的基本向度无不紧紧围绕着民生幸福这一主题。这一民生幸福的价值向度使社会救助兼有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双重性,彰示了社会救助作为实践伦理的特点。
[1]谭家健.墨子今注今译[M].孙中原注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
[2]夏勇.中国民权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转引杨德春.《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J].孝感学院学报,2011(4).
[4]欧里庇得斯悲剧(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转引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