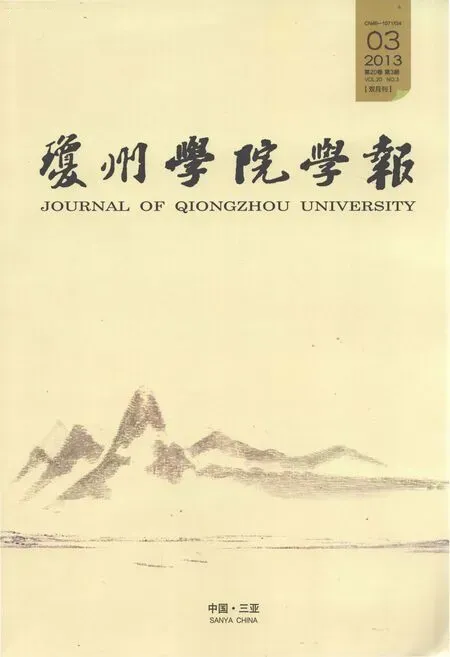“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
2013-04-12文丽敏
文丽敏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2000)
一提到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立刻会反应这是个“原始”社会。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对远古文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所谓“原始”在现代语境中,包含了明显的“粗陋”、“简单”,甚至于“野蛮”这样的内涵,与“精致”、“现代”和“文明”这类的概念相对。这样评说母系氏族社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或许还说得过去;但这样衡量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则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性。即将母系氏族文化视为一种低级文化,是人类尚未脱离动物阶段的产物。“达尔文-马克思”社会进化论为这种认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理论依据。虽然现在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人类社会并不是按照从低级向高级这种阶梯模式发展演变的,但长期形成的线性思维观念难以彻底改变。
母系氏族社会是目前已知的距人类的动物阶段时间最近的文化阶段。这使很多人,包括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其与人的动物性最接近,“动物性”代表“野蛮”则是所谓“文明”社会的公共常识。“兽性”和“畜生”分别是上流社会和底层人民骂人的典型语言。这种联想与母系氏族社会的真相相去太远。就人类文化对其动物性的超越而言,母系文化的贡献应该说是最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的领域:对人私欲的有效控制和对新型两性关系的建构。这是人对其动物性的重大超越,母系文化的主要特征也表现在这个领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堪称辉煌的人类文明成就,反而在后来的父权社会阶段丧失殆尽。如果较真地说,哪个社会离动物性更近,答案很清楚:那一定是父权社会。私有制、等级制和父权制都能在动物性上找到其对应的根源。
母系氏族社会就其主要文化特征来说,具有“神意”性、生态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上古的黎族社会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一、“神意”社会的存在基础
母系社会就其存在基础与管理方式而言,是一个“神意”型的社会。其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以整个氏族公认的“神意”为标准。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以为:上古氏族社会是由巫师和族长控制的社会,而这些巫师和族长当然会利用这样无从监督的特权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形式上,上古氏族社会(包括母系氏族社会)的确是由巫师和族长控制的社会,但他们不是以自己个人立场和意志来掌控这个社会,相反,他们是以氏族公认的神意的标准来管理和引导这个社会。如果巫师和族长假借神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他所在的氏族要么很快就变成等级制的父权社会;要么,氏族会很快失控而导致消亡。可以说,在母系氏族里,只要混进去一个骗子,这个氏族就必然陷入混乱瓦解的困境。母系氏族的基本形态在这种条件下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误解仍然是父权社会的思维定式造成的。在整个父权社会历史中,管理者的贪腐几乎是无法医治的癌症,只能依赖外部监督来制约。当观察者看到母系氏族社会的巫师和族长拥有不受人间外部监督的权力时,便以父权社会的逻辑推测其管理者必然贪腐(而后来的父权社会也的确是以当权管理者的贪腐为契机,从母系氏族社会孵化出来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贪腐的顽症是由私有制的温床培育的,只要有私有制存在,贪腐的动机便将永驻人们的心田。母系氏族社会恰恰是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人们完全可以用强大的神意威慑力量,来约束人的生物性欲望不致越轨。大量的对母系氏族社会的考察表明,以禁忌为标志的神意裁判的约束力远比父权社会以法律暴力的强迫形式更有效,更持久。如果真的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不是封闭的个别村落的状态),那就只能是母系氏族时代。因为,在母系氏族的人看来,神灵的眼睛无处不在,人无法遮盖自己的任何行为。只有那个时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全民信仰”的的社会。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那是个洞若观火的时代,所有的角落都有神明关注。这就是母系氏族的管理者不会权力寻租的根本原因。
母系氏族社会的神意基础是“万物有灵论”。这与后来父权社会的“一神论”有重大区别。“万物有灵论”建构的必然是一个包容平等的社会;而“一神论”建立的必定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万物有灵论”相信,世间万事万物之间可以通过种种神秘的方式相互感知,相互制约。虽然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万物有灵论”的原则也是由人单方面约定的,但先民在确立这个原则的时候并没有从人的单方面立场出发,而是把万事万物当作与人一样的利益体去看待。今天,我们则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人类可以瓜分,可以挖掘的财产,即使是包容性更好的生态主义,也大都是从人的长远需求出发,提出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呼吁。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在现代情境下已经无法避免。
黎族的自然观是母系文化价值尺度的延伸,也是黎族处世态度的基础。在黎族人看来,所有的自然物都是应该敬畏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灵魂,也有自己的喜好。当你没有正当理由去伤害自然,自然必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加倍地惩罚你。人的伤痛、病症、摔跤、溺水、发疯等等,都与被神灵报复和惩罚有关。在黎族人的词典里,没有“意外”这个概念。因此,与周边所有的自然物(不仅包括生灵,也包括像山、石、土地、河川、湖泊等等)平等和睦相处是人类唯一明智的选择。
二、敬畏“神意”
在黎人的神意世界里,“神”“鬼”未分,善恶未明,显示人的价值尺度还未成为自然的尺度,人对自然物也未形成主宰意识。黎族人的信仰形态还未脱离自然崇拜阶段。天地间所有的“鬼灵”都没有组织,没有门派,也没有等级,互不隶属,互不买账。自私放纵则是他们的基本的个体特征。因此,讨好他们,或者回避他们,是黎人的基本策略。对于无法回避的“鬼灵”,则必须用巫术和献祭来摆平,方能保人的平安。过去黎族人众多的生产生活禁忌,相信就是出于回避“鬼灵”的动机选择。
黎族以往的生产生活忌日特别多,每逢忌日全体氏族成员都不能出去劳动,或者禁止某一项农事活动。一直到民国时候,一些支系的黎族忌日每月多达十二三天。[1]69这些忌日的形成,显然是黎族人在长期的神意社会中对自然神灵恭敬与退让的结果。这当然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黎族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缓慢,但从另一方面说,这样的生存态度也带来了黎族长期的内部和谐,亲和自然生态,培养了节俭、诚信、友爱的民族精神。
“万物有灵论”在母系氏族社会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为那时人类的生存方式就包容在自然生态的秩序当中,人类在精神领域尚未完成与自然界的分裂。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还没有“物我”两分的观念,相反,人与万物同为这个世间大家庭的成员。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合作的条件,冲突的化解,都需要大家公认的尺度和原则。母系氏族的人们便依据自身的情感方式(推已及物),在与自然万物的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世间“万物有灵论”的处世原则。例如,人们砍伐树木,打中猎物,都会觉得树木和猎物会疼痛,树木和猎物当然会觉得被人类伤害,他们会伺机报复人类。人类的应对方式,一是尽可能缩小伤害的范围,即只为了生存的必需才去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这在情感上属于迫不得已,情有可原。这与现代滥捕滥杀动物的交易性行为绝不是一回事。二是在此前提下,对已经发生的伤害行为,进行道歉和解释,在精神甚至于物质方面对被伤害对象进行抚慰和补偿,同时,对帮助过自己的神灵进行答谢。这便是人类最初祭祀活动的由来。
其次,“万物有灵论”将人、动物、植物,甚至于我们今天认定的无机物,都视为有情感有灵魂的对象。他们的灵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离开躯体游走(例如人可以做梦),而死亡就是躯体的死亡,他的不死的灵魂当然会追究伤害他躯体或造成他的躯体死亡的人。
保亭县大本地区杞方言黎族的孩子若多病痛,则视为“凶魂”缠身。父母在孩子生日那天,杀鸡请“道公”给孩子做“灵魂棺”(取山上的“莉嫩”草,制作小棺材,捉一只蟑螂放进棺内),全家号哭把“灵魂棺”埋葬。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把“凶魂”埋葬,活人就可平安。[2]384-385
所谓埋葬“凶魂”就是把“凶魂”送走之意。三亚高峰地区哈方言黎族,对没有举行过葬仪的死者,也要补葬“灵魂棺”。
第三,在上述条件下,人们的日常行为严格受“禁忌”的约束,禁忌便是神意社会的基本“法律”,违禁的人将遭“天谴”。当然,这种神意裁判也可以由神的代理人执行,比如巫或族长。过失性违禁,可以通过道歉与补偿性巫术来求得相关神灵的原谅。
第四,预兆是神意社会感知未来情况的唯一窗口,即将进行的氏族重大活动,如狩猎,战争,开荒等必须通过占卜巫术来询问相关神灵的意图。
黎族的“砍山歌”甚多,从中可窥见原始“刀耕火种”的劳动情景。采自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首《砍山歌》唱道:“嗬晰哟,劈园先问地,问地可吉利,是否好运气,运好得谷米,运歹捡树枝。树啊,伙计!”①采录自毛感公唱,内容为黎语意译。描绘砍山劈园时要先祭“山神”、问吉凶,还要讨好“树神”,称它为“伙计”。在黎人看来,劳作是否有很好的回报,除了辛勤的付出,还要看相关神灵的态度。
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调研资料、民间故事传说,了解到古代的黎族社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神意型社会。与之相通的是,所有的母系氏族社会也都是神意型社会。
在黎族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中,动物和植物角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许多故事的情节中,动物和植物的功劳都超过了人类)。它们要么是人类的救星,如保住了黎族祖先性命的葫芦瓜、南瓜、甘工鸟;帮助黎族祖先渡过难关的蛇、黑熊、斑鸠、牛、野猪;要么是人类祖先的对头,如螃蟹精。在黎族人的眼中,它们都有可敬可畏之处。
半坡的母系氏族社会,虽然只能靠出土文物说话,但仍能鲜明的表现出神意型社会的特征来。彩陶几乎就是半坡文化的代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面鱼纹盆。人头像的头上有三角形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亦人亦鱼,人和鱼互相寄寓,又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母系生育图腾。
在黎族的典型图案中,同样出现了人与蛙的合体形象。这种亦人亦蛙的图像说明了母系氏族社会人可以与动物形成平等交融,相互渗透,共荣共生的亲密关系。
黎族祈福的舞蹈《祝福舞》,不仅跳给神和人来看,而且每逢黎历三月的第一个“牛日”,人们都要庄重地给牛跳《祝福舞》,祈盼牛健康成长。在七月晚稻插秧的第一个“牛日”,人们还要郑重地给“稻子”跳《祝福舞》,祈祷禾苗茁壮成长。[1]281
一生一死,是黎族最关注的神秘现象,是神与人关系互动的极致状态。通过“生”,神灵可以获得人的肉身变成人;通过“死”,灵魂也可弃肉身而去,重回神秘世界。
在比较了黎族氏族社会所有的重大活动后,我们发现围绕着殡葬(黎族人称“作鬼”)进行的各种仪式和活动,无论是就时间跨度、参加和涉及人数,还是所需的金钱投入,都远超其他的节庆规模和程度。父母过世的殡葬常常使子孙后代倾家荡产,他们要用牛来祭祀,用织造复杂的“龙被”来覆盖棺椁。整个殡葬活动短则十几天,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对于所有的黎族家庭来说,这都是巨额支出。不仅如此,如果判定某些灾祸是由得罪祖先鬼引起的,还要对该祖先鬼再行祭祀,同样也要牺牲献祭。对需要隆重献祭的鬼灵,黎族人无奈地称之为“吃牛鬼”(必须有牛献祭);对需中等献祭的称之为“吃猪鬼”;对需小规模献祭的称之为“吃鸡鬼”。笃信鬼魂,这是黎族人被诟病,遭误解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海南南部哈方言黎族“哈应”支系的黎人认为:
人死后,死者的灵魂既可保护家人,也可作祟家人。因此,这些地方流行人死后停棺7天、12天、20天甚至几个月不等(视经济条件决定)的习俗。待举行隆重的“作斋”仪式,为死者超度亡灵后,才将死者抬到家族墓地安葬。“作斋”时跳的是《五风舞》。所谓“五风”即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这里的黎族群众认为人死后在一定时间内,其灵魂仍游荡于荒郊僻野,无法归宗,跳《五风舞》就是为其招回亡魂。[1]280
衡量黎族氏族活动的一个形象标志是这个活动是否要杀牛。牛对于黎族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是过去黎族人最看重的家畜。“黎人以牛之有无多寡计贫富,大抵有牛家为殷实,有养至数十头及数百头者,黎内谓之大家当。”[2]牛是财富的象征,衡量一个黎族家庭的富有程度是以牛的多寡来计算的。这首先是因为,牛是黎族从事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牛,稻田便无法耕作。在更久远的年代,黎族是用“牛踩田”的方法平整和耕作稻田,没有牛,即使有再多的土地也没有意义。对于没有牛的家庭,他们宁可出让土地,也要换回耕牛。正因为如此,黎族人对耕牛的重视和爱惜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在黎族比较重要的节庆活动中就有“牛节”(或称“牛日”)。在这一天牛的主人,不仅不让牛劳作,还要敬牛“山栏酒”,为牛跳《祝福舞》。因此黎族杀牛就意味着不寻常的日子到了。
用牛来献祭,在黎族人来看这不是奢侈,而是神意社会里最虔诚的表现,是对神灵和鬼魂的极度尊敬。因为他舍得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作为牺牲奉献。
巫术由于有涉及民族精神心理的强大支撑,所以生命力异乎寻常地顽强。汉族的正统观念一直对巫术嗤之以鼻,“五四”以后的启蒙思想又对巫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也直斥巫术为封建迷信,并动用社会组织和宣传力量对民间巫术活动进行围剿。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根除巫术的影响。黎族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据《三亚市通讯》披露的数据,育才乡(即黎族“哈应”支系聚居乡镇)从1983-1985年,三年间,共做鬼、“作八”(为死人“打斋”招魂)923宗,大约有27万人次参加,杀牛16头,猪1520口,耗资近百万元。而这期间,中国的思想解放与反思运动才刚刚开始,应当说还没有对黎族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正统的意识形态仍居统治地位,宽松的社会气氛尚未形成,这种数据就更能说明问题。
神意社会的基本秩序是靠复杂的生产生活禁忌系统来维持的。黎族早期的生产生活禁忌非常多,保持到民国时期的各种禁忌依然难以尽数。明代《海槎余录》记载黎族祭祀山林打猎时,“有司官兵及商贾,并不得入;入者为之犯禁,用大木枷胫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顾,何其愚也?”外人不理解黎人的神圣法则,当然会发出:“何其愚也”的感叹。而在黎族人看来,私闯禁地这是冒犯神灵的大忌,后果很严重,凡是黎族内部的人都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他们不过是代替神灵来惩罚这些外来的犯禁者。这些禁忌如果不放在黎族母系氏族的神意社会背景下去理解,人们当然就会觉得黎族人愚昧无知,荒唐可笑。
三、与神意沟通
在先民心目中,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也是有感情的。如何使自然中的精怪与神灵受到感动,从而不危害人类,甚至帮助人类,这是巫术关心的基本问题。取悦于神灵不仅要献上精美的食物,还要考虑神灵的精神与情感需求,于是向这些神灵献歌、献舞就成了母系氏族时代巫术的基本构成。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头。
巫术的存在前提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关系。人自视为万物中普通一员,不比飞鸟低贱,也不比虫子高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情感有灵性的。由于人的活动总是要与各式各样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打交道,所以,人必须用合适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它们。这就是早期人类自然崇拜的由来,也是巫术得以施展的广阔舞台。女巫(黎族称“娘母”。有证据表明女巫是黎族最先出现的神职人员,其后在父权崛起和汉文化影响的双重作用下,黎族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道公”)就是那个时代最早的通神专家,懂得如何用适当的态度和方法去调整人与其他神秘对象的关系,从而避免人因莽撞惹祸上身,并使人在这种复杂的交往关系中最大限度地获益。在神意型社会中,女巫就成了整个氏族观察自然界的眼睛、聆听神意的耳朵和氏族的代言人。她们用巫术查验各路神灵的要求和愿望,并且用氏族人能理解的方式解释给氏族成员听,再把氏族的要求愿望用神灵听得懂的方式转告给各路神灵,力促双方和睦相处,防止双方误会冲突。这就是女巫的基本职责,女巫由此成为氏族重大“涉外”活动离不开的翻译和调停人。
是父权社会发动了对母系文化的丑化宣传,将“女巫”妖魔化。“巫婆”在东西方的很多国家都成了吓唬小孩的妖怪。欧洲中世纪对女巫的宗教审判之荒唐,称得上是骇人听闻。女巫被宗教裁判所描述是无恶不作的恶魔,她们煮食婴儿内脏,与魔鬼性交,传播疾病,杀人越货等等。受此影响,在父权社会的传播与叙述下,女巫成了长鼻子,着黑袍,骑扫帚,趁夜色从烟囱出入的恶毒无比,丑陋无比的巫婆。
在这场历史的缺席审判中,女巫从来也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我们今天也只能从流传下来的女巫唱的歌谣中,去窥视那个时代女巫的真面目。
黎族巫术源远流长,不知就里的外人也把黎人巫术传得神乎其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黎族神意社会的强大影响力。1928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穿越海南岛进行考察,当地的汉人(今琼中岭门)还极力劝告随行人员,“在这些土著人家,切莫接过一只碗或一杯茶,千万别用黎人的筷子,以免中毒。”[3]
女巫在父权社会中被丑化成恐怖邪恶的“巫婆”,而我们在黎族娘母的歌唱里看到的是极富人情味的一幕,《娘母驱魔歌》唱道:
睡吧,好宝贝,
妈妈要去田,
爸爸要去园,
安睡在家里,
莫把同伴想。
不要象小牛,
留恋嫩草香;
不要象蚂蚁,
留恋海棠果。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巫术在历史上曾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巫术用来行骗那是发生在父权社会的事情。应该再次强调:在母系氏族社会是没有骗子的。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衡量黎族过去的巫术,自然“迷信”的成分不少,但巫术也不都是“迷信”,其中也包含着不少科学的东西,一些科学方法,其实就是在巫术过程中发育出来的,例如医学。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巫医不分的阶段。最早为人看病的就是巫。巫在驱邪看病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巫医占卜做完法事之后,一般都要给病人服用自己配制的草药。黎族巫医已经掌握了数十种内服外用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地治疗烧伤、发烧、毒蛇咬伤、烫伤、跌打肿胀、骨折、疟疾、瘴气、风湿、惊风、难产、腹泻、胃痛、腰腿痛、癫痫、痔疮、疳积、痧症等等。常用的治疗方法有:内服汤药、火针疗法、针挑疗法、挑痔疗法、挑疳积疗法、灯花炙疗法、艾炙疗法、刮痧疗法、药物熏蒸疗法、药物熏洗疗法、熏贴疗法、佩药疗法、酒疗法、拔罐疗法、药熨疗法和食物疗法等等。1974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动员民间献出草药方就有365个。
当人心是用信仰的方式自律时,其效果最佳,社会成本最低。当人心是用刑法的方式他律时,其效果最差,社会成本最高。今天我们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得不供养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包括公、检、法、税务等等。这种外部监管必须依赖缜密的法律和法规体系来运作,但仍不能杜绝违法犯罪行为。事实证明,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极易被腐蚀。这是当代世界的癌症。今天,当我们的曾经是很质朴的农民也开始把有毒的蔬菜和粮食卖到市场,而给自己留下小量的无毒食品自用时,我们还能怎么说?我们还能说什么?
全体氏族成员笃信神意,意味着在那个时代没有今天让我们头痛不已的“流氓”、“无赖”、“小人”、“恶棍”、“小偷”、“骗子”、“流浪汉”等等角色,房屋无需设防;人心亦无需设防。人们把疑难问题都留给神意来裁决,不必自己费尽心机疑神疑鬼地去搜寻猜测。许多在当下看来是无从解决的复杂问题,在氏族社会那里反而变得十分简单。过去黎族在碰到一些无法裁决的疑难问题时,往往求助于“神意裁判”。雷神就是黎族“神意裁判”的首选神灵。
黎族人当有些事情不能明断的时候,便进行雷神判。如某个人的财物被盗窃,但没有抓住盗贼,只是怀疑某人,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被偷的一方,还是被怀疑的一方,都可以把口水吐到手心里,对对方说:“如果你确实没有偷我的东西,你敢用你的手掌击我的掌心吗?”或者说:“你确实认为我偷了你的东西,你敢击我的掌心吗?”如果是做贼心虚或者是不敢确定,一般不敢与对方击掌。击掌后由雷神审判,雷劈死谁,就是谁做了亏心事。人们相信,雷会劈死做了亏心事的人。[4]
在黎族人眼里,只要人敢于对神灵发誓,他的话和人品就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一直体现在黎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习惯法”中。
当然这种神意型思维模式也使后来黎族人,在历朝汉官、汉商的欺诈与谎言面前吃尽了苦头。这正是早期黎汉冲突的精神鸿沟之所在。“一般来说,黎族群众向汉族商人借贷,都是以半年为期,年复利100%。到期不结账,利上加利,要用田、牛来抵偿。如乐东县永益乡老村容亚璜,在民国22年(1933年)借了汉族商人赵学明200个铜钱,3年未还,便被勒索了1头牛和80箩谷子。”[1]103黎族人对汉族人的看法由此可知。
黎族人对汉人的这种憎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化解。这种情形甚至引起了当时在海南考察的日本文化特务们的注意,并建议日本军队在侵略海南岛时加以利用。①参见金山《日本人眼中的黎族》,《海南历史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
母系氏族社会的人们对神灵也并非一味谦让,而是有自己明确的原则。如果他们觉得某个神灵在人们三请四敬的情况下仍故意刁难,他们会奋起反抗,并利用某种手段去惩罚这个神灵。从这样的关系来看,母系氏族社会(包括父系氏族的早期)人和神的关系基本是平等互动,相互制约型的关系。人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与后来父权社会“一神论”时,人匍匐在地,神高高在上的情形截然不同。
后来的父权社会虽然也经常讲“神意”,但这种“神意”已逐渐沦为人欲的工具,例如,源远流长的“君权神授”论,“天人合一”论,以及历朝历代大肆宣扬的“天降祥瑞”,农民暴动利用的“天机”、“神迹”等等,往往成为欺世盗名者的盾牌。在西方的父权社会,宗教裁判所同样打着“神意”的旗号为人类特定集团的利益服务。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在“神意”型社会中,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可以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社会氏族成员之上。那是一个在“神意”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
历史将会证明,真正的“神意”社会只能存在于母系氏族社会。如果对比母系氏族时期的“神意”形态,后来所有的父权社会都可以称为“世俗的社会”。如果说母系氏族社会是物质匮乏但享用均等,且人心澄明的社会;那么近现代的父权社会就是物质丰裕但贫富悬殊,且人心蒙尘的社会。何者为“文明”,何者为“野蛮”?
[1]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民族志[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清]张庆长.黎岐纪闻[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18.
[3][法]萨维纳.海南岛志.辛世彪,译注.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0.
[4]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