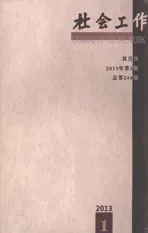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探讨
2013-04-11韦克难黄玉浓张琼文
韦克难 黄玉浓 张琼文
一、研究背景
从海外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的介入来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灾后重建社会工作介入服务选择的是政府与NGO合作的社区重建模式。如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在20世纪末期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地震,这几次地震的灾后重建都突出社会多方参与、NGO参与社区建设的经验,以美国1989年的旧金山大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及1999年台湾集集大地震表现最为明显(刘斌志,2009)。在这几次地震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强调社区自律与居民自助原则,平时进行都市老旧地区的更新、社区重生、再开发事业等的支持工作,在灾后则配合当地社区与居民需求,协助居民进行社区营造式的重建(邵佩君;2003;刘斌志;2009)。
海外灾后重建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是以社区重建为主,体现NGO、政府、企业与居民合作多方参与的模式,注意满足居民的多种需求,注意发动居民参与重建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通过NGO(或NPO)由社区居民组织自己整合社区各种资源,了解居民需求,与居民建立相互的信赖关系及良好的沟通,并注意建立与政府、企业等的伙伴关系与相互利益协调机制,最终达到促进社区再建的目标(刘斌志,2009)。
海外灾后社会工作和社区实践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一是探讨灾后服务的协调。比如Robards et al.(2000)强调在社会工作灾后介入和研究中澄清和准确地测量不同组织间协作的重要性。Harrell&Zakour(2000)指出灾后非正式组织和自助网络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灾害反应的参与,尤其是在孤立和边缘化的社区。Galambos(2005)认为社会工作对于自然灾害的有效反应必须包括整合临床、研究和社会组织技能的介入。二是发展测量和研究工具,以整合灾后当地社区的知识和能力建设。比如Chambers(1994)所描述的参与式乡村测评(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Low et al.(2005)探讨了快速民族志评估程序(Rapid Ethnographic Assessment Procedures-REAP);Victoria(2001)介绍了社区为本的灾害管理(Community-Based Disaster Management-CBDC)。三是探讨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和社区的社会资本。如Pyles(2007)探讨的组织社区中边缘化的民众,或是通过民众的自我组织以争取自己的权益和促进自身的发展。Mathbor(2007)指出社会工作者应该利用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社会凝聚力、社会互动和团结以减轻自然灾害对社区的影响。
国内灾害重建的研究主要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才开展,大部分的研究探讨社会工作者在抗震抗灾和灾后重建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或介入的模式(王思斌,2008;徐永祥,2009;陈涛,2009;柳拯,2009;张和清等,2009;张昱,2009;民政部社会工作司,2008;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民政厅,2009)。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工作和灾后社区建设方面的研究文献,如徐文艳、沙卫、高建秀(2009)提出社区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应建立一个以社区为平台、预防性与治疗性工作并重、以增加外部资源联结和内部资源发掘为根本宗旨的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框架。张昱(2008)认为社会关系的重建是灾后社区重建的重要议题之一。刘斌志(2009)指出灾后社区重建要坚持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民间资源的整合,实行行政主导或社区动员的重建模式。
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社会工作介入的模式
社会工作介入地震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在我国救灾史上尚属首次,没有经验可循。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工作在没有统一规划和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各方社会工作力量本着高度的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深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介入模式。从各社会工作服务队伍介入灾区开展服务的途径和方式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柳拯,2010):
第一种,政府主导模式。这种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是政府已将他们纳入制度体系内,由政府出资金委托服务或购买服务(柳拯,2010)。其最大特点是政府部门主动出面或支持各类社会工作机构协调整合社会工作资源,组建社会工作队伍支援灾区,主要代表有上海社工、广东社工、湖南社工、四川社工等。如由上海市民政局牵头、上海社会工作者协会组织,上海的社会工作者成立的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是其中的典型。上海社工的对口帮扶推动都江堰市本土社工的发展。2008年12月,四川省委组织部联合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派驻社工服务队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2009年3月,四川省民政厅组织“社工百人计划”志愿者在北川雷鼓镇、安县桑枣镇、平武南坝镇等地设立社工站,开展社工服务。湖南省政府在援建理县过程中,将社会工作纳入援建整体规划,将四支社会工作队伍整合成“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为精神家园重建项目提供300万元资金支持。广东省援建工作组在对口支援汶川工作启动一年多以后,将社会工作纳入援建规划,为汶川县政府提供460万元专款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安县政府与中国红十字会、南都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合作成立红十字社工服务中心,将其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拨款近30万元作为社会工作者的个人补贴,投入20万元资金和物资用于社会工作服务基地建设。2011年1月,四川省 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社工教育协会联合成立了希望社工服务中心,由利州区政府每年出资40万元向其购买社工服务。嵌入政府型表现出的特点,与当地政府关系很好,而且经费较充分,服务所需要的物资设施齐备,服务工作人员较多,服务效果较好,受到当地党政和群众的欢迎及普遍好评。不足之处是经费与效益不成比例,有些组织过于注重形式超过内容(韦克难、冯华、张琼文,2010)。
第二种,社会组织主导模式(柳拯,2010)。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一般是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也包括未注册的民间组织和各种国内外的公益性基金会,这些组织内有社会工作者或灾后聘请社工在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其经费来源多为向基金会的项目申请或其他组织(包括海外机构)、私人捐赠。从服务效果来看,这类组织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同,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但在调查中都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对有些NGO表示不满,说他们别有用心,要求对NGO出台更严厉的管制措施。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是在没有纳入灾区援助体系的情况下,由单个社会组织或多个社会组织组成联合体进入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韦克难、冯华、张琼文,2010)。
第三种,高校主导模式(柳拯,2010)。这种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一般是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派出专业教师或聘请专业社工,在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这些社会组织大多没有进行注册。其经费来源以项目申请或其他组织捐赠为主,如在汶川有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高校;在北川县、绵竹市有西南财经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这些学校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强,有详细的工作计划,有督导,背后有学校为依托,可以派出大量的学生志愿者参与活动,学校之间彼此也相互联系、相互支持。这些组织一般与当地的党委、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合作良好,能得到当地党政、社区自治组织的支持,他们也积极为当地政府、党委出谋划策,积极解决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充当二者的沟通桥梁。从服务效果来看,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当地干部与群众关系较好,社会秩序较为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社区活动丰富,当地群众与党政干部对社会工作认识较正确,并普遍接受社会工作的理念,对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认可度、评价较高。在灾区的高校社会工作站规模都比较小,主要原因是经费制约(韦克难、冯华、张琼文,2010)。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模式的初步形成,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救灾响应机制,促进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促进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灾害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专业作用提供有益借鉴。
三、社会工作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存在的问题
社会工作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其作用能效明显,也得到灾区居民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肯定;参与其中的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也得到提高;还能促进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但社会工作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社会工作介入救灾和灾后重建缺乏制度性建设
笔者于2009年受民政部委托,对在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全面调查(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在2009年调查的149个的社会组织中,属于事业单位(包括高校)的组织占26.2%;民政注册组织占26.8%;没有注册的志愿者组织占25.5%;境外的社会服务组织占13.4%;工商注册的组织和其它性质的组织只分别占4.0%。调查结果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组织是没有注册的(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2010年11月仍在灾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12家社会工作机构,大多数也都是依托于高校(如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或完全的非营利组织(如天津鹤童、都江堰华循),完全由政府派出的机构或政府出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较少。简言之,政府的救灾体系中并没有主动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灾后重建中,也没有主动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形成合作,政府对社会工作服务很少购买,使得社会工作在灾区的服务存在种种困难,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极为艰难。
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灾后的恢复重建中主要强调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却忽视灾区的社会建设,如社区人际关系的恢复和发展,社区组织的建设等,导致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在政府救灾体系中还不明确;当地政府对社会工作者开展的活动持观望态度,社会工作者没有实质性的权利,无法参与到政府正式的援救系统中进行工作。例如评估灾民需要是社会工作者擅长的事情,但是社会工作者评估到的需要并不能影响物资发放和救援的政策和执行。
(二)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不高,缺乏合法性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时间较短,社会认知度较低。1988年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才在中国正式恢复,二十多年的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况且由于政府部门至今还没有为社会工作设置岗位,近两年来在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政府才开始重视社会工作,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这一问题可能在汶川地震的受灾地区更为严重,从四川省社会工作教育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到2002年才在四川的高校中开设,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前,社会上基本没有社会工作的岗位,而且社会工作的教育者也较少在社会中开展社会工作的公共教育,告知民众、政府官员和其他的人员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等。这就导致在开展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和政府官员不了解社会服务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和服务没有持续性,参与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多数社工服务机构没有到当地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注册,导致许多社会组织在开展社会活动时,常感到缺乏生存空间。
(三)社会工作服务无固定经费来源,缺乏保障性
在2009年所调查的149个组织(团队)中,有37.6%的组织在其成员内部自筹服务资金。在这些组织中,完全没有财政压力的只占2.0%,没有财政压力的占12.8%,有较大压力的占22.8%,有非常大财政压力的占30.2%。而一项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募集的760多亿元社会捐赠资金中(其中资金652.52亿元,物资折价105.3亿元),58.1%流向只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36%流向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只有5.9%流向公募基金会,而社会捐赠的物资基本流向政府部门和红十字会系统,政府掌握大部分救灾资源。流入政府系统的社会捐助主要投入到基础设施、房屋、学校等硬件建设上,许多从事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无法获得社会捐款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挤压民间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生存发展空间。即便一些机构获得项目经费支持,但捐资方也强调“不给项目办公经费和人员费用”。因此,除有基金会支持的成熟机构,更多在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生存境况艰难,其执行项目处于“断炊”和“休克”的尴尬境地(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
(四)社会工作服务没有当地的人员和社会组织,缺乏长期性
2009年所调查的149个组织(团队)中,有144个组织(团队)回答灾区工作规划的问题。这144个组织(团队)中,15.3%的组织(团队)无工作规划,16.7%的组织(团队)有1至6个月的工作规划,10.4%的组织(团队)有7至12个月的工作规划,12.5%的组织(团队)有13至24个月的工作规划,14.6%的组织(团队)有25至36个月的工作规划,30.6%的组织(团队)有37个月及以上的规划(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
很多项目的短期性,不能对灾区进行持续的帮助,浪费很多之前建立的资源;坚持下来的NGO面临经费短缺,难以为继的局面。由于社工援建灾区的工作模式不是长期性的,工作缺少系统性,导致服务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而培育当地社工并纳入当地救灾体系而非“外来援助”成为许多被访者的共同期待。
灾后重建中很多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持续,造成服务效果不理想。特别是需持续的服务,如心理康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才能保证服务效果。但是由于服务人员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给受助对象带来伤害。
(五)社会工作无统一服务标准,缺乏规范性
2009年调查的149家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中,超过一半(53.7%)的组织(团队)有专职的人员对开展的服务进行督导,12.1%的组织(团队)有兼职的定期督导,18.1%的组织(团队)有时按要求进行督导,16.1%的组织(团队)对自己开展的服务没有进行督导。说明了有一些社会服务组织(团体)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对服务的督导,以提升其自身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
在所调查的149组织(团队)中,23个(15.4%)组织(团队)对所开展的服务没有进行评估,126个(84.6%)组织(团队)对所开展的服务进行了评估。这126个组织(团队)其中54.0%的组织(团队)按项目要求做评估,16.7%的组织(团队)不定期对组织服务进行评估,29.4%的组织(团队)定期对组织服务进行评估。从以上组织(团队)对自身服务评估的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的参与调查的组织(团队)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对开展的服务进行定期评估的认识,这将有利于他们提高自己服务的质量,以更好地满足灾区民众的各种需要(韦克难、张琼文、冯华,2010)。
在2010年调查的12家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中,9家选择了“定期开展评估”,5家选择了“所有项目都要进行评估”。这些评估中有6家是“机构内部和外部人员都有评估”,2家选择了“机构内部自评”。这些评估缺少行业的统一规范,完全依赖这些社会工作站的自律性,服务的深度、效果都缺少统一标准。
从社会工作者本身的职业伦理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起步不久,职业监督机制及职业退出机制尚未建立,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水平及职业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服务技能培训,导致工作质量受到影响。
(六)社会工作服务注重预防与恢复,缺乏发展性
社会工作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恢复、预防的功能,但发展的功能明显地发挥不够。我们通过调查,有受访机构表示“考虑到四川灾区重建工作可能持续长达20年,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需要社会工作者提供长期的服务。从香港、台湾等地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来看,即使灾区重建过程基本结束,专业社工的综合服务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专业社工的综合服务可以协助社区居民去发展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区居民过上健康、稳定的生活,使社会更和谐。”因此,灾后重建,更需要社会工作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居民能力的提升。
四、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模式的反思
在救灾与重建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社会工作服务组织都为灾区群众提供了公共服务。国务院下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救灾作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容。事实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带有均等的特点,即人人有份,人人平等;而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提供的公共福利服务则带有差异化的特点,即针对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可以满足残疾人、老人、孤儿、妇女、儿童等特殊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其中,政府和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发挥服务主体和拾遗补缺的互补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关注灾区的社会建设,需要将社会工作正式纳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政府体系中,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民办社工机构为服务主体、社区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一)加强灾区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并保障其合法性
由于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在灾后重建中没有将社会工作列入规划中,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建设,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存在制度化的困境。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主导是指需要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制度化:
第一,将社会工作纳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政府体系。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能起多大作用,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将社会工作纳入政府救灾体系,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地位、角色、权利,以便让社会工作者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与决策。
第二,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管理服务机构。各灾区可以结合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需要,设立社会工作办公室,由社会工作办公室来统一管理灾区社会工作事务,制定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搭建社会工作交流平台。同时,在临时安置点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整合政府投入的社区福利资源,统一提供社会工作服务。
第三,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灾区社会工作的经费投入。根据国务院2012年公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为城乡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提供物质帮助,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有尊严地生活和平等参与社会发展”,采取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合同委托、服务外包、土地出让协议配建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鉴于灾后重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社会工作服务应该主要以政府购买服务和合同委托为主。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地震初期,在社会各界包括各种基金会和企业都关注灾区的情况下,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比较容易面向社会筹集资金。但在地震过去一段时间后,随着社会关注度的下降,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面临的资金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时,要想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长期地存在下去,就需要由政府向其购买服务,从而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
虽然政府购买服务是主渠道,但社会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一种有效又可以制度化的形式是建立受灾省或市成立的社会公益发展基金,来解决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瓶颈问题。具体做法是由受灾省或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再由财政预算中拨付一部分,筹集500万元以上的经费用于公益事业及社会工作事业发展。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投标,由第三方公益项目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机构,负责评审项目,公益项目评审委员会由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构成;由公益项目评审委员会通过的项目,再交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省或市社会公益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三个部分:资助慈善公益项目、资助社会工作公益服务项目、资助社会企业项目。
(二)灾后社会工作介入必须以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为服务主体,探索建立民办非企业社工组织,促进灾区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
5·12地震之后,由于大多数在灾区的社会工作机构是临时的,导致机构缺乏对灾后恢复重建的详细服务计划,导致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不能具有长期性;社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者几乎全部是外来的,不能形成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力量。基于以上原因,应改革目前在灾区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运作模式,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当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形成留得住的社会工作力量,从而推动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土化、职业化、长期化和制度化(边慧敏、林胜冰、邓湘树,2011)。这也符合中央关于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文件精神,2011年中央18个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突出重点、立足基层、中国特色”的指导原则。其社会参与,就是通过发展民办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来吸纳社会工作人才。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胡锦涛,2012)也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强调“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作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一部分,需要大力发展,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成为参与社会管理的社会力量。
(三)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能理论为指导,重点开展灾区的社区能力建设,提升居民的社会资本,恢复和促进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在灾害发生后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学者们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模式,比如社区发展视角、优势视角、系统视角等。徐文艳、沙卫、高建秀(2009)、张昱(2008)、刘斌志(2009)等都指出灾后社区重建的重要性。徐永祥(2009)基于上海社会工作服务团在都江堰参与5•12汶川灾后重建的经验和社会工作的“嵌入、建构、增能”理念,提出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三个模式,即:政社分工与合作模式、社区信息链接模式、需求评估与回应模式。
虽然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涉及的理论非常多,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增能理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由于灾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服务对象是其中的子系统,服务对象受到了社区、政府、学校、邻居与自然环境的影响,灾害社会工作必须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去关注个人的生活经验、发展时期、生活空间和资源分布等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活动(Meyer,1983);认识到环境或情境因素对促进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的赋权具有重要作用;聚焦于环境中可获得的现有和潜在资源,可强化案主的优势和抗逆力(whitaker,Tracy,1997)。同时,增能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增能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
汶川地震灾后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说明,社区能力建设是很多社工服务组织关注的重点,其中一个有效的途径是“社区组织+社区领袖+社区活动”三位一体的社区能力建设。即建立各种社区组织,作为能力建设的平台,同时也是发展社区协作网络的平台。社工服务组织在开展社区活动时,社区居民通过交往互动可以形成与加强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居民的相互帮助,提高居民的社会资本;社工服务组织通过社区活动,紧紧依靠并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以培育和发展社区组织。在此过程中,发现和培养一批社区领袖,逐步锻炼其项目策划能力、组织实施能力、协调能力等。这种社区能力建设的好处是一方面培训,一方面实践,从而能够真正提高并固化所在社区的能力。这已经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模式。社区能力增加,才能达到居民自力更生,更好建设自己的家园。
总之,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在我国还是首次,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完全靠社会工作者的探索,事实证明,只要按照“党的领导、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突出重点、立足基层、中国特色”去发展社会工作,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灾害社会工作模式。
[1]边慧敏、林胜冰、邓湘树,2011,《灾害社会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2]陈涛,2009,《社会工作者在纹川地震后的调解者角色:机会与限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
[4]刘斌志,2009,《“5.12”震灾后的社区重建:含义、策略及其服务框架》,《城市发展研究》第4期。
[5]柳拯,2010,《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成效与问题——以“5·12”汶川特大地震为例》,《中国减灾》第7期。
[6]高艳青,2007,《以人为本:社区发展的关键》,《理论前沿》第22期。
[7]邵佩君,2003,《台湾集集震灾后社区营造式重建机制之探讨:以军功里和刘家伙房之重建为例》,《都市与计划》第4期。
[8]王思斌,2008,《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介入重点》,《社会工作(学术版)》第11期。
[9]王思斌,《发挥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6期。
[10]韦克难、冯华、张琼文,2010,《NGO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概况调查》,《中国非营利评论》第6期。
[11]徐文艳、沙卫、高建秀,2009,《“社区为本”的综合社会服务: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实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2]徐永祥,2009,《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3]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民政厅,2009,《关于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工作服务情况的调查报告:基于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
[14]喻肇青,2001,《中寮农村社区重建的反思》,《安全永续的国土发展与灾区重建:九二一震灾周年纪念研讨会实录》。
[15]张和清,2009,《社会工作者在灾后重建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定位:以汶川县印秀镇广州社会工作站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张昱,2009,《个体社会关系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中国社会工作研究(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张昱,200,8,《安置社区建设:汶川震后重建的社会工作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
[18]朱希峰,2009,《资源运作:灾后社区社会工作的重要技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19]Chambers,R.1994.“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Analysis and experience.”World De⁃velopment,22(9),1253-1268.
[20]Fei,M.P.&Ip,E.K.P.2009.“Reconstru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post-earthquake commu⁃nity: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Qin Jian Ren Jia,Dujiangyan.”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3),189-200.
[21]Galambos,C.M.2005.“Natural disasters: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consideration.”Health and Social Work,30(2),83-86.
[22]Harrell,E.B.&Zakour,M.J.2000.“Including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disaster planning:De⁃velopment of a Range-of-Type Measure.”Tulane Studies in Social Welfare,21(2),61-83.
[23]Javadian,R.2007.“Social work responses to earthquake disaster: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Bam,Iran.”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50(3),334-346.
[24]Low,S,M.,Taplin,D.H.,&Lamb,M.2005.“Battery Park City:An ethnographic field study of the community impact of 9/11.”Urban Affairs Review,40(5),655-682.
[25]Mathbor,G.M.2007.“Enhancement of community preparedness for natural disasters:The role of social work in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for sustainable disaster relief and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50(3),357-369.
[26]Pei,Y.X.,Zhang H.Q.,&Ku,B.H.B.2009.“Guangzhou social workers in Yingxiu?:A case study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ichuan 5.12 earthquake in China.”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3),151-163.
[27]Pyles,L.2007.“Community organizing for post-disaster social development:Locating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50(3),321-333.
[28]Robards,K.J.,Gillespie,D.F.,&Murty,S.A.2000.Clarifying coordination for disaster plan⁃ning.In M.J.Zakour(Ed.),Disaster and traumatic stress research and intervenetion(pp.41-60).New Or⁃leans,LA:Tulane Studies in Social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