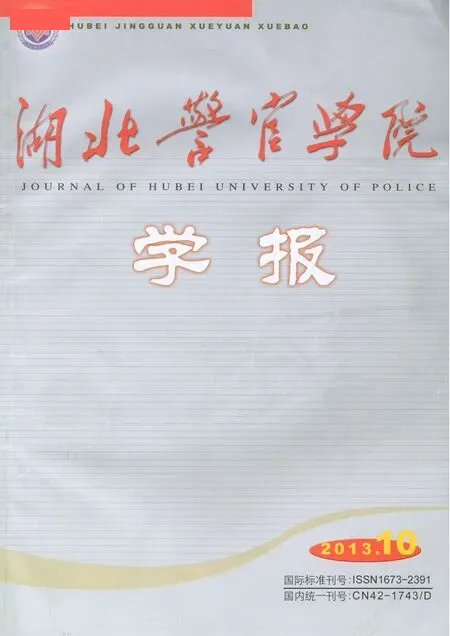“扒窃入刑”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2013-04-11李寒劲冯杨勇
李寒劲,冯杨勇
(1.上海政法学院 法律学院,上海 201701;2.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湖北 宜昌 443100)
2010年9月,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开展了“广州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追踪调查”,电话访问了1050位市民,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受侵害率为6.3%,犯罪类型以“盗窃”与“扒窃”为主;发生在“公交车上”的犯案有所增加;从多年数据动态来看,“扒窃”从2008年起呈持续上升趋势;受访者对广州治安状况的满意度为四成一。[1]可见,扒窃案件已经成为侵害公民财产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顽疾。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将刑法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此,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纳入了刑法的范围。扒窃行为入刑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对犯罪立法所采取的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传统上,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即意味着犯罪成立需要达到一定“量”的要求。[2]这种量在侵犯财产犯罪的案件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数额,只有达到了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即以结果决定是否构成犯罪。而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扒窃的规定来看,扒窃行为本身的实施与否才是判断罪与非罪的关键,扒窃的数额已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立法的改变,使得盗窃罪不再是纯粹的结果犯,对司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扒窃并不是法律用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扒窃是指从他人身上偷窃财物。[3]它产生于反扒实践中,一直在侦查学中使用,是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民警在工作总结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扒窃首次出现在立法上是在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张明楷教授认为,扒窃是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客观上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二是所窃取的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三是所窃取的财物应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4]按照立法机关的解释,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5]可见,无论是学理上还是立法上对扒窃的认识都包含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窃取随身财物两个核心要件。
一、缘由:扒窃入刑的正当性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当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6]
有学者指出,在治安形势不好、犯罪的发案率上升、受害人的激愤情绪强或者民愤极大的情况下,为了一般预防的需要,可以从重量刑,而在犯罪人再犯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为了个别预防的需要,也可以从重量刑。[7]虽然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一味地依赖严刑峻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脱离实际寻找从宽理由。因为只有维护刑罚应有的惩戒功能,才能维护法律权威。尤其是“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后诸多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和公众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国家预防和惩治犯罪也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8]。而扒窃行为的猖獗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加剧,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导致风险控制难度的加大。因此,刑事立法和司法必须按照宽严相济的要求对扒窃行为从严处理,这样才能使被害人与社会公众通过罪犯受到刑罚惩罚而满足公平感和正义感。
(二)刑法必要性原则的本质要求
适用刑法必须遵循必要性原则。这种必要性是指”刑法规范的设定和刑事法律的适用,应当以维护社会最根本的价值所必需为基础和限度。“[9]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10]虽然扒窃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财产损失一般都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扒窃行为人往往长期以此为业,且其再犯的可能性相当高,已严重威胁到了不特定的人,达到了需要采取刑法的方式调整这种行为的地步,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
“由于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法益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在解释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首先必须明确刑法规定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11]根据法益侵害说,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实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12]扒窃行为显然具备了行为犯必须具备的实质,传统的打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刑法对扒窃行为的容忍度降至临界点,刑罚成为了打击这种行为不可避免的手段,从而引发刑罚之网的扩张。实践证明,这种扩张是有效的,从心理上对扒窃分子带来强大的震慑力,有效地遏制了扒窃行为的发生。[13]
二、困境:司法与立法之割裂
(一)选择性执法之危局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将扒窃以行定罪,而非以量定罪,使得过去不够定罪标准的大量按照治安案件处理的扒窃行为需要定罪处理。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大约增加150万起盗窃罪案,罪案一下子增加40%左右。如此,仅盗窃罪一项就超过了2005年所有刑事案件的总和。[14]然而,从当前司法现状来看,除了扒窃入刑第一案以外,各地鲜有扒窃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让这些案件全部进入司法程序,就司法系统现有资源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各地不得不采取应对之策,于是选择性执法初现。
选择性执法(SelectiveEnforcementoflaw)原本是美国法上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警察根据经验确定执法重点,以调和立法权和警察行政权之间的冲突。我国学者对它的理解已经超出美国法的范畴,认为选择性执法是国家根据情势变化,试图获得灵活性,摆脱成文法的僵化而在执法上做出的调整。即什么时候严格执行哪部法律,采取什么执法手段,什么时候放松哪部法律的执行,什么时候严格执行哪个具体的案件,采取什么执法手段,什么时候对哪个案件的执行特别对待等等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执法方式。[15]各地受人员、装备等条件的限制,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方式对扒窃行为进行打击,这有利于针对特定主体采取区别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特定问题,节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对实质正义的需求。但是,运动结束之后的自然放松又使故态复发,这样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也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引发执法腐败,引发新的不公正。
(二)罪与非罪之困惑
举一则案例,张某在公共汽车上扒窃一乘客钱包,被反扒民警当场抓获,张某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其所扒得的是空钱包。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不论数额或者其他情形的限制,所有的扒窃行为都应当定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并没有盗窃到实际的财物,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应定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扒窃行为的定罪进行适当限制。①如2011年6月1日,成都市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召开会议,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办理扒窃案件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关于办理扒窃案件适用有关法律问题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对公安机关办理扒窃案件可以提请批捕的9种情形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笔者认为,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扒窃行为属于以行定罪,而不是以量定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无论是是否盗取了财物都应当定罪,而其盗窃财物的数量只是其量刑的依据之一。②张军在《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中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属于初次扒窃或者是被教唆扒窃的;(2)扒窃数额较少的财物,主动投案、全部退赃或者退赔的;(3)被胁迫参加扒窃,没有分赃或者分赃较少的;(4)确因治病、救济、学习等生活急需初次扒窃的;(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三)既遂与未遂之辨析
在另一案例中,贾某至某商店预谋行窃,当其将手伸入正在购物的王某的挎包时被人发现当场抓获,随后民警从贾某身上搜出作案工具镊子。对于贾某的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也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贾某的行为构成未遂。因为盗窃罪的既遂应采用”失控+控制“说,本案中行为人还未取得财物即被民警抓获,事实上对被害人的财物并未取得控制权,故构成未遂。另一观点认为,贾某的行为构成既遂。理由是:扒窃是行为犯,只要其着手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既遂,而不论其是否窃取了财物。
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典型的结果犯,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规定为行为犯,取消了量的限制,但是行为犯与结果犯一样,也存在既遂和未遂问题。笔者认为,鉴于行为犯之行为有其过程性,其侵犯法益也必然显现出相应的程度性,因此,扒窃行为的既遂与未遂是与其行为的过程紧密联系的,其判断标准自然不能与以行为结果紧密联系的结果犯采取同一标准。因此,扒窃行为的既遂与未遂可从扒窃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来把握,即以是否对法益构成现实侵害为划分标准:已现实侵害法益的,应认定为既遂;尚未现实侵害法益却又有相当危险性的,应认定为未遂。上述案例中,贾某已着手实施扒窃行为,已经在侵害现实的法益,其行为应构成既遂。但是贾某携带工具进入公共场所但因其已被纳入警方的盯防范围,随即被警方抓获,由于其只具有犯罪的意图和准备,尚未实施实际的侵害行为,故构成未遂。
三、路径:扒窃入刑精神内涵之目的正义解读
(一)正确理解扒窃入刑的精神内涵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通过制订刑法,将某些行为类型与刑罚这种具有痛苦性的强制措施联系起来,显然是表明国家对这些行为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因此,刑罚总是具有消极评价的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令行为人痛苦的特征。[16]《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纳入刑罚,代表了国家对扒窃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所给予的否定性的质的评价。正如耶林所说,刑罚必须以外在目的作为其创造者,这种外在目的就是防卫社会,以保护具体的秩序和法益。[17]然而,法条只能体现静态的公平正义,实质的公平正义还有赖于国家刑罚权中的行刑权、量刑权的行使,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真实的公平正义。因此,扒窃入刑只是刑罚静态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真正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定罪量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扒窃入刑的刑罚正义。
(二)细化扒窃入刑的解释
虽然学理上和立法上对扒窃的认识都包含了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共场所、窃取随身财物两个核心要件。但是无论是刑法还是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公共场所管理条例》都没有对何为公共场所进行明确界定,在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时被扒窃,十字路口是否属公共场所?受害人在公共场所放置于身边的财物是否属于随身财物?对这些问题,现行法律均未做明确规定,也未以明确的司法解释予以释明,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困惑和混乱。
有学者提出以列举的方式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但是列举式难免有遗漏。笔者认为,公共场所应当是不特定的人可以出入、停留的场所,而不应根据场所的性质、人流量等来划分是否属于公共场所。而对随身财物,应当采取扩张解释,包括身上或者置于其控制范围之内的财物,但若窃取超出了控制范围的财物就不应当属于扒窃。
(三)加强反扒队伍建设
扒窃多为团伙作案、流窜作案,行为人反侦查能力强,很多受害人被扒窃之后因为数额不大不愿意报警,导致举证困难,现有的警力应对各类刑事案件已经捉襟见肘,面对每天都会发生十来件甚至更多的扒窃案件,无论是精力还是现有的技术设备,都无法支持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运动式的打击模式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对法律规定必然形成冲击,导致“莫伸手,伸手必抓”的信念受到动摇。因此,必须组建专门的反扒队伍,加强反扒人员的技术培训,在人员、经费、装备等方面给予保障,形成反扒的长效机制,从而对扒窃行为形成足够的威慑,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
(四)拓宽非刑罚化途径
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矫治罪犯,使其能够适应社会生活而不再犯罪。而在我国,尤其是从刑罚类型来看,依然以监禁刑为主,非刑罚化方式不足。就轻微犯罪者或者过失犯罪者而言,对其采取一定的教育措施往往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尤其是随着“酒驾”、“扒窃”入刑,一味的严惩虽起到了威慑作用,但是显得教化不足,反而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探索新的非刑罚化途径成为当务之急。有必要借鉴国外规定,在刑法中引入非刑罚化制度,对于轻微的扒窃案件予以规制。
综上所述,扒窃行为被归入刑法,是法律对民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切实保护,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扒窃入刑可以有效地威慑扒窃犯罪,实现刑罚的正义。但是入法只是静态意义上的刑罚正义,要实现动态的刑罚正义还有赖于司法实践中行刑权和量刑权共同作用,只有立法和司法双管齐下才能最终实现刑罚正义。
[1]陶达嫔.广州治安满意度41.0%公交盗窃发案率上升[N].南方日报,2011-07-06.
[2]于志刚.刑法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63.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101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1.
[6]丰华涛,刘志来.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解与适用的探讨[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2).
[7]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22-623.
[8]杨兴培.“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2).
[9]张智辉.刑法理性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5.
[10]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
[11]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8.
[1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49.
[13]冰客.扒窃入刑后城区扒窃案件降三成[N].十堰晚报,2011-10-12.
[14]周详.“醉驾”、“扒窃入刑”陷入执法难堪[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26.
[15]戴治勇.选择性执法[J].法学研究,2008(4).
[16][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87.
[17]邱兴隆.比较刑法(第二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