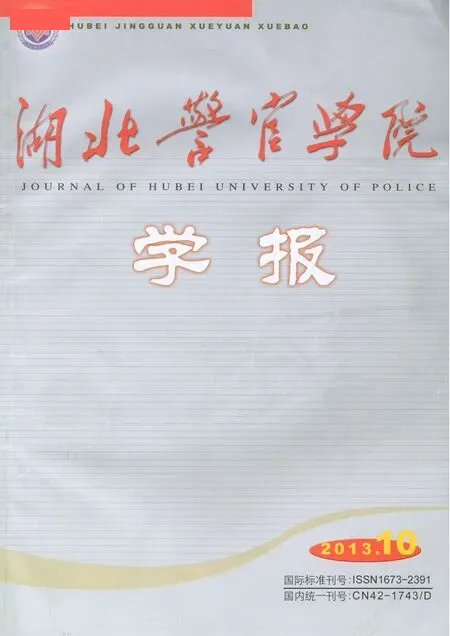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之完善
2013-04-11雷山漫
雷山漫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1997年刑法施行之前,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般比照盗窃罪论处。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刑法第219条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据该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违反约定或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或者明知或应知使用上述行为,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1]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商业秘密,刑法第219条将其界定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从刑法第219条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来看,现行刑法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内容如商业秘密的含义及针对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的规定都直接来源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一致虽然体现了一国法律体系的完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统一,但也因为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简单移植有关部门法的规定,没有很好依据刑法的基本原理,从刑法的特殊性出发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加以分析和处理,从而导致因立法的不科学、不协调引发关于本罪的诸多争议。商业秘密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意义重大,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加强对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研究,完善相关内容是为必须。
一、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形式的完善
我国学术界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有不同的看法,主要争议问题有二:一是本罪的罪过形式是否包括过失;二是若本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这种立法规定是否合理,有无完善的必要。
探讨争议问题一,即过失能否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必须结合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刑法第219条第1款以列举形式规定了非法获取等3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第2款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就引发争议较多的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看,“明知”应指故意没什么争论,“应知”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过失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法条所说的“应知”是行为人负有“应知”义务的表达,至于行为人“应知”而未知,除了从过失角度去理解,别无其他罪过能符合。[2]而且我国刑法第219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行为类型的规定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的全盘吸收,该条中由过失构成的民事侵权行为也被刑法直接吸收过来加以规定,所以依此立法来源分析,侵权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上既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过失。另一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过失存在的范围。除219条第2款外,第1款规定的三种行为是否也可以出于过失?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就第一种行为分析,行为人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是直接故意;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行为中,行为人“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至于“披露”,其罪过形式应表现为故意,而不包括过失。因此就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四种行为类型看,前三种行为类型即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都是故意而非过失,第四种行为类型即“以侵犯商业秘密论”的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则可以是故意或过失。通过上述分析,依罪刑法定原则,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过形式包含过失,但仅限于间接侵犯商业秘密,即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对于争议问题二,即刑法设置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合理,刑法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保留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构成犯罪的规定。该观点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第三人过失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过失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责任,使现有法律条文从结构上看逻辑不通。因为“视为侵权”的第三人转手取得商业秘密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有侵权责任,而其前手即直接违法获取商业秘密的第二人却只有在故意获取第一人商业秘密时才构成侵权,第三人的责任严于其前手,不合逻辑。[3]应将过失直接或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另一种观点则正好相反。如有的学者认为,从刑法条文的字义上作这样的解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从立法精神或立法的科学性而言,似乎不宜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当作犯罪处理。[4]也有观点认为,刑法不追究过失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却要追究第三人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其实是向第三人提出了程度更高的注意义务,确实过于严厉。这样的刑事追究既无合理性,也无必要性。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具有合理性,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将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不利于科技、信息的交流、交易、传播和运用。因为商业秘密以不公开为前提,不具有法律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所以对其给予的法律保护的力度应较专利权、商标权这类公示性强的知识产权弱,法律提供的保护手段主要是民事手段。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在对商业秘密保护中,我们必须注意,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刑事保护的协调及刑事保护的适度,而肯定商业秘密侵权过失犯罪的观点混淆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可能导致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泛化。对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人而言,其主观恶性小,追究民事责任即可,无需刑法介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其不具有较强的刑事可罚性不应给予刑罚处罚,而只宜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5]我国刑法将“应知”这种过失状态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仅非常严厉,也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和自由。如第三人在购买某种技术时,由于疏忽大意没有认识到对方转让给自己的秘密技术是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由此对第三人的购买行为定罪会使人们在科技、信息交易、交流时唯恐自己触犯刑律而不敢为之。[6]因此,刑法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时,应贯彻确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在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正当利益的同时,也要从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衡平权利人私益和社会公众利益,避免对私权的过度保护。对涉及技术、信息等商业秘密的过失侵权行为不宜犯罪化,从而为科技、信息的交易、交流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二,若仅处罚第三人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会有损法律条文的内部协调性。从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看,第219条第2款规定的间接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可由故意或过失构成,但第1款中规定的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以及违约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需要由故意构成。两者相比较,不难发现刑法对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处理反而比对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处理更为严厉。另外,在实践中也会出现违反权利人保密要求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的情况,但却因主观并非故意而只能定性为民事侵权行为。为了解决这种立法的不协调,有学者提出对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可以出于过失,但这样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因为刑法第219条规定的第一种行为,即行为人以盗窃、利诱、胁迫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是直接故意,不包括过失。所以,对应刑法的规定来一一分析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方面,会发现认定过失亦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无法消除刑法法律条文内部规定的不协调。
第三,将过失包括在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中,不符合商业秘密的特点。商业秘密是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而得以存在的权利,权利人对之要采取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一般人无从知晓,而且一些表现为配方、诀窍,甚至纯粹是经验的商业秘密也不存在技术资料的记载形式。在此情形下,依第219条第2款规定,要求行为人了解其前手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真正来源以判断自己对该项秘密的获取是否合法是极为严苛和不现实的。所以,刑法将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过失也可构成犯罪缺陷明显,不仅不考虑客观现实设定了一般人负有“应当预见”的法定义务,而且排除了对商业秘密的善意取得,容易模糊善意第三人与侵权人的界限[7],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后,从其他国家立法来看,发达国家对侵犯商业秘密主观要件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美国用刑法来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只有经济间谍罪和侵夺商业秘密罪两个罪名,且在主观上均要求故意才能成立。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也未将过失作为犯罪处罚。只有日本对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但其过失规定为重大过失,依国外私法理论,重大过失相当于故意。国外刑法对商业秘密犯罪规定的审慎值得我们注意。
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可将刑法第219条第2款修正为“明知前款行为,而故意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比照前款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8]这样在限定了第三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罪过形式为故意的同时,还考虑到第三人间接侵权与第二人直接侵权间刑事责任的大小区别,对前者从轻或减轻处罚,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二、明确、丰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从我国刑法第219条的规定看,侵犯商业秘密罪属结果犯,即法律要求必须具备“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条件时,才能构成犯罪。此条件也正是侵犯商业秘密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的唯一界限。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有关规定直接来源于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刑法第219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相比,除对损害结果有不同要求外,两者文字表述几乎完全一样,区别就在于有无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的危害结果。刑法第219条中规定的“重大损失”及“特别严重后果”是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重要标准,但如何计算“重大损失”和“特别严重后果”,两者如何区分等问题,法条并未明确,这一模糊规定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性和明确性要求,而且由于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专业性强且类型多样,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成为一大难题,各种观点也争论不休。
为了防止刑事责任的不统一、扩大化,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在2001年和2004年做出了两次司法解释,都将犯罪数额作为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其中2004年两高司法解释中的第7条规定实施刑法第219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单纯以“50万元的数额”这种客观损失的“量”为基点确认犯罪与否的立法模式弊端明显,如在客观上会导致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制裁不足,而对因违约等利用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制裁过度。因为盗窃、利诱、胁迫等违法行为和违反合同法、劳动法的违约行为性质不同,前者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后者。如果有人明显是以盗窃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商业秘密的,但只要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在50万元以下,按照现行法律,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对那些以不正当手段盗取商业秘密的侵权者过于宽松。[9]而且司法解释中没有解决商业秘密的价值由谁评估、评估标准的问题,这些专业问题交由刑事法官来解决显然是不合适的。
司法实践中,为了弥补单纯以权利人的损失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不足,在认定“重大损失”时往往结合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商业秘密的可利用周期、商业秘密的使用和转让情况以及行为人对商业秘密的窃取量、披露范围、使用状况等因素,在刑法适用时综合考虑。但刑法立法的不明确给司法实践造成的疑难仍难以较好解决。从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完善上,我们应明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计算范围及方法,可采取司法解释的形式,列举哪些情况属于重大损失,哪些情况属于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同时可以确定相应的数额标准,以解决实践中的困难。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发布的《立案追诉标准(二)》中,就侵犯商业秘密案规定了应予追诉的四种情形,如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因侵犯商业秘密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以上、致使商业秘密权利人破产等。此追诉标准结合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特点,内容较以前丰富,在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外还增加了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使权利人破产、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兜底规定,有利于准确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三、罪刑结构的均衡
罪刑均衡即罪刑结构的协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其基本含义是刑罚一定要和犯罪相称,即罚当其罪。决定刑罚轻重要与社会危害性大小相当,重罪适用重刑,轻罪适用轻刑。[10]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同样应依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设置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没有区别侵权主体身份的不同,也没有区别不同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及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只设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一个罪名,而且基于同一罪名,都在相同的法定刑幅度内适用刑罚。
具体来看,我国刑法第219条将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行为、非法利用不法获取的商业秘密行为、违反约定或者要求利用商业秘密的行为、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等这些性质不同的行为均以单一罪名“侵犯商业秘密罪”予以规制,都适用同一个量刑幅度,忽视了不同行为主体、不同行为方式在侵害同一商业秘密时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程度、犯罪构成要件的差异。又如该条规定的第二人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几种,就行为性质而言,利诱、胁迫手段的社会危害性比盗窃手段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盗窃等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与违反合同法或劳动法的违约行为相比,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向外国企业或组织泄露与向一般人员泄露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具有一定业务身份或职务身份的人员披露使用与一般人员披露使用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刑法对上述问题不加区别地笼统规定在同一罪名下并处以同一种刑罚,不仅有违罪名设置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导致难以发挥刑事制裁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应有作用。
所以,笔者建议,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可细分开来,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考察,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规定轻重不同的刑罚。如以盗窃方式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与以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因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同应规定不同的刑罚;仅窃取而未泄露或未使用与既窃取又泄露并使用,也因社会危害性的区别处以不同的刑罚。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一定业务身份或职务身份的人员比一般人负有更大的信赖义务,他们无故违反信赖义务的行为除有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损害权利人的利益外,还对社会的信任原则危害颇大,因此这类主体违反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要求或约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显然比其他人更具可罚性,应单独规定较重的刑罚。
四、严厉打击经济间谍行为
经济间谍行为是指“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以盗窃、骗取、收买、刺探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非法提供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11]随着全球领域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商业秘密已成为竞争各方的关注焦点。这也使得针对他人商业秘密进行的犯罪活动日见增多,所以经济间谍犯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国际竞争的产物。参看国外立法,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都规定了经济间谍犯罪。美国在《1996年经济间谍法》中专门区分了经济间谍罪和一般的盗窃商业秘密罪,并且将经济间谍罪规定在该法第一条,对其处罚也明显重于一般的盗窃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1款、第2款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在第3款规定:“明知该商业秘密将在国外被利用而泄露者,或自己在国外利用者,得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12]
对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的违法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关罪名,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刑法也有相应规制,但对经济间谍行为,现行刑法却缺乏明确的对应规定。由于将商业秘密泄露给国外或在国外使用的行为不仅对权利人拥有的商业秘密造成侵害,而且对国家利益也造成危害,所以这类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仅仅为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利益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更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境外组织机构及人员针对我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也将随之增多,所以有学者从保护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建议单独规定经济间谍罪罪名并设置较侵犯商业秘密罪更重的法定刑。[13]
在2010年初发生的“力拓案”中,四名当事人被拘后第四天,上海国安局和中国外交部先后表态称,胡士泰等人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37天后,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做出批捕决定。两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对“国家机密、情报”和“商业机密”的认定。前一罪名较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判死刑,而“侵犯商业秘密罪”仅是一般性质经济犯罪,犯罪行为人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后经法院审理查明,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中方雇员王勇等四人于2003年至2009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多次索取或收受钱款,为他人谋取利益。四被告还采取利诱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中国钢铁企业商业秘密,严重影响和损害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给中国有关钢铁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中,2009年中国20余家企业就多支出预付款10.18亿元,仅下半年的利息损失即达人民币1170.3万余元。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胡士泰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案的一审判决中,对四被告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数罪并罚。其中,胡士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和罚金人民币100万元。[14]
根据力拓公司的规定,上述涉案者都需要尽力收集中国钢铁企业内部信息以及中钢协会议的内容,尤其是每年12月至次年铁矿石谈判结束之前谈判关键期有关中钢协会议的内容。于是依靠“胡士泰四人组对中国相关企业给予稳定的优质货源、相较现货更加便宜的长期协议价格;中国的相关企业以现金、银行卡、铁矿石谈判相关信息作为回报”这一条完整的利益链,使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几乎能够做到在中国钢铁业秘密会议的第二天,就能够拿到会议的内容。澳大利亚籍人士胡士泰及另外3个中方雇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中国钢铁企业的商业秘密,致使中国企业在铁矿石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给中国钢铁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我国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定没有体现将商业秘密泄露于国外或国内的区别,无论对国家经济利益造成多大损失,都只能处以相同刑罚。这不仅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在控制知识产权犯罪时同样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不同种类和不同严重程度的知识产权犯罪区别对待。对于上述案件,若刑法有针对经济间谍行为的具体规定,将更有利于对该类行为的打击,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但笔者认为,专设经济间谍罪这一新罪名以打击该类行为会有碍于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努力,该罪名有冷战色彩之嫌,在现实中因较敏感易引发指责,所以为了打击经济间谍行为,可在现有刑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犯罪中单设一款,加重处罚。如规定以经济间谍为目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同时在处刑力度上加以提升,如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以体现对这类行为打击的严厉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S].1997-05-15.
[2]林亚刚.侵犯商业秘密罪再探[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1).
[3]张玉瑞.商业秘密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497.
[4]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47.
[5]唐稷尧.罪刑法定视野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6]赵永红.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429.
[7]蒋自豪,刘迎霜.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研究[A].顾肖荣.经济刑法(第3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2.
[8]陈山.浅析刑法设置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2(2).
[9]魏玮.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的思考[J].百家言,2007(6).
[10]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4.
[11]姜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28.
[12]杜国强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336.
[13]赵永红.知识产权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430.
[14]“力拓案”一审宣判,胡士泰被判十年徒刑[EB/OL].http:∥news.163.com/10/0329/15/62V04HRG000146B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