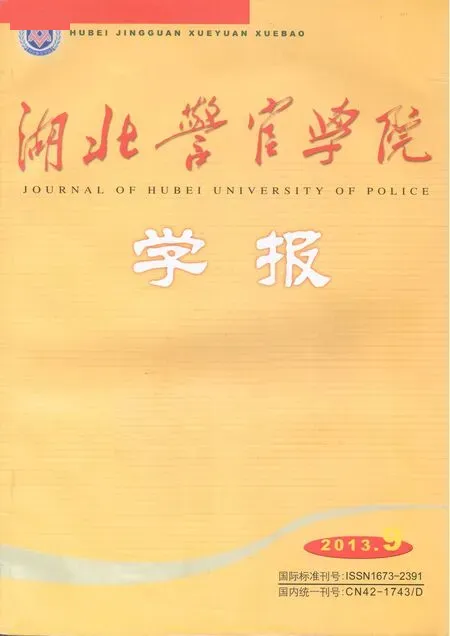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考量
2013-04-11瞿蓓,张玥
瞿 蓓,张 玥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考量
瞿 蓓,张 玥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是从人格的视角反思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危险人格纳入刑事法律的整个过程中。在制刑阶段,构建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犯罪危险人格为补充的犯罪认定标准;在求刑阶段,将危险性人格纳入量刑情节的考察范围;在行刑阶段,对危险性人格进行跟踪、重塑。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将促进未成年刑事政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促进刑罚个别化,实现法治社会的实质公正。
未成年人犯罪;人格化;危险人格;宽严相济
一、刑事法律人格化的提出
刑事法律人格化主要起源于刑法的人格主义思想,其渊源是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人格刑法为现代刑法指明了缩小犯罪圈、收缩刑事法网、发挥刑法功能的改革现行刑制的方向。[1]
刑法思潮经历了从贝卡利亚、边沁、费尔巴哈等人的刑事古典学派的启蒙,古典学派秉持着“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责任”的刑法观,逐步得到发展,以龙勃罗梭及其弟子菲利等人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的基本思想则是:犯罪人并不是根据自由意思进行活动的,而是在遗传和环境的支配下必然导致犯罪,[2]这极大地推动了刑事实证学派的发展。在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看来,“犯罪系由环绕犯罪人的社会关系及人固有性格所必然成立者”。[3]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分别以“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为中心,在刑法价值观上既各有不足,又彼此互补。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综合两派观点,将“人格的犯罪理论”和“人格的刑罚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人格刑法学的构想。
意大利刑法学界承认犯罪人的人格是一个与犯罪行为并存的现实,强调犯罪人的人格在刑法中的作用,是现代刑法最具灵性和最具人性的部分。[4]此后犯罪人的人格逐步纳入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的考量范围,特别是对于犯罪认定和刑罚裁判以及执行均有积极意义。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态势,为此,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后,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刑法(修正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等法律,涵盖了大量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文和规定,以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作为特殊的犯罪群体,通常具有主观恶性小、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可塑性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做好“寓教于审,注重感化”的工作。
从立法技术看,我国没有制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法,又受到普通刑法的限制,未能体现出未成年人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性。从刑法条文看,只要符合刑法条文的构罪要件,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就和一般成年犯罪人一样构成犯罪,并不存在差异。因此,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法条文,都没有从法律制度上体现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必要性
(一)从刑法价值角度
刑法具有谦抑性,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谦抑性价值更为显著。刑法谦抑性是指只有在不得不使用刑罚对侵害法益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时候,才可以将该行为作为犯罪,动用刑罚的手段进行制裁。即凡是适用较轻的判裁方法,诸如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等法律或非法律手段足以制止某种危害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和适用刑罚这一最重的制裁方法。[5]在刑法谦抑性思想的指导下,刑法具有了补充性、不完全性和宽容性的特征。[6]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则是将刑法谦抑性和宽容性的特点体现得愈加突显,使不具有犯罪人格的未成年犯罪行为人能够适当减轻刑罚,减少人身自由的被剥夺和限制,更大程度保护其人权。这恰恰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
(二)从刑法功能角度
刑法功能是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直接产生的社会效应。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效应和社会效应两方面来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构建,是将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凸显,彰显了未成年人犯罪所强调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性原则。虽然惩罚是刑罚的固有属性,但对未成年人犯的人格矫正和重塑使得犯罪人由不能再犯到不敢再犯,最终达到不愿再犯,从而实现特殊预防;同时,通过对具有危险性人格的未成年人的提前介入,阻止已有犯罪意念的危险分子,及时教育法制观念淡薄的不稳定分子,强化守法公民的规范意识。
(三)从刑事政策的角度
第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2009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提出:要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做到“两减少、两扩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正确理解和执行“两减少、两扩大”刑事政策,就是要在审判工作中对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中罪行轻微的,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增加和谐因素,减少社会对抗。[7]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两减少、两扩大”的政策,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所提出的将犯罪人的危险性人格评价引入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强调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人格的矫正和塑造、不再着重强调对行为惩罚的特征相吻合。实践中的缓刑制度,随着《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社区矫正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司法活动的不断深化,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第二,实现法治国家的有效途径。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人权保障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8]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即是将未成年人的人权保障落实到刑事司法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的人权,扩大未成年犯的自由范围,保障未成年犯的基本权利。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法治社会,建立在人权、宪政、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构建,对于现有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在更新的层面上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推动法治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第四,国际刑事发展趋势的需要。保障人权不仅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所要求的,也是未来国际刑事发展的必然趋势。以《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人权宪章》奠定了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9]我国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履行公约义务,不断深化对人权的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发展是尊重未成年人的理性与尊严,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在考虑犯罪行为的同时充分考虑其犯罪人格,缩小刑罚处罚的范围,减小犯罪打击面,扩大自由和权利,切实贯彻刑法人权保障机能。
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构想
(一)在制刑方面,重构犯罪体系,确立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犯罪危险人格为补充的犯罪认定标准
人格刑法学采用犯罪行为和犯罪危险性人格相结合的二元犯罪认定标准,分别从行为判断要素和人格判断要素对犯罪进行认定。行为判断要素主要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如故意、过失、排除性犯罪事由等;人格判断要素则是指依据人格测定的方式对犯罪人的危险人格类型进行分类,包括偏执型、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和表演型人格障碍等。人格刑法学的二元犯罪认定标准要求犯罪人不仅实施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同时要符合犯罪人格障碍类型。
刑事法律人格化是行为法和行为人法相融合的阶段,构建的犯罪体系应该从一元犯罪论逐步向二元犯罪论过渡,因此,构建的犯罪体系应当是以犯罪行为为核心、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补充的犯罪认定标准。第一,犯罪行为必须法定,犯罪人实施了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必须受到刑罚处罚,这是刑罚报复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罪刑法定要求的体现。第二,犯罪危险性人格的认定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明文确定,以避免主观归罪。第三,行为判断是核心和关键,犯罪人的危险人格的判断则是一种补充。第四,对于实施了法定犯罪行为而不具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应当给予区别对待和处理。
(二)在求刑方面,规范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是未成年刑事法律人格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通过全面的社会调查,了解涉案未成年人的人格状况,掌握涉案未成年人的日常表现和帮教条件等,有助于对其正确定罪、合理量刑,实现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人的目标。
规范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不仅可以通过调查反映出涉案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感化、教育和挽救的可能性,而且可以帮助法官公正合理地量刑,还可以为假释、缓刑、服刑管理、跟踪帮助提供参考依据。
从调查主体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对未成年人人格调查的参与主体或由多方共同参与或由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可以由涉案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和案件承办警官、检察官、法官以及涉案未成年人的辩护律师共同参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机构,由该机构负责,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
从调查内容看,人格调查是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进行综合调查。通过全面、客观、细致的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动机,关注涉案未成年人的帮教条件,寻求对犯罪未成年人最适当和最有针对性的处理方式。
从调查方式看,由专业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专业的科学鉴定,结合走访所得到的信息,以确保人格调查的客观真实性。
(三)在量刑方面,将危险性人格纳入量刑情节的考察范围
第一,在定罪量刑之前,除了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品格调查外,还应当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测量和可靠分析。对于犯罪人危险人格的确定应当主客观相结合,通过结构访谈、自我报告和临床评定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由监管机构出具犯罪人自我陈述报告,由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出具结构访谈报告,最后由指定的医院出具临床评定结果。
第二,组建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格鉴定委员会对各方出具的报告进行鉴定。由专门的犯罪人格鉴定委员会对未成年犯罪人人格进行鉴定,可以有效避免人为因素对认定结果的干扰,使鉴定结果更具充分性、真实性和权威性。
第三,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客观犯罪事实和犯罪人的危险人格科以刑罚个别化,将危险性人格纳入量刑情节之中。首先,对实施了犯罪行为同时具有危险性人格的犯罪人,应当考虑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同时处以限制减刑。其次,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具有危险性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来说,非监禁刑的处罚可以避免监狱内的交叉感染,同时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教育改造功能。最后,对于尚未实施犯罪行为,但具有危险性人格的人必须加强管控工作,积极预防犯罪的发生,降低犯罪率和再犯率。
(四)在行刑方面,对危险性人格进行跟踪、重塑
人格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一种行为倾向,是行为人所特有的,因此李斯特主张和倡导“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10]。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构建过程中,不只是将未成年人犯罪人的人格考量停留在制刑和量刑方面,还应拓展和延伸到行刑。行刑是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人格化的重要环节,将直接作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引入犯罪人犯罪危险性人格跟踪调查机制。建立未成年人的犯罪危险性人格跟踪机制,从量刑阶段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测量和分析开始,将对犯罪人格的鉴定报告等所有相关材料随同案卷材料一起移交至各阶段负责机关,并由行刑机关的心理负责人对犯罪人的人格矫正过程实施跟踪,并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危险性调整矫正方法,对危险性有所上升的服刑未成年人进行干预和监管,降低其人身危险性。
第二,在监狱和社会矫正工作中增加人格重塑环节。教育和改造罪犯是刑罚的功能之一,但司法实践中通常忽视对犯罪人人格的重塑。未成年人具有较高的可塑性,人格重塑将有助于犯罪人降低人身危险性,控制犯罪率。一方面,人格重塑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应当在行刑机关中安排专业人员,在矫正过程中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进行人格重塑。另一方面,应当加强服刑人员的文化修养建设、法律意识教育,努力培养其劳动技能,为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在矫正工作中引入社会力量。引入社会力量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集合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行为和习惯进行矫正,对挽救罪犯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工作使得犯罪人的矫正过程不脱离现实社会,可以消除因服刑所造成的与社会发展完全脱节的不良影响,为今后回归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奠定良好的基础,符合犯罪人人格重塑的需要。
四、结语
刑事法律人格化是将犯罪人人格贯穿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全过程之中,在制刑、求刑和行刑阶段,结合犯罪行为,充分考查行为人人格因素,有效地保障未成年人权益。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化,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推行人格化考量,不仅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落实,还有利于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强化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防控,构建和谐社会。
[1][10]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 5:7-8.
[2][日]大塚仁.人格刑法学的构想[J].张凌译.政法论坛,2004(2):39-50.
[3]翁腾环.世界刑法保安处分比较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1.
[4]陈忠林.意大利刑法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 4.
[5]张建军.刑法谦抑性基础的多维度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6(5): 183-224.
[6]黎宏.日本刑法精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4.
[7]张屹,陈静芳,彭锐.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实现路径[J].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1):71.
[8]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 1(6):60-70.
[9]赵琳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3):64.
D914
A
1673―2391(2013)09―0041―03
2013-03-11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