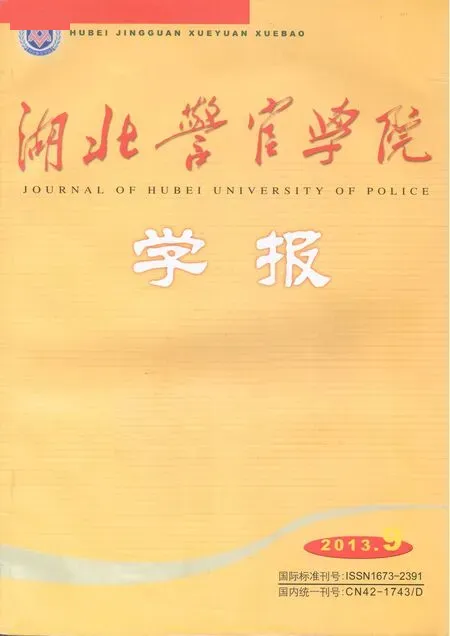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2013-04-11孙大勇
孙大勇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人民检察院,天津300480)
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孙大勇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人民检察院,天津300480)
诈骗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关于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主要有占有说和失控说两种代表性观点。我国司法解释采用占有说。从犯罪本质、犯罪既遂定义和诈骗罪的罪状看,失控说应当是诈骗罪的既遂标准。以失控说为标准,具体分析司法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的案例。
诈骗罪;既遂标准;占有说;失控说
为了规范诈骗罪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16日颁布了《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由此,关于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司法解释采用的是“占有说”。该说认为诈骗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公私财物是否实际被行为人非法占有为标准。如果行为人已经实际获取财物,就是诈骗罪的既遂;否则,就是诈骗罪的未遂。
在一般情况下,受骗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即遭受财产损失)之时,即行为人非法占有或控制财产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诈骗罪的既遂标准是统一的。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被害人已经遭受财产损失而行为人却由于意外因素的介入并没有实际占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司法解释,行为人构成诈骗罪未遂;但是,如果按照失控说或损失说,行为人则构成诈骗罪既遂。司法解释规定: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因此,诈骗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
一、诈骗罪既遂标准的理论纷争
关于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1.占有说。该说认为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以公私财物是否实际被行为人非法占有为标准,即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被骗财物是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行为人已经取得本欲占有的公私财物的,是诈骗罪既遂;反之,则是诈骗罪未遂。这是我国司法解释的观点,也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2.失控说。该说主张以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是否失去对其财物的控制为既遂与未遂标准,即以财物所有人、占有人是否实际失去支配权为界限。凡是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因犯罪分子的欺诈行为,实际丧失了对占有物的控制,是诈骗罪的既遂;凡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所欺诈的财物并没有脱离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控制的,为诈骗罪的未遂。
此外,理论界还有“控制说”、“损失说”、“失控+控制说”等。但这三种观点实际上是上文两种观点的翻版,只是法律用语不同,并无新意。从词源学说,占有和控制的含义是相通的,某人占有了某物也就是实际上控制了某物,二者的法律性质是等同的。因此,“控制说”也就是“占有说”。失控和损失,含义虽不一致,但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却是一致的。某人失去了对某物的控制,也就意味着一定有某个人要遭受财产损失(此时存在受骗人和被害人不统一的情形),这时的法律评价应当是等同的,并不因财产损失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失控说”与“损失说”并无二致。一个人控制了某物,必定意味着另一个人先前已经失去了对某物的控制(也就是占有),因此,“失控+控制说”实际上就是“占有说”。基于此,笔者下文重点探讨“占有说”和“控制说”。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占有了某项财物,也就表明被害人失去了对该财物的控制,因此,无论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实现,还是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立场考察,“占有说”并无不妥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交付财物(丧失对财物的控制),而行为人又没有实际取得该财物时,应如何认定诈骗罪的既遂。例如,被害人受骗,将财物交付给行为人指定的第三人占有时,但交付之时,把不相关的第三人当做指定的第三人,由此遭受财产损失。根据“占有说”,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未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也未实现实际控制财物的结果,因此,其诈骗行为只是处于一种未遂状态。这种忽视被害人因交付财产而使其财产利益遭受完全侵害的事实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与行为人能否占有财产在法益侵害性上是等值的。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而不是行为人取得利益,在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区分既遂与否,其实质是区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法益的侵害程度,从而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通常认为,在同种犯罪中,法益侵害性等值的行为应当处于同一个犯罪形态。因此,在诈骗罪中,只要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无论行为人是否取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相同的,不因行为人最终能否占有财产而有所减损。
其次,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既遂相区别的基本标志,而目的犯中的目的能否实现,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一般认为,犯罪未得逞是指没有发生行为人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危害结果。行为人所希望、放任的结果应当限定于实行行为的性质本身所能导致的结果(即行为的逻辑结果),不包括没有实现目的犯中的目的的情况。在行为的逻辑结果已经发展完毕的情况下,犯罪就已经得逞。诈骗罪的行为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在诈骗罪中,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也由此导致了财产损失,至于财产是否最终被行为人占有则超出了欺骗行为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实现不是行为的必然逻辑结果,不影响犯罪是否得逞的认定。因此,只要被害人陷于认识错误做出财产处分行为后遭受财产损失,诈骗罪即可以认定为既遂。
最后,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符合刑法分则对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形态为立法模式的。按照刑法分则对诈骗罪的规定,诈骗罪既遂有两种形式:诈骗行为+数额较大、诈骗行为+有其他严重情节。在诈骗公私财物行为下,其一,作为定罪要素之一的“数额较大”是以犯罪对象的价值大小而不是以行为人违法所得数额多少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而犯罪对象的价值即被害人财产损失数额;其二,作为定罪要素之一的“有其他严重情节”是以行为人诈骗手段的恶劣性或者被害人由于遭受财产损失而引发的严重后果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与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产无关。由此,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是完全符合立法规定的。
因此,诈骗罪应当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既遂标准(即“失控说”),而不宜以行为人实际取得财产作为既遂标准(即“占有说”)。
二、失控说的具体运用
在此,我们已经确立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然而,现实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廓清“失控说”的实际内涵,为司法的统一适用提供借鉴。
(一)以诈骗房屋等不动产为目标的诈骗罪,应当以不动产的变更登记为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在诈骗案件中,大多数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动产,但也存在一些被害人上当受骗后把自己的房子拱手让人的事件。这类以不动产为对象的诈骗罪数量虽小,但一旦发生往往涉案标的额巨大,对被害人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生活中存在这样两类房屋诈骗情形:其一,行为人通过欺诈行为已经事实上占有该房屋,但一直没有(或没来得及)进行房屋过户登记;其二,行为人通过欺诈行为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但房屋事实上一直在被害人的实际控制下。这两类房屋诈骗案件的犯罪停止形态如何界定值得深思。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如果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仅使被害人作出转让不动产的意思表示,而实际上没有(或没来得及)进行变更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定为诈骗未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动产的转让未履行法定的登记手续,其转让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效力。相反,如果被害人因受骗而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但尚未交付给行为人使用,这种情况下并不影响诈骗罪既遂的成立。因为,房屋的产权变更已经履行了法定的登记手续,行为人就完全享有了房屋的所有权,被害人随即失去了对房屋的处分权,其财产权受到了切实的损害。因此,以诈骗房屋等不动产为目标的诈骗案,应当以不动产的变更登记为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二)诈骗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等财产凭证的案件,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产凭证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的实际控制作为既遂标准
通常来说,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非法占有财物后,就排除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而导致其财产遭受损失。但是,当行为人占有财产凭证时不一定就必然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因为财产凭证虽表示了一定的财产性利益,但只是一种利益的可能性,它不同于财产本身也不同于货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财产凭证可以分为不记名、不挂失的财产凭证和记名、可挂失的财产凭证。首先,对于不记名、不挂失的财产凭证,不论行为人能否即时兑现,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产凭证的控制作为诈骗罪既遂的标准。由于这类财产凭证的无记名性、不可挂失性,谁占有财产凭证,谁就享有财产凭证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性利益已经受到了切实的损害。而无论行为人是否已经兑现,对于被害人来说,其受到的财产损失是等同的。其次,对于记名、可挂失的财产凭证,应当以被害人实际丧失财产凭证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作为诈骗罪既遂标准。由于记名、可挂失的财产凭证,在行为人获取其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时,往往有一个身份审查程序。行为人通过欺诈方法骗得财产凭证,并不一定能够骗过身份审查而获取财物。只有行为人骗过身份审查获取财物之时,才是诈骗行为完成之日。在此之前,被害人的财产性利益只是受到了威胁,但没有实际丧失,其完全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只有行为人已经兑现或者能够定期兑现财产凭证,被害人才彻底地丧失对财产凭证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的控制。因此,诈骗财产凭证的案件,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产凭证所代表的财产性利益的实际控制作为既遂标准。
(三)诈骗转账、汇款案件,应当以被害人把款项存入指定帐号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时下,不法分子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以销售货物为名做虚假广告诈骗钱财的活动十分猖獗。这类“交易”是一种非店面销售,往往需要通过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完成。被害人把款项存入行为人指定的账号,也就丧失了对该笔款项的控制,其必然遭受财产上的损失。事实上,受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规则与操作规程所限,一旦被害人将款项存入行为人制定的账号,就意味着行为人已经可以自主支配这笔款项;同时也表明行为人实现了非法获取货币的目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从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诈骗罪。至于行为人是否已经从银行取出货币,只能说是行为人对所骗的款项如何处置的问题,这并不改变被害人已经失去对该款项的所有权,其财产利益已经完全遭受侵犯的事实。因此,诈骗转账、汇款案件,应当以被害人把款项存入指定帐号作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四)三角诈骗案件,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诈骗罪既遂标准
通常的诈骗行为只有行为人和被害人,被害人因受欺骗“自愿”主动处分自己的财物给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受骗人和被害人是同一人。此外,还存在受骗人和被害人不同一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三角诈骗”。在三角诈骗中,财产处分人是受骗人,但不是被害人。三角诈骗也有两种情形:一是受骗人占有被害人财产;二是受骗人没有占有被害人财产。首先,在受骗人占有被害人财产情形下,行为人通过欺诈方式让受骗人“自愿”处分财产后,被害人就已经丧失对财物的实际控制,诈骗行为即告完成。其次,在受骗人没有占有被害人财产情形下,财产处分行为和获取财物行为之间存在时间差,究竟是以受骗人作出财产处分行为还是以行为人获取财物行为作为犯罪既遂的时间点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获取财物行为(即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诈骗罪既遂标准。因为,尽管行为人通过欺诈方式让受骗人“自愿”处分财产,但由于其对财产的非现实控制性,这就要求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要通过两层考验才告完成。由于这种诈骗行为的历时性,即使其通过了受骗人的考验,也有可能在被害人面前露馅,或者在行为人获取财物之前,受骗人恍然大悟而及时通知被害人。在行为人实际占有财物之前,被害人的财产只是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但没有受到切实的损失,其并没有丧失对财物的控制,诈骗行为也没有完成。因此,三角诈骗案件,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诈骗罪既遂标准。
[1]钱叶六.诈骗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刍议[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2002(6).
[2]张瑞军.论诈骗罪既遂认定的标准及其具体应用[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0(2).
[3]王志祥,韩雪.论炸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J].法治研究,2012(7).
D914
A
1673―2391(2013)09―0038―03
2013-04-08 责任编校:陶 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