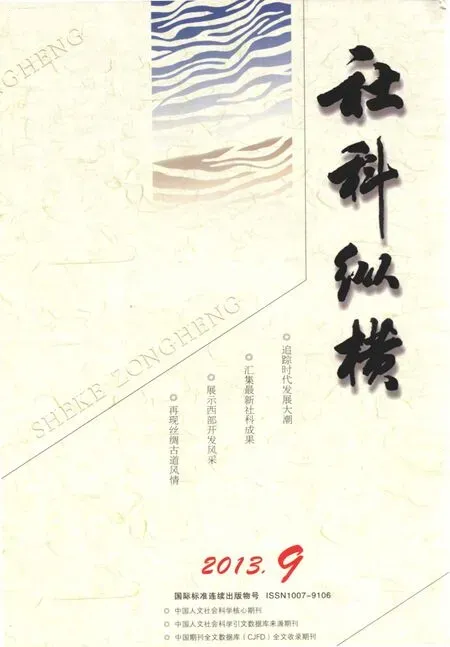高邮王氏训释《左传》之方法及特点
2013-04-11张宪华
张宪华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清乾嘉时期,学界治学崇尚质朴,惩元明学风空疏,弃虚务实,力矫时弊,这一时期,大家迭起,著作颇丰,其中成就最为卓著者当属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王氏家学渊源深厚,又能笃志于学,勤奋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经过终生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学术研究的巅峰,梁启超赞道:“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1]
高邮王氏善于用小学知识从事校勘、训诂和整理古书,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王氏父子二人合作的学术结晶《经义述闻》一书中。方东树认为“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2]此书主要解释群经子史中的疑义,广征群书,汇通古今,其纠正前人误解之文句,为后世所宗,代表了清代汉学派治学的最高水平。在《左传》学方面,《左传述闻》是《经义述闻》一部分,共三卷,216条,其中王念孙说者为81条,王引之论者135条。内容基本为校勘文字和考释经义,每一条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沈玉成、刘宁将之视为“清代考据学派关于《左传》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3]。
乾嘉为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其成就远迈前代,而学术之发达往往要讲求方法的科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道:“然则诸公易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4](P172)他以王氏父子为例,具体研察其研究方法有六: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并认为,“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4](P173)。王氏父子治学,无论其成就,还是其方法,都赢得后人的高度赞誉。王氏父子精于训诂之道,善于运用传统的训诂手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通观《左传述闻》,王氏父子训释《左传》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明字词之古今义
易:古有疾、速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此处杜预注、刘炫、孔颖达之解皆失之。王氏评注疏家对‘易’字之注曰:“易,速也,疾也。古谓疾速为易也,后人不知易有疾速之义,或以为改易,或以为简易,望文生训而古义遂失其传矣!”
怨:古有刺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怨,刺之。王氏评曰:“《正义》以为君怨,为怨怒之怨,失之矣。”
欲:王氏曰:“古义欲与好同义,凡经言者欲皆谓省好也。言欲恶皆谓好恶也。”《左传·成公二年》:“余锥欲放巩伯,其敢废旧典以泰叔文。”
第二,析《左传》中的专有名词
政:专指正卿。《尔雅》:“正,长也。”王氏曰:“正卿为百官之长,故谓之正。”如:
《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左传·哀公十五年》“: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
偪:专指有碍于权。如:
《左传·襄公三年》:“楚公子申为大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偪子重子宰。”
《左传·僖公五年》“: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
第三,破假借,求本字
王引之《经义述闻序》:“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鞠为病矣。”[5]
刘又辛总结王氏父子考订假借字的方法,主要有:
(一)“得经意”——即从经文上下文和全篇文意判断假借字。
(二)利用前人传注,但不迷信传注,以是否能得经意为取舍标准。不合经意的要敢于以“己意逆经意”。
(三)“参以他经”,即同其他经文中的语言材料相参证。这就是用归纳法归纳同类语言材料。做归纳对比研究。
(四)“诸说并列,求其是”。用比较法辨明是非。
(五)“字有假借,则改其读”。即把假借字改读为本字。
(六)有时用同源词材料相参证以求得本字。
(七)利用古音知识及方言材料以证古语本字。[7]
如“又可以为京观乎”“、不可以终”条: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传》:“下而无直,则何谓正一。”《释文》“:何,或作可,误也。”陈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为‘何’字之省,未应遽斥为误。”宣十二年《传》“: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宋十行本,明闽本、监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经》,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误。余谓“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为京观,所以惩有罪也。今晋实无罪,则将何以为京观乎?既曰“何以和众”,“何以丰财”,“何以示子孙”,又曰“何以为京观”,四“何以”文同一例。(《尔雅·释邱》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经》作“可”者“,何”之借字耳,非有两义也。又襄三十一年《传》:“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案:“不可以终”,本作“可以终世”,“可”,即“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终矣”,此又言“何以终世”,作问词以申明之,正与上文相应也。僖十一年《传》:“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文义正与此同。下文言“令闻长世”,又与“终世”相应也。《唐石经》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终”者,传写脱去“世”字,仅存“可以终”三字,后人又误读为“可否”之“可”,遂于“可”上加“不”字耳。《汉书·五行志》引此正作“何以终世”。(宋景佑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终”,乃后人以《左传》改之。)《志》文本于刘歆,盖歆所见《传》文本作“可以终世”,而“可”即“何”之借字,故引《传》直作“何”也。[7]
第四,同义词互训
王氏认为:“凡同义之词皆可互训,而注疏都未之及。”王氏还指出同义词之间,另一字之别义亦可以为训。如“有”与“友”古字通,故友可训为亲、爱、有亦可训为亲、爱。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虽及胡省,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有,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有,相亲友也。
第五,内证和旁证
王氏遇到难解之处,有时还通过内政和旁证来推究竟某些词义,如:
《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使谓原繁曰:‘且寡人出,伯父无裹言。’王氏考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对曰:臣不能贰,通内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从而定“裹言”即“不通外之言,即所谓无密言。”
《左传·文公十八年》:“天下之民谓之饕餮”,“饕餮”二字上下同义,“解者谓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不知饕餮本贪食之名,因谓贪得无厌者为饕餮。饕与餮无异也”。《左传·襄公八年》“冯陵我城郭”,“冯陵”二字上下同义,“解者训冯为迫,不知冯亦陵也”[8]。
限于文章的篇幅,我们每种方法都只能择取一二例加以简要说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邮王氏校释《左传》的某些特点:
第一,音韵学
王氏父子精通音韵学,反映王氏古音见解和研究成果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韵谱:《高邮王氏遗书》载有《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两卷;
书信:《与李方伯书》、《与江晋三书》、《与陈硕甫书》、《与段玉裁书》等等;
序跋:《书钱氏〈答问〉地字音后》、《六书音韵表书后》、《重修古今韵略凡例》等等;
学术专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中涉及古音的文字材料;
王引之《与夏遂园书》,较之乃父又有所精进。
王氏父子之所以能在小学、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们精深的音韵学造诣,“有音韵学家而不治考据者,未有考据家而不通音韵”[9]。他们强调训诂必须将文字与声音结合起来,既要知文字,更要知声音训诂。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谈到训诂的方法时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博访通人,载稽前典。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于所不知,盖阙如也。”[10]
第二,文法的萌芽
中国之文法,传自西洋,其内容包括甚广,在马建忠《马氏文通》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观念,一些学者,如汉代郑玄、唐代孔颖达已经有一些模糊的语法意识,发展到清代王引之之时,已经能够用语法解释经典、串通文意。在训释古书时,王氏父子主要是从文意、文势、文例、文章结构、篇章划分、行文特点、用词特点、句型特点、音韵特点等方面着眼辨误纠谬。如:桓公三年:“今灭德立违”。杜注曰:“谓立华督违命之臣”。家大人曰:“违,邪也。与回邪之回声近而义同。立违,谓立奸回之臣”。晋代杜预做注解时,把“违”解释成“违命”,这里“违”被看作是动词,王引之解释成形容词,“违”是“奸邪”之义,杨树达评论认为似乎更为恰当。
文法学的意识,王氏虽不能明言,而心知之,亦有发明。《左传述闻》一书中在文法方面的收获略述如下:
(一)倒言:即目前语法所谓词序提前。如《左传·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谋而立长亲。”王氏认为应为倒言。另外,王氏又引《左传·昭公十一年》:“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
(二)使动:《左传·襄公十一年》:则武震以摄威之。“摄”同“慑”,慑也。王氏指出:凡懼谓之慑,使人懼亦谓之慑。
(三)指出古汉语虚词的特殊用法。如选用两个虚词表示一个意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将庸何归”,即“将何归。”
在《经义述闻》多条论述里,王引之还注意用修辞方法来解释儒家经典,尽管当时修辞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系统而富地位独立的学科。如《左传》“:广哉熙熙乎”。予谓熙熙,即广也。此处所谓“重言”,即是一种修辞方法,即“叠字”。其他还有互文、省略、对文等等。“《经义述闻·通说》所收各篇论文中,其中批评前人望文生训和增字解经的弊病以及论经文假借各条,尤为明白剀切,为研究训诂学和注释学者所不可不反复细读的重要文献”[11]。
第三,广征博引
王氏父子在校勘《左传》脱字、衍文、错简时,善于依据《左传》文例,证之其他典籍,加以训诂与考证。如“与子上盟”条,《左传·襄公三十年》:“游吉奔晋。驷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使公孙肸入盟大夫。己巳,复归。”王引之判定“盟”字为衍文。这一判定是基于考证“盟”与“誓”的差别而得出的。“用两珪质于河”,是“誓”而非“盟”。他引《曲礼》:“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则饰其牛牲。”《司盟》:“凡盟诅,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连续列举《左传》的九个例证和《穀梁传》的一个例证,考证《左传》凡言诸侯盟,“无不杀牲歃血者”。如果仓卒无牲,则以人血代之,而不用珪。再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子犯以璧授公子,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以及《晋语》但言公子沈璧以质而不言盟,韦昭《注》曰:“信也,沈璧以自誓为信。”证明用珪,为约信而并非盟。因此,“莅牲者,乃谓之盟,投璧不可谓之盟也”。[12]
高邮王氏在校释《左传》时还善于批判吸收当代学者的成果,对顾炎武、臧琳、惠栋、卢文弨、钱大昕、陈树华、段玉裁、阮元、臧庸等众多当代学者之说,往往能够批判继承。如《左传·僖公九年》:“以是藐诸孤”。杜《注》曰:“言其幼贱,与诸子县藐。”顾炎武曰:“藐,小也。”惠栋曰:“案吕谌《字林》曰:‘藐,小儿笑也’。(《文选注》)顾君训藐为小,亦未当。”王引之据《尔雅》、《广雅》,并证之《周语》韦昭注、《文选·寡妇赋》李善注、《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诗经》等,以顾氏训“藐”为小为是,释“诸”即“者”字。王氏无征不信,实事求是,表现出科学求证的态度。
第四,以小学校经
皮锡瑞总结清代经师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通小学表现在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成就斐然。清人多重考据,反对空谈义理,像王氏父子这等大师,对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小学与经学的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训话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段注说文》王念孙序)有的人之所以沿袭旧误,“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经义述闻》阮元序)皮锡瑞说:“经师多通训诂假借,亦即在音韵文字之中;而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13]
王氏父子重视小学,并在小学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直接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也推进了乾嘉考据学的繁盛。高邮王氏四种,堪称以小学明经学的典范,不仅是清代考据学派小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精于小学,长于校雠,是他们有别于其他众多学者的治学优势。对《左传》的校释,只是用小学校经的成果之一。
王氏父子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崇高的声誉,阮元誉为“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黄侃称王氏是“继往开来,成小学中不祧之祖”。王氏父子超越别人之处就是对科学方法的掌握和自觉运用,这些方法给后世研究训诂的人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途径。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27.
[2]方东树.《汉学商兑》,《续修四库全书》本[M].第0951册:593.
[3]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99.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
[6]刘又辛.通假概说[M].成都:巴蜀书社,1988:69.
[7]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449—450.
[8]王引之.《通说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773—774.
[9]杨向奎.《王念孙王引之〈高邮学案〉》,《清儒学案新编》五[M].济南:齐鲁书社,1994:325.
[10]王念孙.广雅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
[11]郭在贻.训诂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05.
[12]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444.
[13]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2.